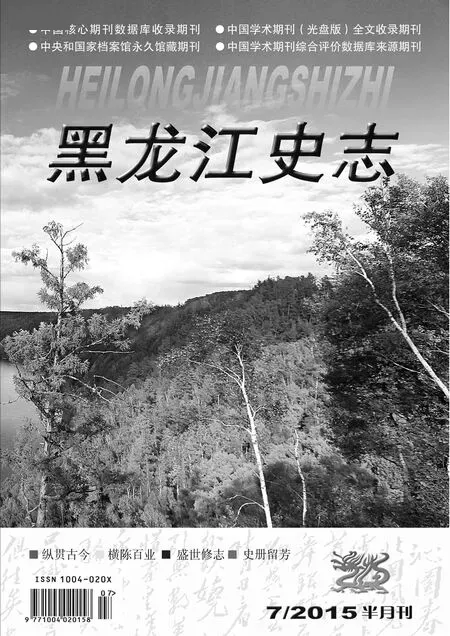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狐貍精”形象的變遷
王振興 陳 杰
(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 四川 汶川 623000)
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狐貍精”形象的變遷
王振興 陳 杰
(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xué)校 四川 汶川 623000)
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關(guān)于山精野怪、仙靈圣佛描寫的作品不在少數(shù),而狐貍精作為精怪內(nèi)的一大分支,擁有龐雜的故事體系,歷來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在漫長的歲月里,狐貍精的形象一變再變,即使在同時代的不同作品中,狐貍精的性格品質(zhì)也很可能截然不同。這種反差所展現(xiàn)的往往不止文字表象那樣簡單,托物言志、御物談心,隱藏在后面的往往是作者對人間百態(tài)的唏噓,是一個時代社會風(fēng)貌的體現(xiàn)。
文學(xué);狐貍精;形象;變遷
中國文化作品中盛久不衰的精怪體系可分為兩大類:一則妖怪,二則妖精。前者從字面意思上便給人一種不可捉摸的恐懼,因為“怪”而不被知,形成難以言喻的壓迫感;后者雖與前者同出一源,但給人的感覺卻是截然不同,它由最初形容極富神秘化的精怪逐漸演變成了男子對女子略帶戲謔的愛稱或世人對姿色迷人女子的代稱。在世俗世界與文學(xué)世界接觸之地,妖精的指代范圍日漸縮小,幾乎成為了狐貍精的代名詞,其褒貶在各種環(huán)境中有所不同,具體而言,則需要切入各個具體時代進行分析。
一、魏晉之前的狐貍精
與中國的悠久歷史相對應(yīng),作為精怪體系中一大類的狐貍精早在圖騰崇拜時期就已登上了歷史舞臺。此間,狐貍精作為神靈、瑞獸受到膜拜、供奉,地位尊崇。傳說大禹的妻子,啟的母親涂山氏便是一只九尾白狐,《吳越春秋》記載:
“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yīng)矣。’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涂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于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謂之女嬌。”
或許,這時的狐貍還不能稱之為“狐貍精”,它們有如巫山神女般高貴神圣,并偶爾沾染塵世的存在,為人類降下福澤。
《史記·商君列傳》中,有“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同‘腋’)”之說。以當(dāng)時的生產(chǎn)生活條件來看,六畜之一的羊,價值不菲,傳聞百里奚也不過價值五張黑公羊皮(當(dāng)時奴隸的市值)而已,而上千張羊皮也不如一狐之掖,雖然貌似夸張,但也可例證狐貍皮毛的不菲價值。
此外,屈原在《九章·哀郢》中寫道“鳥飛反故鄉(xiāng)兮,狐死必首丘”,這與《禮記·檀弓上》中“狐死正丘首,仁也”一語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忘本即是仁,一種高尚而令人稱贊的道德情操。到了漢代,“九尾狐”的地位更加尊貴,成為太平盛世的祥瑞之兆。
“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當(dāng)盛也。”
同時,在漢代雕刻中,九尾狐與白兔、蟾蜍、三足烏之屬并刻于西王母座旁,以示禎祥。由此可知,晉以前有關(guān)狐貍精的文學(xué)作品,多持褒揚的態(tài)度,無論是從狐貍未成精時的價值,還是狐貍精的道德形象,抑或雌性狐貍精堪配王后的高貴身份。可見人們對其頗為敬重,也是時人重視名德與歸鄉(xiāng)情結(jié)的體現(xiàn)。
當(dāng)然,也有其他形象。《山海經(jīng)》中記載了生活在青丘之山的九尾狐,雖然能令“食者不蠱”,但它也是以人為食。再者,古人論及亡國之君,往往在塑造一個昏庸乖戾的暴君之時,添加一個禍國殃民的狐貍精作為君王性情大變、不斷施加苛政的補充條件。一如劉向《列女傳》所說:“妲己配紂,惑亂是修。”到后來,狐貍精與紅顏禍水逐漸合流,成為一體。
二、兩晉南北朝的狐貍精
東漢以后,“狐貍精”逐漸從神壇走下,降落為塵世之物。如西晉郭璞的《玄中記》中說:“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稱天狐。”這與先晉時期的同類相比,超凡之力仍在,但擇偶標(biāo)準(zhǔn)業(yè)已下降了不止一個檔次,雌性狐貍精變得“人盡可夫”,雄性狐貍精則蛻化為人言變色的采花大盜。至于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人們根據(jù)道教修行理念作出了玄之又玄的解釋,即采陰補陽、滋陽補陰有助于人、魔、妖、邪等修煉之途更進一步。
兩晉南北朝時代,諸國攻伐連連,民不聊生。能夠給人帶來精神慰藉的佛道二教頗為盛行。與此同時,門閥制盛行,選官任職皆看門第,出身決定地位,能力與奮斗難以取得上層的青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tǒng)論在當(dāng)時可是毋庸置疑的金科玉律。身份既定,位處高層的士大夫們閑來無事,竟然閑出了一份暢玄的雅致。伴隨而來的是放浪形骸之外的奇端異行,房中術(shù)的流行也使豪門貴胄紛紛沉溺于欲海之中,穢行丑聞連連,令人瞠目。筆者以為,狐貍精的顛覆性轉(zhuǎn)型正是此時代之風(fēng)情所造就。
雖然此間由于晉人尚狐,對之評價不可一概而論,但狐貍精形象的墜落已成定局。這時,狐貍膽小謹(jǐn)慎的性格被突出,而它面若桃顏女子的長相也被不斷的夸張下去,導(dǎo)致其性別走向單一。
三、隋唐宋元的狐貍精
自兩晉志怪小說現(xiàn)身,到了唐代文學(xué)作品中的狐貍精形象可謂是多姿多彩。狐貍精不但能變幻成美女,亦能變換成男性,神通廣大,法力奇高,甚至很多與狐有關(guān)的詞匯開始出現(xiàn)并流行開來。張鷟在《朝野僉載》說:“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dāng)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狐貍精”似乎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接近了許多。有關(guān)它的傳說,也是神乎其神。《酉陽雜俎》記載:“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為人矣。”
至于說,為何唐人會有這種怪誕的想法,大概是,“第一,古人認(rèn)為狐貍元氣充沛;第二,認(rèn)為狐貍天生喜歡捉弄男人。”可能還有第三個原因,即狐貍的體態(tài)和形貌與女人似乎總有些說不清的類似之處。這使得狐貍與美女之間更容易引發(fā)人們對二者易容變形的豐富聯(lián)想。白居易曾專門描寫過狐貍變幻美女的完整過程,細致生動,引人遐想。
古冢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
頭變云鬟面變妝,大尾曳作長紅裳。
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時人靜處。
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
忽然一笑千萬態(tài),見者十人八九迷。
假色迷人猶若是,真色迷人應(yīng)過此。
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惡假貴重真。
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為狐媚害即深,日長月增溺人心。
于是,“狐貍精”這個詞就成為形容、甚至貶低女人的一個專用詞匯。
唐傳奇中,有不少狐貍精幻化成美女來誘惑男人的故事。于是就有了“狐媚”這個令人浮想聯(lián)翩的詞匯。譬如:宋州刺史王璇,“少時儀貌甚美,為牝狐所媚。”即便遇到下人和兒童,也是“斂容致敬,自稱新婦”,言辭委婉,很有嫵媚。后來王璇官做的越來越大,狐貍才不敢來了,“蓋某祿重,不能為怪。”
唐代的狐貍精多為“害獸”,似乎完全繼承了兩晉南北朝的狐文化,但在《任氏傳》中,作者沈既濟描繪了一個守貞潔,不畏強暴,且持家有術(shù)的狐貍精“任氏”。作者亦感嘆:“異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節(jié),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
狐貍精的形象不呈一面倒的趨勢,一則體現(xiàn)了對不同時代復(fù)古繼承的文化碰撞,二則展示了隋唐文化的包容性。宋人對一些難以解釋的問題,便從唐朝盛傳的鬼神之事中尋求答案。唐朝立廟事狐的習(xí)俗在宋代得到繼承,狐在受到非議的同時,依舊以“狐仙”的身份享有香火的供奉。
中國凡事講究正名,即使是地府中惡名昭彰的鬼王,也憑借以惡制惡的功勞,被人塑像歌頌。狐貍精既享供奉,于是為其正名的故事也不在少數(shù)。《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五十三《計真》中就寫到:計真之妻乃狐貍所變,她隱瞞身份接近計真,感情甚篤,臨死之際,又將身份告知丈夫,但計真依舊愛她。這在體現(xiàn)狐貍精魅力十足之刻,借用傳統(tǒng)的人狐戀,使狐貍精的善良、鐘情的一面得到展現(xiàn),貌若天仙的狐貍精進一步成為凡塵男子心中的期待。
元代,文化不昌,狐文化繼承居多,無甚新意。
四、明清時期的狐貍精
漢賦唐詩宋詞元雜曲明清小說,每個時代都有獨特的文體代表,每類文體都為方便情感之表達,時代之記述。明清時期的小說由于流俗而更開放的文風(fēng),在記事敘事上趨于便利,進而使狐貍精的形象刻畫入木三分。
明清時期關(guān)于狐貍精的作品,以許仲琳《封神演義》與蒲松齡《聊齋志異》最具代表。《封神演義》借狐貍精殘忍取代蘇妲己之身份并誘使商紂王毒害忠良、降禍百姓,從而為周師滅商進行正名。“助紂為虐”只為加速敵人的腐朽,似乎有了些許悲壯的意味。但縱觀《封神演義》,也令人扼腕嘆息,狐貍精雖不辱使命,圓滿完成了頂頭上司女媧娘娘下達的任務(wù),可其身后依然滿是差評。人們往往只記恨行事者,選擇性遺忘操縱者,或多或少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捏柿子”準(zhǔn)則——挑軟的捏。
《封神演義》中的千年狐貍精、九頭雉雞精與玉石琵琶精陪伴在大神女媧身旁,而女媧指給她們的成仙之路并非努力修行,多行善事,反倒是為解私怨而指派其去禍國殃民。這一命令由大地之母女媧娘娘發(fā)出,倒是頗有些諷刺意味。
清代,文人對狐貍精依舊“情有獨鐘”,其中以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為最。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
“聊齋志異雖如當(dāng)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屈,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diào)改弦,別敘畸人異行,出于幻域,頓入人間,偶述鎖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
這不但指出了《聊齋志異》緣何為人所津津樂道,而且指其以記載狐魅為主,尤為形象生動,這與其俗名《鬼狐傳》可謂不謀而合。
蒲松齡在繼承前人思想的同時,予以發(fā)展,他筆下的狐貍精大致可分為三類:殘害生靈之狐;天真爛漫之狐;多情勾人之狐。
殘害生靈之狐,表達了人們對此類事物的擔(dān)憂與恐懼。據(jù)說,它們與人接觸會使人受到傷害,甚至丟掉性命。《伏狐》就記述了“太史某,為狐所魅,病瘠”。同時在《狐入瓶》也有“萬村石氏之婦,祟于狐,患之,而不能遣”的描寫,這與宋朝時屢見不鮮的狐貍精附身事件大同小異。然而,關(guān)鍵就在于“小異”,宋朝對于狐貍精附身的描寫是為了表述時人所不能認(rèn)知的一些超常事物,《聊齋志異》中對此的描寫則是為了強調(diào)一種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無論是魅惑太史之狐,還是石村之狐,它們都在當(dāng)事人的反擊下死于非命,有點“不成功便成仁”的意味。
天真爛漫之狐融入人世且無有害處,如《嬰寧》中的嬰寧,她身為狐女,卻崇尚美好的愛情,心地善良,頑皮風(fēng)趣,常以歡笑面對一切。
多情勾人之狐當(dāng)中,有小部分亦如魏晉時期“人盡可夫”的妖狐,但更多的體現(xiàn)了另一種風(fēng)情,流露出濃濃的情義。《狐聯(lián)》中便寫焦生遇見了兩只欲與同歡的狐貍精,在焦生堅持不允的情況下,亦不強求,反留下了一幅令人稱絕的對聯(lián),充滿了性挑逗的意味。古時文人開些葷段子,多借文字游戲為之。而《汾州狐》中的汾州通判朱公與狐共戲,久生情愫,在朱公將要與其分別之際,非但不做糾纏,反給予協(xié)助。再如《毛狐》中的少婦,《狐諧》中的狐娘子皆是如此。至于《胡四姐》中的四姐,更可謂是有情有義。而《胡氏》中所描繪的雄狐,雖最初試圖強娶主人家的千金,甚至帶狐兵前來挑戰(zhàn),但在遭遇挫折之后,也能轉(zhuǎn)而和談,終以歡喜收場。
《聊齋志異》中的三類狐貍精,是偌大體系的代表,也是對該文化的總結(jié)性整理。其形象豐富多彩,亦如人之千人千面,表達了人們對這一事物的復(fù)雜感情。作者描寫的對象雖為鬼狐精怪,但始終不離當(dāng)時的社會環(huán)境,借精怪之口言談時事,以精怪之能參詳內(nèi)情——文人們借此一筆一劃勾勒出更加離奇怪異的人類社會。故筆者以為,志怪小說,借鬼狐說人事,雖為小說,亦有史書之功效也!
五、結(jié)語
狐貍精是一種被賦予人類情感的虛幻曾在,也是被擬物化的人,這來回之間的轉(zhuǎn)變,正是一個個未被包裝過的真實社會。筆者以為,通觀魏晉至明清文學(xué)作品中的狐貍精形象,神性日趨淡化,人性逐漸強烈為其最大特點。
當(dāng)代中國,諸如古代曾廣為流傳的“狐貍精”之類的神鬼之說,一概被斥之為虛妄。如今的狐貍精,未必擁有出眾的容貌,但風(fēng)情萬種的妖嬈卻是必備的技能。她們,令男人垂涎而又恐懼,令普通女人“羨慕嫉妒恨”。也許,這正是古代神鬼之說當(dāng)中“狐貍精”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