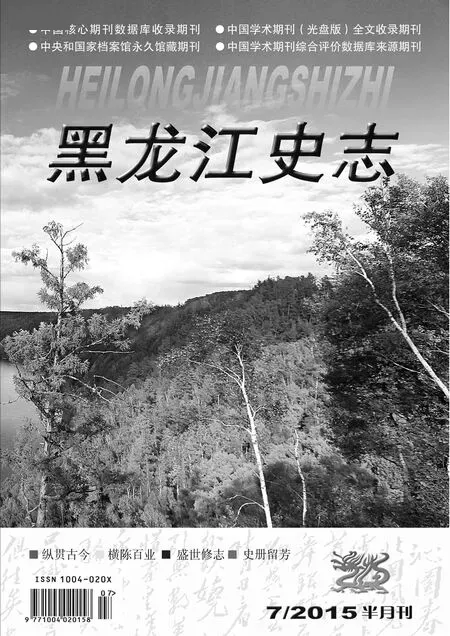南朝時期的佛馱跋陀羅
李 淼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46)
緒論
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是印度佛教義理輸入漢地的高潮時期,眾多的外籍僧人前往漢地弘法,使漢地佛教的理論體系日趨完善。這一時期外來僧人中,以鳩摩羅什和佛陀跋陀羅最為重要,學界有關鳩摩羅什的研究成果不少,而由于資料缺乏等原因,對佛陀跋陀羅的研究卻一直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佛陀跋陀羅(359—429)是東晉南北朝時期的天竺禪修高僧和譯經家,對于中國早期佛教的發展影響深遠。他的前半生在天竺、罽賓修學,后半生在漢地行化,輾轉于青州、長安、廬山、江陵、建康等地,與后秦和南朝宋的統治者均有交往。佛陀跋陀羅在律行、禪修、義學等方面均有杰出表現,其譯出的多部佛典為后世華嚴宗、凈土宗、禪宗、律宗、密宗、天臺宗、涅槃學派、毗曇學派等多個宗派和學派提供了理論基礎。
留存至今的佛陀跋陀羅完整的傳記都出于佛教僧侶史家之手。一是由僧祐(445—518年)所撰,收入其所編的《出三藏記集》,二是由惠皎(497—554年)所撰,收入其《高僧傳》。如陸揚在《解讀<鳩摩羅什傳>——兼談中國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與史學》中所說,前輩學者“常常將傳記資料和其它性質的資料放在一起考訂比附,尋找相互之間的的共同點和不同點,而沒有意識到這些不同性質的文本往往其傳達歷史訊息的方式和目的是不同的。……而這恰恰是研究中古佛教僧傳所首先要注意的層面。因為我們所面對的首先是中古作家心目中的鳩摩羅什。他們在向讀者塑造這一形象并傳達這種文化宗教的主旨時,其敘述的安排是非常關鍵的。”[1]39-40對于佛陀跋陀羅這樣留存的資料較少的研究對象來說,尤其依賴對這些傳記的分析和解讀。故而本文斗膽擬以此題,以兩種《佛陀跋陀羅傳》(《佛馱跋陀傳》)為中心,對佛陀跋陀羅來華之后引人注目的事跡加以分析,并以此揭示東晉以后南方佛教的自覺趨勢。雖不免效顰之譏,亦足以申述一二。
佛陀跋陀羅與鳩摩羅什之矛盾
佛陀跋陀羅被逐出長安的事件,是中國佛教史上一樁有名的公案。史傳所載這一事件的原因,一則佛陀跋陀羅稱:“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導致“關中舊僧,咸以為顯(即佛陀跋陀羅)異惑眾。”二則佛陀跋陀羅的弟子自稱修成阿那含果,而佛陀跋陀羅未加檢問,導致流言。鳩摩羅什的學生僧、道恒就以這兩點為借口將佛陀跋陀羅逐出長安。[2]70然而湯用彤先生早已指出,佛陀跋陀羅與長安舊僧的矛盾,實則其原因“在于與羅什宗派上不相和”。[3]17[12]
在從海路到達東土之后,佛陀跋陀羅首先就前往長安,與鳩摩羅什相會。即《高僧傳》所稱“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2]70可見,佛陀跋陀羅剛剛到達中土,就已經聽聞鳩摩羅什高名,對從游于鳩摩羅什可以說也抱有期待。而鳩摩羅什對于這位來自自己祖居地天竺,又和他一樣出于中亞僧團的佛陀跋陀羅感到親切,對他的到來最初也是十分歡迎的,史稱“什大欣悅”。然而隨后,二人幾乎立刻就產生了矛盾,在與鳩摩羅什的論學中,佛陀跋陀羅發現鳩摩羅什不似傳說中那么佛法高深,并且不留情面地發問“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而鳩摩羅什則回答“: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學者以為這和自稱修成阿那含果一樣體現了佛陀跋陀羅向來不謹慎的個人性格,而這也是造成他后來被逐出長安的原因。[4]133-138然而如果細究佛陀跋陀羅后來的一貫的表現,與其說這是他性情不謹慎或者乖張的表現,不如說這是一種耿直。而他對鳩摩羅什表現出來的情緒,除了針對其禪法不正宗之外,更直接的是對其傳教方式的些許不滿和失望。
《高僧傳》對于佛陀跋陀羅來華的原因著墨頗多:
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 賓。睹法眾清勝,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咨訊國眾,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馱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學,其童齔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于大禪師佛大先。”先時亦在賓,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于是舍眾辭師,裹糧東逝。[2]70
智嚴到達 賓之后,尋找能夠“流化東土”的高僧, 賓僧人向智嚴推薦了佛陀跋陀羅。在智嚴的苦求之下,佛陀跋陀羅同意來到中土。佛陀跋陀羅東來雖不是完全主動,但來華的目的卻十分明確,即《僧傳》所說的“流化東土”、“振維僧徒,宣授禪法”。隨后,佛陀跋陀羅經海路來華,路途也頗為曲折:
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蔥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并傾心資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于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余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眾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后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后于闇夜之中,忽令眾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一舶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2]70
“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蔥嶺路經六國”,徒眾還屢次遭遇風暴、盜賊等危險,都被佛陀跋陀羅一一化解。惠皎花費如此多的筆墨來描述傳教路途的艱辛。除了要表現佛陀跋陀羅有未卜先知的神異功能之外,應當也有以過程的曲折來襯托佛陀跋陀羅傳教的決心。在佛陀跋陀羅被迫離開長安時,他感嘆“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申,以為慨然耳。”[2]7[12]可見,佛陀跋陀羅東來,目的明確,決心堅定。
從佛圖澄至于鳩摩羅什,十六國時期的著名僧人都與各國統治者關系密切,從而為傳教提供便利,同時也為自己取得了崇高的身份和地位。而這對經歷艱苦來華傳教,而且堅守著印度傳統佛教游化為生的佛陀跋陀羅來說,顯然并不適應。《高僧傳》稱:“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余僧。并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眾同。”[2]7[12]在這里,佛陀跋陀羅表現出對于與統治者交往不感興趣的態度。當佛陀跋陀羅被迫離開長安時,姚興感到遺憾,感嘆:“佛賢沙門,協道來游,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派使者希望將其追還,佛陀跋陀羅“無欲聞命”,毅然南下。[2]7[12]有學者表示不能理解姚興對佛陀跋陀羅離開而發出的感嘆,認為佛陀跋陀羅“很少同皇宮中人來往,所以他的被驅離長安,顯然也是得到了后秦皇宮中政治勢力的默許甚至是推波助瀾的”。[4]136其實,正是由于姚興誠心崇信佛教,而佛陀跋陀羅卻對與王室交往沒有興趣,若即若離。姚興雖然對佛陀跋陀羅的離開感到惋惜,以至于他離開后還抱有希望,派人欲追回佛陀跋陀羅。但佛陀跋陀羅對于以鳩摩羅什為領袖的長安佛教界“往來宮闕”的狀況不能適應,沒有順從姚興的挽留而留在長安。所以,當僧、道恒向他下達“逐客令”時,佛陀跋陀羅說:“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申,以為慨然耳。”明確表達了對是否留在長安的不以為意和在長安處境的不滿。
佛陀跋陀羅與慧遠之關系
在所有與佛陀跋陀羅交往的中國僧人中,廬山慧遠對佛陀跋陀羅的親近顯得有些異乎尋常。早在佛陀跋陀羅尚在長安遭到排斥時,身處南方的慧遠就極為關心他的處境,派遣弟子曇邕致書姚興為佛陀跋陀羅辯護。并且在這時已經邀請佛陀跋陀羅翻譯經律。佛陀跋陀羅離開長安后,到南方后的第一站就是廬山,這應當也是出于慧遠的延接。陸揚認為,與鳩摩羅什相比,佛陀跋陀羅擁有的正宗禪法更加符合寺院主義的理想,慧遠的同情,不僅是針對佛陀跋陀羅個人,更是維護佛教教團重修行的準則。[1]86這是很深刻的見地。但從慧遠對佛陀跑跋陀羅的評價來看,他對佛陀跋陀羅的推崇似乎有另一層面的原因。
在《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統序》中,慧遠這樣評價佛陀跋陀羅:
舍夫制勝之論,而順不言之辯。遂誓被僧那,以至寂為己任,懷德未忘,故遺訓在茲。其為要也,圖大成于末象,開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以寢患,達忿競之傷性,齊彼我以宅心。于是異族同氣,幻形告觫,入深緣起,見生死際。爾乃辟九關于龍津,超三忍以登位。垢習凝于無生,形累畢于神化。[5]344
除了在修行方面,他贊美佛陀跋陀羅“辟九關于龍津,超三忍以登位,垢習凝于無生,形累畢于神化”之外,更強調“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以寢患”,明確表達了他對佛陀跋陀羅在長安不預世事的贊許。
事實上,佛陀跋陀羅到達南方后,依然堅持著獨立于統治者的態度:
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遺,悉皆不受,持缽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小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慚愧。[2]7[12]
一方面不排斥與貴族、世俗官僚接觸,一方面又若即若離,保持自己獨立的地位。與袁豹的交往即是明例。同時,“持缽分衛,不問豪賤”,對施主的不分貴賤,一視同仁。
而慧遠在與上層政界人士的交往中,對于諸如帝王、高官、起義領袖等諸色人等,都保持著友好的關系,但都明顯不似鳩摩羅什那樣出入王庭,極為親密。在這些政界人士中,有人為慧遠修建寺廟或布施供養,慧遠會欣然接受,有人上山,慧遠也以禮相待。至于涉及政治性的交往,慧遠則針對不同對象、不同情境,分別做出靈活應對,巧妙周旋。其中有幾個特點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從不下山相見。晉安帝聲討太尉桓玄,自江陵回京師,途經九江,輔國將軍何無忌勸慧遠候迎。慧遠稱疾不行,后安帝遣使慰勞,慧遠修書答謝。二是不談政治問題。桓玄征伐荊州刺史殷仲堪,軍經廬山,要慧遠下山相見,慧遠稱病。桓玄上山,問及對征討的看法,慧遠緘口不答。三是不以政治身份做區別取舍。盧循占據九江后,上山會見慧遠。慧遠與盧循的父親“同為書生”,遂給予熱情接待,“歡然道舊”[2]2[12]6。有人進諫,說盧循是“國寇”,接待他會引起王朝的懷疑。慧遠說:“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豈不為識者所察,此不足懼。”[2]2[12]6四是不為封官所動。“玄后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騁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瑜丹石,終莫能回。”慧遠以堅毅意志,拒絕了桓玄的召請。[2]2[12]9觀慧遠與上層政界人士的交往,與佛陀跋陀羅的態度幾乎如出一轍,這很有可能也是慧遠對佛陀跋陀羅倍加贊賞的一個原因。
事實上,慧遠在對待世俗統治者更為人所熟知的是他所作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明確表明了他有意確立佛教獨立地位的態度。他將佛教徒分為兩類,一類是“在家奉法”的居士,他們在家禮佛弘教,應當與世俗之人一樣,禮敬王者,服色也應與俗人相同。一類是“方外之賓”,即出家沙門,他們立志追求出世解脫,不順從世俗教化,與世俗禮教有所不同。慧遠力主沙門不敬王者,以維護僧人的獨立宗教生活和佛教在社會中的獨立自主地位。努力維護佛教獨立地位的慧遠,對于與統治者保持距離乃至遭到驅逐的佛陀跋陀羅自然抱有一種同情和親切感,從而對他激賞有加。
南朝佛傳作家筆下的佛陀跋陀羅
前文已述,留存至今的佛陀跋陀羅完整的傳記都出于佛教僧侶史家之手,即僧祐(445—518年)所撰《出三藏記集》和惠皎(497—554年)所撰《高僧傳》。二者的主干內容、敘述次序和措辭等方面都極度相似,僧祐的版本應當就是惠皎版本的底本。然而,《高僧傳》的篇幅多出《出三藏記集》一半。惠皎在僧祐版本的基礎上添加了更多的細節,來表達他自己對于佛陀跋陀羅的認識和評價。
例如,佛陀跋陀羅在長安時,舊僧道恒等人驅逐他離開長安,《出三藏記集》并沒有記錄佛陀跋陀羅當時的回應,而在《高僧傳》中,佛陀跋陀羅說:“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申。以為慨然耳。”一語將佛陀跋陀羅描述為立志于弘法傳教的高僧形象。再如佛陀跋陀羅離開長安時,《出三藏記集》之言“興尋悵恨,遣使追之。”[5]54[12]而《僧傳》的描述則生動的多:
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游,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敕令追之。賢報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于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2]7[12]
不僅皆姚興之口表達了對佛陀跋陀羅的稱贊,而且以“無預聞命”、“率侶宵征”變現了他疏離后秦統治者的堅決態度。諸如此類都在字里行間表現對佛陀跋陀羅的稱頌。
在《高僧傳》的序錄里,惠皎對前代所撰《名僧傳》表達不滿: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2]5[12]5
陸揚指出,惠皎的工作是要以佛教的標準而非世俗的標準來給要影響的僧人做佛教史上的定位。如果光有世俗的所謂名聲而缺乏真正佛教意義上的“高”的話,那么對于惠皎來說就是“本非所紀”。而另一方面,拋開世俗之名而尋求佛教意義上的高僧,那么惠皎也可以將讀者的眼光導向那些不太為人所知但卻對宗教有真正貢獻的教徒,或者為人所知不為人所知重視的貢獻。[1]39-40惠皎的這一立場很大程度上也是要確立佛教界對自身歷史和人物獨立評判的權利。這一切正是南朝時期中國佛教界的一些代表人物積極尋求精神獨立的表征,對佛陀跋陀羅的青睞正是這一傾向的表現。
[1]陸揚.解讀<鳩摩羅什傳>——兼談中國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與史學[K].中國學術(第二十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2][梁]釋惠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K].北京:中華書局.1992.
[3]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
[4]尚永琪.胡僧東來——漢唐時期的佛經翻譯家和僧人.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
[5][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