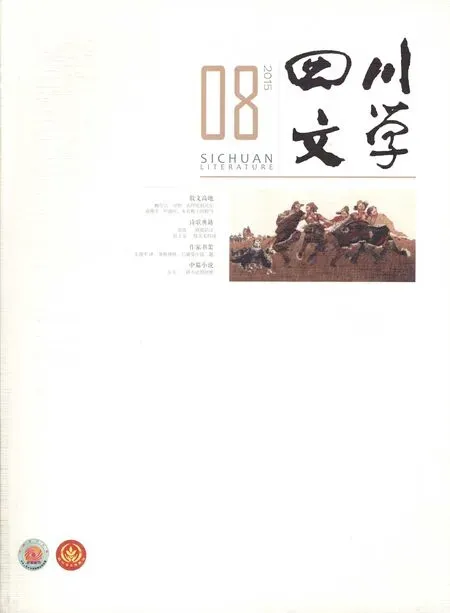一溪云外“琴”何在?
○ 李成琳
離開海南的前一天,突然下起瓢潑般的大雨,雨幕彌漫,雨聲響亮,轉瞬之間仿佛淹沒了世間所有,只有雨,成為此時此刻的主宰。在雨中,莫名地想起九百多年前的蘇東坡,當他再次被貶從廣東惠州赴海南儋州在六十余日的長途跋涉里,是否遭遇過如此的滂沱大雨?已近暮年的他在大雨中還能吟出“雨已傾盆若,詩乃翻水成”,“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等詩句嗎?
起意與澄邁
決定于炎炎夏日去海南,其實是因為蘇東坡。兩年前的夏日,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里那張刻有“紹圣二年東坡居士”的館藏宋琴,終于有幸得以撫彈,心生牽掛的同時也有了追尋東坡足跡的起意。查閱蘇東坡的年表,“紹圣二年”乃公元1095年,正是花甲之年的東坡謫居廣東惠州之時。但查詢他在惠州的生活,其最著名的詩句乃“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琴的“身影”遍尋不著。兩三年后他離開惠州再貶海南島的儋州,我在王國憲于清康熙年間所寫的《重修儋縣志敘》中讀到其評述東坡的文字:“以詩書禮樂之教轉化其風俗,變化其人心,聽書聲之瑯瑯,弦歌四起,不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辟南荒之詩境也。”詩書禮樂,弦歌四起,讓人心生向往,海南儋州就這樣成為暑期攜女兒出行之目標地。
而“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詩句出自蘇東坡赴儋州途中所作的一首詩,詩題為《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風急雨,戲作此數句》(見《蘇東坡海外集》),少見的敘述性長題,夢中所得之“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成為千古名句,但我更喜歡其中的“幽懷忽破散,詠嘯來天風”,不知抗戰時期重慶琴人楊少五與浙派琴家徐元白一起創辦的“天風琴社”的得名與之有關系乎?
追尋蘇東坡在海南的行蹤,一個與蘇東坡澄澈豪邁的氣質很匹配的地名——“澄邁”躍入眼中。宋紹圣四年,即公元1097年的6月,毗鄰瓊州海峽的澄邁老城成為蘇東坡登臨海南的第一站,也是他3年后離開海南的最后一站。在這里,有一個名叫趙夢得的儋州人曾在家里款待過蘇東坡,趙家花園的兩個亭子上曾留有蘇東坡所題寫的“清斯”、“舞琴”二匾,他們二人是否在園子里撫琴弦歌,已不得而知,但東坡一上島便“歇宿澄邁通潮閣,游永慶寺”,卻是有文跡可尋的東坡行蹤之一。
澄邁正好在海口和儋州之間,匆匆停駐間,已很難找尋915年前的東坡遺跡。“倦客愁聞歸路遙,眼明飛閣俯長橋。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澄邁通潮閣》)蘇東坡筆下的通潮飛閣早已不復存在,后來被貶來瓊任資政學士的李光書寫蘇東坡詠通潮閣的詩碑及《通潮飛閣碑記》亦不知其蹤跡,而始建于宋代的禪林圣地永慶寺,也在歷次戰亂中頻遭損毀并最終于“文革”損毀殆盡。數年前重修擴建的永慶寺規模宏大,莊嚴瑰麗,但千年古剎的舊痕老韻不再,只有站在菩提樹下,文殊花前,體味那婆娑婀娜的禪意和清涼……因為蘇東坡,這座有太多“現世”記號的永慶寺,還是給了我一種別樣的感覺。
儋州與書院
繼續前行,在火辣辣的陽光里奔儋州去。一路的藍天白云,一路的浮想聯翩,還沒到儋州,就先自激動起來,就像那年到汨羅江畔的屈子祠,一路的江水流逝,卻一路的《離騷》《天問》與《九歌》,感覺時光如江水流逝了兩千多年,屈原卻仍然活在人間。蘇東坡也如此,九百多年過去了,依然讓我們千里迢迢而來,依然讓我們有怦然心動的急切。
進入儋州城區,很快就發現有“東坡書院”的路牌,以為就在近處,便想立馬趕去。海南的朋友說,還遠著呢,得先入住,午餐之后休息一下再去。正午的太陽也無法消解我們的急切,午餐后我們就出發前往東坡書院所在的中和鎮。
在鄉間公路上走了很長一段路,耀眼的陽光下,農舍,牛群,莊稼地,茂盛的植物,汽車掀起的塵土……正有些倦意的時候,眼前突然出現一大片清清爽爽的開闊地,樹木蔥蘢間,一道朱砂紅的圍墻,一座純白色的門樓,在小河、稻田和草地的映襯下,格外醒目。這就是東坡書院了,雖然院門正在維修,“東坡書院”的木匾尚未掛還原處,但藍天下這座一塵不染的門樓,其簡潔和端正,讓人恍然瞥見蘇東坡的背影!
從旁側的一道小門進去,院落比我想象的大,青石小路,綠蔭蔓草,花樹芬芳。一座小小的竹亭立于一棵大榕樹下,竹亭的旁邊置有大大的木桌。坐下來,喝一杯“東坡茶”吧,淡淡的,澀澀的,有一點回甘。儋州的朋友告訴我,這“東坡茶”相傳是當年蘇東坡針對海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的氣候配制的,由野菊花、五色花和福建茶沖泡而成,有祛濕、清涼、解毒之功效。而竹亭上有副對聯:“南島文章儋耳筆,東坡居士孟婆茶”——記得在某本書里看到過“孟婆茶”的典故,說的是江浙一帶的傳說,人死后的陰魂走在黃泉路上都會去喝一碗“孟婆茶”。此茶喝后,就把一生經歷的人和事統統都忘記了。這副對聯把“孟婆茶”寫進去,是想說“東坡茶”還有“忘憂”的功效吧?
“東坡茶”讓我們忘掉暑熱,加之游人甚少,可以清靜自在地徜徉并懷想。這個濃蔭下的蓮花池,池面蓮葉田田,幾近鋪滿,東坡當年與好友黎子云在此垂釣,“坡公嘗于池畔舉酒灑栗呼引五色雀”,那是多么活潑的場景,仿佛能聽到他們爽朗朗的笑聲!蓮花池上的載酒亭,翹角重檐,匾額對聯,古色書香彌漫。亭中懸掛一紅底橫匾題為“魚鳥親人”——垂暮之年的蘇東坡再貶儋州,除了幼子蘇過相伴,舉目無親,魚鳥花草皆為親人。東坡詩云“此心安處是吾鄉”,盡管初來乍到“食無肉,病無藥,居無所,出無友”,他仍將海南的一花一木一魚一鳥視為親人,這個載酒亭承載了蘇東坡多少曠達超然的思緒和感懷!
載酒亭后就是載酒堂,這是東坡所留遺存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在儋州居住和講學的地方,始建于紹圣四年,即公元1097年冬。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云:“紹圣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這“為屋三間”指的便是“載酒堂”。蘇東坡初到儋州,官職是“瓊州別駕”,再加上他的鼎盛文名,州官自然不敢怠慢,安置于官舍,禮遇有加。但好景不長,赫赫貶官居官舍,總有人看不下去。一代文豪的蘇東坡被逐出官舍,無地可居,還在桄榔林中搭蓋茅屋住過,且自命為“桄榔庵”,寫過《桄榔庵銘》。這時候,當地有個名叫黎子云的逸士,將其舊宅重建,并取《漢書·楊雄傳》中“載酒問字”的典故命名為“載酒堂”,請“大學士”蘇東坡在此為海南學子講學。東坡欣然應允,而且一講便是3年,海南歷史上第一個進士便出自這里。清代的戴肇辰在《瓊臺紀事錄》里的一段話代表著史家和海南人的評價:“宋蘇文公之謫居儋耳,講學明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
載酒堂里的對聯讓人流連,印象最深的是:“靈秀毓峨眉縱觀歷代縉紳韓富以來如公有幾,文明開儋耳遙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滋多。”是啊,如公有幾?上下五千年,如公有幾?!
遺憾與追尋
在贊嘆和流連之間,還是有一種遺憾如影隨形。我走遍了整個東坡書院,不管是在古意氤氳的載酒亭、載酒堂,還是在后人緬懷的欽帥堂、迎賓堂,我尋遍了所有的碑刻、木刻、書畫、圖片和文字,連蘇東坡離島前在澄邁寫給好友趙夢得的手札都還在,就是不曾尋到“弦歌四起”的影子。在遺憾中逛至后院,一片豐潤竹林映入眼簾,想起蘇東坡的“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使人瘦,無竹使人俗”,有風拂過,感覺那竹林里有琴聲飄蕩,神思恍惚間,東坡一邊講學一邊撫琴的場景歷歷如在眼前……
一叢叢青竹,是東坡的最愛。琴,又何嘗不是?我們讀他的琴詩,游山玩水時在聽琴,會客訪友時要聽琴,寫詩作文時在聽琴,甚至睡夢中也在聽琴,琴成為他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知微妙聲,究竟從何出。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聽僧昭素琴》)寫出了琴給予他的寧和美妙的感受。“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和陶貧士七首》)寫出了琴給予他的自在自得的真趣。“神閑意定,萬籟收聲天地靜。玉指冰弦,未動宮商意已傳。悲風流水,寫出寥寥千古意。歸去無眠,一夜余音在耳邊。”(《減字木蘭花》)寫出了琴給予他的清凈意境和高古逸韻。我們從他的詩文里,隨處可以讀到琴在他生命中的分量,儋州三年,怎么可能沒有琴呢?
據張右袞《琴經·大雅嗣音》記:“古人多以琴世其家,最著者——眉山三蘇(蘇洵、蘇軾、蘇轍),斯皆清風頡頏”。東坡早年的琴詩《舟中聽大人彈琴》,寫的便是聽父親彈琴的感受,詩云:“彈琴江浦夜漏永,斂衽竊聽獨激昂。風松瀑布已清絕,更愛玉佩聲瑯珰。”琴音把他帶進清幽的仙境,如玉佩般純凈的琴音使他陶醉。據唐中六先生《巴蜀琴藝考略》書中記載,蘇東坡“一生寫琴詩四十余首”,琴論《雜書琴事》,備述那時的琴界琴人軼事,且多次為琴曲填詞,說“蘇東坡是一個能琴的人,是一個深知琴理的人,是一個生活中離不開琴的人”。其所言極是。
紹圣三年,即蘇東坡赴儋州之前一年,隨東坡貶居惠州的侍妾王朝云因病去世。東坡在悼念她的“六如亭”上曾題有這樣一副對聯:“不合時宜,惟有朝云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這副對聯,讓我們觸摸到蘇東坡的深情,也看到琴在他深情里的存在。而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里的那張刻有“紹圣二年東坡居士”的宋琴,是否“獨彈古調”之琴?這張琴的背后還有著怎樣深情的故事?
在蘇東坡的《雜書琴事》里所記載的《書王進叔所蓄琴》,有說當時他仍在儋州,有說是他離島途經廣州時所記:“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后一指為妙,以蛇蚹文為古,進叔所蓄琴,前幾不容指,而后劣容指,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該文寫于“元符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099年,東坡元符三年六月,即公元1100 年才獲赦北歸,據此推斷,此文當寫于流放儋州期間。記得前幾年有臺灣學者考辯研究湖南省博物館館藏古琴,其中有張刻有“進叔”二字的宋琴,其論文里推測此琴乃東坡此文所記之琴。
《書王進叔所蓄琴》的寫作時間,離東坡去世不足2年。琴,在蘇東坡一生里,可謂貫穿始終。
在揮之不去的遺憾里,惟有于蓮池上、榕樹下、竹林前,遙想他當年在這里會客垂釣,談詩論畫,種花侍竹,獨彈古調,對酒當歌。“幾時歸去,作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云。”這是我最喜歡的東坡琴詩《行香子》,其所憧憬的圖景何其澄澈,何其美好,何其曠達!儋州的東坡,“一壺酒,一溪云”都有了,獨獨缺“一張琴”!
缺席與追問
是什么原因讓琴在東坡遺存里“缺席”?儋州如此,惠州如此,多年前去過的杭州蘇東坡紀念館似乎也如此,寫下過“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記游定惠院》)等琴詩文的黃州,其蘇東坡紀念館里也沒有琴的蹤影,就連東坡故里四川眉山,也只是在2007年開館的“三蘇紀念館”里有一處“舟中聽琴”的“仿真塑像”,有赫赫聲名的“三蘇祠”里,琴好像也是“缺席”的。在大名鼎鼎的林語堂所著的號稱“二十世紀四大傳記”之一的《蘇東坡傳》里,近400頁的皇皇巨著里,將他的詩文書畫甚至瑜伽煉丹都寫到了,就是沒有琴!是蘇東坡詩文書畫之名太盛而淹沒了他的琴名嗎?琴的“缺席”帶給我們的僅僅只是遺憾嗎?
林語堂在《蘇東坡傳》里寫到東坡寫信給朋友說:“我一生之至樂在執筆為文之時,心中錯綜復雜之情思,我筆皆可暢達之。我自謂人生之樂,未有過于此者也。”蘇東坡愛詩文勝于愛琴,歷朝歷代的后人更多從他的詩文里得到快樂和共鳴,“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 (《辛稼軒詞序》)“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自覺氣索。”(《東坡之詩文》)但這似乎也不該成為讓琴“缺席”于蘇東坡生命歷程的理由呀?
東坡曾有詩云:“千年寥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舟中聽大人彈琴》)琴者,情也。“凡音者,生人心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樂記》)琴者,禁也。“禁邪歸正,以和人心。”(南宋·劉籍《琴議篇》)琴者,凈也。凈情性,靜人心也。琴在東坡的藝術生命里是“不死”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琴,既是東坡精神內蘊及價值核心的源頭,又是其過程和結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東坡澄澈曠達之風神與其如精金美玉的詩文書畫,無疑都有琴的烙印,這是如此“不約而同”的“缺席”可以掩去的嗎?
從東坡書院出來,已近黃昏,儋州的朋友說,不遠的海邊還有一處值得一看的“古鹽田”,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歷史!我腦子里閃出的第一個問號竟然是:蘇東坡去過嗎?當夕陽映照下的千年古鹽田神奇而壯觀地呈現在眼前時,心里蕩漾著驚嘆和震撼,也莫名地推想這里一定有東坡的足跡。尋尋覓覓,“東坡鹽槽”在一個美麗村姑的指點下奇跡般地現身,據傳當年東坡來到這里,被仙人掌刺傷,便用此鹽槽的鹽水敷治腿傷……站在古舊的“東坡鹽槽”邊,想到我們日日不可或缺的鹽竟然以如此本樸而詩意的方式存在并延續千年,在日日吹拂的海風中“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而琴并非我們日日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盡管古人說“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且“無故不撤琴瑟”,但沒有琴,似乎并不影響日常的生活。在社會的流變中,琴逐漸被邊緣化,甚至被人們忽略和遺忘。這種忽略和遺忘,是否折射著我們對內心世界的一種輕慢?對東坡琴的忽略,是否折射著今人缺失對內心世界更深層次的探究?“東坡鹽槽”的鹽水依然可以療治傷口,東坡琴還能重新“浮出水面”嗎?
“琴上遺聲久不彈,琴中古意本長存。”(《次韻子由以詩見報編禮公借雷琴,記舊曲》)回到重慶,看到一則有關東坡書院的消息,題為《海南儋州將投資20億蘇軾謫居地修建東坡文化園》,從今年開始,“儋州將用5年時間,打造以東坡文化為品牌的東坡文化園”。在這個用“重金”打造的“東坡文化園”里,對“東坡文化”的研究、考釋和觀照是否會更多角度、更少遺憾?在古琴回歸與復興的大背景下,我們是否在欣賞東坡詩文書畫的同時,也能品味“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弦”(《醉翁操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