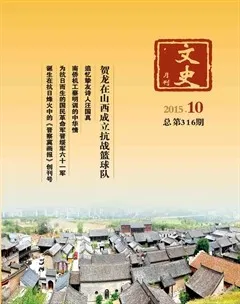追憶摯友詩(shī)人汪國(guó)真
汪國(guó)真老師因病于今年4月26日凌晨2時(shí)病逝,終年59歲。我與他相識(shí)二十載,從相識(shí)、相交、相惜到相信,一段段故事,一句句話語(yǔ),讓我永難忘懷。
相 識(shí)
我與汪國(guó)真相識(shí),是1996年3月,當(dāng)時(shí)山西一位好友約他和我同在北京的勞動(dòng)大廈拜見另外一位好朋友。在這之前,我就已經(jīng)讀過他的詩(shī),也是他的忠實(shí)讀者。第一次見到汪國(guó)真,給我的深刻印象,至今想來好似昨天一樣歷歷在目。當(dāng)時(shí)的他,斯斯文文,俊秀的臉龐上戴著一副秀瑯架眼鏡,越發(fā)顯得文雅,帥哥一個(gè)。40來歲的他,看上去像個(gè)大學(xué)生,毫無鋒芒畢露的那種詩(shī)人狂態(tài),卻靦腆得如同一位姑娘。
當(dāng)時(shí),我從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國(guó)畫系剛畢業(yè)不久,正籌備在中國(guó)美術(shù)館舉辦的“迎九七香港回歸九十七牛作品展”。剛走出校門的我初出茅廬,年少氣盛,有種急功近利的心理,就請(qǐng)教汪老師該如何辦好這次畫展,并希望他能給出建設(shè)性意見。汪老師聽了我的一些想法后沉思良久,對(duì)我說:“繼山,你太急了,干什么事情都不能太著急,要耐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勤修苦練。這次畫展是你來北京第一次向京城美術(shù)界展示你的開始,要以交流學(xué)習(xí)為主,其它為輔。”他告訴我說:“繪畫重視基本功,師法自然,苦練不止,始有成功可能。先把這次畫展當(dāng)成演練場(chǎng),循序漸進(jìn),推進(jìn)式前進(jìn),未來一定會(huì)圓夢(mèng)的。”短短的一段交流讓我感到熱血沸騰,渾身增添了無窮力量。汪老師還送我一句話:“才須學(xué)也,非學(xué)無以廣才”供我自勉。
同時(shí)汪老師還建議我北京展完再回家鄉(xiāng)河南巡回展出,每一場(chǎng)畫展他都會(huì)站臺(tái)出席,親臨指導(dǎo)。一位全國(guó)知名詩(shī)人能夠?qū)ξ疫@樣小字輩如此眷顧與恩賜,我感覺遇到這樣的好老師真的是三生有幸。我與汪老師可謂一見如故,他不但沒有高高在上的名人架子,而且還把我當(dāng)成了知心的朋友。對(duì)于我這樣的一個(gè)文藝青年,如同二月的春風(fēng)、三月的甘霖。多少年來,我一直未能忘記這次與汪老師的談話,是他的諄諄教誨以及對(duì)人的真誠(chéng)友善給我無窮的力量和信心。這種力量和信心猶如其詩(shī)中所寫:“從少年到青年,從青年到中年,我們從星星走成了夕陽(yáng)。”
我想,在每個(gè)人的人生道路上,都會(huì)遇到對(duì)自己影響重大的人,或良師或益友或親朋,有的能幫助你度過難關(guān),有的甚至能改變你一生的命運(yùn)。
相 交
1997年5月4日,我的個(gè)人畫展鄭州巡展在河南省博物館舉辦,汪老師如約專程從北京趕到鄭州前來指導(dǎo)。在這次畫展上,還展出了我與汪老師合作的幾幅作品,吸引了眾多的目光。汪老師的到來在畫展上引起了轟動(dòng),許多青年學(xué)子觀眾圍著他索要簽名。很多人說:“名人來了,詩(shī)人來了!”真正感覺到了他受青年人的熱捧和愛戴,體會(huì)到了他的詩(shī)深受人們喜愛。在這之前,汪老師對(duì)河南很多地方相對(duì)陌生,這之后的幾年里,我陪他去了洛陽(yáng)、南陽(yáng)、信陽(yáng)、焦作、開封、新鄉(xiāng)、周口、平頂山、三門峽等地市,去了云臺(tái)山、雞公山、雞冠洞、黃河三峽、伏牛山、桐柏山、賒店明清古鎮(zhèn)等景區(qū),所到之處,汪老師都給當(dāng)?shù)仫L(fēng)景區(qū)留下了珍貴的墨寶,至今他的題詞還鐫刻在河南各大景區(qū)。在河南,我和汪國(guó)真還應(yīng)邀多次走進(jìn)軍營(yíng)、高校、中學(xué)、小學(xué)為當(dāng)?shù)貙W(xué)校學(xué)子們作勵(lì)志人生報(bào)告會(huì)、學(xué)習(xí)詩(shī)歌與繪畫座談會(huì)。也就是從那個(gè)時(shí)候開始,汪國(guó)真開始慢慢從詩(shī)詞轉(zhuǎn)向書法創(chuàng)作。他對(duì)我講:“因?yàn)槌雒耍叩侥睦锶思叶枷胱屇懔粝曼c(diǎn)墨跡,如果字寫不好多丟丑,所以一定學(xué)好書法。”
記得大概是2000年的秋天,我們從洛陽(yáng)回來的第二天,汪國(guó)真突然臉色發(fā)黃,體力不支,馬上送到北大醫(yī)院辦了住院手續(xù)。經(jīng)過檢查,醫(yī)生說是得了急性肝炎,拍了片子被醫(yī)生診斷患惡性腫瘤,這可把大家嚇壞了,擔(dān)心誤診,汪老師的家人和幾位朋友又把他送到另一家醫(yī)院再次拍片檢查,最后確診腫瘤為良性。那次重病可謂虛驚一場(chǎng),但事隔15年,汪老師仍然是因肝癌離去。也許當(dāng)時(shí)的肝病留下今天的禍患,加之這些年他工作勞累,常年游走于全國(guó)各地,每天工作日程排得滿滿的,從沒見他休息過,常年超負(fù)荷的工作,積勞成疾是奪去汪國(guó)真生命的罪魁禍?zhǔn)住?/p>
正是這場(chǎng)大病使汪老師無限感慨地告訴我說:“千萬不要讓自己病了,這一病幾個(gè)月躺在病床上什么事也干不了,太可惜了!”不過汪國(guó)真畢竟是汪國(guó)真,等幾個(gè)月他大病初愈后第一件事就詭秘地告訴我說,這幾個(gè)月在病床上學(xué)習(xí)研究了譜曲,自己可以譜寫曲子了,并說自己譜寫了詞曲,讓我?guī)椭腋枋衷嚦獛资住?duì)于他大病一場(chǎng)痊愈后立即會(huì)譜曲這件事我非常吃驚,好似他突然有了特異功能一樣不可思議。對(duì)于其他作曲家,譜了曲還作詞是一件難事,而對(duì)于汪老師來說作詞那就太簡(jiǎn)單了,他后來作詞作曲譜寫了大量歌曲。記得我們?cè)俅纬霾畹搅寺尻?yáng),他觀賞了黃河三峽后,回到賓館即興作了一首詞曲《黃河三峽之歌》,當(dāng)?shù)刂两褡鳛槁糜瓮平橹琛kS后,汪國(guó)真又為河南多地景區(qū)填詞譜曲,如《信陽(yáng)雞公山之歌》、焦作《云臺(tái)之戀》、南陽(yáng)《丹江水清清之歌》等。他的歌曲還被眾多明星如那英、蔡國(guó)慶、孫悅、白雪等人演唱,廣為流傳。
相 惜
汪老師真正畫畫是從2003年“非典”之后。“非典”期間大家都出不了門,那時(shí)汪老師每天在家研習(xí)繪畫。一場(chǎng)“非典”過后,他會(huì)畫畫了,并且畫得非常有靈氣、有悟性。涉及題材多種多樣,除了人物之外,我看幾乎沒有他不敢畫的,他無拘無束不受學(xué)院派的影響,表現(xiàn)形式別具一格,深受許多美術(shù)愛好者和收藏家的喜愛。我們常常在一起創(chuàng)作探討到深夜,他為我的作品賦詩(shī)作詞,常常為一幅作品的合作苦思冥想到凌晨。有一次我畫了一幅昂首向前的拓荒牛,他立即作詩(shī)并題跋:
埋首向前不偷懶,
犁田墾荒年復(fù)年。
牧童一曲黃昏調(diào),
晚霞絢麗鋪滿天。
汪老師在另一幅作品上題跋:
世人都愿世風(fēng)揚(yáng),
黃牛精神應(yīng)可當(dāng)。
莫道前路多坎坷,
轟轟烈烈干一場(chǎng)。
習(xí)近平主席在亞太經(jīng)合組織會(huì)議(APEC)上引用汪國(guó)真的一句詩(shī):“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zhǎng)的路”,傳為佳話。我也非常喜歡這句名言,為鼓勵(lì)我,汪老師為我題寫了這句詩(shī)句,連寫了好多張才滿意,他說:“有了朋友才有自己的一切,有朋友的地方才有風(fēng)景,我要把這幅作品寫出精、氣、神來,寫出我最滿意的作品送給你。”寫完之后,還專門為我題上:張繼山賢弟留存。后來我在汪老師這句詩(shī)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作出一幅作品,我把它直接命名為《人比山高 腳比路長(zhǎng)》。
1997年至2006年十年間,我與汪老師常年穿梭于全國(guó)各地,一同去浙江杭州、寧波,山西太原、運(yùn)城等地釆風(fēng)寫生,在北京參加各種書畫展、筆會(huì)等活動(dòng),云里霧里飛來飛去,結(jié)下了深摯的情誼。汪老師在我1998年出的一本《我的牛世界》一書中寫序道:“我們會(huì)記得過去,也更憧憬未來,我珍惜和繼山的友誼,我禱祝他事業(yè)成功有日!愿我們都永遠(yuǎn)不放下手中的筆!”
相 信
汪國(guó)真是改革開放以來詩(shī)壇最紅的詩(shī)人之一。他的詩(shī)影響了一代人,甚至幾代人。
汪老師對(duì)我講過兩件事,一件事是:2013年習(xí)近平主席在亞太經(jīng)合組織會(huì)議(APEC)上引用了他的詩(shī)句。那天晚上他從外地坐飛機(jī)回北京,剛落地,打開手機(jī),短信像潮水般涌來,朋友們都在告訴他這件事,因?yàn)椤缎侣劼?lián)播》把兩句話播出來了。他說:“習(xí)主席能背下我的詩(shī)詞,我覺得挺欣慰的,說明我的讀者遍布各個(gè)階層、各個(gè)文化層、各個(gè)年齡層。”這樣的事我親自見證過無數(shù)次,這些年陪同汪老師無論走到哪里都有他忠實(shí)的“粉絲”。另一件事是上世紀(jì)九十年代初,汪國(guó)真正處于大紅大紫之時(shí),在中國(guó)文壇刮起了“汪旋風(fēng)”。那年初,汪國(guó)真到上海,在上海文壇掀起軒然大波:他在上海南京東路新華書店簽名售書,那天下著蒙蒙春雨,讀者排成長(zhǎng)龍隊(duì),從樓上一直排到樓下,盛況空前。他在短短3小時(shí)內(nèi),簽售了4000冊(cè)“汪詩(shī)”,用掉7支簽名筆!據(jù)我所知,任何一位上海作家簽名售書,從未出現(xiàn)如此場(chǎng)面。
這些年關(guān)于汪老師的議論,有的人說他的詩(shī)不是詩(shī),淺薄得很,是“迎合”少男少女,甚至有人掀起一番“倒汪運(yùn)動(dòng)”。但更多的讀者說他的詩(shī)別具風(fēng)味,給人清新之感。在與汪老師多年來的交流中,使我漸漸明白了“汪旋風(fēng)”最初是怎么刮起。在我看來,他不是一團(tuán)稻草,不是一桶汽油,不是在頃刻之間騰起烈焰。他如同煤球爐,經(jīng)過慢慢引燃,爐火漸旺,終于“紅”了起來。
我認(rèn)為,汪國(guó)真詩(shī)有三個(gè)精神特征:青春、勵(lì)志、溫暖。對(duì)于青年人來說,汪國(guó)真的詩(shī)能夠浸透普通大眾心靈。而當(dāng)我問到汪老師時(shí),他告訴我說:“他的詩(shī)有三個(gè)特點(diǎn):一是通俗易懂;二是能夠引起人的共鳴;三是經(jīng)得起品味。”他說:“符合了這個(gè)藝術(shù)規(guī)律,就會(huì)顯現(xiàn)效果。”對(duì)于對(duì)他的詩(shī)產(chǎn)生反對(duì)的聲音,汪老師說:“我不想把人生耗費(fèi)在摩擦中,浪費(fèi)在批評(píng)和反批評(píng)中,世態(tài)難免有炎涼,只求我心靜如常。如此風(fēng)來何妨,無風(fēng)怎知什么叫清爽;如此浪來何妨,無浪怎知我豪放……” 他說:“對(duì)于詩(shī)人來講,人民說你是詩(shī)人你就是詩(shī)人,不被人民承認(rèn)你就什么都不是。人民是什么?人民是由一個(gè)一個(gè)的人組成的,它是一個(gè)整體。如果你否定了大眾,那你的人民如何談起?當(dāng)然,除了人民的看法,還需要時(shí)間的檢驗(yàn)。”
評(píng)價(jià)一位藝術(shù)家的成就,一個(gè)重要的尺度,就是他對(duì)多少人的精神世界產(chǎn)生過影響。在這個(gè)意義上,汪國(guó)真是一位非常有影響的詩(shī)人,他的句子,曾被一代人抄寫在本子上,記在心中。
跟隨汪老師多年,我所了解他的一生經(jīng)歷是這樣的:1956年6月22日生于北京。中學(xué)畢業(yè)以后,曾在北京第三光學(xué)儀器廠當(dāng)工人。后來考上暨南大學(xué)中文系,1982年畢業(yè),分配在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工作。他是一位青年,為青年寫詩(shī),寫青年之詩(shī)。他曾經(jīng)自稱他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得益于四個(gè)人:李商隱、李清照、普希金、狄金森(美國(guó))。他追求普的抒情、狄的凝煉、李商隱的警策、李清照的清麗。他的詩(shī),最初是在許多青年雜志上發(fā)表的。青年雜志的發(fā)行量大,擁有眾多的青年讀者,從此,他的“青春詩(shī)”漸漸在青年心中扎了根。年復(fù)一年,他在青年中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形成了龐大的讀者群。雖說他也在文學(xué)刊物上發(fā)表一些詩(shī),然而,此時(shí)文學(xué)界對(duì)他幾乎一無所知。青年雜志《女友》看準(zhǔn)了“行情”,特邀他開辟了“汪國(guó)真專欄”。他還擔(dān)任《中國(guó)青年》《遼寧青年》的專欄作者。
出于對(duì)“汪詩(shī)”的喜愛,有的青年讀者收集“汪詩(shī)”,抄錄成冊(cè),出現(xiàn)了“汪詩(shī)”手抄本,也得到了青年讀者的認(rèn)可和擁戴。一位女教師把“汪詩(shī)”手抄本交給在北京學(xué)苑出版社當(dāng)編輯主任的丈夫看,她的丈夫主動(dòng)找到汪國(guó)真,愿為他出版第一本詩(shī)集。1990年4月20日,汪國(guó)真的第一部詩(shī)集《年輕的潮》交稿,5月20日便由學(xué)苑出版社出版。汪國(guó)真向我透露,此前,他曾把自己的詩(shī)集交給南方一家出版社,在那里未遇“伯樂”,壓了很久未能出書。5月19日,《北京晚報(bào)》為汪國(guó)真詩(shī)集的出版發(fā)了一條幾行字小消息,翌日王府井新華書店立即涌來大批青年讀者購(gòu)買“汪詩(shī)”。《年輕的潮》竟重印5次,總印數(shù)高達(dá)15萬冊(cè),這在中國(guó)當(dāng)代詩(shī)壇上是不可想像的數(shù)字。7月4日,汪國(guó)真的詩(shī)集《年輕的潮》被《新聞出版報(bào)》列為十大暢銷書之一,文藝類圖書僅此一本。10月,汪國(guó)真應(yīng)邀到北京多所大學(xué)作詩(shī)歌演講,受到大學(xué)生們的熱捧。這清楚地表明,“汪詩(shī)”不是“自上而下”、由詩(shī)壇權(quán)威捧起來的,卻是“由下而上”、由青年讀者擁戴而形成“熱點(diǎn)”。
與汪老師同行的這些年,不論在哪里,隨時(shí)都能遇到當(dāng)場(chǎng)背誦“汪詩(shī)”的“粉絲”,他仿佛成了青年中的“知音”。在當(dāng)時(shí),論資歷,汪國(guó)真很“嫩”;論作品,他也不過出了幾本薄薄的詩(shī)集。然而,他已成了中國(guó)詩(shī)壇一顆耀目的新星。他的成功,道出了一個(gè)道理:不論作家還是詩(shī)人,應(yīng)該真誠(chéng)地貼近廣大讀者,尤其是貼近年輕讀者。只有和廣大讀者心相通、心相連,才可能使文學(xué)家走出象牙之塔。
他的詩(shī),在今天一些人讀來或許不夠“有感”,也難以澎湃“90后”“00后”的心潮,然而,他曾經(jīng)的確陪伴無數(shù)年輕人青澀而迷茫的青春旅程。在今天的青春視野里,有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匯聚的信息海洋,也有無數(shù)開啟心扉的精神食糧可供選擇,汪國(guó)真和他的詩(shī)句,就影響著那一代青年。“既然選擇了遠(yuǎn)方,便只顧風(fēng)雨兼程;沒有比腳更長(zhǎng)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要輸就輸給追求,要嫁就嫁給幸福;你若有一個(gè)不屈的靈魂,腳下就會(huì)有一片堅(jiān)實(shí)的土地……”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這些詩(shī)句,如一彎清淺的小溪,流過干涸的青春原野。對(duì)于一個(gè)詩(shī)人來說,沒有誰能始終活躍在心靈的舞臺(tái)上,但只要他曾經(jīng)給一代人的心靈留下印跡,他就值得人們銘記。青春因?yàn)辄c(diǎn)燃,所以銘記,因?yàn)樵煸L,所以懷念。
微信朋友圈里,不少70后轉(zhuǎn)發(fā)汪國(guó)真老師的消息和詩(shī)句,感懷傷別。如果說,這一代人在實(shí)現(xiàn)精神大成后,逐漸在生命的旅程中淡忘了汪詩(shī),那么,今天的感念則是對(duì)那一段闊別的青春的集體性重溫。詩(shī)是文化大家族的小精靈,是穿透心扉的無形力量。在青春的重溫中,我們的心靈曾有幸被詩(shī)熏陶過。那個(gè)年代,汪國(guó)真的詩(shī)讓青春在一種純粹的精神旅程中實(shí)現(xiàn)自由放飛。今天,詩(shī)歌難以在時(shí)代的大潮中激起那樣的精神浪花,我們也并不苛求每一個(gè)時(shí)代都要有詩(shī)的激蕩才能銘刻青春的印記。但是今天的青年人,他們的年華又將在怎樣的精神陶冶中走向成熟呢?固然,現(xiàn)代吸引眼球,刺激神經(jīng)的物事紛繁,很多青年人要么浮躁而迷失,要么流俗而追星,要想讓青年人獲得當(dāng)年那種神往般的專注,殊非易事。但在另一方面,作為文化人也應(yīng)該沉思,要怎樣擔(dān)當(dāng)起鼓蕩這一代人青春的使命?回首往昔,汪國(guó)真用或許淺近的筆觸慰藉了一代青年人的心靈,那么今天的文化人又該以怎樣的精神養(yǎng)分致這一代人的青春?這是汪老師的離世留給我們的深層思考。
汪老師不愧是當(dāng)代多才多藝的詩(shī)人,人到中年,益見光彩。但令人嘆息不已的是,汪老師猝然而故,距囊括他的詩(shī)歌、散文、書法、繪畫等多種作品的新詩(shī)精選集《青春在路上——汪國(guó)真新詩(shī)精選》出版不足一個(gè)月,他贈(zèng)送給我的書法,真的成了“歷史的絕筆”!汪老師走向了遠(yuǎn)方,把背影留給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