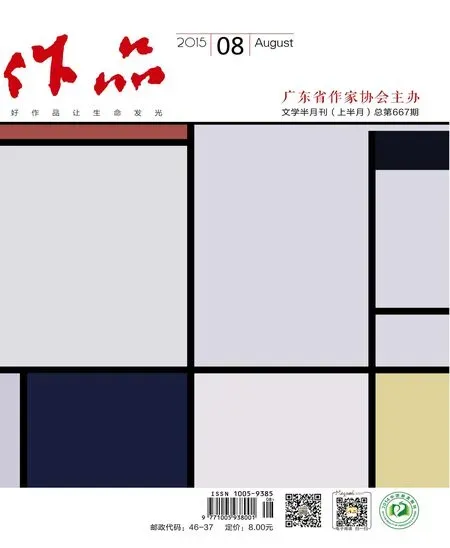忍冬草與一座城市的近代史
文/林淵液
1
我得承認,對汕頭這座城市的認識,是從小公園開始的。小公園其實不見公園,它是一個老街區的統稱。
2
汕頭嫲的家就在小公園福海街,孩提時候,每年我都會隨奶奶和父親來這里做客一兩遭。有些往事,我們是必須懷著深厚而清澈的感情來回憶的。當年我們住在汕頭轄下的小縣城,很有些鄉下人的意味,去汕頭嫲家做客,猶如過盛大節日般隆重。很多天前大人們已經有過籌謀,各種手信各種叮囑各種緊張、興奮和期待,還有大人們一句嚇唬人的口頭禪:再這樣不帶你去汕頭嫲家里了!那些天,跟伙伴兒玩鬧的時候就多了一樁心事,有時口角一彎莫名奇妙地露出笑意,有時又因惦記著大人們的告誡,把自己的心提一下,瘋勁也就收斂一些些。
起早,候車,坐車……經過二十公里的路程終于到得汕頭汽車總站,我被奶奶牽拉著,用自己小小的腳丫子開始丈量汕頭的土地和橋梁,穿過解放大橋,穿過回瀾橋,走過紅磚樓,很快便到鎮平街了。福海街就是鎮平街上的一丫樹枝。奶奶一路和汕頭嫲的鄰右打著招呼,便到了福海街10號。汕頭嫲住的是二樓,樓下的喧嘩聲把她打擾到了,我們踩上木板樓梯的時候,她已經趕到樓梯口迎接我們。她說接到我父親的信函后,已數念好些時日了,終于把我們盼到。仰望視角中的汕頭嫲,她的滿頭銀發在晨曦映襯下,似乎有一種神啟的光芒。
在我童年的認知里,小公園老街區呈現的是類似于北歐童話和德國童話里的世界。整個街區仿如一個龐大的洋宮殿,樓房有三四層高,墻是晃白晃白的,上面刻滿了好看的浮雕花紋,鑲嵌著廊柱、凹陽臺和門窗。廊柱仿佛是有雌雄之分的,陽剛的宛如彬彬漢子,灑脫利落;陰柔的宛如窈窕淑女,花冠錦飾。恍惚之間,他們全都活了起來,挺拔著身子,在宮殿里隨著音樂,慢慢跳起了勇敢而優雅的舞。他們的身后,是一扇又一扇的彩色玻璃窗,櫻黃、玫紅、寶藍、檀綠……窗眉上長滿裝飾性很強的忍冬草、飛舞著金鳳凰,不知什么時候,就有一個伸展著翅膀的光屁股胖小孩探出頭來……這種突兀而驚駭的美麗,無疑地有著極強的侵略性,它像一把長纓槍,挑破了那個小女孩旖旎夢想的海平面。我猜想,當年的她,在汕頭嫲的眼里,一定是木訥的,笨鈍的。置身于小公園,只有眼睛這個感官是她能夠用上的,其他的感官通通都暫時性地退化,或者禁閉了,腦瓜更是。
汕頭嫲卻也未曾嫌棄過我。她面容清秀,知書識理。她的話語很輕,但舌頭里有魔力。聽父親說,她的信件也寫得很有書香氣。多年之后,又聽父親提起汕頭嫲,說她是富人出身,當初出嫁的嫁妝足足有十箱八囊。汕頭嫲與奶奶聊天的時候,我總是坐在她們的膝邊,安靜地聽,似乎那話題里有我喜歡的情節。其實她們聊的都是家長里短。汕頭嫲有六個孩子,我只見過二伯五姑和細叔。五姑是嫁了香港客的,難得回來一趟。二伯、細叔與汕頭嫲一起住。細叔高中畢業后上山下鄉,從英德娶了當地老婆回來,細嬸講的是廣府話,我們視若畏途,很少與她交流。細叔長得白面書生模樣,但他訥于言,止于禮,我與他顯得隔膜。二伯性情有點古怪,終生未娶。他長相黑瘦,特像許多年后我在電視里看到的索馬里難民。一開始我很懼怕他,但他卻是喜歡逗我玩。有時會神秘地取出一塊玉,與我談論它的質地、聲音和寂寞的夢想。我眨巴著眼睛,聽得一頭霧水。后來從父親口中得知,二伯是販賣古玩生意的,也只是小本生意而已。二伯與汕頭嫲同睡在一個狹長的房間,二伯敞亮的床正對著小客廳的門,中間碼放著一排五斗柜作為隔斷,里頭就是汕頭嫲的床。我們到來之際,二伯是把床讓出來的,自己打地鋪。汕頭嫲有時會爭要我去陪她睡,但我喜歡與奶奶擠在二伯的床上。怕生的意思還是有的,更重要的是,二伯的床頭頂就有一扇漂亮的彩色玻璃窗,它所發散的磁場深深吸引著我。我喜歡后仰著頭,看著那扇窗子冥思,然后沉沉睡去。在我童年生活的小縣城里,街路上行走著的盡是身著藍、白、黑這等素色衣衫的人,很難見到一些活彩。我一直堅信,那扇窗玻璃的色彩于我是有美學啟蒙意義的。
或許,我只有繼續動用當下的理解能力,才能解開當年的迷惑面紗。這個小女孩,她所居住的小縣城,房子是典型的潮汕民居,一座小小的“下山虎”建筑,兩家人共同分享著。她家住在右手邊,半間客廳、一間大房和一間小房。這一帶都是平房,灰頭灰臉的,僅有的裝飾就是有點花邊紋飾的山墻,潮汕人稱為“厝頭角”,大多也剝脫模糊了。還有大客廳的瓦頂上不知道誰的祖先種下的一簇仙人掌,原也不是審美的用途,是辟邪祛災的。仙人掌在溫濕的南方不容易開花,但在廳頂的這一簇每年夏天都會嫣紅姹紫地開上個把月。某一天,視野里有了不同尋常的建筑物,那一定是外婆去老爺廟祭神把她捎上了。廟里看到的是塑著金身髯髯有須的大男人,他呆板地端坐著,臉上的慈祥和傻勁一樣是一成不變的。這個人被稱為福德老爺。廟宇很小,卻是眼花繚亂的,有人間煙火氣的。趁著外婆上香磕頭的時候,她經常跑出廟外門樓肚看壁畫,早已斑駁褪色了,但外婆眼力好,說那是百鳳朝凰。她抬頭的時候,看到了藍天映襯下彎彎翹起的屋檐,外婆順著她的眼光,說:“厝角頭是有戲出的。”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那是民間藝人用碎瓷片做成的嵌瓷工藝,左邊厝角的那一出戲,外婆當時說的是“桃園三結義”。這,就是當年這個女孩的日常和非日常兩種美學遭逢,老舊的,傳統的,民間的。
對于異質的入侵我一直心懷感激。從這點看我極有可能是一個危險分子。我覺得,只有異質能夠把靜態點破,能夠把火把點燃。當然,它的危險性和致病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輕則生態失衡,重則世界覆滅。
小公園的歐式建筑風格就如一個文明的入侵者,溫柔卻又強勢地攻占了汕頭這座城市。一百二十多畝的面積,十九條街道矗立起騎樓建筑。
多年后的今天,我才從建筑學家們的口中,學到了一些專業名詞。雖然對它們的具體樣式一知半解,但大意是可以理解的。在小公園老街區,既可以找到古希臘、羅馬的建筑烙印,又可以找到哥特式風格、文藝復興風格、巴洛克風格和古典主義風格,大多以嵌入浮雕和壁畫等裝飾繁復的外墻、拱券、弧形山花為主要特征。與當年那個女孩眼里的映象相互指認,有些事情越來越清晰,有些事情越來越迷糊。
3
當我重新站在福海街10號的門口,歲月已經對這個世界的人和事施行了騰挪大法。三十余年過去了,我也已于二十年前來到了這座城市。
當年通往小公園的路不知道什么時候斷的,那個歐洲童話般的夢境,永遠地定格在古舊的絨面像紙上。只是,世上事縱橫交錯。不管是筆直通天,還是蜿蜒曲折;不管是被大江阻斷,抑或隔著巍峨大山,總有重新接續的那一天。
雨蒙蒙地下著,我撐著一把紫色的涂層傘尋到了福海街。抬頭看著那個我曾經眷戀的凹陽臺,那一根我曾經倚靠過的廊柱,那一扇我曾經心儀的彩色玻璃窗,似曾相似,卻又面目全非。整條街都荒棄了,泥沙蒙面,蛛絲攀掛。門是被封住的,進不得,退又不甘。
打電話問過父親,他說,細叔夫婦早就搬離了小公園,而汕頭嫲和二伯一直住在這里。汕頭嫲過世的時候二伯還通知父親前來吊唁。二伯患有肺病,還沒上壽就走了,這一次,沒有人通知父親過去。我對汕頭嫲與我們一家的緣分懷有深深的好奇。父親說,汕頭嫲以前在小縣城居住過頗長的一段時間,他們家與我們家比鄰而居,汕頭嫲的丈夫在汕頭一家商行當賬房,一年半載難得回家一次,她一個人提攜六個子女。奶奶是早就孀居的,帶著父親一個孩子,兩家人因此相依為命,很像是兩個媽媽帶養著一群孩子。汕頭嫲很喜歡父親,就把他契為義子。一契一義,都是舊時樣式,在近現代文明的面前,莫非,它是應該隱退的。這么說來,我今天的尋而無蹤也應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那一陣子,我的內心其實懷著極大的痛苦。我的周圍出現了一場文明人的惡斗,它使我手頭的工作因為人為因素而困難重重。我很愿意超越出來,像一個小男孩撥弄著手中的樹枝,觀看兩只螞蟻的打斗。可是,當一只螞蟻只擁有螞蟻的視角,在他打斗的時候怎會明白這一切竟然是如此渺若草芥。更為可怕的發現是,當我不得不與魔鬼對面而晤時,我身體里潛藏著的另一個魔鬼也趕忙出來應戰。這件事情對我的傷害是雙軛的。
我在小公園漫無目的地走,竟然走了七天。每天,晨曦初起的時候就出門,信手拿著一個相機,看到漂亮的山花、拱券和廊柱就拍下來,如果有一兩株五瓣梅從廊柱的縫隙邊鉆出來,那就更見生機了。小公園的街道是環狀放射的,據說,這個世界上,只有巴黎和小公園是這樣的設計。以前,聽汕頭嫲講過一個段子。外地人到小公園,迷路是家常便飯。第一次問路,回答說是小公園;第二次問路,回答還是小公園……十八次的重復之后,他終于恍然大悟:原來汕頭有十八個小公園。與這個路盲可有一比,我也是轉著轉著,就回到了小公園中央區。不過,去街角轉彎處的錄音鋪聽一下潮劇,去老字號小食店吃蠔烙和水晶球粿,這都是蠻享受的。這里的荒涼和滄桑本是應該讓我痛上加痛的,可是,事情卻朝著相反的方向走去。我凌亂郁結的心緒,竟然在那些蛛絲纏繞的忍冬草撫慰之下,慢慢地舒展開來,似乎我真可以是一個置身度外的小男孩,對世上所有螞蟻的糾結安之若素。我終于明白了,為什么那么多老汕頭人把小公園當成休閑、懷舊的一個所在,時不時地就愿意來這里走走、品品、看看。它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舊。舊,是一種能夠打動人的內心柔軟角落的品質。它有剝脫的墻體和浮雕,有上世紀的汕頭人若隱若現的身影,有歷史感,有滄桑感,有風雨的聲音和歷練,有陽光自東向西的輪回。另一個特點是:慢。慢是什么?慢是把一顆薰衣草的種子種下去,等待它破土而出,成長,開出花來;慢是把內心醞釀得如酒般濃的情感,折疊在一封八行箋里,寄出去,等待回音;慢是把繡花針插入蜻蜓圖稿的尾部,用長短針繡一針一針地把它繡出來,讓它展翅飛翔。
小公園的撫慰是非特異性的,卻是籠罩性的。
4
為什么在保守而傳統的潮汕大地,出現了這一大片歐式建筑街區?
而整座城市的中心東遷之后,歐式建筑風格為何不再維持?
為什么它像這座城市褪下的一枚蛻殼,再沒有活體和活力?
而有那么多老汕頭人對它津津樂道,它當年的風光到底如何?
為什么這片街區的繁榮年代,汕頭并不曾為它留下翔實的史料?
而民間口述者的口水似乎一直源源不斷……
是的,我并不僅僅把小公園當成一個童年的夢境,也不僅僅把其當成療治心頭之傷的懷舊之所。我現在所看到的,肯定只是一個小小的局部,就如一個潛海員在海底看到了一片奇特的珊瑚礁,海葵、海綿、海星、海參、海膽早已把這當成了幸福家園,幼魚們也在其間自在穿梭。軟體動物雖然以蠱惑人心的顏色和觸手把什么東西遮掩了,但那骨架還在,它是否就是傳說中若干年前的一艘沉船。站在這里,我仰望、俯視、左瞧、右看,那都是不夠的。它太龐大了,我必須一直往后退,往后退,我必須奔跑著往后跑,才能夠離真相更近一些。我必須知道過去的過去性,還必須知道過去的現存性。
我一直相信,一種宏大建筑的背后,一定有一個發達的文明體系。希臘的梁柱式廟宇、羅馬的圓穹頂建筑、中世紀哥特式天主堂、中國封建王朝的大屋頂宮殿,莫不如此。那么,支撐小公園的文明是什么?
我希望首先從地方文史資料進入小公園的歷史。令人遺憾的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汕頭市政廳于1921年設立),那一段的歷史資料相當匱乏,《潮州志》關于汕頭的大事記,內容大多為軍閥余部戰爭、紅色革命、自然災害等等。在圖書館地方文獻特藏部,僅僅找到兩本相關資料,一本是《汕頭指南》,一本是《六十年來之嶺東紀略》。后者是時任汕頭市長的蕭冠英所著,該書已成為研究那段歷史繞不過去的一份史料,令人禁不住為民國范兒致敬,這是題外話。而在檔案館,除了幾張修筑某街路、建筑某工程的工料表之外,一無所獲。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民間對于小公園的繁華有著細碎而夸張的描述。他們把當時的汕頭稱為“百載商埠”,汕頭港外洋往來吞吐量曾居全國第三,商業之盛居全國第七,每天是“商賈云集,萬國樓船”……在小公園商業騎樓,多的是洋行、酒樓、歌肆、賭館、妓院、匯兌行、米棧、綢緞莊、洋布行、抽紗行,當然,還有藥材鋪、腳屐鋪、柴鋪、修船鋪、打銅鋪、打錫鋪、打石鋪等等,不一而足,據說,中央酒樓的播音唱曲,整晚整晚地不曾停歇,是汕頭的不夜天。這個中央酒樓幾經變遷,等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父親時不時去汕頭嫲家里走動,它已經變成了一個百貨公司。直到此時,它依然是汕頭一個萬眾矚目的商場,似乎能夠去那里走上一趟,人也變得高尚起來。有一次,父親從汕頭回家,鄰居聚過來聽講新鮮行情。父親說,百貨公司二樓樓梯口放著一個哈哈鏡,人一照,就變成胖子,臉胖,肚子也胖,他伸出雙臂比劃了一圈。鄰居的大姐姐不信,卻又躍躍欲試,便說,要她未婚夫帶著去參觀一下。父親吞吞吐吐欲說又止:可是,那地方人真擠,魚龍混雜,聽到一個女孩子尖叫,說是有人渾水摸魚,捏了她的雙乳。
這個軟紅十丈的地方,似乎從一開始我就嗅到了它的復雜和含混氣味。我猜想,它在當時,就是一個小上海,商業與消費娛樂至上。而在它最繁華的地段,依然有各種不和諧的音調在提醒著。外國的領事館雖然不集中,但足足有十一家。而大多數洋行,卻以“販賣豬仔”名世。所謂販賣豬仔,其實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在沿海地區誘騙和擄掠華工的勾當。繁華的姓氏是屬于富者的。這一段充滿血淚的歷史,聞之令人心酸。
我不否定,在汕頭港經商的大多數商人,是善于把握時機、聰慧和精明的,他們贏得巨額利潤過上奢華生活也無可厚非。但在這些傳奇故事當中,經常也攪拌著一些沙礫。小公園有一處房子非常出名,被視為“富人厝”,叫做“乾泰厝內”。據說其原先主人林乾泰是福建人,在汕炒地皮發了跡,捐錢買了一個小官職。他最早在此地建大夫第,清光緒18年間(1892年)建成乾泰厝內,成片66幢。他勾結官府,無錢不賺。最后卻因結怨晚清大吏,又涉案包攬鴉片煙稅,導致敗家破產,地產像切豆腐一樣,一格一格地賣出。
我曾經拜訪過乾泰厝內,多已荒蕪,只有陳老師一家,在一幢經過修葺的房子里堅持著。他是在這里出生的,已經老了,思維雖還清晰,但吐字困難。他女兒真姐帶我參觀了房子,站在二樓天臺,看到荒廢的后院,有榕樹和一些不知名的老樹高高聳起,不禁心里頗為悲涼。那些樹,與往日所見有異,不知是否遠離人氣所致,它們有些成精的意味。但愿真姐夜來不會怕黑便好。真姐對林乾泰一無所知,只把他當成一個出名的富人,不予藏否。就像許多老汕頭人把小公園當成一個了不起的地方一樣,也確實不知道如何藏否呀。
汕頭的歷史并沒有為小公園的存在留下太有力的憑證,但我們可以繼續往后退,退到中國和世界的近現代史。鴉片戰爭之后,汕頭作為一個通商口岸,西方文化加大傳入力度。教堂、醫院、學校、育嬰堂、修道院等西式建筑首先傳入。之后是領事館、別墅、海關、銀行、商行、火車站、汽車站、碼頭……這些都是文化的先行。最重要的,還有資金的投注。二戰之后,全球經濟留下了一條長長的傷疤。海外華僑把資金抽回,投向家鄉,商埠的繁榮自不待言。小公園的建筑,大都商住合一。華僑們被改造過的視野和文化,在這里重新落地生根。
我一直懷疑,民間的力量是否如此強大,可以把整座城市翻天覆地。后來,得一位當城市規劃師的朋友援助,看到一張當年小公園街區的規劃圖,一切才恍然明白。我們的政體,自古以來都只有從上至下一個系統,在城市的規劃方面,它無疑地為騰空信筆的大手筆提供了寬闊的空間。將近一個世紀之前是這樣,相信現在也是。
5
歷史的烽煙已然退去,但我心里卻明白如鏡。誘發中國啟動現代化的方式,是從侵略開始的。租界的設立、通商口岸的開辟、港灣租界地、鐵路附屬地的圈占等等,都是通過不平等條約來實施。在我們的城市,近代化的過程中攪拌著的就是殖民化。我們的開放是被動的。我們的美麗是被動。我們的富裕是被動的。我們的文明是被動的。我們的城市是被動的。
幸好,它已經過去了。
忽然,記起建筑學家維特魯威講過的一個動人傳說:
科林斯市的一名少女在婚期來臨之際患病身亡,乳母把她生前鐘愛的東西聚集在籃子里,放到她的墓碑頂上。為了籃子里的東西在露天里盡可能放得長久,便用一塊石瓦蓋住。籃子底下剛好有忍冬草的根穿過,春天,它從籃子下蔓生出藤葉來。它的藤沿著籃子的側邊成長起來,由于被石瓦壓住,所以長成了渦卷形的曲線。據說,這就是希臘建筑中科林斯柱頭的由來。
我更愿意把這座城市的一段歷史,也想象成美麗的少女躺臥的地方,雖然她已經走了,但頑強的忍冬草自會從籃子底下蔓生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