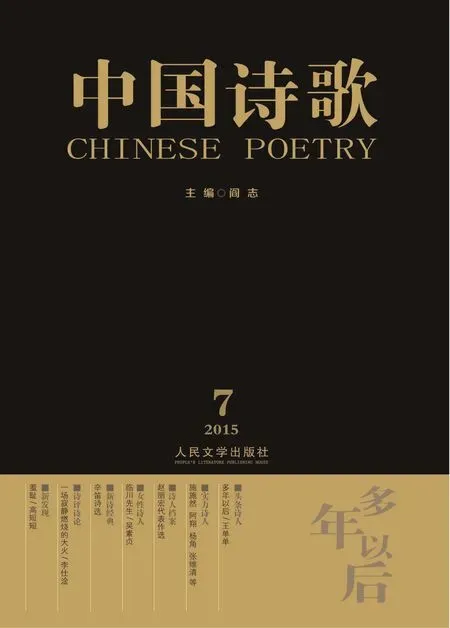九葉詩派的中堅力量
——辛笛詩歌導讀
□鄒建軍 王金黃
九葉詩派的中堅力量
——辛笛詩歌導讀
□鄒建軍 王金黃
辛笛是九葉詩派的重要詩人,也可以說是九葉詩派的命名者,因為在1979年出版《九葉集》的時候,據說是由他為這本詩集取名的,后來成為了九葉詩派的起始,這就是歷史的機緣巧合。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只有《中國新詩》所團結的一批詩人,并沒有“九葉詩派”這個名稱,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詩歌社團叫九葉詩社,而在三十年之后,主要在《中國新詩》上發表作品的九位詩人,要出一部作品集,沒有合適的名字,辛笛成為了它的命名人。他從十二歲時就開始了詩歌創作,并在當時讀書學習的南開中學小有名氣。后來,詩人在清華大學就讀外國語言文學的時候以及在英國愛丁堡大學讀英國文學期間,開始與英美詩壇的多位詩人有了接觸和交往。在這個階段,辛笛受到了英美詩人如艾略特、葉芝等人的重要影響,開啟了真正的詩藝探索之旅。在九葉詩人群體中,他是作品數量較多而且質量較高的一位,并且越到后來越有著更大的發展,寫出了許多優秀的詩作。
辛笛從事詩歌創作的歷史很長,從小開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期,雖然偶有間斷,卻能夠一直堅持下來,并且形成了幾個重要的創作時期,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和嘗試探索,在思想上與藝術上形成了鮮明的特點。
1
辛笛的詩歌作品,體現了詩人感覺的獨到與思想的深刻,如《航》、《嶗山歲月》。他的作品數量不是最多,然而質量很高、影響很大。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他對于詩的感覺很獨到,并且有理性和思想作為支撐。有沒有詩的感覺,決定了詩人是否可以寫詩,以及能否寫出真正的詩。詩人首先對于周圍的事物要有相當高度的敏感,要擁有強大的觀察力與感受力,凡是過眼之物都能產生熱度與亮度,只有這樣,才會有詩的發現與詩美的創造。辛笛以中國古典詩詞作為詩歌創作的起點,后來又自覺而集中地向西方現代派詩歌進行揣摩和學習,并且頗有心得,獲得真功。“從日到夜/從夜到日/我們航不出這圓圈/后一個圓/前一個圓/一個永恒/而無涯的圓圈/將生命的茫茫/脫卸與茫茫的煙水”(《航》)。此詩表現詩人在大海上航行的感覺,前不見海岸,后不見大陸,天地自然與人生世界,都只是處于一種茫茫之中,如此獨到的感覺也許只有詩人才有,并不是每一個坐船的人都可以產生。同時,這并不只是一種感覺,而是將眼前的所見與人生的際遇相聯系,與世界本真的狀態相聯系,一切出自于感覺,但表現的卻是哲學的境界。他能夠跳脫出一般乘船者從日到夜、再從夜到日的航行疲憊和思維麻木,對人生與世界的本質展開深入對話,從而發現人、船以及大海之間微弱而一體化的趨向。辛笛的許多作品所呈現出來的,基本上是詩人的感覺與印象,然而并不僅僅止于這樣的感覺與印象,而是有著詩人自己獨到的發現與思考,有著對于人生、自然、社會與戰爭的看法,體現了他獨立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太陽落山晚霞照海/人影漸長人聲漸歇/熱鬧過后寂寞漸漸深沉/還是不如不曾熱鬧也罷/住一天還可住一輩子可不成/這兒不是我的歲月/——呵,我是不屬于此地的人”(《嶗山歲月》)。從這首詩的形成過程與主要內容來看,作為一名游客的詩人自嶗山上下來,與照海的晚霞、漸歇的人影相伴,進而想到“在古榆樹下盤腿趺坐”的道士,發出了喃喃的心聲——“我是不屬于此地的人”;他從自我的感覺出發,把青島嶗山風景區里的人生與自我的人生方式和價值取向進行對比,發現自己并不屬于此地,表明了儒家向外進取與開拓的人生方式,與道士所代表的道家無為思想之間有很大的距離。在這首詩中,熱鬧與安靜、此岸與彼岸、人間與世界、一天與一生之間構成了一種哲學化的對照關系,這就是詩人在如此短的詩中所表現的深刻的思想,以及高遠的人生境界。辛笛善于通過外在的世界與內在的世界、自然世界與人類世界、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差別,一方面加以復合保存與展示,另一方面借此產生語言上的巨大張力,呈現出其感覺的獨到與思想的深刻之間巧妙的聯系與有機的統一。
2
辛笛的詩歌十分注重意象的呈現。他的詩歌作品,首先是以意象或形象來表達所有的內容,其次是讓詩中的意象與現實生活里實際存在的事物相比,并作出一些必要的變化,從而讓詩歌意象更加奇特和精致,如《手掌》、《水仙花之戀——有贈》。詩人在詩中不只是抒寫一點想法,或者只是對于一點自我小情緒進行抒發,而是把所要表達的東西轉換成意象(當然有的時候只是形象,即具體的物質化的存在,而沒有詩人的自我情感與思想),并且將意象打磨到一種特別新穎與精致的程度,從而引起讀者的特別注意。“形體豐厚如原野/紋路曲折如河流/風致如一方石膏模型的地圖/你就是第一個/告訴我什么是沉思的肉/富于情欲而蘊藏有智慧”(《手掌》)。這首詩里詩人通過一系列具體可感的形象對一個人的手掌進行排比化的展示,連續以“原野”、“河流”和“石膏模型的地圖”、“沉思的肉”四個意象來呈現手掌所具有的“豐厚”、“紋路曲折”、“風致”以及“富于情欲而蘊藏有智慧”四個側面的不同特征,以這些清晰的意象來構成一個大的手掌意象,這在當代中國詩歌作品里是少有而罕見的,就是放在整個世界最近一百年來的詩歌作品里,也是一種獨立而奇特的存在。不論寫的是誰的手掌(多半是詩人自己的),它的新穎與奇特、別致與精彩、美麗與精妙,都是遠超前人的,也足以讓后來的寫作者感到為難。像這樣具有表現力的意象,在其詩歌作品中是大量存在著的,這正是其詩之所以有別于其他詩人最主要的原因。當然,辛笛的詩中有些只是形象,還沒有達到意象的高度,而且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然而即使是形象,它們與古人或今人詩歌中的形象比較起來,也存在著相當大的區別。但是,辛笛絕大多數的作品里還是形象與意象的相雜。“從北國的天外飛回/捧來了帶著薄薄田泥移植的你/迎著新歲的暮暮朝朝供奉起你/你金黃的蕊、你白玉的瓣/恰像是縞袂黃冠/下面鱗莖襯托著幾葉青青”(《水仙花之戀——有贈》)。這里的水仙花多半是形象,是對水仙花這一水生植物的細致描寫,當然是以詩人和水仙花對話的方式得以呈現,其內涵自然也是深厚的,因為其中的信息量相當豐富而且富于變化,不過這里所說的不是心理與情感方面的信息量,而是詩歌形式上與結構上的信息量,所以說它不是意象而是形象。我們也不可否定形象的意義,它可以讓我們更加全面與感性地把握水仙花的形體,從而在此基礎上把握全詩的內質和情感。抒情主人公“我”從北國坐飛機,小心翼翼地帶回來一盆水仙花,在新年到來的歲月中將其供奉起來,在近距離的細致欣賞過程中,發現它原來是如此的美妙,“金黃的蕊”、“白玉的瓣”兩個比喻,則讓水仙花開始有了生命的呼吸而靈動起來,給自我的生活帶來從未有過的生機與活力,從中感受到“春天的信息”。辛笛的詩歌,無論是對形象的刻畫,還是對意象的呈現,都極具視覺的感染力,五彩繽紛,絢麗多姿,這自然離不開詩人敏銳細膩的觀察力和無限馳騁的想象力。
3
辛笛擅于把真摯的情感處理得溫潤流轉,情真意切娓娓道來,可以說含蓄委婉而飽滿深情是辛笛詩歌的另一大特色。詩人所屬的九葉詩派承接了中國新詩現代主義傳統,他們在詩歌創作中一并追求現實與藝術,企圖在感性和理性兩者之間求得適當的平衡,而詩中所蘊含的脈脈深情無疑是平衡之美的重要體現。因此,在直面現實的歷史感與時代感激發下,辛笛的詩雖然產生了強烈而深厚的情感,“由香港到倫敦/你一路就數數看有多少份《泰晤士報》;/可是時代到底不同/東方的人民由警覺中已經起來,/已經起來”(《贈別——一九四七年八月三日送李陵》),但面對理性制約的藝術訴求,詩人不允許自己的情感如火山般噴涌、如大海般澎湃,更不允許淪為個人感傷主義的頹廢;同時,詩人也反對情感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口號式吶喊,所以當“今天有人對你輕輕地說:/不離開生長的國土/不懂什么才是最難于割舍”時,主人公“我”既沒有悲觀絕望,也沒有奔走呼號,而是相信“一天待你回來時,也會如此說。/今天瘦長個子的你,孤獨的你,/沒奈何的你,/坐著這個稀奇古怪會劃水的東西走了/我從今再不想叫它是‘船’”(《贈別——一九四七年八月三日送李陵》)。可見,懂得克制的情感并不顯得壓抑、透不過氣,反而更能彰顯詩人的一往情深和平靜下的暗涌激流。在《巴黎旅意》、《月光》、《有客》等詩中都能明顯地感受到詩人對于祖國家鄉的深情款款,“花城好比作一株美麗耐看的樹/可是歐羅巴文明衰頹了”,“誰能昧心學鴕鳥/一頭埋進波斯舞里的蛇皮鼓/就此想瞞起這世界的動亂”(《巴黎旅意》),即使身處萬里之外、紙醉金迷的異國,心中卻時刻掛念著家國和世界。此外,詩人對于自然景物也充滿了蜜意柔情,面對“崇高純潔柔和”的月光,“一種清亮的情操一種渴想/芬芳熱烈地在我體內滋生”,“我如虔誠獻祭的貓弓下身/但不能如拾穗人拾起你來”(《月光》)。辛笛一方面綜合運用和借鑒西方現代主義手法,將觸景之深情化入繽紛的色調和各種意象共同構成的畫面之中,“古色斑斕的塞納河/初秋的空氣明透如水/緞子衣裳無心在輕盈中觸著了/涼意又何獨惜于遠來客”(《巴黎旅意》);另一方面,積極吸納中國古典詩詞的精華融入自己的新詩創作之中,尤其注重詩歌意境的建構以安置無限豐沛的情感,“緩而未停,仍是悠紆地,那驢項的鈴聲,/靴底踏著的沙石溢出輕微的唏噓,/客主握手了更互道個好,/閑適的羸驢隨意噓了一噓,/氤氳的雨氣跟著渾成了白的暈痕,/咦,多事的鈴兒有時響亮的一聲,兩聲——”(《有客》)。在這里僅出現一次的客與主只是握手寒暄,相比于反復描寫的驢鈴,似乎成了無關緊要的邊角余料,然而,主客之間依依不舍的深情厚意充滿于“多事的鈴兒”聲之中,在讀者耳旁綿綿不絕。到了后期,詩人的一些詩作如《人間的燈火》和《祖國,我是永遠屬于你的》,開始嘗試著以歡暢奔放的方式來表達情感,直抒胸臆,但相對于辛笛一生的創作,這次的轉變并不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同時,這也反映出不同的時代背景會促使詩人不自覺地采取相對應的情感表達方式,在政治開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美好時代真情呼之欲出,含蓄和遮掩則成了一種負累。
4
豐富而變化的詩體形式,讓辛笛的詩作愈加顯得闊大與高遠,不像有的詩人雖然有一些好詩,但格局過于狹小,風格呈現也較為單一。《印象》、《弦夢》、《月光》和《祖國,我是永遠屬于你的》等詩作,就代表辛笛詩歌所具有的多樣化的詩體形式,而且這些詩歌分屬于不同的創作時期。從總體上來說,對話體、小詩體、象征體、戲劇體、格律體、半格律體,各體皆有,并且也都發展到了一定高度。按照詩人不同的人生階段來劃分,在他早年和晚年創作了一些舊體詩,很有古意與韻味;在南開中學與清華大學期間所寫的詩,則多半具有現代風味,有的甚至比較晦暗而且不易讀懂;三四十年代所寫的一些詩,大半是自由體與半格律體,以對話為主要的方式;西行訪問時期所寫的,則以與自然山水相關的抒情詩為主;八十年代以后的詩,更多的是自由開闊且具有禪意哲思的抒情詩,這些詩與國家、民族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具有更為深遠的社會意義。“燈籠后的影子/隨著無盡的日月/也是那么/一晃一晃地/獨自成長了/成長了/又來聽流水的嗟嗟”(《印象》)。這是詩人早年寫作的一首詩,源自于他童年時代所生活的自然環境的一種回憶,以及對于“十五年”之后自我的一種期許,對于時間流逝的惆悵和對于空間變化的感慨,都被納入這樣一首小詩之中。雖然不似古代的絕句,卻具有特別的格局與特殊的意緒。“你不是宗教是大神的粹思/憑借貝多芬的手指和琴鍵/在樹葉上階前土地上獨自/我如虔誠獻祭的貓弓下身/但不能如拾穗人拾起你來”(《月光》)。每一行都是同樣的長短,五行為一節,一共三節,雖然不全押韻,但句式卻是一樣的整齊,顯然這是現代意義上的格律詩,在詩人的作品中雖然不多,卻也別具一格,表明他在詩體藝術上所做的努力。“我的脈管流著你熱呼呼的血液,/我的心胸燃燒著你長征的火炬,/我的每一粒細胞都沉浸著幸福,/我的每一根神經都彈奏著尊嚴,/我是個百分之百的中國人,/在金不換的愉快中,/我從來沒有想到什么叫作卑微!”(《祖國,我是永遠屬于你的》)這首詩里的句式與艾青后期的詩相比,幾乎沒有什么區別,都以排比的方式抒寫飽滿的詩情,全方位地表達對祖國的深情和愛戀,語言質樸而開闊,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與祖國進行對話,把自我的內心掏出來以展現真我和對祖國的忠誠,這樣的抒情方式在中國當代許多詩人的作品里都存在,然而辛笛的此類詩也有自我的獨立性。詩中的我是詩人的自我,不是一種所謂的大我,也不是空洞無物的虛化的我,這里的“我”就是飽經憂患、堅持奮斗的詩人自己。據說他在建國初曾經無私地捐獻出自己從抗戰時期收藏的一大箱國寶,改革開放以后又向國家捐獻了15萬美金,如果沒有如此高尚而純粹的愛國主義情懷,他也不可能寫出這樣的詩篇。當然,在他的詩中,更多的是與英美現代詩人相似的自由體的現代詩,有的類似早期象征派的作品,語言枯直簡要,意象晦暗不明,而在詩歌表現中卻是高度壓縮的,不如后期詩歌的自然開闊與語言明朗,風格也比較內在和陰晦。“濃蔭綻開著棋子的白花/靜的長街上/繁促的三弦響/一人踏著步來了/又竟自去了/而遺下一團綠的夢/悵惜的夢”(《弦夢》),以及“俯與仰一生世/石像之微笑與沉思/會讓你憶念起誰/秋天的落葉如在昨夜/黑的枝干有苔莓/告訴你林中路的南北”(《對照》)。這樣的詩作,與“五四”早期周作人與李金發等人的作品是相似的,在詩體上是來自于西方的象征主義詩派,而不是中國古典詩詞。以上都可以說明詩人對于詩歌體式有所探索,也達到了相當的程度。不過,由于其體式變化比較大,所以我們也很難在不署名的情況下,認出哪些詩是他的,哪些詩是別人的。
5
辛笛詩歌的語言是相當別致與醇厚的,從《姿》、《一個夏天的午后——有贈》、《印象》、《巴黎旅意》等詩中,可以得到切實的說明。不論是早期、中期還是后期的詩,其語言都是相當講究的,以自然清新、質樸簡潔為主導風格。不過,各個時期詩歌語言的風格也并不一樣。比如他早期的詩,語言就富有青春的朝氣,中期的詩比較簡約灰暗,后期的詩則更加澄明,不論哪個時期,總體來說其詩的語言是有味道的,只要你細細地品味就可以發現。“你嗎,年青的白花?/可是你是吹彈不起的/你會立時立地破了/就像一個水泡泡”(《姿》)。這首詩多半是寫詩人對一個女子的印象,她是那樣的青春朝氣,然而她卻不懂世事的艱難與生存的不易,詩人對于她的擔心與向往,從每一個句子中都委婉地表現出來。詩人在設想之中與她展開了對話,“說你是一幅畫里/不可少的顏色”,“饒他一個平常的過路人/能不投擲一瞥憐愛的眼/而為你圣潔的光輝所感動”,可以顯露出她的美麗形象與綽約風姿,“而有一點淡淡的馨涼/可是凝神的眼看了你/就嘗有一點野百合的苦味”,也可以從中見出詩人對這名女子的曲折心態與復雜情感,而這些全部是通過飽帶情感的語句抒寫出來的。“蘇州洞庭東山/這是我來過的第多少次呀!/難得的是人間的解脫/勇于探尋一顆熱誠的心。/指指點點道旁的果園樹/枇杷和楊梅早已退出季節的舞臺了/眼看深色的是小小的綠橘/淺色的是歸客稀見的棗子和銀杏/在火熱的太陽下遐想/花果山的秋天還會遠嗎?”(《一個夏天的午后——有贈》)在夏天,一切都是充滿綠色的生機,春天之后的另一番景象,這就是春末夏初的江南風情,詩人通過自我的眼睛,把這里的一切植物以及它們各自不同的生命景象,一一呈現出來,讓我們能夠真實地感覺到詩人內心世界的豐富與變化,以及江南自然風物的美麗與演變。最后一句“在火熱的太陽下遐想/花果山的秋天還會遠嗎?”把詩人此時此地一切的思想情感,特別是對于生命的贊賞和對于秋天的向往,表達得十分到位與精彩。從語言風格來說,辛笛的詩歌語言就像一個夏天的午后,“冰冰涼的井水/好意地從另一個世界/喚住了我們”,“多高興呵/紅的沙瓤黃的沙瓤”,詩人“為我們切上了/一桌剛從市集上買來的西瓜”(《一個夏天的午后——有贈》)。此外,他的語言還像那株無限盎然的水仙花,在經過詩人藝術之手一番細刻精雕之后,“綽約的風姿凌波來去/依舊似醉如癡”,“林間的鳴鹿走來/為它平添一點顏色”,“一室就有你的清香/一窗就有你的麗影”(《水仙花之戀——有贈》)。由此可見,詩人在不同時期的創作變化是確實存在的,但也有一以貫之的東西,那就是語言的委婉與精致。
總體而言,辛笛以自己的優勢成為了九葉詩人群中重要的一員,就是在今天來看,他本人的諸多藝術追求和其詩歌自身的審美價值也能給予我們重要的啟示。首先,他的詩是高度自我的,特別是早期與中期的詩作,沒有特殊的生活與情感經歷是寫不出來的。就是到了后期,當他的詩思漸次明朗的時候,也是以自我的方式進行歌唱,如《嶗山歲月》和《祖國,我是永遠屬于你的》這樣的作品。詩人的自我在當今時代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完全不存在任何問題,可是在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卻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許多詩人都失去了自我,不敢發出獨立的聲音,或者以所謂的“大我”來遮蔽自我,從而導致近半個世紀里許多詩歌變成了假大空的東西。其次,他的詩是具有詩情畫意的,并且是高度自我的詩情畫意。“游女坐在咖啡座/星街是她日常的家/天空的云沉入那一杯黑色咖啡/閃爍在她靈魂的泥淖深處/大開的窗子/正靜靜地對著/古色斑斕的塞納河/初秋的空氣明透如水”(《巴黎旅意》)。這首詩寫于詩人留學英國時期,詩中對于西方大都市的印象就像是一幅象征主義的油畫,層次分明、色彩濃麗、結構合理,如果詩人沒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就不可能有這樣的藝術作品產生。辛笛之所以在每一個時期都有優秀作品出現,與他本人對于詩的理解相關,更與他長期處于一種自由狀態有著相當大的關系。新中國成立以前,他曾經在光華大學、暨南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以后卻長期從事食品與煙草銷售的領導工作,所以他對于詩歌和文學的愛好與創作是完全業余的。然而,他早年對于文學的接觸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學之夢,特別是在南開中學與清華大學讀書期間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習和浸淫,后來又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對于英國文學有著深入研究,這些都奠定了他那深厚的文學基礎與文化素養,所以他一生都沒有能夠離開文學、離開詩歌。正是在這樣的自由與自然之中,他才取得了優秀的詩歌成就,并對后世詩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