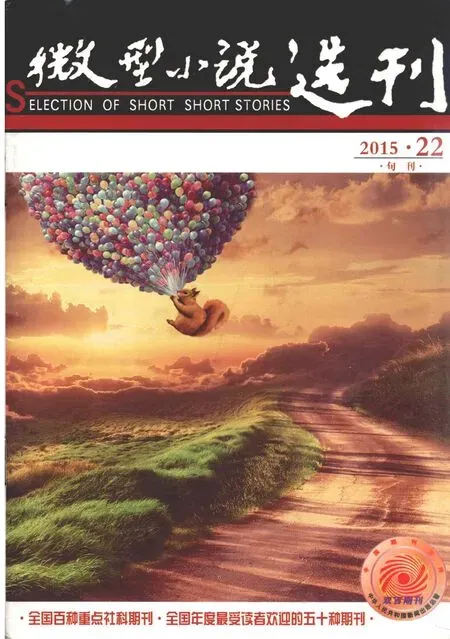宰殺兔子
□陳榮生 譯
宰殺兔子
□陳榮生 譯
我沒想到要去宰殺兔子。
這只兔子的名字叫塔戈,她是我們養(yǎng)的3只新西蘭白兔中的一只。那只大公兔我們起名為波波苔爾,另外一只雌兔叫作拉戈。拉戈已經(jīng)懷孕快要生了,如果塔戈也跟著懷了孕,那么我們這個(gè)小小的三角戀家庭(譯注:指這三只兔子)很快就會(huì)走上正確的軌道,按我們的目標(biāo)每年給我們提供200磅兔肉。
但是,問(wèn)題出現(xiàn)了。不管波波苔爾怎樣努力,塔戈總是拒絕接受他。一個(gè)星期接一個(gè)星期再接一個(gè)星期,波波苔爾一直以高昂的熱情履行著男性職責(zé),但是塔戈卻一直是頑固地沒有受孕。
如果一只雌兔不會(huì)生產(chǎn),她唯一的去處就是湯鍋!
“如果到這個(gè)周末她還未懷孕,”我對(duì)瑪麗說(shuō),“那么就只好如此了。我們得要另外一只雌兔,而我就不得不……這你是知道的。”
周末終于到了,正如我估計(jì)的,塔戈還是沒有懷孕。
“明天,”我伸手去摸開關(guān),把床頭燈關(guān)了,“我明天就去做。”
黑暗中,我聽到瑪麗在重重地呼吸。
“你肯定嗎?”
“是的,”我說(shuō),“是時(shí)候了。”
我那天晚上無(wú)法入睡。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會(huì)兒,我在夢(mèng)中想到了第二天一早要做的事,它們就像某個(gè)15英尺高的被打碎和扭曲了的巴格斯邦尼,在哈默恐怖電影中跌跌撞撞尋找出路。
我躺在床上,眼睛睜得大大的,凝視著黑暗,在思考,在回憶。
早上大約5點(diǎn)鐘,我溜下床,穿好衣服,躡手躡腳地走到樓下,我想盡快把這件事做完,最好是在瑪麗還在睡覺的時(shí)候就把它做完。我們的房子后面有一處小小的牲口棚,拉戈、塔戈和波波苔爾分別在他們各自的籠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