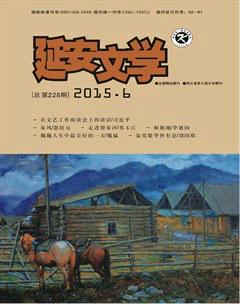“靈暈”消逝后大眾文化時代的藝術
康天琦

當資本主義發展到19世紀末時,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已經達到了之前所有社會階段生產力發展無法比擬的水平。這種高水平生產力對文化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同樣也是之前所有社會階段無法比擬的,藝術品被大規模的復制;大眾第一次與所謂的上層階級站在同一水平線上看待藝術品;藝術失去了古典時期作為其生長土壤的經驗,失去了藝術“本真”的諸多特征。藝術發展第一次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呈現出危機,本雅明把這叫做“緊急狀態”。
一、關于“靈暈”
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第一次談到“靈暈”,他指出“我們把靈暈定義為一種距離的獨特現象,不管這距離是多么近”,對這個描述,他緊接著補充道“當一個夏日的午后,你歇息時眺望地平線上的山脈或注視那在你身上投下陰影的樹枝,你便能體會到那山脈或樹枝的靈暈。”這便是本雅明對于“靈暈”的解釋,事實上,本雅明更是廣義地詮釋了“靈暈”。“靈暈”即代表著本真性,更與時空空間有關,“靈暈”的消失就意味著本真和距離的消失。“靈暈”的消褪就代表了大眾影響的日益增長,它的消褪同時加強了藝術品的展覽價值,削弱了人們對藝術品的崇拜價值。“靈暈”同時與戲劇舞臺有前,它的消褪即證明了攝影技術取代了觀眾。
在20世紀30年代歐洲處于巴黎和會后短暫的虛假和平之中,納粹主義在德國的影響日漸深遠,納粹一方面積極為戰爭做準備,另一方面通過公眾傳媒和獨特的藝術理論向整個世界宣揚納粹主義、美化戰爭。這一切的原因在于當時的藝術發展已經是一種大眾文化的發展方式,將藝術品作為商品、用一切技術手段對這種藝術品商品進行包裝、復制,這不僅使藝術品喪失了本真性的自由和超越,同時也將藝術發展的古典時期經驗的土壤摧毀,本真藝術在藝術品市場化的大流中失去了以往藝術品發展的地位,這使得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藝術發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不僅僅機械復制帶來藝術品數量上對本真藝術的壓力,同時也由于機械復制所造成的個性的消失,更為重要的是古典藝術以時間和歷史的經驗為土壤的藝術品已經被機械復制所倡導的市場導向所擊敗,藝術品在意義上呈現出一種空洞和虛無,它不再體現藝術品所創作的時代特征和歷史積淀。而面對失去意義或者說失去作為存在土壤的經驗后,藝術立即取得了具有敏銳嗅覺的政治的注意,它將藝術作為宣傳自身理論、對公眾進行思想抑制的一種積極手段,而納粹在那一時期所宣揚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試圖說明藝術來源于戰爭,為了藝術而進行的戰爭就是一種藝術行為。這一口號說明了藝術存在被政治取代的最極端、最嚴肅的應用,將藝術品作為反對猶太人、宣傳民族仇恨的積極手段。
在這一大的背景下,我們再回頭看看“靈暈”。本雅明將靈暈看作是一種遙不可及的距離,這種距離是無形的但無時不刻的存在著;這種距離就像欣賞一幅大師的畫作,你會和它產生共鳴,但你永遠無法了解作者想要表現什么。從人類感知方式而言,人類感知的組織形態,它賴以完成的手段不僅由自然決定,而且也由歷史環境來決定。在我們看待藝術品時,我們感知它的手段和方式同樣受到歷史條件所制約。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靈暈”——將其視為藝術品創作時存在于藝術品內部的歷史的、現實的條件,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獨一無二性就越發明顯越發無可復制。所以說“靈暈”與本真性有直接的有關,“靈暈”的消失即本真的消失。
而在本雅明寫作《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這一著作時,這種“靈暈”卻處于一種消逝殆盡的狀態。
二、“靈暈”消逝的原因
與大眾文化產生的原因相同,“靈暈”消逝的原因同樣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大規模發展,資本主義進入到了發達資本主義階段,技術手段以驚人的數量復制藝術品,使藝術的發展陷入危機。這一危機首先體現在繪畫領域。由于照相術的產生和發展,用照相的復制能夠展現出那些肉眼無法捕獲、卻能由鏡頭一覽無余的方面,相比繪畫,照相術所捕捉的范圍更廣、更加具體;同時,由一張底片可以沖洗出無限張相同的照片,這種數量優勢是繪畫無法比擬也所不能及的;這些照片由于復制的關系無法辨別真偽,所以在這里強調真偽就變得毫無意義。技術手段的復制不僅僅使被復制的藝術品與傳統的藝術作品相區分,并且與復制品相比更加獨立,能達到傳統藝術品無法達到的環境、領域中進行傳播,例如教堂唱詩班的贊歌可以成為一張唱片在個人的客廳播放。
雖然復制品所進入的環境一開始并沒有觸及藝術品存在的土壤——歷史的、環境的經驗,但傳統藝術品在與復制品的比較中,越來越不占有任何優勢,最終竟然放棄藝術的本真性,放棄了“它實實在在的綿延到對它所經歷的歷史的證明”。由于復制技術通過制造出許許多多的復制品以一種摹本的眾多性取代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復制品能夠在持有者或者觀眾的特殊環境中供人欣賞,傳統藝術作品所代表的歷史實在性的體現變為虛無,藝術存在的意義第一次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在這一過程中,大眾的影響超過以往任何時代。從中世紀神學解放出來的經過文藝復興、啟蒙主義的熏陶,注重自由的大眾在20世紀初形成一種欲望,一種“想使事物在空間和人情味兒上同自己更‘近”,這種欲望促使大眾利用復制品來克服任何真實的獨一無二性,這就促使了復制品大量的存在和更大規模的復制。也就是說機械代替了人類。
三、“靈暈”消逝的后果
當藝術的本真性從藝術品中消逝后,藝術發展陷入了一個巨大的危機之中。
傳統藝術起源于儀式服務和表達崇拜,從原始時期洞窟的巖壁上所畫的對火的崇拜到中世紀教堂中有關基督的壁畫,或是從巫毒教對圖騰崇拜到佛教對手珠的推崇,這一切都表明傳統藝術作為儀式服務和表達崇拜的使用價值,“這個儀式性基礎無論多么遙遠,仍可以在世俗化的儀式甚至在對美的崇拜的最褻瀆的形式中辨認出來”。技術手段的復制方式將藝術從對儀式服務和表達崇拜的存在基礎中完完全全地解放出來,藝術存在的土壤不再是由歷史經驗的繼承和發展,因此藝術的本真性及藝術的自由性和超越性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古典藝術的形式由于使用其價值的衰落,古典藝術形式逐漸沒落。
而作為失去使用價值和存在土壤的藝術品,作為崇拜慶典之物的作用越來越少,相應的,作為藝術品另一種價值的展示展覽作用就在不斷加強,藝術作品的五花八門的藝術復制手段使它越來越適于展覽,直到它的兩級之間的量的轉移成為它本性的質的變化。對藝術品展覽價值的強調是在發達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階段不可避免的事實和必要的手段,一方面它通過這種展覽肯定了藝術品作為商品在市場生活中對生產力的肯定;另一方面,這種展覽價值的背后代表著組織和控制生產力的階級對整個社會的控制力,這種控制力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結成一張獨特的大網,作為一種新的異化力量而存在。
技術復制手段給整個社會的藝術發展制造的危機是空前的,失去本真性的藝術品相繼失去了它存在和發展的土壤、實際的使用價值、甚至在精神層面的存在的意義,不能表現任何對現實超越的藝術作品顯得空洞和乏味,文化工業的發達使這種現象愈發深刻。而這種失去儀式存在基礎的藝術品由于功能喪失,其整個功能就被徹底翻過來,在展覽成為了藝術的主要功能,而這種功能存在的社會實踐就是政治。
四、“靈暈”消逝時代的
藝術表現形式
由于“靈暈”的喪失,藝術的展覽價值就成為藝術存在的唯一功能,而這種展覽功能的直接產物就是照相術和電影。
關于照相術和繪畫之間的討論早在19世紀就已經開始,這場討論最先開始的是技術復制手段和傳統藝術之間的對話。由于技術手段的產生,藝術存在的崇拜根基開始動搖,傳統藝術的自律性不復存在,而在這時,繪畫還是主要的藝術生產手段,復制技術僅僅為它服務,所以,當時人們討論的重點是照相術是不是一門藝術。
而到19世紀末期,照相術的展覽價值完全取代了崇拜價值,并且隨著技術手段的發展,一種全新的展覽價值手段——電影開始得到發展和壯大。有關電影的展覽價值,本雅明通過電影與舞臺劇的比較做出陳述,“舞臺演員的藝術表演無疑是由演員親身向公眾呈現的;然而一個銀幕演員的藝術表演卻是由攝影機提供給觀眾的,這帶來了雙重的后果,把電影演員的表演提供給公眾的攝影機無需把表演奉為一個內在整體。”舞臺劇所經歷的歷史發展路程除了舞臺的位置、場景的布置、表演的目的和用途的變化之外有一點似乎永遠不會發生變化即舞臺劇與觀眾的直接接觸。在觀眾欣賞一出舞臺劇時,這一表演過程是不能被中斷的、是與觀眾直接互動的過程,演員在舞臺上為觀眾表演,演員從舞臺上可以看到觀眾對自己表演是否滿意;同樣,在舞臺下,觀眾可以感受到來自舞臺的各種情感,就像人與人之間當面交談的情感傾訴一樣。而在電影里,銀幕所呈現給觀眾的是經過剪輯、拼接、后期制作而成的作品,這一作品包含著更多的技術優勢和精巧的結構、節奏的安排,但卻缺失與觀眾的直接交流。在任何一部電影的制作過程中,制作組不會向觀眾開放影棚,制作的過程不會完全像電影中的流程一致,也許會由于資金、場景等等因素先制作結尾然后制作開頭等等。這一過程的不連貫和演員與觀眾的不直接的交流割裂了舞臺劇天生的與觀眾的直接聯系,使觀眾從演出的觀摩者變成了批評家。
電影工業的另一產物就是“明星”,它是最具代表的“靈暈”喪失時代藝術表現形式的具體化表現。對于電影來說,攝像機所記錄的影像就是演員的全部,演員在攝像機前的表演是服從于攝像機的所指引的視覺實驗;電影演員不再根據觀眾的反應來調整自己的表演,他并不是親身向觀眾進行表演。因此,電影演員在攝影機面前的表演要調動“整個活生生的身體,卻不得不放棄靈暈”,他不具有與他所表演角色的認同。所以說“靈暈”的消失即創造性的消失。
五、“靈暈”消逝時代
大眾所起的作用
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品》中這樣描述大眾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大眾是一個發源地,所有當今以新形式出現的藝術作品的傳統行為莫不由此孕育出來。量變成了質。大眾參與的巨大增長導致了新的參與方式的變化。新的參與方式首先以一種聲名狼藉的方式出現。”我們可以看出,本雅明對大眾的評價一直處于對大眾的肯定階段,將大眾的需求看做是機械復制時代藝術品發展的重要原因,這種需要就是消遣。與傳統藝術不同,大眾對藝術的要求不是對傳統藝術的專心致志的欣賞,而是娛樂性的消遣,并且這種消遣要求把藝術吸收過來。“消遣娛樂的人同樣可以形成習慣。不僅如此,在消遣狀態中把握某項任務的能力還證明他們解決的是一種習慣的東西。藝術提供的消遣表明一種暗地里的控制,即對新任務在多大程度上能由統覺解決的程度的控制,更進一步說,鑒于個人總是企圖回避這些任務,藝術就要對付這些最困難而又最重要的任務,在此它能夠把大眾動員起來。”
責任編輯:侯波 ?薛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