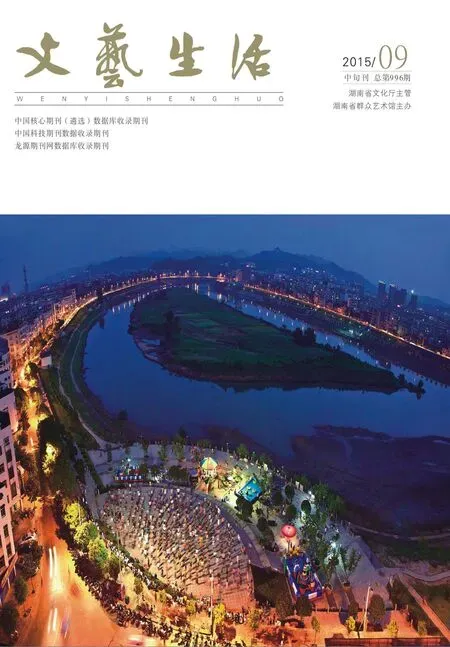淺析沈從文湘西世界作品中的愛情書寫
李旭星
(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北京100024)
淺析沈從文湘西世界作品中的愛情書寫
李旭星
(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北京100024)
文學中不可缺乏對于情感的書寫,而愛情書寫更是體現兩性之間微妙關系的極為特別的描繪方式,同時也是透過這種生命存在狀態探尋人的存在與人性終極的方式。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的愛情書寫獨樹一幟,本文結合沈從文的具體作品,分析沈從文對于湘西世界愛情描寫的“原生態”角度以及其透過愛情之窗對生命之美與生命之力的極致書寫。
湘西世界愛情書寫原生態神性生命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幅奇景,沈從文的作品經歷了近九十年的文藝風雨洗禮仍閃耀著其獨特的光芒。不同于依附于宏大歷史敘述之上的左翼文學,不與燈紅酒綠的海派文學相謀,沈從文始終簡直從自己的“希臘小廟”中眺望至美至善的純凈景色。文學評論界中向來復雜的愛情書寫,也在沈從文的筆下有了特殊的沈氏風格。
一、以愛情為本體的“原生態”角度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后,周作人從西方思想家靄理斯的性學思想處向中國知識分子引述了性心理學的部分觀點,同時,周作人自己也提出“獸性與神性,合起來便是人性”,“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應得到完全滿足”,應在理性對人類本能的適當抑制與調節下達到“靈肉一致”①。周作人對于自然人性尤其是性心理的自由觀念,影響了沈從文對于人性的進一步認識——人在物質生活的基礎上,更有著對于感性與理性、人性與神性、本能與道德相互統一和諧的不懈追求。在沈從文筆下,愛情也是人性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無需刻意的壓抑克制,是一種美的表現形式。愛情主題或者與愛情相關的描寫在文學創作和評論中常被賦予著復雜的目的性和功用化的理解,相較之下,沈從文從一個嶄新的,或者說,從一個五四啟蒙后早就應該出現的本體角度出發去看待愛情以及這一人類日常行為的表達。
首先,沈從文將愛情書寫從社會歷史的大角度中萃取出來,使之成為真正的關注對象。中國現代文學中對于愛情的描寫并非乏善可陳,但以主流宏大敘事為代表的許多文學創作中,愛情書寫被蒙上了一層羞于言說的意味,正如吳蓀甫之于王媽、林道靜之于她的三個戀人——一方面,愛情描寫被視為略顯負性的因素而隱去;另一方面,性別甚至愛情成為每每涉及到社會階級、政治話語時的附庸成分——戀愛與愛情是關乎階級或政治話語的暗示與演繹,而社會階層與政治取向又反過來影響和干預兩性之間的情感關系。這種在歷史洪流中沉浮的兩性關系正與沈從文所提倡的自然人性所違背。因此,沈從文在以表現湘西生命為主的作品中,刻意將社會歷史的背景淡化甚至略去,只保留湘西本地最為淳樸的風俗習慣,驅動男男女女之間相互吸引、相互深愛的是單純的個體情感的悸動。如《神巫之愛》中的神巫與啞女,《媚金·豹子·與那羊》中的媚金同豹子。作為背景陪伴著故事中一對對戀人的,只有同樣純凈的湘西的水與月。
相應的,偏離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敘述的同時,沈從文也將自己的湘西夢帶離了現代文明——現代化的都市邏輯、戀愛與婚姻、道德倫理等等過度規束都為健康奔放的自然愛情做了讓步。在難以為現代文明觸角所顧及的物質貧瘠的湘西社會,現代都市的燈紅酒綠和消費邏輯全不適用。沒有應酬自如、甘愿沉淪的交際花,有的只是《丈夫》中迫于生計賣身養家的船中妓女;沒有欲壑難填、空虛無聊的行尸走肉,有的只是如花狗般淳樸健美的湘西的靈與肉;沒有離婚、出軌等繁雜的情感和倫理糾紛,有的只是諸如《蕭蕭》中蕭蕭與花狗、媚金與豹子間極度的熱愛所產生的迷戀與結合。沈從文的湘西世界是純粹的,其對于自然人性與“神性”相和諧統一的追求亦表現在擺脫現代文明對于人性的過度壓抑和約束。沈從文淡化社會組織、有意的忽視體制帶來的所謂的社會“進步”,將男男女女們重新歸入理想中的伊甸園,發乎情,不止于禮。
二、關乎生命的極致表達
沈從文將個體存在分為“生活”與“生命”兩個層次,“生活”代表著人生存下去所必須達到的物質層次,而“生命”則“惟對現世光影瘋狂而已”,其自身就“有光熱”②。愛情作為一種自然人性的表達與追求,必然成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沈從文對于愛情的書寫,也表現了他內心對于供奉在“希臘小廟”中的生命之火所體現的美與力的追求。
愛情關乎生命之美。沈從文向來不吝嗇對于筆下人物之美的塑造,他只愿將愛情贈與那些“相貌極美又頂有一切美德”③的湘西生靈。生命之美意味著兩性之間關系的平等與和諧,也即以相互愛戀為前提,莊重而專情,愛情本身可以肆意奔放,然而愛情本身是嚴肅且圣潔的道德律。如《蕭蕭》中,蕭蕭作為童養媳接受了無愛的婚姻,性意識覺醒的她并未因童養媳的封建身份束縛自己的情欲,而是和健康強壯的湘西漢子花狗體驗了愛情的美好。甚至是湘西水域船屋中的妓女,“也永遠那么渾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時得先交錢,再關門撒野,人既相熟后,錢便在可有可無之間了。”同時,產生愛情的誘因也是“頂美”的,神巫愛上花帕族啞女是因為女子秀媚通靈的眼睛;媚金與豹子因歌結緣便私定終身……不為金錢,無關權勢,當愛情退去傳統道德審視下的丑陋外衣時,沈從文賦予了它極度的自然氣質和神圣的純潔性。在《阿黑小史》、《夫婦》、《雨后》等作品中,愛情還與自然合為一體,兩性的結合與自然萬物相互順應、交融,如《月下小景》中的一段描寫:“懸在樹上的果子落了地,谷米上了倉,秋雞伏了卵,大自然為點綴了這大地一年來的忙碌,還在天空中涂抹華麗的色澤,使溪澗澄清,空氣溫暖而香甜,且裝飾了遍地的黃花,以及在草木枝葉間傅上與云霞同樣眩目顏色。一切皆布置妥當以后,便應輪到人的事情了。”自然仿佛在啟迪凡人的“神性”,為同樣具有生命力的可愛男女準備著新房和婚床,自然果實與愛情同時成熟、收獲,戀人們在自然中得到關于“神性”的最高體悟。諸如此類關乎自然及生命的原始之美、道德淳樸之美的意象群也使得其區別于其他商業化的情色描寫,成為表現沈從文理想之光的一顆星火。
愛情體現生命之力。沈從文曾表示,愛情是“身心健全的年輕人”“盡種族義務”、“生理上求發展”④的生命之源。沈從文的筆下,湘西的男子強壯有力,血性耿直;湘西的女子柔情似河水,熱情似篝火。湘西男女的愛情隨性、灑脫,只隨原始的生命沖動而生,不可抑制,不可拖延,同時也成為湘西男女互訴衷腸,溝通生命靈性的方式,是代表健康生命、響應自然及神性召喚的行動。與表現湘西世界奔放情欲相對的,是沈從文對于城市人的愛情書寫。《八駿圖》中衣冠楚楚的教授們因為違背自然本性的禁欲紛紛“害了點小病”,甚至病態的“想從那大理石胴體上凹下處凸出處尋覓些什么,發現些什么”⑤。愛情的缺失和對于本性的畸形壓抑使得人的生命之力萎縮,變得萎縮、怯懦,甚至失去了真誠、質樸的品質,變得謊言連篇,虛偽不已。而真正體現沈從文對于愛情崇高感的理解,在于沈從文對于愛情與死亡之間的聯系。“一個人生命之火雖有時必熄滅,然而情感所注,在有生命處卻可以永不熄滅。”⑥整日將性命交予河流山川的水手和從事著并不安定工作的妓女相戀,將愛情的野蠻與隨性發揚到了極致。翠翠的父母也選擇以先后殉情來求得愛情的專注。《巧秀與冬生》中巧秀母親與打鐵匠相愛,最終面臨族人非難時并未茍且偷生,選擇以“沉潭”表達對自由追逐愛情的忠貞信仰。《月下小景》中的女孩情愿與儺佑在歌聲中雙雙死去,也不愿忍受土司王的野蠻茍活。為愛抗爭、為愛殉情,沈從文常以最為壯烈的求愛來表現人追求自然發展的本能——“愛能使人暗啞——一種語言歌呼之死亡”⑦。
三、結語
總而言之,沈從文向來不吝嗇于展示湘西世界的原生之美和生命的魔力,愛情書寫在沈從文的筆下成為一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史無前例的圣潔果實——作為一名現代文學史上的巨匠,他能夠巧妙的掌握愛情書寫的尺度和價值,力求寫盡愛情的美好與偉大而并非其猥瑣與色情。囿于中國現代歷史的諸多原因,文學界魚龍混雜的愛情書寫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難以為主流敘述做更為細致和理性的區分,然而沈從文的真摯和自始至終對于神性的追求賦予了這類書寫超脫世俗的審美體驗,成為經典。
注釋:
①周作人.人的文學[J].新青年,1918(05).
②③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1卷)[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295,209.
④沈從文.給一個中學教員.沈從文全集(17)[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 2002:325
⑤沈從文.八駿圖.沈從文作品新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3-116
⑥沈從文.看虹摘星錄后記.沈從文作品新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326.
⑦沈從文.生命.沈從文文集第七卷[M].廣州:花城出版社,香港:香港三聯書店聯合出版.1982-1984:295.
I207.42
A
1005-5312(2015)26-0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