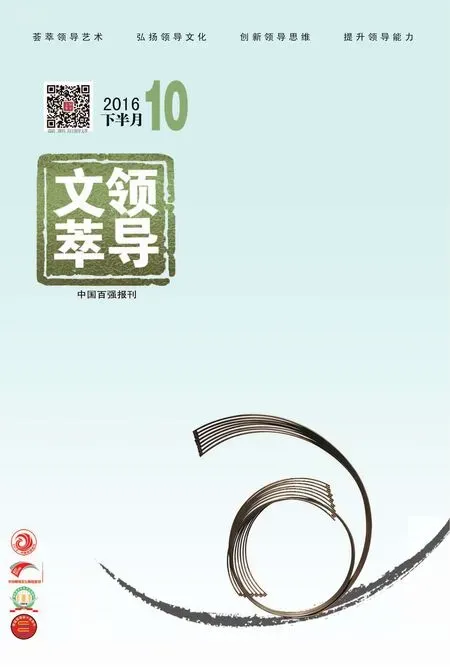我的大哥饒漱石
饒玉蓮+++景玉川
饒漱石是我同父異母的兄長,比我年長28歲,他參加革命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因為大哥1928年離家后,一直沒有音信,所以小時候父親也沒有跟我談起過他。1946年國共和談期間,在南昌一中教書的父親偶然在校圖書室一份畫報上看到北平軍調(diào)部國、共、美三方代表會談的報導,畫報上刊登了共方顧問饒漱石的照片。這位顧問名字與我大哥相同,相貌也有點像,但大哥離家時沒有小胡子,照片上的饒漱石卻留有小胡子。因世上多同名同姓的人,所以父親一時不敢認定這位中共代表團顧問饒漱石就是他的兒子、我的大哥。雖說如此,父親還是悄悄帶著那份畫報來到臨川老家,拿出畫報與幾位堂兄弟共同辨認。大家仔細看了照片,也不敢肯定,都覺得照片中的人既像又不像。經(jīng)過商量,他們決定找一位信得過的鄉(xiāng)間教書先生,請他幫助代筆給北平軍調(diào)部寫封信(避免我父親的筆跡被國民黨當局認出來)。信是試探性的,大意說:我們家有個兒子外出多年沒有消息,名字也叫饒漱石,不知是否同名同姓?如果不是就請原諒;如果是,就請按信上地址回一封信,免得家里人牽掛。過了不久,果然北平來信了,信寄到了臨川老家,寫信的真的是我外出多年的大哥。信中說他外出多年,也惦念家里的親人,曾請人探聽過家里的情況,但都說找不到這個村莊。父親和他的堂兄弟接信后非常高興,又請那位鄉(xiāng)間教書先生接著去了一封信,訴說家鄉(xiāng)的苦難。不久,北平又回了一封信,安慰說他知道家鄉(xiāng)的貧困,但相信今后一定會改變,希望我們耐心等待。并告訴說他的地址不定,今后不要再來信了,怕收不到……這件事,當時我和姐姐并不知道,只覺察那幾年父親有一卷東西總是藏來藏去,很神秘的樣子,我猜測,那可能就是我大哥給家里的回信。
1949年5月南昌解放,我們這才知道大哥當了大官,已到了上海,是第三野戰(zhàn)軍的政委,上海市委書記。率部解放南昌的陳賡將軍曾來中學看望我父親,說:感謝您培養(yǎng)了饒政委這樣一個好兒子。此后,父親才較多地跟我們談起大哥,說大哥有理想,有抱負,成績好,尤其語文、英語出眾,遇事冷靜,講話邏輯性很強……
南昌解放時,姐姐饒石蓮正在大學英語系讀三年級,由于敬佩大哥,她將自己名字改為饒漱芬。陳賡將軍回上海時,將她帶到上海。姐姐原本以為大哥會給她安排一個理想的工作,但大哥卻要她去“革大”學習。結業(yè)后本來組織部門準備將她留下,由于大哥不同意,她和她的男友便被安排一同去松江參加土改。土改結束后,他們雙雙被分配到無錫紡織學校教書,沒有給一官半職。我的二哥饒章泉1949年大學畢業(yè)后也想留在上海,但大哥要他回江西。當時江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正人同志對我父親說想把我二哥安排在中南局(當時江西屬中南局管轄),父親說他哥哥不同意。二哥只好先進“八一革大”學習,結業(yè)后分配到中學教書,直到后來他報名參加志愿軍。
1950年抗美援朝期間,我和二哥在父親鼓勵下報名參軍。經(jīng)過幾個月的集訓,1951年我被分配到北京裝甲兵司令部搞機要工作。1952年大哥調(diào)中組部工作,他到北京不久,就到裝甲兵司令部來看我。這是我們兄妹倆第一次見面,但我一點也不感到陌生,一見面就覺得非常親切。這以后遇到節(jié)假日,我便會上大哥家,與他共同進餐,或陪他散步,看電影。那時我已有了男朋友,但我沒敢?guī)洗蟾缂遥驗榻憬阍鴰杏焉纤沂潞笫艿剿呐u。我的男友自尊心很強,大哥沒邀請,他絕不會主動提出登門(他沒有見過饒漱石,后來卻受到大哥一事的牽連)。1953年我從部隊轉業(yè),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yè)經(jīng)濟系石油專業(yè)。讀書期間,到了周末,我經(jīng)常去大哥家,與他有過一段不長,但非常愉快的接觸。只是我發(fā)現(xiàn)他這時身體似乎不大好,精神比較差,經(jīng)常處于疲憊狀態(tài),寡言少語。但他生活仍然有規(guī)律,衣著飲食簡樸清淡,他不抽煙,不喝酒,沒有高檔衣服,汗衫都是補了又補。有一次,我對他說:現(xiàn)在上課要做很多筆記,用蘸水筆很不方便,能不能給我買一支自來水筆?大哥說:現(xiàn)在大家都很艱苦,有條件用自來水筆的人恐怕不多,你還是與同學們保持一致,不要顯得特殊。我訪蘇時,帶回一支鋼筆一樣的圓珠筆,給你做個紀念。說實話,這支筆沒有什么使用價值,只是一件小禮物而已。在北京同大哥接觸近兩年,這是他送給我的唯一一件紀念品。
1954年初寒假,我回到南昌。有一天,父親像是問我又像是自言自語:這一段時間報上怎么不見你大哥的名字,怕是有什么事吧……對政治我不大懂,所以也無法回答父親。寒假結束后我回到學校,不久,學校給我一項任務,要我每周周末去大哥家陪伴大哥。(當時不知原因,多年以后才猜測是當年2月高崗自殺未遂,可能有關部門擔心饒漱石自殺才派我去陪伴他)這一段時間,我與大哥接觸時光最多,他好像也沒有以前那么忙,我陪他聊天,還陪他去看過演出。我們談話時內(nèi)容比較廣泛,我們談家鄉(xiāng)的舊事,談父親在治學上的優(yōu)缺點,說到高興時,他會雙手有節(jié)奏地拍打沙發(fā)的扶手。他說父親雖說愛接受新的知識,做了很多讀書筆記,但由于探索面太廣,所以每一方面都難精……其實這一段時光是大哥最痛苦的日子,可當時我卻懵懵懂懂,一點也不知道,他也不會告訴我。
這學期結束,我告別大哥回南昌度暑假。快開學時,政治氣氛突然緊張起來,全省傳達了8月17日中共中央發(fā)出的《關于向全體黨員和青年團員傳達高饒問題的指示》,父親雖是民主黨派,但作為副省長,也聽了傳達。這消息如晴天霹靂在我們家震響,一連幾天,愁云慘霧籠罩著我們家。大哥的出事對父親的打擊不言而喻,因為大哥是父親最喜歡的兒子,是他的精神支柱。1954年饒漱石出事,谷思義也開始受到冷落與不公。從1955年起,單位經(jīng)過一年多的審查,沒有發(fā)現(xiàn)谷思義任何問題,但仍遲遲不給他授軍銜。文革中我隨同丈夫一同被下放到江西邊遠山村,1973年才回廠,在食堂做會計,直到退休。我的二哥饒章泉,1958年從志愿軍轉業(yè)回江西中學教書,文革中因大哥的關系曾被隔離審查一個多月。我的姐姐饒漱芬從中專教職考上了浙江大學電機系,畢業(yè)后在上海楊樹浦發(fā)電廠任技術員,文革中因與大哥的關系她不斷受到批斗、毆打,最后被逼自殺,死后連骨灰也不知何處。
(摘自《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