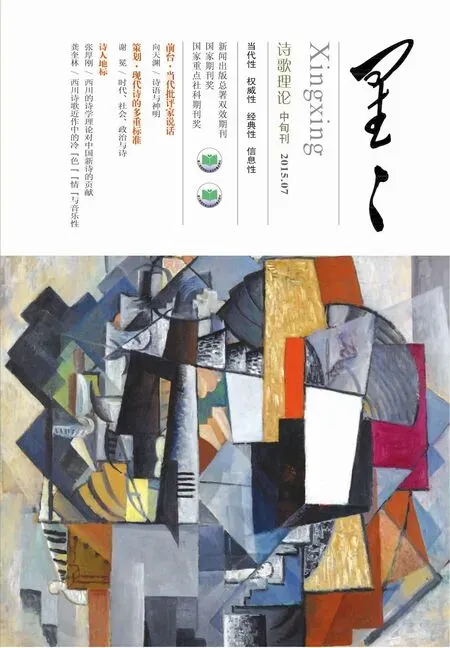詩性“物”語
邵 波
詩性“物”語
邵 波
閱讀本期推薦的三首詩歌,會自然發現顯露詩間的詩人對“物”的發現與迷戀。情感的脈動被主題詞似的“物”連綴起來,與詩歌節奏不斷產生碰撞,牽引出了源源不斷的詩情意緒,可以說,這些詩化之“物”背后隱藏著詩人對人、生存、愛情、際遇、命運等命題的探問。
宋曉杰的詩《中草藥》對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草藥及其煎服的過程有著細致入微的刻畫,將草、植物與人的關系凝結在了“藥性”里,“就那么多了,我們不會比古人/更善于攀援和行走,不會比穿行于/深山老林的他們,認識得更多/草和植物們脾氣各異,是否合得來/都要親手試一試、親口嘗一嘗”,淵源深厚的中醫傳統流傳千年,把脈開方中已將植物的藥用效果與人的肌理病癥結合起來,一種貼近人性體驗的醫術流淌的正是人們對生存的切身感悟——“體貼和甘苦”。“手搭命脈,就走進身體的迷宮:/這兒是主干道,那兒是小分枝兒/哪一條都得仔細清掃,不許有落葉/也不許走走停停。整套的機組嚴密而龐大/卻需要草本、木本的溫良,去撫恤潤澤”,宋曉杰在細微的生活經驗中發現詩意因子,把內心的激情壓縮為對事象的描摩,壓低情感的“沸點”,盡己所能收集平俗生活里蘊藏的詩美信息。“手捧粗瓷大碗,照不見影子/卻深知生活的濃度……”她將浪漫的吟詠抒情轉化為冷靜的宣敘白描,自我的張揚消退為與“物”齊觀的傾聽和凝視,從中發掘平凡人生、普通事物中隱匿的個人歷史和生存哲學,透射出了現實生活的朦茸質地。
日常生活的平凡與多艱,“藥”詮釋得淋漓盡致,而個體對生活的體認、理解也存留在真實的生存境遇中,那里的物象更加直露、可感,“生活的迷宮,路很窄/前方總是四面高墻/十年前的我還是個孩子/在離家幾十里的小縣城洗盤子”,寂之水的《洗碗工的夜晚》便道出了頭腦深處艱辛的少年時代,用“物”的感知撫摸現實生活的單調、堅硬、冷熱,“吃番薯,冷的,熱的/硬的,爛的,半生不熟的/一點點吃掉黑暗”,洗盤子、紅腫的手、媽媽的凍瘡、番薯這些“物化”時代的痛,無不折磨著成長的記憶,讓生活本身的殘忍、粗糲與困頓,加重了詩作的感情張力和強度,使詩歌進入現世生活的核心,敲擊著每個人的靈魂。詩人以客觀、真切的人性體驗試圖喚醒人們對底層生存狀況的關注,反思現代社會人類精神衰敗、貧血的癥結。寂之水在詩思與生活、理想與現實、靈魂與肉體的雙向拉伸中,痛苦且虔誠地找到了現實與寫作的平衡點,拉近了詩歌與生活的距離,同時也有意迫使詩思向生活的深處延展。
楊曉蕓的“物”是兩條“可愛”的魚,“我多次觀察到,在狹窄的水缸/兩條魚首尾相依,合成漆黑的棺材形體/為了彼此貼得更緊,它們整夜整夜地/不擺動,兩條魚恍若一條魚”,《就像兩條魚》中勾勒出了人與魚之間微妙的聯系,詩人借兩條首尾相依的魚,象征了男女生活中的依偎和支持。她并未就魚的細節展開描寫,而是把注意力定格在仿若“滄海桑田”的一幅畫面之上,以女性細膩的筆觸在生活的海灘上撿拾生命的彩貝,搜集貼近凡俗生活的詩性碎片,帶有一縷溫情與感動。“就像我們。我們的身體相互交織/風從糾纏不休的腳趾中快樂地穿越/一夜又一夜,只是時光的一瞬/只是我靠在你的懷里,看你抽煙/煙灰飄落的一小截”,生活中的意趣、想象和細節遍布詩歌的角落,流淌在身體和思維的空白之地,暗夜的孤獨因為有了另一半的陪伴而變得親切可感。在夜里這種靜謐的安撫猶如兩條一動不動相互安慰的魚,充滿了感性詩意的味道,“我們寧愿/如此低調/就像兩條魚,愛得近乎于死”。
對“物”的尋蹤是新詩前進和突破自我的詩學傳統,也是當今詩家“及物”寫作的要旨。三位詩人,三首詩作均返歸生活現場尋找聚合詩情的焦點,對日常事物重新編碼,將之分散轉化為個人的寫作經驗,最終使詩人主觀的心緒狀態與客觀的原生情態相藕合,最大限度地拓展了詩歌藝術的生長空間,彰顯出了抒情主體的生存狀態和人文關懷。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