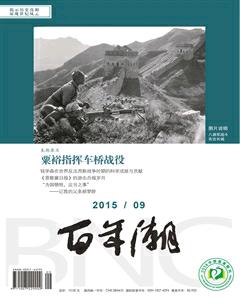《晉察冀日報》的游擊辦報歲月
陳春森
七七事變后,八路軍挺進華北,創建了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晉察冀邊區抗日根據地,隨即創辦了《晉察冀日報》。這份創刊于1937年12月11日,至1948年6月14日終刊的報紙,十年半時間共出版2845期,是我黨在敵后根據地創刊最早、堅持時間最長的報紙,是在極其殘酷的戰爭環境和極其簡陋的工作條件下長年堅持出版的鉛印日報,是晉察冀邊區黨和人民對日寇作戰的一面不倒的旗幟。
1938年3月,21歲的我來到五臺山,在晉察冀軍區參加了八路軍。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潘自力得知我是高中學生,在曲陽縣辦過抗日報紙《前進報》,說我是軍隊里急需的知識分子,要求我迅速到《抗敵報》(《晉察冀日報》的前身)報到。我當時有點想不通,說我來參加八路軍是為了到前線拿槍殺鬼子的。潘自力對我說,抗日敵后戰場沒有前線與后方之分,所有工作都是抗擊日寇的前線。從此,我在晉察冀日報社經歷了十年游擊辦報的整個過程,其中八年抗戰艱苦游擊辦報的經歷更使我明白了潘自力這句話的意義。
游擊辦報首戰告捷
1938年,日寇調集五萬兵力,從平漢、平綏、同蒲、正太各線發動了向晉察冀中心地區的多路進攻。敵人的主要目標是摧毀我邊區黨政軍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報社也是日寇圍攻的重要目標之一。
報社在阜平縣創刊不到三個月,就遭到敵機的瘋狂轟炸,大部分設備和紙張被炸毀,同志們只好翻過長城嶺,轉移到五臺山大甘河村繼續辦報。如何在戰爭中堅定意志、保存自己、辦好報紙,邊區黨委和報社的領導對此提出了明確要求。潘自力曾在一次抗敵報社的編輯會議上說:“報社要在游擊狀態下堅持出報,要在黨的新聞崗位上堅守陣地,要動員群眾與日寇戰斗到底。你們在敵后辦報就是新聞戰線上的抗日戰士。”
鄧拓于1938年春來到報社,接替舒同任報社主任。他召開報社五人會議,討論在游擊戰爭環境中的編輯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他提出的三條意見:(1)不論游擊戰多么頻繁艱苦,出報一定不能間斷;(2)增加社論,還要增加評論和短評,加強報紙的抗戰政策指導性;(3)油印改鉛印,縮短刊期間隔,強化報紙的抗日宣傳鼓動作用。
1938年9月,日軍開始圍攻五臺山,一方面打擊八路軍,另一方面要搶糧。八路軍反圍攻的戰斗異常激烈。那時報社只有十幾個人,為了多出幾期報紙,盡快將敵人進攻的消息傳達給人民,并抓緊進行反圍攻的輿論指導,報社沒有馬上離開五臺山大甘河村駐地。8月底,報社發表《加緊秋收與保留青紗帳》《徹底克服太平觀念》的社論。9月又發表社論,批評平漢線附近地方割掉青紗帳而使游擊隊失去活動陣地的做法。隨后又連續發了《加緊動員,粉碎敵人的圍攻》《怎樣進行堅壁清野》等社論。
9月的一天,日寇圍攻根據地的部隊已經逼近五臺山地區,報社迅速部署轉移。這是報社自1938年8月16日改為鉛印報后,第一次帶著印刷機開始“游擊辦報”的戰斗。出發時,報社的隊伍(加民工)已有近百人,沉重的印刷設備靠一支15頭驢騾的運輸隊馱運,轉移的隊伍在長城嶺東太行的險峻大山中艱難前行。為了保密,報社番號是“晉察冀軍區游擊支隊”。為了安全,報社的編輯記者都配發了手榴彈,但只有很少的槍支。從此,一支“一手拿筆,一手拿槍”游擊辦報的新聞隊伍活躍在北岳高山峻嶺之中,我們也首次感受到了游擊辦報的艱難。

報社隊伍到達龍泉關益壽寺時,敵情已萬分緊急。在瓢潑大雨中,鄧拓去龍泉關區公所動員當地群眾幫助接運印刷機器和物資,并迅速轉移到南山的一個只有十幾戶人家的瓦窯村。報社隊伍一到村里,電報收發員馬上開始收報,編輯們迅速編輯稿件,工人們架起機器開始印報。我們在瓦窯村住了五天,搶著出了四期日報。報紙印出來后迅速發出去。到第五天,前方報告有敵情,敵人快到龍泉關了,離我們只有十公里,我們只好把印刷機器抬到牲口背上,全體同志迅速轉移到了平山縣臥龍村繼續出報。在那里,我們又奮戰了一個多月。
這次在游擊中辦報共經歷了2個月的時間。我們拉著15頭驢騾,走了3個縣,住了4個小山村。報社的領導和編輯、記者、電臺收電員、發行員、印刷人員齊動手,夜以繼日地寫稿、排版、印刷、發行,搶時間出報22期。這22期報紙的形式和內容都十分豐富。有4開、8開、16開,有兩版、四版以及《抗敵外報》(是不用編號的報紙),有社論、新聞,還發表了多篇戰地通訊等。《老百姓》《海燕》兩個副刊就是此時創刊的,當時我擔任《老百姓》主編,顧寧(司馬軍城)任《海燕》主編。因為出現敵情要隨時轉移,報社只好在相對穩定時出大報,出不了大報就出小報,出不了正報就出外報,出不了兩版就出一版,重要事件及時出《號外》,沒有白報紙就用土黃紙。出版的報紙依靠地方政府和民兵及時發送到根據地四面八方。社論評論多、編寫快、印刷快、發行通暢、轉移迅速是當時我們游擊辦報的一大特點。可以說,報社第一次轉戰游擊辦報首戰告捷。
當時,日寇狂妄地叫喊要“南取廣州、中攻武漢、北圍五臺”,邊區和全國的抗戰形勢都很緊急。那時,華北抗日根據地廣大軍民對抗日戰爭的認識和如何抗敵備戰等問題都迫切需要引導。為此,《晉察冀日報》利用社論、評論提出和解決軍民的思想認識問題,發揮了黨的方針、政策的宣傳指導作用。從1938年9月抗擊日寇大舉“北圍五臺”起,報紙適應反圍攻大戰的迫切需要,一期接一期地發表了許多篇社論。
陸定一到晉察冀邊區考察時看過《抗敵報》后,在延安《解放》雜志上發表文章指出:“晉察冀的報紙工作確實是做了模范,并給了我們寶貴的經驗。……《抗敵報》在戰時每期有權威的社論,極其具體而且實際,沒有不切實際的空談。……是各地辦報的榜樣。……不僅為晉察冀立了功勞,也為全國的抗日戰爭立了功勞。”晉察冀邊區政府主任宋劭文看過《抗敵報》上關于戰時動員組織工作的問題和建議后,立即寫文章在報上發表,接受報紙的建議,并采取措施著手解決。邊區黨報《抗敵報》發表的社論,都是結合各個時期各個方面的實際問題發表的。社論及時,其效果就立竿見影,不僅促進了實際問題的及時解決,而且結合實際,有利于讀者政策水平、理論水平的提高。
不倒的旗幟
1939年至1940年兩年是報社游擊辦報的第二個階段。在這個時期,報社隨軍區機關轉移行軍走了五個縣,在大迂回的長途行軍中,同志們克服一切艱險堅持辦報。由于隨軍區機關行軍目標太大,報社三次被圍,一次被敵人飛機轟炸,損失慘重。

1939年春天,報社轉戰到阜平縣馬蘭村。秋冬,日寇調集兩萬人,分七路圍攻阜平地區。晉察冀軍區機關和部隊從根據地腹地轉到外線。敵人撲空以后,窮兇極惡地開始了分區“掃蕩”,到處燒殺擄掠,并把《抗敵報》作為打擊的重要目標之一。為躲避日軍的圍攻,報社被迫從阜平縣西南的馬蘭村轉移到了北部山區,又向東穿越曲陽、唐縣、完縣,到達易縣。當發現日軍尾追包抄過來,報社又趕快向西轉,在大山中急行軍突圍。報社在這次大迂回的行軍中,還在唐縣的大山里(楊家庵)堅持出版了五期鉛印報。這支身背步槍和紙張,牲口馱著沉重的印刷設備的浩浩蕩蕩的新聞隊伍,冒著嚴寒長途跋涉500里,經過五個縣,被稱為敵后游擊辦報的一次“運動戰”。12月3日中午,報社進入易縣劉家臺以北的芝麻溝時暴露了目標,日軍的三隊飛機突然襲來,沖著被圍困在兩山峽谷中的報社行軍隊伍輪番轟炸,情況十分危急。鄧拓命令所有人員急速就地隱蔽,但報社還是蒙受很大損失,幾位同志傷亡,部分牲口被炸死或炸傷,一部分鉛印設備和印刷物資被炸毀。這時又得到情報,南邊唐縣的日寇又尾追過來,北面淶源的日軍也正向報社駐地芝麻溝地區合圍。在這種萬分緊急的情況下,報社迅速將犧牲的戰友掩埋,將鉛印機等印刷物資就地堅壁,趁著黑夜急行軍100里才沖出合圍,幾經周折到達阜平縣北山區的上下車道,在康兒溝等村莊住下繼續出報。
1940年11月7日,《抗敵報》更名為《晉察冀日報》。我們在馬蘭村才出報2期,從11月9日開始,惱羞成怒的3萬日軍又分兵13路向晉察冀邊區開始了瘋狂的冬季“掃蕩”。這是日軍在百團大戰中遭到八路軍重大打擊后的一次報復性的“大掃蕩”,聲稱要徹底毀滅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當得知敵人正在向報社所在地包圍過來時,報社從阜平北部的連家溝出發迅速向南轉移。當東路敵人從定縣、曲陽到達王快附近時,南路之敵已從靈壽、行唐進到阜平城南莊地區,離阜平城不到30公里,情況萬分危急。報社同志不得不把一部分沉重的印刷機器暫時埋在沙河北岸,全部人馬跨過帶冰碴的大沙河,飛速行軍到達阜平西南深山中的馬蘭村。當夜,全報社各部門的同志不顧急行軍的疲勞,又馬不停蹄地投入編印報紙的戰斗,連夜突擊編印并發行了兩期八個版的鉛印日報,將《邊區黨委為粉碎日寇冬季“掃蕩”告同胞書》等信息及時傳達給根據地的廣大軍民,極大地鼓舞了邊區軍民反“掃蕩”的斗志。第二天,敵人再次向報社駐地瘋狂包抄過來,當距報社駐地馬蘭村還有五里時,報社的同志們迅速沖出包圍圈,以急行軍的速度向著平山縣滾龍溝村轉移了。
從馬蘭村轉移到平山縣滾龍溝后,雖然在阜平方向還有敵人在活動,但當地群山險峻,敵人暫時難以到達。報社抓緊這難得的戰斗間隙,經過兩天的休整,第三天即開始出報,而且是改出8開兩個版的日報,信息量隨著工作量的增加而大大增加了。在后來的29天里,晉察冀邊區這個在反“掃蕩”中發揮著巨大作用的日報連續出版了25期,一張張報紙每天載著黨的聲音、勝利的戰斗消息源源不斷地從滾龍溝這個小山溝里發行出去。從此至1943年,報社以滾龍溝為根據地,邊打游擊邊辦報,工作面逐漸擴展起來。
1940年12月17日,《晉察冀日報》創刊三周年紀念大會在滾龍溝召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書記彭真和根據地其他領導人胡錫奎、李常青、姚依林等出席。此時,邊區冬季反“掃蕩”已勝利結束。會上,彭真充分肯定了報社的成績,把《晉察冀日報》比作“邊區人民向新中國前進的燈塔”。他說:“我相信從艱苦戰斗中壯大起來的這個黨報,有充分力量戰勝一切困難,向前邁進。”彭真在給《晉察冀日報》創刊三周年的題詞中寫道:“《晉察冀日報》是統一邊區人民的思想意志和鞏固團結共同抗日的武器,也是邊區人民忠實的言論代表和行動指針。它將成為邊區文化戰線上的鐵的正規軍。”鄧拓代表報社宣誓:“一定要為黨報事業奮斗到底,為堅持華北抗戰、堅持晉察冀根據地奮斗到底!”報社的同志們也紛紛表示,《晉察冀日報》作為一面不倒的旗幟,要更高地飄揚在邊區的土地上。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堅持
1938年、1939年、1940年的游擊辦報,使報社在戰火中經受了考驗。報社認真總結了抗戰初期這幾年游擊辦報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在反圍攻、反“掃蕩”的游擊中加強和改進辦報工作的新要求:行軍中只要有24小時駐地時間就要爭取出報。文章要短小,在3000字內做文章。改裝輕便印刷機,全部印刷設備輕裝化。組成八匹騾子的精干運輸隊。精簡報社隊伍。報社人員分為兩個梯隊:第一梯隊是辦報人員,編輯精簡到四五個人,每人都配發手榴彈,印刷發行小組帶機器設備隨隊,每期印數最少也要5萬份的15%以上;第二梯隊是武裝梯隊,負責偵察敵情,帶槍保衛報社的安全。在幾個群眾基礎好的地方分設物資點,將笨重的印刷機器、設備分幾處堅壁起來,做到隨到隨用。建立公開和秘密的發行交通網,使報紙能最快運達,并與軍區保持密切的聯系。

不久,日軍對晉察冀邊區的“大掃蕩”又開始了。1941年和1943年是日寇對晉察冀邊區山區根據地圍攻、“掃蕩”最瘋狂、最殘忍、時間最長的兩年,也是報社犧牲人數最多、游擊辦報最為艱難、辦報風險最大的兩年。
1941年,日本帝國主義為發動太平洋戰爭,急欲“肅清”八路軍,穩定華北占領區,對我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實行了野蠻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日軍調用了7萬兵力,采用“鐵壁合圍”“梳篦式清剿”“馬蹄形堡壘戰”“魚鱗式包圍陣”等戰術,連續反復進攻,多面分進合擊,妄圖一舉“剿滅”我邊區的主力部隊和我邊區的首腦機關。晉察冀日報社也是日軍“大掃蕩”的目標之一。
8月13日,日軍向晉察冀邊區北岳中心區進犯,平漢、正太鐵路的敵人迅速逼近平山、靈壽北部山區,離報社駐地滾龍溝已經不太遠了。敵情緊急,軍區通知報社馬上轉移。報社為了多出報在原地堅持了十天。到8月23日,報社趕出了九期報紙,連續發了兩篇社論:《開展對敵宣傳戰》和《紀念百團大戰一周年》,發了專論《識破并粉碎敵偽的治安強化陰謀》,轉發了延安《解放日報》關于八路軍、新四軍在各地打勝仗的消息,還發表了蘇聯紅軍擊潰德國三個師的勝利消息。
8月24日,日軍已經逼近報社的駐地滾龍溝,報社決定迅速轉移,但前進的道路已被敵人切斷。此時,報社與軍區司令部失去了聯系,敵情無法摸清,報社只剩下獨立作戰一條路了。在這種情況下,報社領導臨危不懼,沉著應對,經過簡短的磋商后,認為滾龍溝一帶群眾基礎好,地形比較熟悉,決定就留在滾龍溝與敵人周旋。報社領導決定將報社化整為零,組成編輯、印刷、電臺、發行等若干小組,分散隱蔽在大山里活動,并隨時保持聯系,利用游擊間隙力爭多出報。敵人獲知報社就藏在滾龍溝的大山里,于是在滾龍溝外的陳家院設立了據點,封鎖了滾龍溝口,把報社團團包圍起來。日軍在飛機的掩護下,從滾龍溝口由東向西“掃蕩”,反復搜山。這天,敵人步步進逼,敵機低空飛來飛去向同志們隱藏的地方轟炸掃射。社長鄧拓和政治指導員謝荒田堅定沉著指揮大家隱蔽擊敵。鄧拓嚴肅地對秘書楊國權等五人小組的同志們說:“現在情況很嚴重,大家要從最壞處著想。如果敵人沖上山來,我們就和他們拼了,寧死不當俘虜!你們有手榴彈,在萬不得已時,就拉開它與敵人同歸于盡。我和老謝有手槍,會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報社各小組的同志分散在山上的深溝密林里與敵人周旋,敵人四處搜山,包圍堵截,但就是找不到我們的蹤影,只能無可奈何地朝山上亂放槍。我是編輯組組長,在戰斗的間隙還組織編輯抓緊時間編稿子。在滾龍溝被圍困的40多天里,我們還出版了30多期報紙。被傳為佳話的“七進七出鏵子尖”的故事就發生在這里。
在敵人頻繁搜山,報社處境異常困難的情況下,報社的印刷點只好隱蔽到溝掌里一個小山村——鏵子尖。所謂鏵子尖,是形容這里的山像鏵犁的尖頭那樣陡峭尖利。因為此地只有兩戶貧窮人家,我們人多沒有房子可住,大部分人搭窩棚或露天而宿,而把最重要的“寶貝”印刷機安放在老鄉那個沒有窗戶,四處散發著難聞牛糞味,用亂石壘起來的不足六平方米的破牛圈里,一期又一期的報紙就是從這個牛圈里印刷出來的。雖然條件異常艱苦,但是我們人人斗志昂揚。由于手工操作印報勞動強度很大,加上敵人封鎖經常吃不到糧食,大家餓得渾身無力,只好到山上挖點土豆、蘿卜、白薯充饑。大家日夜輪班出報,每天工作時間很長,實在太累了就在牛圈里鋪上一層草,兩個人背靠背休息一會兒。那段時間日軍頻繁上山“掃蕩”,敵情一天幾變。敵人來了,我們就把機器和印刷用品包起來埋進土里,再蓋上茅草進行偽裝,然后大家迅速轉移。敵人走了,我們挖出機器再繼續印刷報紙。在敵人圍攻的40多天時間里,我們曾七次埋下機器,又七次刨出機器來印報。同志們就是這樣在上有飛機轟炸、下有日軍搜山的情況下,克服巨大困難,憑著堅決戰勝敵人的勇氣和誓死保衛邊區的大無畏精神頑強地堅持出版報紙。僅僅在1941年一年中,報社就有十位同志先后壯烈犧牲,還有四位同志因生病無法醫治而不幸病故,報社減員嚴重。
1943年,日本侵略者對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已是強弩之末,因此對邊區的摧殘掠奪空前嚴重。日寇糾集了四萬多日、偽軍從平漢、正太、同蒲等鐵路沿線的據點出發,向北岳山區猛撲過來。五臺、繁峙、盂縣、正定、靈壽、行唐等據點的敵人分路向阜平合圍。這年的2月,報社從平山的滾龍溝、陳家院又遷回了馬蘭村及其附近的栗樹莊、坡山村辦報。此時的報社仍處在敵人的合擊圈內,敵情十分嚴重。
9月16日,反“掃蕩”大戰開始后,報社按照“在駐地停留24小時就出一期報”的要求,力爭在離開馬蘭村之前再出一期日報。22日,偵察員報告,東西兩面的敵人離報社所在地還有20里,報社為了爭取到一天一夜的出報時間,決定全社動員。只見編輯、電臺、印刷、發行等各個部門就像一臺機器一樣同時轉動起來,連夜趕出報紙。每當印出100張報時,我們就歡呼一次勝利;當印到800張時,全體報社人員激動到了極點,大家歡呼跳躍:“800張!勝利的800張!”這歡呼聲表達了我們抗日新聞戰士心中的勝利喜悅。而此時敵人已經逼近馬蘭村了,鄧拓宣布撤離,全體報社人員立即行動,快速向東南轉移。報社人員前腳走,敵人后腳就撲進了馬蘭村。9月22日這一期報是我們冒著被敵包圍犧牲的極大風險出版的,是我們在游擊辦報中最大膽最英勇的一次對敵斗爭。

報社離開馬蘭村后急行軍,躲開了東西兩面圍上來的敵人,鉆進了南山的誠信溝。此時天色已黑,山洪暴發,隊伍冒著傾盆大雨,腳踩著山洪沖下來的爛泥漿,奮力爬上四道嶺。第二天太陽升起時,大家稍事休息就又準備開始出報,誰知這時我們仍處在敵人的包圍圈里,處境十分危險。軍區急電,要求報社立即向西轉移,到靈壽縣西部山區去找可以隱蔽的地方出報。9月24日夜,報社下到山腳,準備通過北營進入靈壽的西北山區。前一天偵察員偵察過北營沒有敵人,當報社隊伍趁夜進村時,突然與日寇遭遇,走在最前面的人員發現敵人迎面過來時想通知后面的人躲避已經來不及了,雙方在近距離密集交火。混戰中,報務員鄭磊俊被敵人射中倒下,運輸隊員曹斗斗、報紙發行員安志學當場壯烈犧牲。鄧拓正騎馬走在隊伍的前面,聽到槍聲驟起,他迅速跳下馬,但腳尚未著地,他的坐馬就中彈倒地而亡。在敵情不清的情況下不能硬拼,鄧拓傳令大隊后撤。第二天,當我們從受傷的日本俘虜中得知昨晚遭遇的是日軍的一個運輸隊,他們搞不清我們的來歷,在胡亂地放了一陣槍后便丟棄物資逃走了。這次是報社同志們在游擊中與敵人直面相遇的一次極其危險的遭遇戰,雖然不幸犧牲了三位同志,但是使這支年輕的新聞隊伍受到了一次鍛煉。為了擺脫敵人的圍堵,報社繼續向外線轉移。經過長距離行軍,隊伍進到靈壽、阜平、平山交界的高山地帶,登上了海拔2000多米高的玫瑰坨,跳出了敵人的圍攻中心,轉到了接近外線的比較安全的地帶。
玫瑰坨上的日卜是一個只有兩戶人家的小山村。一位年過花甲的牧羊老人帶著老鄉忙著給我們騰房子,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這支“一手拿筆,一手拿槍”的八路軍新聞隊伍。當時報社有110個人,小山村根本沒有條件解決這么多人的住宿問題,我們就自己動手砍樹枝、割茅草,架玉米秸,搭窩棚,連老鄉的豬圈、牛棚都利用起來搭成臨時編輯室、電臺室、發行所。報社只借了老鄉兩間小草房,這是當時最好的房間了。一間給領導研究工作用,另一間用于電臺收電兼印刷。稍事休整后,我們于10月4日就開始在這個小山村秘密出報了。我們在玫瑰坨前后隱蔽了12天,共出版報紙12期。報社發行員、交通員很快與當地發行網打通聯系,把連日出版的報紙秘密分發出去。
報社在玫瑰坨出報雖然很隱蔽,但仍很快又被敵人發現了。10月15日黎明,一股日軍從阜平城南莊向玫瑰坨上的日卜襲來。在敵人距日卜還有10公里時,報紙還未印刷完成,太危險了。因為這里地處高山頂上,四面開闊,根本無處躲藏,如再不撤離就有被敵人圍住全殲的危險。萬幸的是,軍區得到消息后,及時派來一個團截住了來襲的敵人,敵人被打得狼狽敗退,報社終于得救了。緊接著軍區又來電,說敵人有可能再來偷襲報復,要我們立即轉移陣地。報社馬上出發,連續跋涉兩晝夜,進到盂平縣的龍耳清。這個小村靠近五臺縣“無人區”,是晉察冀北岳區西南邊緣地帶,處于反“掃蕩”作戰的外線地區。報社就在龍耳清這個小村住下來,把反復偷襲報社的敵人甩得很遠。
報社利用沖到外線的空當,隱蔽在敵人的封鎖溝旁邊繼續出報。其實這里距敵人據點并不遠,只是此時據點里的敵人大都集中到根據地腹地“掃蕩”去了,據點里留守的敵人并不多。盡管如此,我們在這里出報仍要冒很大風險。我們就在敵人眼皮底下的龍耳清村隱蔽出報44天,出版了28期報紙。這期間,報社時刻未放松對敵警惕。我們做好了敵人一旦向外線“清剿”,報社就立即轉移到“無人區”去的準備。不久,敵人果然發現了報社在龍耳清出報的情況,于是從根據地中心區直接向報社的駐地龍耳清奔襲過來。當敵人距離報社只有10多公里的時候,報社領導一聲令下,大家齊動手一天內就把機器和出版物資全部堅壁妥當,隨即組織起精干的隊伍,只帶一架油印機,一臺電話機,一臺收發報機和新聞稿件,每人帶上槍和手榴彈,迅速離開龍耳清向西跳出河北,轉到五臺、盂縣交界的“無人區”。此時是11月底,太行山上已經是滴水成冰。大家趁著夜色一路急行軍而去。太行山山高路窄,“無人區”一片荒蕪,只覺嗖嗖野風和困倦饑寒陣陣襲來,我們找不到一點吃的東西充饑。當行軍到一處被敵人燒毀的殘墻邊時,大家靠著墻背著風打個盹兒,稍事休息后又繼續前進了。我們這支年輕的新聞隊伍,在莽莽太行的“無人區”里忽南忽北,左右穿插。大家頂著凜冽刺骨的西北風前進,上身只穿著一件空心棉衣,下身穿一條單褲(軍需供給不上),冷風嗖嗖往身上鉆。盡管凍得渾身打戰,但我們互相鼓勵著前進,隊伍里始終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鄧拓在到達馬蘭村回顧這一艱難行軍時還賦詩一首:“風雪山林路,悄然結隊行。兼程步馬急,落日水云橫。后路殲頑寇,前村問敵情。棘叢探斤斧,伐木自丁丁。”
報社隊伍在“無人區”里轉戰19天,鍛煉了斗志,沖破了艱險,保存了實力。當得知敵人已從根據地腹地陸續撤退時,我們又返回阜平馬蘭村繼續出報。
1943年末反“掃蕩”大戰勝利結束,時任中共晉察冀分局副書記的劉瀾濤對晉察冀日報社在反“掃蕩”中的英勇表現和工作成績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說:“三個月苦戰中,我們的《晉察冀日報》卻始終未停刊,一直為邊區人民服務,他們受到群眾擁護、愛戴。這就是我們宣傳工作的勝利。”在邊區反“掃蕩”結束后的群英會上,各界代表一致決議表彰晉察冀日報社,指出報社在開辟敵后新聞宣傳和文化事業上有突出功績,在反“掃蕩”中克服困難始終堅持辦報不動搖,有重大貢獻。
一支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新聞隊伍
我們這支滿懷抗日救國激情的新聞隊伍來自五湖四海。主任鄧拓是福建人,副主任洪水是越南人,記者倉夷是南洋華僑。他們那時都很年輕,多數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抗戰中期又來了一些年紀稍長者,如副總編及副社長鄭季翹、婁凝先、張致祥、胡開明、李荒等,他們也只有30歲左右。報社這支隊伍從抗戰初期的十幾個人,逐步發展到500多人,抗戰結束時達到700人左右。抗戰期間,報社進出總人數達到1000多人。
由于報社的骨干都是共產黨員,所以這支隊伍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我們報社是一個團結的集體,大家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共同進步。編輯部里只有一匹馬,是鄧拓的坐騎,但是他經常把馬讓給體弱多病的同志騎。我們是個朝氣蓬勃的團隊,是個能文能武的戰斗隊,每人都擔負著多種任務,既是編輯,又是記者,還是戰斗員。辦報時能寫稿、編輯;行軍時能偵察、放哨、搬運物資設備;遇敵時能與敵人武裝對抗。在緊急情況下,編輯記者時常還被派出去偵察敵情,通過敵人封鎖線去與地方黨委取得聯系。
我們這個集體有著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在行軍、采訪和發行中與敵人遭遇、戰斗是經常的,我們每個人都隨時準備著為抗日犧牲生命。特派記者雷燁在平西、冀東、北岳山區轉戰四年,寫了大量抗戰通訊報道。1943年4月,他到平山縣曹家莊去采訪時被敵包圍,他不顧個人安危,組織群眾迅速轉移,讓和他同行的同志帶領群眾突圍,他堅定地說:“你們快撤,要死死我一個。”他斷后并與敵人交火,打死了好幾個敵人后身負重傷,為了不當俘虜,他用最后一顆子彈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當地老百姓懷念他,為他立了紀念碑,栽上了“雷燁樹”。歸國華僑倉夷是報社的優秀編輯記者,在抗戰前線8年,發表過通訊100多篇。他在一次執行采訪任務時慘遭敵人暗害,犧牲時年僅25歲。優秀發行員霍進禮在送報途中遇敵,壯烈犧牲。醫生許力為了掩護報社病號轉移而中彈身亡。報社國際新聞編輯組組長、優秀共產黨員、從貴州遵義來到敵后堅持抗戰的胡畏,電務隊臺長、技術干部黃慶濤(至今尚未找到烈士的家屬),報務員鄭磊俊,發行人員、共產黨員弓春芳、安志學,印刷工人侯春妮,運輸隊員曹斗斗在1943年反“掃蕩”期間壯烈犧牲。鄧拓為這7位烈士賦詩悼念:“故鄉如醉遠,天末切棲遲。瀝血輸邦黨,遺風永夢思。懸崖一片土,臨水七人碑。從此馬蘭路,千秋烈士居。”他們為堅持敵后抗戰,為黨的新聞事業,把滿腔熱血灑在了晉察冀的土地上。在游擊辦報中,報社共犧牲了40位同志,病歿了19位同志,他們永遠長眠在燕趙大地上。英雄的遺骸被安葬在老根據地阜平縣馬蘭村的鐵冠山邊。報社烈士的英名鐫刻在阜平縣烈士陵園的“忠魂碑”上,永垂千秋!
(編輯 王 兵)
(作者曾任《晉察冀日報》編輯部副部長、編委,《人民日報》編輯部副主任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