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文化的對抗(外一篇)
張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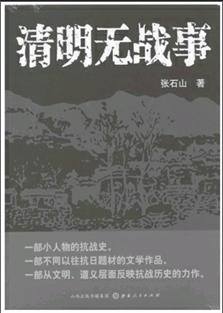


2005年, 由筆者擔綱首席編劇的20集電視連續劇《呂梁英雄傳》在央視播出。大致說來,應該算是同時同類題材電視劇中較好的一部。但由于各方面局限,拍攝完成的作品,沒有完全體現出我的劇本所達到的高度。
不覺就過了十年。
2015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我希望自己在影視作品創作方面有所舉動、有所突破。于是,有了寫一部有關題材電影的動機。
所以動心要寫一部抗戰題材的電影,不是誰的指令部署,我在主觀上有更為深層的內在驅動力。如同十年前一樣,這是筆者投身抗戰紀念活動的一次當代踐行。
就我的有限觀賞所及,中國抗日題材的影視作品,粗制濫造者太多,精品闕如。一般編劇的套路,令人生厭:鬼子殘暴而愚蠢,我們的抵抗則堅決而慘烈,最終是我們大獲全勝。淺薄粗俗,不一而足。
全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過去了七十年。中華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所付出的代價,無比巨大;對全人類優秀文明戰勝法西斯所做出的貢獻,無與倫比。作為影視作品來反映反思那場戰爭,我們和西方的差距之大,不可以道里計。即便與前蘇聯相比,我們同樣難以望其項背。這樣的狀況和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成比例,與東方泱泱大國的形象不符。這足以令人慚愧,令人耿耿于懷。
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我們不應該簡單地譴責編劇,貶斥他們無能。多年來的思維定勢,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局限了大家的眼光。嚴格的審查制度非常必要,但審查尺度始終不明晰,編劇動輒得咎、無所適從。正劇因之少見,鬧劇于是層出不窮。
而怨天尤人絲毫無濟于事。中國人為反法西斯戰爭付出了無與倫比的慘烈代價,在影視藝術的表達方面,決不應該只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自我欣賞自我陶醉,早已應該走出去,或曰“打出去”。
身為一名中國作家,我是否能夠超越平庸、寫出具備走出國門走向世界那樣水平的作品來?
首先,這要牽扯到對中國抗戰的理性認識。
改革開放以來,國人迎來了偉大的思想解放。重新認知抗日戰爭,不再是禁區。這方面,國人已經達成了許多共識:
抗戰對于中國,是中華民族近代百年屈辱失敗史上的第一場大勝;亡國滅種的危機,激活了中國全民的抵抗意志;這是一場全民抗戰,絕非一黨一軍可以獨自勝任。
種種共識之外,我也逐步形成了屬于自己的獨立思考。
我認為:
從全球格局來看,二戰是全人類眾多偉大文明與反人類的德日意法西斯的大決戰;中國抗戰,是偉大的華夏文明對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的殊死抵抗;中國抗戰,是反法西斯大格局中東方戰場最偉大的事件,同時,中國抗戰是華夏文明與全人類文明的協同作戰。
當然,任何文學創作最忌諱外在說教,作家所有的思考必須通過講述故事與刻畫人物自然流露出來。
在電影劇本《清明無戰事》所講述的故事里,我著力塑造了一位曾經的鄉紳。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多是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鄉紳,在事實上成為鄉土自治維系鄉間社會平衡的中堅。他們身上曾經最多保全了中華文明、士子傳統。在和平年代,他們行為世范、道德表率;在國難當頭的時節,他們毀家紓難,垂范千秋。他們多數并非虛構的階級敵人惡霸“黃世仁”,而是山西抗戰史上開明士紳劉少白、牛友蘭那樣的人物。
理直氣壯歌贊這樣的人物,正是理直氣壯歌贊華夏文明。
自鴉片戰爭以來,古老的中世紀東方帝國與西方現代文明乍然相遇,連連敗退。一種極具破壞力的思潮鋪天蓋地:我們的文明已然落伍,不配保全、不可信賴。在這種思潮之下,于是將滿清的政治腐敗、經濟滯后、軍備落伍等等,一股腦兒歸罪于華夏文明。
華夏文明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文明?我們要不要熱愛弘揚這一文明?這個問題極其嚴肅。
我堅定地認為:戰爭或有一時之成敗,并不能就此判斷文明之高下。仗恃暴力、弱肉強食,那是叢林法則,與人類文明風馬牛。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橫掃歐亞,豈能證明當時歐亞文明落伍落后!
在文明對話方面,偉大的華夏文明博大精深強韌厚重,浩浩乎存于天地之間、卓然挺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我們的偉大文明,從來沒有失敗過。
仁者無敵。我們的文明根本就沒有敵人。
全球抗擊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說到底正是全人類文明的勝利;中國抗戰的勝利,則是華夏文明的偉大勝利。
在《清明無戰事》這個故事里,在那一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中國曾經的鄉紳身上所葆有的華夏文明,形成了與日本侵略者所推行的法西斯文化最直接的對抗。法西斯文化的殘暴無恥暴露無遺,而華夏文明雍容博大、強韌無比,凸顯出永遠不可被戰勝與征服的無與倫比的生命力。
不曾被入侵者的刺刀和滑膛槍征服的華夏文明,卻遭到了中國人自己的踐踏、遭害與破敗,這是極其令人痛心的事實。
歷史發展到當今,搶救與恢復傳統文明的呼聲不絕于耳。強韌的華夏文明屢經劫難,總是能夠劫后余生。大地在、山河在、人民在,給人以偉大的信心。
《清明無戰事》的劇本完成之后,曾經在北京召開過研討會。由山西省作協和中國作協《文藝報》聯合舉辦,有國內著名劇評家李準、仲呈祥等參加。大家給出了一致的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一個有重大突破的劇本。如果拍攝成功,將不僅是中國影壇的一部好電影,而且完全可以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然而,又是令人哭笑不得,電影的攝制計劃中途夭折。我們山西不是出現了“塌方式腐敗”嘛,這樣的形勢之下,曾經慨然答應全額投資的老板中途跑路,人間消失。
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社長李廣潔先生,在一次偶然相遇的場合,聽我講述了“清明無戰事”的故事。李先生大為激賞。當下發出稿約:老張,你把這個故事寫成長篇小說,我們來出版。
電影,是一門綜合藝術,編劇完成之后,離不開導演和演員的再度創作。單單就劇本而言,和小說頗有共通之處,可謂大同小異。當然,作為小說,需要小說式的敘述語言和敘事筆調。
《清明無戰事》,日后或許能夠拍攝成為一部電影吧。現在,多承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同仁襄贊,這個故事首先以小說的面目呈現給讀者。
從《呂梁英雄傳》到《清明無戰事》,時間是整整十年。
對于紀念抗戰,身為作家,書寫有關作品,我自認為有責任在焉。
關于改編《呂梁英雄傳》,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闡述了一點當時的思想,題曰《歷史的擔當》。
從“歷史的擔當”到“文化的對抗”,我的抗戰題材寫作在向深層掘進。
從我們的那個東鄰小日本的表現來看,從當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來看,抗戰在形式上是結束了,在歷史的最終判定和文化對抗的意義上而言,戰爭沒有結束。
我在用我的筆進行戰斗。
我知道,這不是一個人的戰斗。
文明的互動
——《六福客棧》自序
1、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全人類優秀文明與反人類的德日意法西斯的大決戰;中國抗戰是華夏文明與全人類文明的協同作戰。那是東西方文明的偉大互動。
當下,東方西方乃至全人類都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偉大勝利,這是東西方文明互動的繼續。這是協和萬邦的人類文明大合唱。這種文明互動,已成世界潮流。全人類的進步事業,指向世界大同,無可轉捩。
文明的坐標從來都在身后。紀念二戰,追溯歷史,冀幸能夠找到并點燃一粒歷史的火種。
希望我們所創寫的這部《六福客棧》,能夠成為東西方文明互動的一個實績。
2、上個世紀50年代,好萊塢拍攝的由英格麗·褒曼主演的電影《六福客棧》轟動歐美,女主角艾偉德成為了西方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
格拉蒂絲·艾偉德,生于1902年,出身英國平民家庭。基于堅定的信仰,于1930年輾轉萬里來到中國山西的偏僻小縣陽城傳教。這位英國弱女子,在陽城傳教布道整整十年。十年間,艾偉德在陽城開辦客棧、收養孤兒、救助難民,做過許多善舉。其間,曾經被當時的民國陽城縣政府聘任為禁足督察,為掃除纏足陋習幾乎走遍了陽城的每一座村莊。其突出的工作業績,受到民國政府嘉獎。
深深愛上中國的艾偉德,于1936年申請加入了中國國籍。
抗日戰爭開始后,艾偉德收養難童、救助傷殘,不辭辛勞、不遺余力,弘揚踐行了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不僅如此,她還利用特殊身份,冒險出入日寇占領區偵察敵情,為國軍與八路軍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軍事情報。同時,艾偉德通過歐美國際媒體,無情地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種種戰爭暴行,因之受到日寇的通緝。艾偉德聲稱:我是中國人,我要和自己的同胞共赴國難。
到1940年,由于此前日寇的飛機幾次轟炸陽城、屠殺了上千和平居民,艾偉德心系難童孤兒的安危,毅然帶領百名兒童離開陽城;這支隊伍徒步南出太行、翻越中條,最終一人不少全部平安抵達當時的大后方西安。這一壯舉,在當時即為世人傳頌,艾偉德由之贏得了“孤兒母親”的崇高贊譽。
——以上即為艾偉德其人真實故事的大略梗概。
3、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令人耿耿于懷的是,艾偉德其人其事竟被塵封屏蔽。中國人對之一無所知,山西人對之一無所知,陽城人對之一無所知。
中國人到底怎么了?我們屬于一個翻臉無情、忘恩負義的族類嗎?
歷史的屏蔽果然那樣厚重、那樣令人絕望,我們到底還能不能發見歷史的真相?
在知道真相之后,中國人到底能不能做點什么,以洗雪那莫須有的污名?
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的嚴肅拷問,無可逃遁。
公元2015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中國抗戰勝利70周年。70年來,關于艾偉德的著作,無論是傳記還是小說,包括兒童讀物,在西方出版了數十種之多。而在我們中國,在艾韋德的故事主要發生地,卻沒有幾本堪以匹配的出版物。
艾偉德的故事,是繼續屏蔽雪藏還是讓人知道?艾偉德身上體現出的偉大人道主義精神,是理直氣壯地宣揚還是視而不見任其自生自滅,這中間頗有徑庭。
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李廣潔社長,一錘定音,力主推出這樣一本書,以介紹艾偉德其人其事、以紀念偉大的抗戰。
紀念抗戰,中國作家責無旁貸。創寫這樣一本書,事實上成為我們紀念抗戰的當代踐行。
經過幾個月的勞動,《六福客棧》一書終于如期完稿。
4、客觀評判,這本《六福客棧》是由中國作家創寫的關于艾偉德其人其事的第一本著作。
與外國人所寫的同一題材的著作相比,本書至少有兩個方面的突破。
第一方面,是內容廣度的拓展。
本書不僅向讀者全面準確地介紹了艾偉德其人其事,而且向讀者展現了當代中國人“了解艾偉德、紀念艾偉德”的實際狀況。
中國人并非忘恩負義之徒,也決不是麻木不仁之輩。中國人懂得感恩;中國人受到艾偉德精神的感召,正在繼承與光大這一精神。無疑,這才是“紀念艾韋德”的本質意義所在。
5、本書在第二方面的突破,是文化認知高度的把控。
就我們的有限涉獵所見,西方關于艾偉德的宣傳報道、傳記書寫包括電影故事編撰,多有高推艾偉德的超然境界、對之過分神話之嫌。在西方人的敘述中,艾偉德幾乎就是一個天生圣人。積貧積弱的中國、落后愚昧的中國人,需要艾偉德來傳播福音、救助眾生;而虔信上帝的艾偉德,由于信仰堅定,幾乎無所不能。其中的“西方敘述立場”非常明顯。
事實上,恰恰是在艾偉德還遠遠沒有成為“艾偉德傳奇”的時候,艾偉德就已經來到了陽城。她在陽城呆了十年,這十年,正處在中華民國的“黃金十年”時段。她一定真正接觸到了當地無數的中國人——那些具備了“民國風范”的中國人。正是通過這些中國人,艾偉德終于探知了華夏文明的底蘊。她在陽城申請加入了中國國籍,從此,艾偉德認定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并以此而自豪。
中肯地評價,籍籍無名的艾偉德是在陽城獲得了她的成長,方才最終成為了“偉大的”艾偉德。
再者,對于傳教士前來中國傳教傳道,往往被敘述成一種單方面的居高臨下的“文化給予”。理性地認識,當他們遭遇了博大厚重的華夏文明,其傳教傳道的過程應該是一個文化互動的過程。在理性認識和文化認知的引領下,本書努力探詢并藝術地再現了這種文化互動。
6、艾偉德祖籍英國,服膺上帝,信仰堅定,基督教文明最早哺育了她;
艾偉德來中國大陸20年,到中國臺灣13年,她加入了中國國籍,發乎內心認定自己是一名中國人。艾偉德融入了中國,崇尚仁義道德,偉大的華夏文明滋養了她。
是文明的互動,培育出了艾偉德精神;艾偉德精神,最終成為了全人類優秀文明的共同結晶。
艾偉德和艾偉德精神,因之贏得了永生。
艾偉德在抗日戰爭期間拯救百余名中國孤兒的故事,發生在陽城,發生在中國,所以也不應該埋沒在中國。
希望我們的這部《六福客棧》,成為一個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