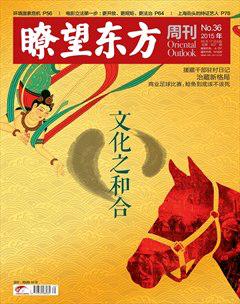網上敦煌:IDP的國際努力
王斯璇+姚瑋潔

2004年6月22日,國家圖書館在善本庫開辟專庫,作為敦煌遺書特藏庫,將館藏的1.6萬余件敦煌遺書妥善保存。圖為工作人員在展示遺書修復過程
倘若22年前,在英國薩塞克斯的第一次“敦煌遺書保護研討會”上向世界各國專家描繪這樣一個場景:未來,無論身處何方,都可以在世界性的網絡數據庫上,免費查閱到全球各地所藏敦煌文獻最為清晰的數字圖片,或許會被取笑是癡人說夢。
今天,全球最大、最具雄心的敦煌學合作項目——國際敦煌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已成為保護、研究敦煌文獻的國際合作典范。
自1994年成立至今,全球共上傳敦煌西域文獻數字化圖片460357拍。其中中國國家圖書館上傳圖片133402拍,英方約158000拍。學界對敦煌西域文獻的需求,由此大獲滿足。
大英圖書館和中國國家圖書館,作為IDP項目主力,仍源源不斷向網絡輸送著敦煌精美的畫作和珍貴的文字章節。
若此項目最終完成,預計圖片將超過100萬拍。
季羨林曾言:“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而IDP項目,將中英緊密相連。
失落就需要反彈
敦煌,之于每一個中國人,或多或少,都有某種揮之不去的慘淡記憶。
1900年6月22日,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無意間發現日后舉世聞名的敦煌第17窟,“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然而1907年和1908年,洞中很多精華被英國人斯坦因和法國人伯希和送出中國。
如陳寅恪所說:“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80年代中國的敦煌學為什么落后?就是因為看不到原件。”中國國家圖書館IDP項目第一任負責人林世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國圖老館長袁同禮意識到,中國敦煌學的發展,光靠伯希和提供的敦煌寫本照片資料遠遠不夠,“我們得去找,去拿。”遂派人赴法英協助外方進行敦煌遺書的編目,并對外藏重要的經史子集、藏外佛教文獻等資料拍照寄回。這些資料的影像回歸,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敦煌學的發展。
二戰后,此項工作擱置。直至上世紀60年代,英、法、中所藏敦煌遺書開始互換縮微膠卷。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料獲取的困難,但很多文字仍難以釋讀。
“為了看那些縮微膠片,我們在圖書館里一點點搖著機器,看一個小時,機器的燈泡太熱,就要關掉降溫,再繼續。”林世田回憶。
當時已經出版了根據縮微膠卷影印成冊的黑白圖冊,然而,“字的顏色,紙的紋路,都無法反映原貌。”他說,過去日本敦煌學之所以領先中國,也是因為“他們去英法看原件很容易。看不到原件,我們永遠落后”。
1981年,日本京都大學教授藤枝晃應邀赴南開大學舉辦敦煌學講習班。后有訛傳稱藤枝晃開講便道“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引起中國學者不滿。
以季羨林為首的22名專家聯名上書中央,創建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批復撥款100萬元,其中17萬余元撥給國圖,建立國圖敦煌資料研究中心。落后多年的中國敦煌學才得以快速復蘇。
“神話般的開局”
1993年,時任香港王寬誠教育基金會歐洲代表的劉錫棠,負責資助通過英國皇家學會和英國科學院赴英訪學的中國博士后,一位中國學者的訪學報告,引起了這個中國人“對于敦煌無聊的好奇”。
參觀大英圖書館所藏的敦煌文獻后,此前對敦煌只知一二的劉錫棠發現,1901年到1916年間斯坦因自中國運回的藏品,大部分還只是完好無損地保存在大英圖書館中,而未曾廣泛開放給研究者。
他覺得,“自唐代始,絲綢之路便是中國與世界關聯的紐帶。敦煌遺書的價值完全不止于中國,是全世界的重要遺產。”
不只敦煌藏品,包括中國境內絲綢之路其他遺址出土的重要文物、繪畫以及超過20種語言文字的寫本,流散世界各地。國際學者面臨的大問題有二:其一,仍有大量藏品亟待修復和編目;其二,藏品分散,學者難見敦煌遺書原件,更難以利用、研究。
這也正是當時世界敦煌學最大的難題。
“我們流失的,暫時回不來。但現有的也不能輕易給你看原件。”林世田說,“敦煌遺書畢竟是1000多年的歷史文物,你也看我也看,那不行。”
彼時,如林世田所言,“大家都在尋找新的途徑,怎樣既利于保護又方便學者研究。”
1993年,“敦煌遺書保護研討會”上,大英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等幾大敦煌文物收藏機構繼續探討,當時剛剛完成博士學業的魏泓(Susan Whitfield)提到了互聯網。
“那時網絡還非常年輕,沒有多少網站,也沒有多大的儲存空間,幾乎所有人都質疑,為什么要提出電子化這個方案。”IDP總負責人魏泓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
幸運的是,“每個人都希望一起在文物保護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1994年,在中英獎學金基金會的支持下,一個5年、2.5萬英鎊的IDP計劃出現,魏泓被任命為協調員。IDP旨在為世界敦煌文獻收藏機構解決藏品保護和編目,構建合作交流的平臺。各收藏機構共同建立完整的網上數據庫,目錄數據和高質量的數字化圖像相鏈接,并附有其他相關信息,使各國學者能充分利用藏品。
然而,這個“神話般的開局”面臨著諸多難題。“事實證明,難度超出想象。”魏泓說。
“為什么我們還沒有完成”
當時各藏品編目還在進行中,鮮有電子名錄,且記錄混亂。僅就英國圖書館而言,斯坦因3次遠征中國及中亞地區帶回的藏品,敦煌遺書只是其中一份。
藏語和其他語言書寫的手卷當時為其他部門管理,此外還有斯坦因在羅布泊、塔克拉瑪干沙漠或者古絲綢之路沿線發現的超過15種語言和筆記的手卷。它們保存在不同的機構,采用不同的編號和保存方式。
1994年起,魏泓著手設計數據庫,并詳細制定IDP的標準規范,細化到清晰度的要求、圖片錄入、處理過程的步驟,甚至命名規范。1998年IDP數據庫建立,首批超過2萬件手稿上傳至網絡,人們終于明白了IDP的可能。
2001年,中國國家圖書館作為第一個合作伙伴,加入IDP項目。
中國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副主任張志清回憶說,合作伊始,印象最深的就是魏泓對于“標準”的堅持。
英方為中方配以最精密的PHASEI數碼掃描設備,制作敦煌寫卷的高清晰圖像。“但是掃描出來的紙都有紙毛,顯得不漂亮。”張志清說,“按國圖以往普遍的數字化標準,這就足夠了,我照一張600DPI的,轉成300、400DPI就可以直接上傳。”
但按魏泓要求,“修圖要至少兩個小時,圖片邊緣放大,臟的地方一點點抹去,速度非常慢。”張志清說。中方提意見:“要這樣下去,IDP不知道要做多少年。”
“一些人希望能夠快點做完這件事,我們始終覺得應該考慮長遠,用高標準來要求是正確的。”魏泓說,“不過學者們通常會感到沮喪,特別是中國學者們會問為什么我們還沒有完成?”
7年時間,IDP形成“分布集成”的合作方式,在國際上每個合作機構設立服務器,負責上傳本地所藏的包括敦煌遺書在內的絲綢之路文物文獻。
對于讀者來說,在IDP網站可以“集中式”檢索,比如輸入“妙法蓮華經”,立刻會出現中、英、法等各個國家藏館的資料。
盤活了敦煌學
如林世田所言,IDP不僅是一個數字化項目,“它作為平臺,通過國際會議交流、學術講座,把整個敦煌學盤活了。”
通過IDP,交流最多的是敦煌遺書的修復問題。
“日本人過去怎么修?在敦煌遺書的背面裱褙。這也是我們館最早時候的做法,是中國傳統字畫的裝裱方式,拿一張宣紙在背后通卷托裱,更結實。”林世田介紹,“但敦煌卷子背面都是有信息的,一裱褙,查不出來了。”
西方的修復則是使用化學膠水,或者在敦煌卷子上包裹絲網,“破壞非常大,絲網很細,時間長了卷子都碎成渣。”
中國人提供了4點意見:其一,搶救為主,哪兒破補哪兒,最少的干預;其二,整舊如舊,保留原卷一切歷史信息,最好保持在現有的狀態不再改變;其三,可逆修復,避免通卷托裱,修好之后想拆隨時可以拆掉;其四,保留完整修復檔案。
國圖的敦煌遺書長約1萬米,按此原則已修復6000多米。英國人也承認自己過去的修復是一種“善意的破壞”。“國際上的學者交流,慢慢統一了修復的原則和方針。”
“當然,英國對敦煌遺書的保護也有它獨特的地方。”張志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比如,有些敦煌卷子之所以是黃色,是因為造紙過程中在黃檗水中染過。
黃檗含小檗堿(黃連素),味道極苦,蟲子不愛吃,因此染黃的敦煌卷子沒有一個蟲眼,看起來也非常漂亮。
“為此,英國人專門研究古代中國人到底如何用黃檗染黃紙,是刷的還是染的?里面的成分為什么能防蟲?針對這個問題還專門出書。他們在保護研究上很扎實,我們是該學習的。”張志清說。
IDP定期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議,也為世界敦煌學研究人員提供了交流的平臺。
在國圖召開的IDP第六次會議,大英圖書館教授吳芳思曾提供一幅收藏在該館的敦煌挎包圖,由“一層一層寫著字的厚紙粘成”。
“要研究紙上的內容,就必須揭開。但是揭開,挎包就完了。到底是保護挎包還是揭開內容?吳芳思提出了這個問題。”張志清回憶。
與會的60多位中外敦煌學專家、修復專家和圖書館員,為此爭論不已。北大歷史學系的一位教授強調:“一定要揭開,我從面兒上就能看出,這是唐代歸義軍的史料,張議潮在敦煌率兵起義,反抗吐蕃。必須看看里面是什么,太有意義了,說不定能改寫歷史。”
修復專家則認為,可以通過修復妙手,恢復歷史原貌,延長文獻壽命。
英國專家的意見是避免修復,“沒條件就這么放著,防止修復性的破壞。”

2008年11月18日,參觀者在法國巴黎的中國文化中心觀看立體復制的敦煌莫高窟第275號石窟
“這種交流很有意思,專家學者暢所欲言,對他們各自的研究領域都有發現和促進。”張志清回憶,“甚至中英雙方對到底該用什么樣的柜子、盒子來保護敦煌遺書,都要交流。”
144個楠木柜子
國圖善本部專家曾對財政部領導說,“國圖的敦煌遺書從上世紀30年代為躲避戰火運到上海秘藏起,一直在十幾個木箱中放著,不少人說英、法收藏敦煌遺書的柜子比我們好多了。”
財政部對此非常重視,“還有這事兒,要多少錢?”隨即批款350萬元用于敦煌遺書新庫房的建設,“做了144個楠木柜子,1.2萬個楠木盒子,把敦煌遺書完完整整保護起來了。國圖經過請示,還用這筆錢做了3個大葉紫檀柜子,把國圖藏的《永樂大典》也都保護起來了。英國人來看,表示贊賞。”張志清說。
在他看來,“IDP讓中英雙方更親近。”
2005年,張志清、林世田應IDP邀請赴英訪學,在參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時,意外發現了館藏7萬張有關中國的老照片,其中一張“叛軍士兵”深深震撼了張志清,照的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革命軍,打完仗,“小伙子站一排,拿著槍,大汗淋漓,特別精神。”張志清回憶。而此前國內所見的老照片,中國人大多樣貌畏葸。
新發現讓張志清激動不已。他告訴魏泓想選一些照片帶回中國展覽,魏泓欣然同意:“把這個項目也列到IDP項目中,我們除了做敦煌,還希望做中英兩國的文化交流。”
在魏泓的聯絡下,張志清和林世田在大英圖書館、英國皇家亞洲協會、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以及一些私人藏家處,挑選中國近代歷史照片500余幅。2008年,“1860—1930:英國藏中國老照片”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展出,轟動一時。
“因為敦煌,世界了解了中國。”張志清說,“而敦煌學,又把東西方學者、文化、教育、包括情感,都連接起來。”
“各自的資源不流失”
2001年中英開始IDP合作,第一個周期5年,其后得到延續。
“IDP政策好就好在不觸動你的利益。”張志清強調。
他介紹說,大英圖書館作為牽頭人,“網絡它來弄,服務器它給大家買,大家的資源存在各自的服務器里,通過數字化的方式共享。”
而關鍵在于,“各自的資源不流失。”
這和世界數字圖書館有極大不同。“美國國會圖書館也搞世界數字圖書館,每年要求我們國圖提供20部珍貴典籍,所有珍本數字化后的圖片必須提供給它,它再來組織傳上網。那就等于我的資源給它了。”張志清說,“但英國非常尊重我們的權利,學者只能用于研究,它是不能出版的。如果出版必須通過收藏方,嚴格執行,很公平。”
至于數字化后,遺散四方的珍品是否可能回歸、如何回歸,“我們會協助政府和民間團體,一如既往地努力。”張志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