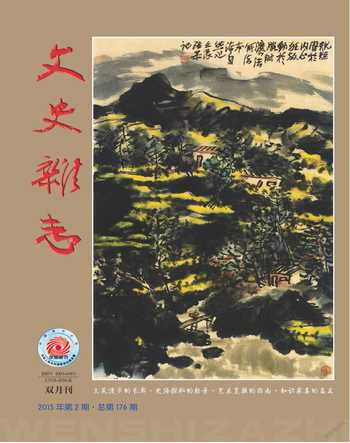中國文化人類學的先行者李安宅先生
郭一丹
李安宅先生被稱為翻譯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藏學家、思想家,其實他也是一位人類學家,被視為燕京學派社會人類學代表人物之一、華西學派人類學領軍人物。這位學貫中西、涉獵廣泛的學者更是一位中國文化人類學的先行者和開拓者。他的學術和思想在他所處的時代經世致用,利用厚生,而他本人卻淡泊名利,隨緣而器。
1900年,李安宅出生在河北遷安縣潵河橋白塔寨村,父親開設中藥堂,坐堂行醫。因其大伯膝下無子,他被過繼給了大伯。因其三叔在遵化縣任郵局局長,李安宅寄住三叔家,就讀于遵化縣立五中。1921年,因李安宅三叔調至天津郵局,李安宅也擬在郵局謀職,于是去上天津青年會夜校,一邊學習英文,一邊考取了郵務生。1923年,他以一名“選生”的身份求學于齊魯大學,選讀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比較宗教學。1924年,齊魯大學保薦 “選生”李安宅到燕京大學繼續深造。1926年春期,他獲得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服務研究班”職業結業證書并留校當助教,以工讀自給的方式一面繼續求學讀書,一面從事工作,同時也從事一些共產黨的地下工作。1929年,李安宅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正式畢業,1934年至1936年去往美國留學,回國后以所學專業知識為國家為社會服務,從事各種工作都游刃有余,取得了很大成績。歸國后,李安宅在燕京大學任教,擔任燕京社會學系講師、研究院導師,擔任英文刊物《燕京社會科學研究》和中文刊物《社會學界》主編。1941年,李安宅被聘為華西大學教授兼社會學系主任,創辦華西邊疆研究所,任副所長,組織力量積極開展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研究。1956年,李安宅調往西南民族學院,任民族問題民族政策教研室副主任,后又在學院改教英語。1962 年,李安宅調往四川師范學院擔任外語系主任兼副教務長,教授英語,之后一直供職于川師,一面教書育人,一面整理、翻譯自己的著作。在李安宅的人生軌跡中,他不僅僅是一位坐在搖椅上的書齋學者,其在治學的同時也常常以學術直接服務于社會,如在成都倡導成立石羊場社會研習站,意在使華西大學與中國鄉村建設學會合作,使學者和學生能借著服務媒介認識人群,考察具體實施結果,找出問題癥結,寫成報告以供政府參考。不僅如此,研習站還強調“服務、訓練、研究”三位一體,鼓勵師生從故紙堆中走出來,走進真實的社會,服務社會。這種理念與燕京大學的北平平郊村實驗點可謂不謀而合。
一、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1929-1934年間,李安宅過了幾年漂泊不定的生活,曾擔任過哈佛燕京社編譯員、三路河中學教師、農大社會科學講師、平民大學教授、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調查室翻譯。為了生存,他四處謀職,但從未放棄繼續求學。他師從黃子通進修康德哲學,也同英國劍橋大學的呂嘉慈教授等合作,摘譯孟子,并將呂嘉慈的著作《意義之意義》《文學批評》翻譯出版。這兩本著作即《意義學》《美學》。
李安宅在燕京大學求學及工作期間,開始致力于翻譯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兩性社會學》(即《蠻野社會里的性及抑窒》),譯稿于1928年完成,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于1929年開始翻譯馬林諾夫斯基的《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因故未能按時完成,1935年利用在美國考察祖尼文化期間,將譯稿全盤續完,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兩部譯著對中國文化人類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李安宅還翻譯了卡爾·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即《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引論》第五編,介紹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希望能對中國建設社會史、社會思想史有所助益。此外,他還編寫了《語言底魔力》(北平聯友社,1931年),翻譯出版《美學》(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編譯出版 《巫術與語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巫術與語言》可以說是李安宅對語言學進行譯介的綜合成果,書中第一章“巫術底分析”是根據弗雷澤的論文《交感巫術》編寫,參考了弗氏《金枝》的框架,闡述了人類社會的巫術習俗因由、種類和地位。第二章“語言底魔力”是根據馬林諾夫斯基、呂嘉慈和奧格登等學者的觀點編寫,闡述語言文字在人類社會中被賦予的魔力現象及其在生活中具體的體現,從而產生語言禁忌等現象。第三章“語言的綜合觀”是薩丕爾《論語言》一文的中文譯文,從語言學理論的角度闡述語言在使用中的現象、成因、語言與文化的關系、語言歷史的變遷以及語言與國家政治間的關系,等等。《巫術與語言》是國內較早關注語言的社會層面的專著,涵蓋了語言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引發人們對語言與文化、語言與思想之關聯的濃厚興趣,啟發人們對語言本身就是人類文化組成部分之命題的思考,具有重大的學術開拓價值。
二、功能主義人類學的傳播者
1936年,李安宅從美國留學歸來,學術關注點從語言學的編譯轉向了人類學和社會學。功能學派人類學對李安宅影響至深。早在他翻譯馬林諾夫斯基的《兩性社會學》時,他就說“人類學所關心的比較,不但中國本身人群眾多,文化復雜,是極豐富的園地;而且中國已成了各文化底聚會地,在這里考察文化接觸的現象,適應的過程,變遷的轍跡,推陳出新的可能在在都是啟發……人類學所關心的功能,在中國這樣處處需要重新估價的時候,正是要問功能所在,而用不著徒事中外新舊等空名之爭辯”。他認為,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實用的,能將社會現象放入整個生活系統里面,看看具有什么作用功能,而非是一堆毫無相干的流水賬式的散碎紀錄。這種研究方法對于當時中國的學術研究有著相當的積極意義。中國是個嚴格的父權社會,在上個世紀早期的中國,傳統家庭模式正在發生轉變的時代,亟有必要介紹功能主義人類學理論。
此外,李安宅推崇功能主義人類學,主要在于它的實地研究(田野調查)方法。他在翻譯馬氏的《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時曾直言不諱說,譯介這部著述是因為它在實地工作經驗方面對中國社會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因為這本書是在直接提倡(實地工作)這種方法。若在西洋的學術界已是大聲疾呼,在素來不重實學、不重實地經驗的中國,更有加緊提倡的必要。”[1]他認為,中國學界吃了中外兩種八股文的虧,是為說話而說話,為書本而書本,“并不曾針對了實在界加以直接體驗的工作而有所對策,所以充滿了腦筋與筆墨的只有不自覺的二手貨,而無為創作力量的頭手貨罷了。”[2]而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方法,可以使人立刻分出遠近布景、增添一種新的眼光,從而養成一種“透視力”;人類學的嚴格訓練教會我們做實地研究、實地工作,因此,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正是針對八股文習氣所下的“頂門針”。李安宅非常推崇著者馬氏那種借助人類學研究方法來觀照自身文化、心理的觀點,因此,他認定了人類學是切乎國情的學術,是中國所需要的學術。在譯者序中,他還非常詳細地介紹了人類學的理論淵源和發展狀況,以及人類學的用途、研究對象與人類學可能會為中國所作出的貢獻,等等,為國內讀者介紹這些“人類學的前鋒思想與成績”。李對馬氏人類學理論不遺余力地進行譯介,使得功能學派人類學在早期中國得以傳播,為國內讀者了解西學、觀照中國社會做出了極大貢獻。
李安宅不僅對馬氏的學術理論、生平、學術經歷、語言天才、對弗洛依德心理分析理論的借鑒等都加以細致的推介,關鍵之處還在于他還加以自己的理解與創造性修正。例如,馬林諾夫斯基的原著書名本為《蠻野社會里的性及抑窒》,但經過研讀原著,李安宅發現此書其實是對于蠻野社會的性和文明社會的性的比較研究,著者馬林諾夫斯基自己在第一編的第五章也說道:“我與傅羅易德及旁的心靈分析家的研究領域是一個,不過我是將性的題目分別處置,以便加重社會學的方面,且以避免母子依戀或‘立別度’(libido,以性欲為人生活動的基本動力)底性質如何這樣聚訟理論的分別。”(libido即現在所說的性力、性欲或本能沖動)因此,譯者李安宅將譯本名字修正為《兩性社會學》,這樣顯得更為正確嚴謹,避免讓讀者望文生義,以為是一本偏枯專門的著作,因此“不合于一般讀者”。可見,對于原著他是真正弄懂了,消化了,并站在中國普通讀者的立場,為中西文化思想的真正交流與溝通默默做出自己的努力。
三、以“禮”為中心的人類學家
李安宅最初的成名之作為《〈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充分展示了他對于“內證的”“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探索、研究能力及他對于國粹主義的批判態度。當然,李安宅自己還在對人類學的初期摸索中,因此那時還較少采用“人類學”而是“社會學”的說法。他指出“本文下手的方法,完全是客觀地將《儀禮》和《禮記》這兩部書用社會學的眼光檢討一下,看看有多少社會學的成分。換句話說,就是將這兩部書堪稱已有社會的產物,分析它所用以影響其他的社會現象(人的行動)者,是哪幾方面”[3]。李安宅所關心的是兩書內容的整個實體而非細節細目的排比,他無意作更多的章句考證。在他的眼中,學術研究的社會價值比純粹的紙上蒼生更有價值。因此,從一開始,他就沒打算作一篇遠離社會的晦澀之作,而是希望能將兩書這一文化“由著圣人的天啟,降到社會的產物”[4],努力剝去文化試圖對社會大眾保持的神秘性。他認為禮教是社會的產物;關于禮教的書籍,也同樣是社會的產物,所以一切關于禮教和禮書的神秘性都可凈出。
我們也看到,李安宅的確剝去了兩書的神秘性,但并沒有剝去它們的社會價值。他通過對禮的本質、禮的功用、禮的理論、禮與語言、物質文化、樂、知識、宗教、社會組織、政治的關系與影響,條分縷析地剝離出禮的實質,視野宏闊而不失精深,洞察細微,把握要害。他對抱殘守缺、食古不化進行了批駁:“現代的國粹家活在現代,死不肯脫去古時的殼,硬要將死殼加在活人身上,那就未免缺德,所以我免不了要辭而辟之。”他在用自己的“學”努力引導社會的“術”——對此遺業“消極防阻禍害”與“積極增進福利”的方面進行批判性繼承。
李安宅在禮的本質中就鮮明地表達了他對“禮”的人類學解讀。《檀弓下》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李安宅認為直情就是天然狀態(state of nature),而禮道是用人為品節的功夫,這其實和人類學家將天然加上人為就等于文化的理念是毫無二致的。他在書中說明禮的本質、功用(后來所說的功能)、行禮的資籍和禮的理論。他指出禮的本質就是源于人情的文化,以人情為本,以節儀為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但時異勢變,禮有不合者是可以改變的,原來所缺乏的也是可以創造的。而禮的功用是可以積極增進福利的,有消極防阻禍害的,也有為客觀之測量標準的。禮可以使人別禽獸、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成就政治家的勢力;也可由禮而知人識人。禮還可以防敗,意思是以節文養成習慣,作為預防,不能任由性情而為,因此,“禮”正是文化之有別于人的本能的地方。而禮的積極功用的大端在于講信修睦、養生送死事鬼神等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使人們外諧而無內怨,等等。李安宅談到“禮儀”的時候,很注重層次性,注重中庸核心思想的呈現。人類學家認為,“中庸”就是介于“野蠻”與“文明”的中間狀態,而李安宅把握了這種要義。從他在書中提到禮儀的詩學態度、白日夢與宗教的關系。他對禮儀的等級、交換、道義以強調,并不排斥禮起源于原始的互惠交換模式,認為“道義”則與人類學之交換理論中的“obligation”異曲同工,同樣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互依共存。總之,在人類學家的眼中,《〈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一書就像一本以禮為中心的人類學導論,是中國人類學以西方人類學理論觀照、修正、解釋與融合中華文明的人類學中國本土化的最早實踐。[5]人類學家對此書的人類學解讀與詮釋的確具有獨特的眼光與視角。
四、印第安祖尼人銘記的人類學家
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祖尼小鎮的博物館和遺產中心,在“研究過祖尼人的人類學家”的殿堂中,李安宅赫然在列。他之所以被美國祖尼人銘記,不僅僅因為他是一位來自東方的“他者”,而更因為他恰如其分的“文化主位”視角的貼切運用——他不滿足于前人文獻的敘述,而是在結合文獻與田野的基礎上進行再思考。
人類學家極力推崇田野工作方法,認為研究者不能過多地坐在屋子里夸夸其談,而是應該走進廣袤的田野,走進歷史現場,必須自己親自去考察,否則無法核對其真實性。李安宅踏入田野以前,也曾讀過人類學家對祖尼人的相關論著。同拉德克里夫·布朗一樣,李安宅也不迷信前人的文獻,經過了3個月身歷其境的觀察,他采用了“文化相對論”的理解與詮釋,得出了與美國人類學家不同的結論。在祖尼人研究的過程中,參與觀察、深入訪談、社區研究、跨文化比較等基本的人類學方法他幾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實踐。
1934年至1936年,李安宅先后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耶魯大學人類學系學習,參與新墨西哥州祖尼人的社會調查,撰寫《關于祖尼人的一些觀察和探討》。他以一個進行田野訓練的學生身份對美國人類學家提出質疑與商榷。他的不揣冒昧和鋒芒銳氣,他的扎實研究功底使其很快脫穎而出,引起美國人類學界的矚目。因為,在他的田野工作中有一種深深的民族情結,這種情結就是了解別的民族的智慧,以此來教導自己的民族。我們不難看出李安宅的學術品格與人文關懷。
通過田野觀察,他實事求是地指出祖尼社會宗教的功能:“在于它乃是一種生存斗爭的手段。宗教活動不僅是要用來對付未知世界,而且也要左右著世俗世界的各種活動。”[6]他進一步舉例說明,祖尼人宗教性的戲劇舞蹈的社會功能不僅僅主要用于祈雨祈雪,也發揮著社會協調力的功能。在這里,我們不難看到馬林諾夫斯基功能學派人類學理論對他的啟發與影響。
在對祖尼婦女與不固定的丈夫的關系的觀察與探討中,他得出了“真正重要的是婦女根本不受男人控制……處于一種不受壓制的地位上”[7]的結論,并從中觀照出中國婦女的的困境。在李安宅這位中國早期的人類學家眼中,這種生活其實只是一種值得理解的共棲生活,是一種人類生活而已,完全沒必要視為洪水猛獸。李安宅之所以能沖破三從四德、三貞九烈等中國傳統文化觀念,而產生出這樣的同情之理解,正是人類學的他者觀為他奠定了必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對祖尼人害怕成為“自己人民的領袖”是因為擔心成為“被指控為行使巫術而遭受迫害”或“個人興趣”的觀點,李安宅則直陳己見,指出其錯誤之處關鍵在于“套用本族文化法則進行推理”。李安宅對充滿了競爭的西方世界進行了激烈的批評,稱人民從小就接受這樣的教育——世界是造來給他剝削的,如他不沖在前頭,就將被拋在后面;但是別的社會卻認為,人們互相予取更加和諧,人要盡可能地謙恭,同時又具備很高的區別對待不同事物和辨識價值的能力,只要是他獲得首領地位的方式和手段是合理的,就能被人們安然接受。既然是這樣,那沒有人會再去做一些無謂的爭權奪利的事情——不僅徒勞無功,反而為自己增添更多笑料而已。在李安宅的“他者”眼光中,祖尼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是值得學習的。在殖民主義思潮仍盛行的上個世紀30年代,李安宅這樣的人類學見識與眼光是具有前瞻性和學術勇氣的。
五、藏族地區人類學研究的先行者
《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一書是李安宅教授在藏學研究上累年辛勤耕耘的結晶,是國內外公認為通過實地考察和對文獻資料的研究而撰寫的有關藏族宗教史的首部杰作。他對藏傳佛教文化研究的那份執著、投入與熱情感動著人們,因此被稱為佛教密宗的“在家人”。
上個世紀30年代,為了抗戰建國,為了擺脫在北平的艱難處境(李氏夫婦拒絕為日本文化機構服務),李安宅夫婦來到邊疆進行調查研究。在李安宅看來,要溝通漢藏文化,必須研究喇嘛教。西洋傳教士利用漢藏互不了解的情況,常常挑撥離間,伺機制造事端,因此極有必要對藏族宗教進行研究,發表文字,溝通漢藏文化,借以抵制別有用心的造謠。在眾多的研究者中,李安宅先生應該是一位以“他者”眼光最細致入微的觀察者和研究者。他運用功能主義的研究方法、對宗教與社會關系的深刻揭示,嚴謹的治學態度等備受關注。學界對他的藏族人類學研究評價極高。李安宅對拉卜楞人民的觀察很接地氣。他的有關記述為內地了解西北邊疆打開了一扇視野開闊的落地窗。他的“文化相對論”、他對“邊民”的了解之同情的人類學視角,在當時中國的學術語境中具有開拓之功。
例如,他對天葬那種“處之自然”過程細致入微的描述,他本人對這種“獻給旁的生物”葬俗冷靜理性的觀察、描寫與理解讓人充滿敬佩;他對藏族人民宗教給予人們的“內在的價值”,如“人不完全靠吃飯生活”、因“對于人類生活的價值衡量”高而“不能容忍死刑”,認為“自做的,必要自贖”、不會享受“對于靈性發展以外不必要的東西”、“欣賞他們的簡單生活”、“滿足于享受生活”、“性格好、喜歡音樂、敢于冒險”……[8]的觀察總結以及理解與同情更讓人敬佩。這種在認識論和社會文化的相對論在當時的中國非常前沿,非常難能可貴。他對佛教以前的信仰和早期佛教本教(黑教)、寧瑪派(紅教)、薩迦派(花教)、噶舉派(白教)、格魯派(黃教)以及格魯派寺院拉卜楞寺都進行了系統詳實的研究,對拉卜楞和它的施主、寺院組織、主要神佛、訓練和課程、公開聚會及拉卜楞人民進行了多維視角的觀察與詳細調查。李安宅的藏族宗教研究是詳細而系統的,既有歷史的維度,更有現實的觀照。他對藏區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正是典型的人類學研究范式,為中國文化人類學豎起了早期的學術標桿。
李安宅先生一生坎坷,屬于他的學術光陰并不夠多。他的學術成就也一度被忽視。學界紛紛為他鳴不平。“以往有關中國人類學史的著作,較多關注的是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等學者,而同樣出自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并取得重要學術成就的李安宅卻較少被提及。”[9]通過對李安宅先生的人生經歷的簡單回顧,可以說從純學術的角度來看,這位以郵務生半路出家的“選生”不是一位皓首窮經之鴻儒,但是我們可以從這位齊魯大學選生、燕京大學選生、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進修生、耶魯大學的進修生的身上看到一種淡泊名利然而卻鍥而不舍的科學精神。他并非為了學術而學術,更非為了個人成名成家而追求學術。他堅持從事以“學”愛國,以“術”救國的信念支撐他踏上了這條艱辛的道路。我們不難從他對“禮”的研究、對西方著述的譯介到對拉卜楞的研究,從燕京大學到華西壩,從學術研究到邊疆研究、服務、宣傳(或訓練)“三位一體”的社會服務中看到他的“學”與“術”的自由切換軌跡。他的“學”比一般書齋學者具有更加豐富厚重的生命體驗和社會底蘊,他的“術”又比普通社會工作者具有更多理論探索的學術背景和文化底蘊。
注釋:
[1][2][英]馬林諾夫斯基著,李安宅譯,《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M],中國民間文化出版社,1986年,P.3,P.1。
[3][4]李安宅,《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P.1,P.1。
[5]參見陳波,《李安宅與華西學派人類學》,巴蜀書社,2012年。
[6][7]李安宅,《〈儀禮〉與〈禮儀〉之社會學的研究》附錄一:《關于祖尼人的一些觀察和探討》,[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P.82,P.94。
[8]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1989年,P.228。
[9]齊釗,《個人心史與學派歷史勾連的困境與張力——評〈李安宅與華西學派人類學〉》,[J],《民俗研究》,2013,1。
作者單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