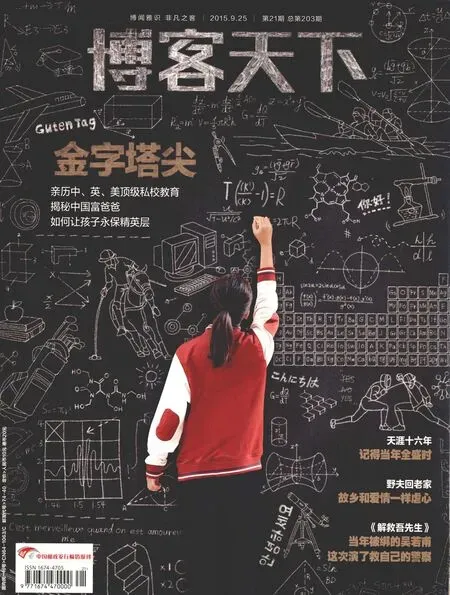李泉:所有的不自然都無法通往自由
文 李冬梅 圖 尹夕遠
李泉:所有的不自然都無法通往自由
文 李冬梅 圖 尹夕遠
年少時痛苦的練琴經歷,對名利的追逐不時成為李泉的噩夢,為了自由,他選擇了流行音樂
當李泉彈鋼琴唱歌時,十指好像要將琴鍵擊碎,表情和肢體語言瞬間豐富起來。忽而怒目圓睜,忽而仰天沉醉,上一刻還在調皮嬉笑,下一刻就深情款款,黯然神傷。如果鋼琴有一張臉,那么,它的表情就時刻顯現在這位彈琴者的臉上。
即使在《蒙面歌王》的舞臺上,藏在漆黑的蝙蝠俠面具后面,他那雙寫滿表情的眼睛還是有著很高的辨識度。有人告訴他,面具可以遮住你的臉,卻遮不住你的演奏和演唱。李泉解釋說,他知道自己怒目圓睜的樣子“不太好看”,但那完全是一種自然流露。“可能是因為我小時候太壓抑,最后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
“我今天真的沒有任何悲喜,比賽只是個游戲。”在這檔音樂真人秀節目中,李泉在第四輪即告失敗,還沉浸在被他演繹得驚心動魄的《草帽歌》中的猜評團剛剛擦干淚水,一臉驚愕。“他的能力真的凌駕于我們之上”,他的“對手”“流浪者”說。
選擇摘下面具的李泉,面對失敗,眼里只有平靜和羞澀。“可惜了,可惜了”,人們在社交網絡上評論,可惜的并非是李泉的過早離場,而是他的“不紅”。
46歲的李泉早已過了對“不紅”耿耿于懷的年紀,“想去別人玩兒的地方玩一下而已”,他這樣解釋自己近兩年來出現在幾檔電視音樂選秀節目上的原因。“我在玩我自己的東西,根本沒想過要當第一名。玩音樂就要把音樂玩得特別瀟灑。別人可以玩你的音樂,玩名次,但你不能在心里跟他們玩同一種東西。你們都在玩,但玩的東西一定是不一樣的。”

自由
14歲的李泉呆坐在劇場舞臺上的那臺鋼琴前,汗如雨注。臺下的老師和同學們等待著巴赫的《意大利協奏曲》第二樂章在他的十指間奏響。這是李泉人生中第一場個人音樂會。計劃90分鐘的演奏,已經順利進行了一半。長達15分鐘的《意大利協奏曲》是老師幫他挑的,光譜子他就背了一年半,此時,曲譜卻從他頭腦中不翼而飛,臺下的老師同學面面相覷,觀眾議論紛紛。過了一會,李泉猛然站起身,奪門而逃。
“巴赫,我恨他入骨。”李泉回憶說,這個噩夢仍陰魂不散。在夢中,他是一個拼命回想著自己在即將開始的比賽中要彈奏的曲目卻頭腦空空的少年,醒來時,往往滿身冷汗。“怎么想都想不起來(曲譜)了。”又一次被這個噩夢驚醒后,李泉才想起自己已經很久沒有比賽過了。
李泉曾經是中國千千萬萬個“少年琴童”之一,被下放到貴州山區的父母把4歲的李泉“過繼給了鋼琴”,這是兒子的戶口留在上海的唯一希望。從8歲到大學畢業,李泉是在大大小小的鋼琴比賽中度過的,除了鋼琴,“不知世間尚有他物”。
每到上海進入寒冬,僵直的十指觸到冰冷的琴鍵,李泉回憶練琴之苦,“幾乎每一個指尖,因為開裂都包裹著厚厚一層膠布,而考試演奏會時為了觸鍵敏感又必須取下,害得我們每個人上臺演奏前都要先擦拭前一位在琴鍵上留下的血跡。”在過關斬將進了音樂學院,他每天練琴至少四個小時,最高榮譽拿過亞洲鋼琴比賽的大獎,但這樣的成績在強手如云的音樂附中只排末尾,因為其他同學會練七八個小時的鋼琴。“我從小就生活在功利中”,他痛恨無休止的比賽、競爭,因為這些是“是非常不人性的東西”。
“我是為了想要自由才想要唱歌的。”坐在自己制作公司的辦公室里,李泉將雙手輕輕地搭在沙發上,窗外是一片開闊的高爾夫球場。他回憶起當年決定進入流行音樂這行時,沒有選秀節目,沒有《我是歌手》,中國的音樂產業也不甚發達,唱歌、寫歌看上去并不能成為職業。“練琴太苦了。”所以,流行音樂拯救了他,歐美、港臺、爵士、搖滾、電子、流行……他甘之如飴。
他開始自己寫歌,唱歌。“每天在練琴的時候偷偷彈唱十分鐘自己喜歡的歌,找三五同學圍繞聆聽,是一件無限愜意的事。年級舞會,大家高潮之時,我唱著自己寫的歌,看著大家相擁簇簇,便是我無限滿足之時。”
流行音樂成為他的“一個新的出口”。“我就覺得,哇,在這個出口里面,還有些音樂是那么真實的!這比我們從小練的辛辛苦苦去比賽,要真實得多。”
“古典音樂的叛徒”,老師和家長這樣定義他。與父親的關系也劍拔弩張。李泉回憶,雖然父親經常在外地,卻經常回家檢查他的功課成績,“不行,就揍一頓”。最讓他不能接受的是,有一次,父親竟然從貴州回到上海,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偷偷跟蹤了他兩天,為的是看他“有沒有好好練琴”。結果,又是一頓暴揍。
“突然有一天,我覺得我這種生活沒法過了。”18歲的寒假,又一次與父親發生沖突后,李泉“突然就不行了”,“在那之前,我是一個在學校可以干壞事但是在大人面前絕對服從的人,但那天我就突然一下不行了。”趁父親下樓買東西的空暇,他跑了出去,“大衣也沒穿”,在通宵電影院和街心公園睡了四天后,他投奔了一個自己也不認識的同學,與家庭徹底決裂。
那一年,父母按計劃移民美國,他拒絕同往。此后八年再沒有跟父親聯系。“我前半輩子都是被強迫的。但就從那天開始,所有的世界都改變了,所有的生活都是我自己選擇的。”
真實
“我做唱片的初衷就是‘真實’。我做第一張唱片,一開始,我不管別人喜歡不喜歡。我是因為要真實才選擇這個行業的。”李泉告訴《博客天下》,1993年,還在讀大學二年級的他與魔巖唱片的張培仁簽約,“就想要自己做樂隊自己寫寫歌”。
1992年,作為魔巖文化創始人之一的張培仁,將產業化的制造法則帶入“一無所有”的內地,成功締造了“中國火”、“唐朝”和“魔巖三杰”的搖滾神話。1994年,他以“中國搖滾新勢力”之名,讓內地的地下搖滾歌手像流行明星一樣站在了紅磡舞臺上。“我那時候的革命情懷是很重的。我說革命情懷一點都不夸張,我身邊那幾個人包括張培仁,我們是要來這個音樂里面革命的。就是要革那些我們討厭的假大空的命,就是要做真的東西。我們是熱血的。”李泉回憶那時呼喚英雄的樂壇,每個人身上的理想主義都被點燃了。
除了“中國火”,魔巖還有一個“中國海”計劃,簽約對象是上海的何訓田、丁薇、李泉。然而1995年,魔巖突然從大陸“戰略性撤退”,沒有留下任何交代便不辭而別。留下了“何勇瘋了,竇唯成仙了,張楚‘死’了”的江湖傳說,還留下了一個茫然的李泉,“(魔巖在大陸的)整個四年我們這些人情感都是投入在里面的。我在魔巖出了兩張唱片,幾乎沒怎么發行,也沒有做過什么宣傳……我當時是不接受的。我比他們(魔巖三杰)更氣憤,至少他們火了一把,我什么都沒有。”那時的李泉留著長發,長身玉立,器宇軒昂,夢想成為像Sting、Queen那樣的巨星,把“所有人都愛自己”視作理所當然。
好好做音樂就行了。我們那代音樂人,心態要非常平和才行。他把自己定位于一個行業里的“老工匠”、“老師傅”
帶著疑惑和失落,帶著滾石時代留下的理想主義烙印,李泉一邊稀里糊涂了答應了系主任留校任教的邀請,成為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一邊繼續與何訓田、朱哲琴們做著小眾音樂,也幫范曉萱寫了《我要我們在一起》《哭了》這樣的流行爵士歌曲。
1999年,李泉去臺灣時,跟張培仁在酒吧偶遇,“他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李泉說著,大笑起來,“這段尷尬的經歷過去了。沒有什么過不去的坎兒。”他至今與張培仁仍然保持著不錯的關系,“我的明星夢曾經做過兩次。當然,第一次其實是英雄夢。”
第二次明星夢是簽約BMG后,李泉覺得自己終于邁入主流唱片業,他雄心勃勃。《走鋼索的人》讓他在港臺一舉成名,公司為他量身制定“明星計劃”:新加坡、臺灣、香港、內地……未來看似一片坦途,“明星夢又開始膨脹了。”然而命運再次踩滅了他對聲名的渴望。2000年,正準備大舉進軍亞洲市場的時候,臺灣民進黨上臺,規定只要是有大陸背景的藝人都不準在臺灣表演。這個規定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里沒有更改過,“從那年開始我就不做明星夢了,因為我不是這個命。”
現在,在被問及命運的可能性時,他半真半假地笑著說,“如果不是2000年民進黨上臺的話,可能我也會變成一個明星,寫著更流行的歌”,像汪峰,像周杰倫。
平和
現在,李泉慢慢走向了真正的平靜。“好好做音樂就行了。我們那代音樂人,心態要非常平和才行。你有什么作用,就起一點。哪怕很小,起一點就行。”他把自己定位于一個行業里的“老工匠”、“老師傅”。
“我是一個特別膈應的人。”李泉對《博客天下》說,以前的自己不接受媒體采訪,30歲前“連談戀愛都不說話”,到臺灣某電臺宣傳《走鋼索的人》,每次DJ問他要放哪首歌,他都要說:我現在覺得這張唱片真的做得不太好,可不可以不要放歌?有人勸他,你這首歌如果這樣寫,也許別人更容易接受,他說:“我如果這樣寫,會覺得我沒穿褲子。我是習慣穿褲子的。”不被理解,他暗自感嘆:“聽過好的,嘗過好的,可能就是一種悲哀吧。”
內地流行音樂的黃金十年終結于1996年。隨著唱片業的急速衰落,音樂成了一門最不值錢的藝術,用李泉的話說就是,“都快成要飯的了”。
“再往下走就堅持不下去了,就要妥協了。我不要把自己的理想徹底撒一地。”
2005年,做完《劃火柴的女孩》后,他決定徹底放棄歌手身份,“用其他方式去堅持”。他先后創辦了音樂學校“泉音堂”和音樂公司MBOX,“泉音堂”成立的第一年,他幾乎賠光了自己做音樂時攢下的所有積蓄。
“開始是我跟兩個同學,還有幾個工作人員,什么都是我們自己:教課、寫教材、彈曲子。頭一年半,每天都在學校。我編了趣味性的教材,想讓一個小孩一周就學會一首歌,一年會彈三四十首他自己喜歡的流行音樂。他們不需要去彈那么多枯燥的東西。”這個實驗最終敗給了沉疴宿疾的教育體制,直到李泉做出妥協,聘用專業的校長和管理團隊,“也幫小孩考級”,才剛好能自負盈虧。
2014年6月的一天,正在跟李泉一起錄唱片的李榮浩接到了電話,通知他獲得臺灣金曲獎最佳新人獎,兩人沒反應過來,“莫名其妙”,五味雜陳。少有人知,十年前,李榮浩曾經是李泉與朋友合資開辦的音樂公司MBOX旗下藝人,他看好李榮浩的才華,送他參加唱歌比賽,想給他出唱片。然而公司其他股東卻毫無信心:誰會喜歡這樣的音樂呢?大家更不知道如何操作李榮浩。
這正是轉型成為經營者的李泉的矛盾,一方面,他內心始終放不下音樂人的標準,另一方面,市場瞬息萬變,音樂產業像流水線工廠,在不斷復制相似的產品的標準下,沒有人愿意冒險嘗試新的事情,也沒人愿意“花時間慢慢做”,他還簽趙薇做過歌手,“因為她的演出和銷量是絕對有保證的。”他想要讓趙薇的粉絲“通過她去欣賞這些作品,然后慢慢改變聽音樂的結構”。
什么樣的想法都有過,什么樣的糾結都有過,什么樣的實驗都做過。李泉說,他不能說是一個所有實驗都做完的人,但的確想過很多東西去改變音樂市場。
2012年,在李泉放棄做歌手的第七年,他決定回來了,做一張沒有任何商業考量的唱片:《天才與塵埃》。唱片是自己掏錢出的,做了兩年多,頭一年已經錄好,他不滿意,重新找了團隊,重新編曲,重新寫歌,反復的打磨讓他幾乎彈盡糧絕,收尾時,為了省錢,他住進了蘇黎世一家沒有獨立衛生間的旅館。
到了巡演,為演出做市場推廣的甚至不是專門的演出公司,臺下坐的都是朋友,臺北、北京、上海,三場演唱會,“如果純粹靠票房的話,那會很慘”,雖然演出沒有掙到一分錢,但他感到了久違的松弛,“那三場音樂會對我特別重要。”他想好了,自己就想做一個反規矩的事兒。“行業已經沒落成這個樣子,在這個行業中你即便順從了規矩,也是半死不活的,你還不如堅持做自己。”
“我們從小是因為追求自由才玩的音樂,后來自由變成套在身上的枷鎖了。你作為這個時代的人,這個時代就這樣了,那你怎么辦?成天躲在家里發神經?”他想通了,希望自己能活得“自然一點”。他在微博里寫:“所有的不自然都無法通往自由,就像所有的不寬容都無法通往愛。”
“終于明白我不是天才,也不是塵埃。”那一年的北京演唱會,他在臺上唱,臺下的父親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了他做的音樂。
責任
時間仿佛并不存在。和幾十年前一樣,李泉如今依然孤身一人,和幾十年前一樣,他在上海的家依然是理想主義者的音樂據點。“我的同事朋友都知道,我家永遠都是有人的,即使我不在家的時候,也可能是有人的”。他告訴《博客天下》,自己喜歡跟有才華的人在一起,互相激勵,也激發靈感,“一塊兒搞音樂的朋友,是我的哥們兒,已經成為我的生活了。”
這些有才華的人中,有他學院時代的目空一切的鋼琴兄弟聶鈞,大學里終日與他排練、“聊著看不到明天的理想”的樂隊哥們兒安棟,也有被他帶到《蒙面歌王》的返場舞臺上的電音才子B6。
鋼琴和電子,也正是他在“裂變”路上的兩個方向,兩個不同的無法調和的李泉。
十幾年前那個發誓要“用自己的才能打動世界”的少年,如今只想要用音樂“跟世界聊聊天”。
2014年,他又出了一張唱片,《再見,憂傷》,“可能這將是我最沒有企圖心的唱片”,他的標準是自己覺得好聽即可。“記得小時候寫歌,就好像是要把自己燉得噴香的大醬湯倒出來給大家喝的感覺,因為那時外面好清新,內心很沸騰。現在滿街聞著都是味精好喝的大醬湯,心里反沉到安靜,倒要好好燉出一鍋鍋自己的味道來了。”
成為玩家的李泉享受著他的自由,開始頻頻出現在上海爵士音樂節和搖滾音樂節等現場演出的舞臺上,他戴著大號熒光潛水鏡與B6玩電子樂;他去內蒙古采風,去貴州做與民族音樂有關的音樂劇;跟建筑師朋友合作聲音建筑展,在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跟導演張元合作,拍攝音樂微電影《艷遇》。
另一方面,他仍然放不下學院派的“責任感”。要求自己“即使上電視,哪怕只有幾分鐘的表演,也要拿出以前在錄音室的態度來進行表演。”《蒙面歌王》的舞臺上,他選歌的標準是“值得傳承”和“有價值”。“音樂首先是個行業。一個行業是怎么傳承的呢?不是因為別人喜不喜歡你來傳承的,而是你真正的內涵,真正的技術,真正的對這個行業追求的體現。一個藝人也好,一個藝術家也好,他應該把自己最誠懇、最經過磨練的東西拿出來,而不是像商人那樣去斤斤計較別人的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