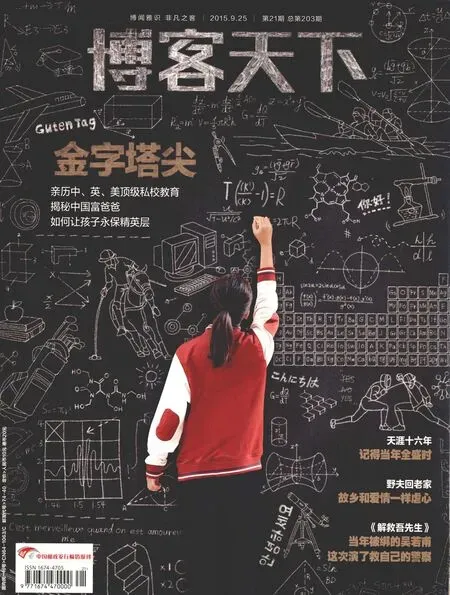桃花源記
文 Alex Halberstadt 譯 蕭東兮
桃花源記
文 Alex Halberstadt 譯 蕭東兮
為了躲避挑釁的目光與公然的歧視,一群同性戀者躲進了大山里的叢林,建造了屬于自己的“世外桃源”
幾年前,美國田納西州環境保護部門的動物學家大衛·威瑟斯(David Withers)在迪卡爾布縣(DeKalb County)附近溪流的河床間研究小龍蝦時,意外發現了一條沒有標記的路。那本是無人問津的地方,至于這條路就更沒留意過。可是那一天,他打算一探究竟,于是開著卡車前行,很快他就置身于一片奇怪的營地之中。
威瑟斯下了車。周圍的幾棟房子就像無法辨認的野生菌類一樣,東倒西歪地散落著。引起他注意的是附近一個牲口棚,一側刷著巨大的黃色字母“歡迎回家”(Welcome Home)。出于好奇,他走向一棟看似有人居住的簡陋小屋,抬手敲門。
前來應答的女人看起來滿臉驚訝。她告訴威瑟斯,他闖入了同性戀公社,并禮貌地請他離開。晚些時候,威瑟斯給他的朋友,附近卡儂縣(Cannon County)的藝術中心總監、公開出柜的尼爾·阿佩爾鮑姆(Neal Appelbaum)打電話講了自己的見聞。阿佩爾鮑姆一點也不意外,告訴他那個地方叫艾達(Ida),住著十幾位LGBTQ人士(編者注:指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及酷兒Queer,也是同性戀者的意思),而牲口棚上的字母并非“歡迎回家”,最后一個字母是“o”,不是“e”—“歡迎同性戀者”(Welcome Homo)。
如果你是LGBTQ,但年紀不超過35歲,想必不太會有和整個社會格格不入的記憶。更早一些,同性戀們的社交活動只是主要集中在幾個大型沿海城市,小心躲避著公眾視線。酒吧、餐廳、海灘度假屋、偏遠的社區,成了他們的“避難所”。人們彼此心照不宣,大部分時候不會遭遇挑釁的目光與公然的歧視。生活在這些社區的年輕人常常將對方視作家人,因為大部分人早就脫離自己的原生家庭。但對個別人來說,這種逃避式的生活顯然遠遠不夠,不斷地掩飾、偽裝,就像是給出了讓別人定義自己生活的通行證。于是,這類人漸漸選擇遠離城市,尋找不用對自己身份認同做出過多妥協的庇護所。
1979年,同性戀權利活動家、共產主義分子,來自洛杉磯的哈里·黑(Harry Hay),熱切地向同性戀群體喊話—“拋棄那層模仿異性戀者的丑陋的綠色青蛙皮吧”。同時,他也是 “激進的精靈”(Radical Faeries)這場反主流文化運動的創辦人。跟提倡同性戀者要與異性戀者享有同等權利不同—比如可以結婚或者領養小孩,“激進的精靈”推崇的是同性戀者擁有獨特天性,有著與異性戀者不同的使命。正是這種使命感,將他們帶往美國的鄉村,并逐步匯集、聚居下來,邊遠地區的定居點是這些“精靈”們的“圣殿”。如今地球的三塊大陸上,松散地分布著十幾個類似的被奉為“圣殿”的地方,但在哈里發出呼喊的那一年,“精靈”們的處女航剛剛抵達中田納西的制高點之一—肖特山(Short Mountain)。直至今日,那里依舊是美國規模最大,歷時最久,最負盛名,并吸引最多人造訪的同性戀及跨性別戀者的家園。
從房屋建造的樣式,放養的山羊和種植的菜園看,這里就跟課本上的公社沒什么兩樣。可不用太多時間,你會發覺那里有個地方被命名為“變性脊”(Sex Change Ridge),而爬山道的名字是“另類搖滾”(Fruit Loop),有辦事員稱自己是“女皇”(Empress)—事實上,居民都按各自的喜好取了新名字。每隔兩年,還會有一次歷時約一周的集會。

肖特山的一對伴侶
同性戀者主要還是住在相對偏遠的地方,且大多選擇遠離政治,而卡儂縣的人則對政治抱有某種天生的狂熱
在被開拓為定居點的數十年間,來自各地的人們在這里相聚又別離。盡管不時有人搬去附近不計其數的衛星村,但仍把這里當作第二個家,享受著它私密的氛圍。這里的存在談不上是個秘密,只要你在搜索引擎里敲進幾個關鍵詞不用費勁就能找到。不過,“占領華爾街”運動之后,這里的人們出于對個人身份曝光的擔憂,很多與我交談過的人都拒絕透露真實姓名。這么一來,我想就簡單地把這里叫作“公社”吧。
卡儂縣的每個人都知道公社。在過去36年間,大家相安無事,幾乎沒有發生過搗毀財物,扎破輪胎,或者用噴霧書寫謾罵性話語的事。這種和平得以維持,并不是什么地方性的奇談,或者說是自由主義思想逐漸滲入縣里人頭腦的原因—同性戀者主要還是住在相對偏遠的地方,且大多選擇遠離政治,而卡儂縣的人則對政治抱有某種天生的狂熱。“在我們南部有種說法,每個男人都是自己城堡的國王。”縣長麥克·加努恩(Mike Gannon)說,“如果你來這里只是埋頭做自己的事,那么沒人會來管你的。”
這里的不同黨派正是如此各自埋首于自己的事務的,直到2003年。那年,阿佩爾鮑姆買下了位于伍德伯里(Woodbury)市原先屬于保羅·麥爾登農場(Paul Melton farm)的土地。他是個5英尺6英寸(約168厘米)高的猶太光頭男人,時年47歲,留著絡腮胡,以前是注冊會計師。很快,他成了全縣最忙碌的開發商、地主和房產商。他相繼當選縣商會和工業同業會的主席,并受聘成為藝術中心主管。當地人按照南部的習慣,稱他是“尼爾先生”。他幾乎染指了所有縣里的功能部門,毫不諱言縣長加努恩在2018年任期屆滿后,他會投身競選縣長。在加努恩看來,阿佩爾鮑姆得勝率極大。這將會使他成為全縣歷史上首位非基督信仰、非異性戀、非娶女性為妻的縣長,并且他或許還會是美國南部地區第一位公開同志身份的縣長。
在美國,同性戀者正經歷著史上最快速、最具顛覆性的變革。6月,最高法院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在一派歡呼聲之余,也觸發了一種哀悼式的追憶。麗薩·科倫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我懷念的是身為同性戀的那種特別之處。”她是暢銷書《歡樂之家》(Fun Home)的作者,還是同名百老匯音樂劇的詞作者。
讓我好奇的是那些住在荒郊野外,比如田納西州的“同志們”,是否也感到了類似的失落。在遠離東西海岸的中部腹地,同性戀與異性戀者會如何相處,畢竟他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分歧—雖然選擇鄉村生活的反社會同化的同性戀者,和他們保守的福音教會派鄰居們都反對同性婚姻,但理由卻天差地別。我也對公社的未來心存好奇:如果人們擁有自由來去的權利,所謂“圣殿”,對他們又意味著什么呢?
圣殿
不得不承認,同性戀者會選擇卡儂縣,實在奇怪極了。在肖特山陡峭的北部,有一個馬廄,游客們可以在馬背上端著倒滿啤酒的高腳杯慢慢享用。接近山頂處,聚集著很多教堂。1萬4千名居民中,擁有超過70座教堂,比例甚至超過了傳統的“圣經帶”(Bible Belt,美國中西部正統派教徒聚集的地帶)。20%的人住的是拖車。最近一次國家電視臺來這里架設播出天線是1994年,那時一個名叫“同盟退伍軍人后裔”(Sons of Confederate Veterans)的組織差點說服縣里答應他們在縣旗上加上內戰時南方聯盟軍旗幟的元素。
同性戀者并非最早來到肖特山的一群怪人。這里曾是非法釀酒商的根據地,茂盛的植物也在經年累月中掩蓋起脾性倔強的人的蹤跡,令他們免遭外人不友善的窺視。肖特山的奇特之處在于,平地就像從半球形的小山間突然冒出那樣,當地人把它叫做“凸巖”,更形象的說法是,這里的地勢就像熱氣騰騰的披薩餅上鼓起的起司泡一樣,因此無論是工業還是大農場都沒法在這扎根。不遠處的卡儂縣不時會傳來幾聲狗叫,或者是汽車引擎回火的聲響,聲音在山坡間來回震蕩,能傳出好幾英里遠。
在“變性脊”得名很久以前的1973年,一群大概十幾個來自加利福尼亞北部的政治激進分子從一對退休夫婦那兒買下了肖特山的一大片土地。他們呼吁停止越戰,改善種族間關系,還出版了一份地下報紙。“我們聽說過爭取同性戀自由的運動,并且支持他們,”米洛·派恩(Milo Pyne)是那個激進政治組織最早期的成員之一,“對于性取向,這里的氛圍很包容。”
沒過多少年,來自西海岸的那些人就選擇了離開。“有人覺得他們無法彼此忍受,有人組成了家庭,向往更穩定的生活。”派恩回憶,“但我希望這個社區能夠繼續存在下去,于是就四下打聽其他適合來這里住的人。”
在一次前往新奧爾良(New Orleans)的旅途中,派恩(那時他的名字還叫做格思里Guthrie,如今他認為自己是雙性戀者)碰到了幾個同性戀。一個念頭在他腦中冒了出來。他在一本同志間很流行的雜志上刊登了廣告,邀請大家來肖特山。“那時,全國各地都可以嗅到一種危險逼近的氣息。”派恩告訴我。在1978年,丹·懷特(Dan White)在舊金山市政廳槍殺了美國第一位公開同性戀身份的政客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當法院裁決懷特犯下的是過失殺人罪而不是謀殺罪后,舊金山的同性戀團體洗劫了商店,掀翻了警車。
肖特山的最初幾年相當艱難,好在一直有從城市來的同性戀者決定常住下去。之后,艾滋病的流行更加增添了這里的庇護色彩。有一段時間,這里幾乎成了艾滋病人的收容所。“不過,在叢林里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的醫療看護。”派恩回憶。也開始有女性搬來,成為公社的一部分,但那時是少數群體,還引發了不少爭議。
1985年,派恩決定離開,謀求成為植物學家。那時的公社已經成為一塊磁石,吸引著四面八方的同性戀者。“對縣里很多上了年紀的人來說,肖特山上的居民從最早的嬉皮士變成后來的同性戀者,這種改變幾乎察覺不到。”派恩說,“他們看到的只是那里住著一群長頭發的年輕人,總在山里干一些奇怪的事。”
對絕大部分搬來這里的人來說,公社是他們第一次接觸鄉村生活,把這里當作思考人生各種可能性與假設的實驗室。桑德爾·卡茨(Sandor Katz)在公社住了17年。他是在十幾歲時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的,不久后就決定要離開城市。那是1970年代。卡茨陷入回憶:“我漫步在紐約的東村,看到一張別人扔了的缺腿的咖啡桌。我找來一個朋友,問他怎么修。那時我28歲,完全不懂怎么才能給桌子裝上一條腿。”不久后,他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那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的生活,雖然我說不清楚具體究竟是什么”。認識幾個在公社住過的人,他們建議他去肖特山看看。自1993年搬來這里,卡茨就一直住到現在。
去山里住,意味著必須具備一些生存技能。卡茨后來學會了打獵、造屋、掘井、保存食物。在他53歲的時候,他懂得怎么讓食物發酵,還在距公社幾英里遠的地方開辦了工作坊。上課的地方是一間1820年代建造的農舍,就是由他修復和擴建的。“城里的男同性戀者正在成為逐漸失去技能的群體。”卡茨認為,“學習這些帶有陽剛氣質的技術能夠給人很多能量。”他和幾位朋友有時會開玩笑把公社叫做“肖特山返工進修學校”(Short Mountain Refinishing School)。

位于肖特山的一家酒廠
離開
1月底的整個紐約覆蓋著灰白的積雪,籠罩在一片憂郁的氣氛中。我動身前往肖特山,租來的尼桑轎車的前保險杠還在路上碰掉了。到達了伍德伯里(Woodbury)后,阿佩爾鮑姆和他的丈夫加思·霍金斯(Garth Hawkins)帶我走完了通向公社的最后一段路。
如果是孤身一人,我想肯定沒辦法找到公社的入口,它隱蔽在山腳一條看起來危險又可疑的路邊。之后,我們跟其他十幾個公社居民在建于內戰前的農舍里享用了素食晚餐。那里是人們的廚房,也是平時聚會的地方。我向一個穿著鼻環的女人介紹自己,當時她正在用金盞花和其他我無法辨認的植物泡茶。“你好。”她握了握我的手,“我叫‘Altercation’(有爭執的意思)。”我想去廁所,有人給我指了路,到了那兒才發覺竟是個露天的四座“馬桶”。就在我去廁所的路上,不知道什么活物突然在我的面前一閃而過,無邊的夜色中我們距離如此之近,以致脖頸后的汗毛立刻倒豎了起來。在這里的每分鐘都提醒著我不要離開城市的理由。
我是在1980年代后期,在中西部學院(Midwestern college)上學時認識阿佩爾鮑姆的。那時他就展現出了擅于解決問題的天賦,這種才能在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當中十分難得,并且他從不拒絕承擔責任。畢業后,他在芝加哥住了十多年,是艾滋病聯盟Act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的活躍分子,開了一家回收公司,買下了自己的第一個物業,并遇見了現在的丈夫霍金斯。霍金斯如今是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的預備役成員。
漸漸地,他們越來越疲于應付城市生活,選擇了搬到卡儂縣。卡儂縣至少同時具有兩個其他地方沒有的好處,首先這里有規模可觀的同性戀社區,其次由于生活成本低,他們未必需要做全職工作就能應付得來。當然,這里并不完美。如果他們要買一本書,或者買一顆洋薊菜,需要前往25英里外的默夫里斯伯勒(Murfreesboro),但對阿佩爾鮑姆和霍金斯來說,優勢遠遠勝過了它的不便之處。
他們搬到伍德伯里不久,阿佩爾鮑姆得知一家伐木公司正在出售一大塊與公社相鄰的土地。當地人很擔心地會賣給他們不熟的外人,以及過度伐木可能帶來的危害,但沒人有什么解決的方法。最終,阿佩爾鮑姆用從父親那里借來的錢買下了535英畝(約2.2平方千米)土地,禁止森林采伐,隨意架設天線,以及過度開發房地產,并把土地分成小塊,以成本價賣給一些愿意在公社長期生活,但買不到或買不起公社土地的人。正因為此,他喜歡將自己稱為中田納西男同嬉皮士們的大施主。
當阿佩爾鮑姆陷入沉思時,他的額頭會稍稍往后仰,手臂交叉在胸前,下顎向前伸出,從領口處露出一小撮胸毛。他的打扮看起來像夏令營指導員,說話的語氣有點單調,沒什么感染力。因此,當他提起鄰居羅尼·蒂蒙斯(Ronnie Timmons)家的公牛掙脫了韁繩,上下蹦跳著逃去路邊時,我一下竟沒有搞清楚他是不是在開玩笑。但他容易情緒激動,上下揮舞的手勢完全不足以流露他內心的波瀾。“我不擅長上電視。”阿佩爾鮑姆說,“我沒法穩穩當當地坐著超過21分鐘。”
阿佩爾鮑姆對金錢的態度很特別。他相信錢在各個領域發揮的巨大影響力,并樂衷賺錢,但另一方面好像又不太在意積累財富。他痛恨任何形式的浪費。我不小心在桌子上撒到了一些咖啡,正想伸手去拿紙巾,他立刻遞給了我一塊海綿。
“沒關系,尼爾。”霍金斯那抑揚頓挫的聲音從客廳里傳來,“他可以用那些紙巾的。”阿佩爾鮑姆和霍金斯住的房子,是中田納西第一座完全使用太陽能源的房子,霍金斯的聲音就在其中久久回蕩著。

卡儂縣的兩個居民。左為服裝設計師,二人身上的服飾由他設計。
房子建得很好又牢固,但樓下他們睡覺的地方用的是水泥地和夾板墻。“這房子的裝修遠遠超出了我的需求。”我剛到那不久,阿佩爾鮑姆就這么跟我說,“你看!它簡直是一座宮殿!”他開的是有些破舊的雪佛萊2000型轎車,每小時的車速不超過35英里。這種節儉風格,令寵物都感到不安。阿佩爾鮑姆只是用單個英文字母給他的貓兒們取名。在一只叫A的貓丟了、另一只叫B的貓死后,他給接著收養的兩只貓分別取名C和D。在這個家里,最奢侈的東西恐怕要數那輛久保田拖拉機了。我去的那天,拖拉機正好借給了他們的鄰居,安靜地停放在牲口棚附近。有些時候,喜歡戴牛仔帽,穿西部樣式襯衣的霍金斯會跳上拖拉機,在上面悠悠然地抽完一整根雪茄。
2006年時,這個地方再度掀起一陣波瀾。藥品執法管理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和一隊郡治安官逮捕了名叫杰夫·楊(Jeff Young)的當地人,在他的物業內繳獲了大量大麻,并沒收了楊在肖特山的土地,很多都位于公社附近。美國法警局(US Marshals Service)決定向開發商開放競拍這塊土地,又是阿佩爾鮑姆化解了這次危機。
動物學家布瑞恩·米勒(Brian Miller)曾在附近的洞穴里發現過一些品種奇特的甲蟲和火蜥蜴。得知此事后,阿佩爾鮑姆輾轉打了很多電話,找到了后來誤入公社的威瑟斯—或許在這個地方還能發現什么其他珍稀物種。威瑟斯在屬于楊的土地上,開始挖掘一些溪流的河床,還真的找到了兩種瀕危物種—布勞利叉龍蝦(Brawley’s Fork crayfish)和肖特山龍蝦(Short Mountain crayfish),之前在科學界誰都沒聽說過。接下來就好辦了。阿佩爾鮑姆開車拜訪了聯邦和州辦公室的各個官員,連續向他們發去不計其數的郵件、電話和備忘錄。2012年,當他們終于決定宣布將這個地方作為野生動物管理區保護起來時—田納西州歷史上第一塊成為動物保護區的土地—阿佩爾鮑姆登上了國家新聞。
他做的遠不止這些。此外,他買下了一些房屋,雇了一隊工人翻修,把它們改造成出租屋,還設法給身無分文的公社成員找住處。即使是伍德伯里(Woodbury)這樣的鄉下地方,心懷慈悲的地產商人也不好找,因此阿佩爾鮑姆又設法拿到了地產經紀人執照。很快,人們在碰到問題時會想到給他打電話,他看起來也樂意解決大家的各種問題。他幫助快失明的鄰居翻修了房子,幫助其他人申請醫療保險,領結婚證,甚至預約牙醫……
以家庭護理工為生的約翰·格林威爾(Joh n Greenwell)在肖特山住過一段時間,在69歲時死于癌癥。他給家人留下一份遺書,將25萬美元遺產贈予了阿佩爾鮑姆。他把這筆錢用于建水池、道路,購買糖尿病藥物,還為公社買下了另外90英畝(約0.36平方千米)土地。
談生意的時候,阿佩爾鮑姆總會特別強調自己的同性戀身份,這種做法常常惹惱他的朋友,對手,其中也包括霍金斯。在應聘藝術中心總監時,他開誠布公地告訴招聘委員會,“我是同性戀—如果這會對你們造成困擾,請直接告訴我”。“我們都是有罪之人。”其中一個面試官回應。
2013年,阿佩爾鮑姆和霍金斯在紐約曼哈頓的市政廳登記結婚。“我要讓卡儂縣的每個人都知道他是我的伴侶。”阿佩爾鮑姆這么說。他的這種坦率并非每個人都買賬。“尼爾從不帶他的丈夫出席任何場合。當然,我也希望他最好不要那樣做。”88歲的奧斯丁·簡寧絲(Austin Jennings)說。她曾是國際獅子會(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總會會長,也是卡儂縣的名人(霍金斯說,其實阿佩爾鮑姆去哪兒都帶著自己,只不過簡寧絲不認識他罷了)。“我才不在乎你是不是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女黑人政治活動家)。”伍德伯里的副市長查理·哈勒爾(Charlie Harrell)認為:“你來這里了,那么就好好干,我們會像對待別人一樣對待你的。”
我與哈勒爾,還有市長帕特里克是在市議會大樓走廊盡頭一間裝修考究的辦公室里進行這場談話的。當被問起與公開出柜的同性戀共事有何感想時,“我不認為尼爾是同性戀”,帕特里克這么說,“他就是卡儂縣的居民。”
公社的事務不再能夠完全占據阿佩爾鮑姆的精力。2009年,他從當地的報紙上看到卡儂縣很有可能會失去“三星地位”,這意味將流失一大筆可觀的補助。卡儂縣落選的主要原因是縣里沒有自己的網站,事實上,那里的當政者沒有一個明白電腦是怎么回事。阿佩爾鮑姆讓自己的朋友制作了網站,并以1000美元的價格賣給了縣里。“我其實只是在這里隨便轉轉。”他說。縣長加努恩對阿佩爾鮑姆隨處可見的身影并不反感,于是他來這里的次數就更多了。
“那時我一邊和太太養著孩子,一邊和另一個男人過著‘雙重生活’,直到再也無法忍受。”布萊克說
他似乎總能找到解決各式問題的方法。縣議會和本地高中需要更換取暖設備和空調,是阿佩爾鮑姆親自填寫了各種表格,從聯邦政府那兒申請到了補助。“我也看過那些補助申請材料,但完全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69歲的市長帕特里說。此外,阿佩爾鮑姆還靠出售“肖特山咖啡”賺來的錢幫忙重新修整了公園里的綠植。
用阿佩爾鮑姆的話來說,他很多為人處世的方式都是從母親多蘿西·利伯曼·格魯斯金(Dorothy Lieberman Gruskin)那兒學來的。格魯斯金是位舉止優雅的女性,在她的中年猶太女性朋友圈里有著能完美應對各種困擾的好名聲。“她并不是特別吸引人,也說不上熱情,但她是那種會幫離婚的朋友找公寓,幫人找工作或者謀生計的人。”阿佩爾鮑姆說,“我一直都想成為像我母親那樣的人。”在婚禮上,阿佩爾鮑姆戴了母親的一條古董珍珠項鏈,當他為這篇報道拍攝時,也堅持換上了那條項鏈。

這是“激進的精靈”組織中的一名成員。在一次聚會中,她向上帝“獻酒”
狂歡
我是個重度咖啡上癮者以及超級宅男,因此對肖特山的生活沒什么很大興趣,但有一個疑問一直盤踞在我的腦中—在“同志驕傲大游行”如此盛行的當下,為什么還會有人成群結隊跳上火車,或者開上幾天幾夜的車去肖特山這樣的地方“朝圣”。終于,到了兩年一度集會的時候,我又再次回到了那里。
在這場春季狂歡中,肖特山幾乎被人潮淹沒了,根本不可能把車開到公社的入口。我只能一路走著上山,置身于一片樸樹和爪子樹林里,粗糙的葡萄藤錯綜復雜,纏繞其中。當我的眼前豁然開朗,竟有一種庫克船長第一眼瞥見考艾島的沖動。
山上各種性別、年齡,身形、膚色的人都有,個個穿著奇裝異服—就像在有哈利·波特歷險記之前,他們就聽說過有那么一個地方。草綠色的山丘上站著人身牛頭怪、半機械人、魔術師,或者一些人身上只是孤零零掛著幾片金屬或常春藤枝蔓。一個穿著皮革裝,女施虐狂打扮的人,一邊牽著一只獨角獸,一邊和我打了招呼;一個孤獨的男人坐在木頭上,T恤上是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的畫像;我經過兩個躺在草地上的年輕人,聽到他們說“……或者我們該起來給自己弄些咖啡喝。”
集會上,我無法對那些畫面視而不見,對那些聲音充耳不聞,但它們卻沒有給我留下過于深刻的印象。肖特山不像其他同性戀聚居地,這里似乎并不會向你索取什么。狂歡節上所謂的階層—性別、種族、年齡、魅力、金錢、權利—似乎只在那幾天里存在,便迅速煙消云散了。從早到晚,大家吃著東西,喝著酒,我能夠想到的唯一適合描述眼下場景的詞是“克制”。絕大部分穿過大半個國家來到這里的人實在太年輕了,根本不知道60、70年代是怎么回事,也不懂得公社里過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生活。
我跟一個細胳膊細腿,穿著斜粗紋棉布上衣的男人交談起來。看樣子,他年輕時應該是個帥小伙。赫克托·布萊克(Hector Black)在紐約的皇后區長大,打過二戰,從哈佛大學畢業,加入過貴格會(Quakers,沒有成文的教義或圣禮,直接依靠圣靈的啟示指導宗教活動與社會生活,具有神秘主義特色)。他的大半輩子都投入了政治運動,同時在田納西州的庫克維爾(Cookeville)經營著一家有機農場。
據他說,自從出柜后,他每一次都參加肖特山的集會。那已經是20年前的事了。
“那時我一邊和太太養著孩子,一邊和另一個男人過著‘雙重生活’,直到再也無法忍受。”布萊克說,“我已經70歲了,從沒有錯過這里的任何一次集會。”
就在我們說話的時候,兩個20多歲,身形瘦長的年輕人經過他的身邊,身上只有幾塊布,還抹著不少迷彩顏料。“你們叫什么名字?”布萊克問。
“我叫Artemis(阿耳特彌斯,月亮與狩獵的女神),”其中一個回答,“他是Summer(夏天)。”
“真的很高興能夠認識你們。”布萊克很有禮貌地大聲回話。然后,他揮舞著手中的藤條,就像在給自己開路那樣,一步一步朝肖特山下走去。■
本文由《紐約時報》資訊與版權公司授權《博客天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