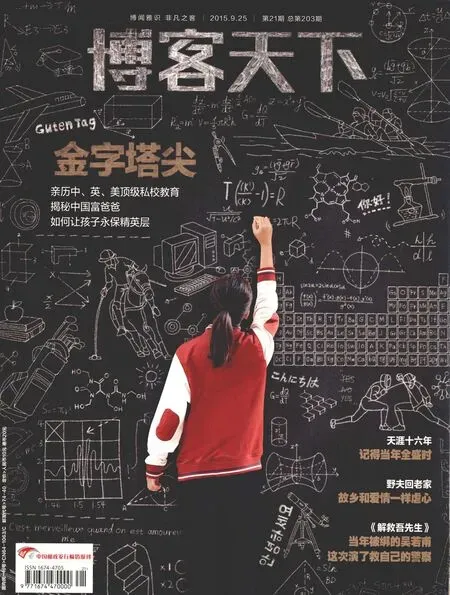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
文 李健華 編輯 卜昌炯
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
文 李健華 編輯 卜昌炯
當(dāng)年他們在那些優(yōu)質(zhì)中學(xué)念書時,還只是一個人名,多年后,他們成了名人
憶及自己的中學(xué)時代,知名主持人曾子墨最深的一個感觸是像“牲口”。
她曾經(jīng)就讀的人大附中在全國都享有盛名。這是一所以培養(yǎng)高分學(xué)生著稱的重點中學(xué),過去10年間,北京市高考狀元近半都出自該校。近乎100%的一本上線率,更是讓這所學(xué)校充滿傳奇色彩。能進入該校就讀,往往意味著一只腳已經(jīng)踏進了重點大學(xué)的大門。
“那時候,凡是期中、期末和各種名目繁多的全區(qū)統(tǒng)考,六門功課加在一起的總分,班里和年級一定要排名次。名次,也成為檢驗學(xué)生優(yōu)秀與否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曾子墨在自傳《墨跡》一書里回憶。
在這樣的校園氛圍下,自稱“一直舍不得對自己高標(biāo)準(zhǔn)嚴(yán)要求”的她,很快生出了使命感—不能不考第一。那時,她的同學(xué)們都稱考試第一名的人為牲口,這個名號隨即也落到了她的頭上,一次又一次。
這種唯分?jǐn)?shù)論的價值觀后來直接影響了她大學(xué)時的專業(yè)選擇。高中畢業(yè)時,成績優(yōu)異的曾子墨獲得了保送北大的機會,她最后卻選擇了當(dāng)時錄取分?jǐn)?shù)最高的人大國際金融系,理由很簡單:“考分最高的專業(yè)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我的分?jǐn)?shù)不比別人低,別人能學(xué)的,我也要學(xué)。”
從曾子墨的回憶筆觸中,很難看出她對傳統(tǒng)應(yīng)
試教育的情感。但在人生觀的培養(yǎng)上,她對自己的中學(xué)教育持正面態(tài)度:“我漸漸明白,無論考試、工作,還是其他事,人可能都是這樣,當(dāng)別人認(rèn)定你是第一,你便會暗示自己不能不做第一,多少次反復(fù)與輪回過后,突然有那么一天,你終于蛻變,成為真正的第一。”
和被分?jǐn)?shù)成全的曾子墨不同,同樣是重點中學(xué)出身的韓寒,經(jīng)常被分?jǐn)?shù)傷害,無論考了低分還是高分。
關(guān)于韓寒在上海著名高中松江二中的故事已經(jīng)流傳很廣了,大都知道他是“差生”。其實,韓寒的初中時代,成績并不算差。據(jù)韓寒父親韓仁均在《兒子韓寒》一文中透露,韓寒入讀聚集了上海金山區(qū)大批尖子生的羅星中學(xué)時,幾門課平均成績是91分,但由于班上都是高分學(xué)生,他只能排到42名,“倒著數(shù)反而方便”。
有一次,韓寒難得超常發(fā)揮,在一次數(shù)學(xué)測驗中考了滿分,結(jié)果卻被老師認(rèn)定為“作弊”,還將其父親叫到了學(xué)校。
這件事給韓寒造成了很大的打擊,“陰影籠罩了我整個少年生涯”,他在博客中寫道。
自此以后,他見到數(shù)學(xué)課和數(shù)學(xué)題就心生厭惡。多年后,重新看待這件事時,他如此總結(jié):“雖然蒙受冤屈,這件事卻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那些更值得也更擅長的地方,我現(xiàn)在的職業(yè)都是我的摯愛,且我做得很開心。”
“雖然蒙受冤屈,這件事卻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那些更值得也更擅長的地方”
比考試更重要的事
若把時光撥回到數(shù)十年前,或許會發(fā)現(xiàn),分?jǐn)?shù)對一名中學(xué)生來說,也可以不那么重要。
很多人潛意識里認(rèn)為民國是一個“大師輩出”的時代,而不少“大師”的中學(xué)成績都很一般,比如讀大學(xué)時數(shù)學(xué)考了15分的錢鐘書,比如只會寫作文其他科目都很糟糕的聞一多……但這不影響他們在“大師”的路上越走越遠(yuǎn)。
考試從來不是他們的唯一出路—除了考試,他們還有別的更重要的事情可做,不管在普通中學(xué),還是在精英中學(xué)。
1922年秋,12歲的曹禺考入了天津南開中學(xué),成為初中二年級的一名插班生。這所學(xué)校由教育家張伯苓和嚴(yán)范孫兩人創(chuàng)辦,是南開系列學(xué)校(一所大學(xué),三所中學(xué))的開端。在“德智體三育并進而不偏廢”的教育理念主張下,南開特別注重學(xué)生的綜合素質(zhì)培養(yǎng)。
曹禺后來專注于話劇藝術(shù),便與他在該校的求學(xué)經(jīng)歷有關(guān)。南開中學(xué)很早就有編演話劇的傳統(tǒng)。1908年,張伯苓赴歐美考察教育,回國后大力提倡話劇(當(dāng)時稱“新劇”),常常與學(xué)生同臺演出。

2014年6月15日,美國加州,微軟創(chuàng)始人比爾·蓋茨與妻子梅琳達(dá)出席斯坦福大學(xué)畢業(yè)典禮
此種氛圍下,曹禺萌發(fā)了對話劇的興趣,加入了南開新劇團,之后遇到了他的啟蒙恩師—新劇團副團長、戲劇大師張彭春。后來他回憶:“《雷雨》的構(gòu)思很早了,在南開中學(xué)時就產(chǎn)生了一些想法。但是,當(dāng)時還不知道寫個什么樣的戲。”
南開中學(xué)也是經(jīng)濟學(xué)家吳敬璉的母校。1941年,小學(xué)畢業(yè)后,吳敬璉考進因為戰(zhàn)亂而遷到重慶的南開中學(xué)。
“我雖然只在南開念過兩年書,但南開給予我的基本訓(xùn)練方面的影響,卻是極其深遠(yuǎn)的。除語文、數(shù)學(xué)等功課外,從邏輯思維、語言表達(dá),公民課上關(guān)于如何開會、如何選舉、如何表決的訓(xùn)練,直到每座樓進門處鏡箴上的‘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的儀態(tài)要求,都使我終身受用不盡。”吳敬璉回憶說。
民國時代的中學(xué)有公立和私立之分,由于教育經(jīng)費緊缺,公立教育普遍很差,有錢人家的孩子多半會進入私立學(xué)校。除此之外,一些教會學(xué)校也在當(dāng)時的精英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
冰心1914年就讀的貝滿女中(今北京市第166中學(xué))是北京最早引進西方教育的女校,由美國基督教公理會于1864年創(chuàng)建。
冰心剛到學(xué)校時,“很拘束,很郁悶。《圣經(jīng)》課對我本來是陌生的,那時候讀的又是《列王紀(jì)》,是猶太國古王朝的歷史,枯燥無味”。不過,她很快被學(xué)校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學(xué)會”吸引。這是同學(xué)們練習(xí)演講辯論的集會,不僅讓她“磨”出了臉皮,某種程度上也培養(yǎng)了她對文學(xué)最初的興趣。
“點燃一把火”
如果把目光投射得再遠(yuǎn)一點兒,在那些世界知名的超級中學(xué)里,會發(fā)現(xiàn)精英教育的另一種力量—它不在于遇到什么樣的老師,而在于遇到什么樣的環(huán)境;它對一個人的影響,有時候僅僅是一次機會,或者是一次小小的點悟。如同愛爾蘭劇作家葉芝所說: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比爾·蓋茨對計算機的迷戀,最初是從中學(xué)時代玩“三連棋游戲”開始—他13歲時編寫的第一個軟件程序,就是為了玩三連棋。讓一群十幾歲的少年接觸計算機是西雅圖湖濱中學(xué)俱樂部母親們的主意。
“那時我正在該私立學(xué)校上中學(xué)。這些母親們決定,應(yīng)該把一次義賣捐獻(xiàn)物所得的錢用來為學(xué)生們安裝一臺終端機,并為他們付計算機機時費。”蓋茨回憶,“還在1960年代末的西雅圖,就讓學(xué)生使用計算機,這是一種相當(dāng)令人驚訝的做法—對此,我將永遠(yuǎn)懷抱感激之情。
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當(dāng)年在英國名校哈羅公學(xué)就讀時,跟韓寒一樣是個“差生”。他形容自己的中學(xué)歲月是“畫面中一塊醒目的灰色補丁”。唯獨學(xué)校每年一度的校園演唱會激起了他的熱情和自信。“那些詞句激發(fā)的振奮人心的愛國情緒從此以后留在他身上,成為他政治行為的主要推動力。”這是丘吉爾之子對父親的總結(jié)。
當(dāng)然,也有對這種貴族學(xué)校一點都不領(lǐng)情的,比如曾在伊頓公學(xué)就讀的作家喬治·奧威爾。他在一篇文章中吐槽:“我待在伊頓,只是因為獲得了獎學(xué)金,我并不屬于在那里接受教育的絕大多數(shù)人的社會圈子。”聯(lián)想到他一貫特立獨行的作風(fēng),有這樣的言論也不足為奇。
不扼殺學(xué)生的個性、自由、為學(xué)生成長提供盡可能多的空間和機會,這些大體是西方精英教育的共性,也是區(qū)別國內(nèi)應(yīng)試教育、唯分?jǐn)?shù)論的一大亮色。幼時在臺灣接受中國傳統(tǒng)教育、中學(xué)時赴美讀書的李開復(fù),對此有很深的體會。
李開復(fù)的初高中都是在美國念的。他曾經(jīng)就讀的橡樹嶺高中位于田納西州,該校近年來的排名一直維持在州前10。橡樹嶺是一所因核彈實驗室而聞名的神秘小鎮(zhèn),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彈“小男孩”就誕生于此地。
李開復(fù)對橡樹嶺高中寬松、自由、快樂、充滿鼓勵和贊揚、不看重排名的學(xué)習(xí)環(huán)境記憶猶新,這與他在臺灣上學(xué)時的情況截然不同。
“在臺灣,我們要在課堂上將雙手背后坐得筆直,要在操場里聽沒有意義的校領(lǐng)導(dǎo)訓(xùn)話。每天早上醒來,我們想到的是沉重的課程、繁多的作業(yè)以及嚴(yán)格的考試。”李開復(fù)在《世界因你不同》一書中寫道。
橡樹嶺高中的功課很少,反而每天都會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項目,這讓李開復(fù)一度感到不習(xí)慣,“比如當(dāng)時,歷史課教到美國印第安人的時候,不是用課本告訴你發(fā)生了什么,而是讓一個團隊寫一個話劇,或者是基于移民者和印第安人的辯論”。
直到多年后,李開復(fù)才意識到這種教育的特殊魅力:“美國孩子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都是在這些稀奇古怪的題目中得到鍛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