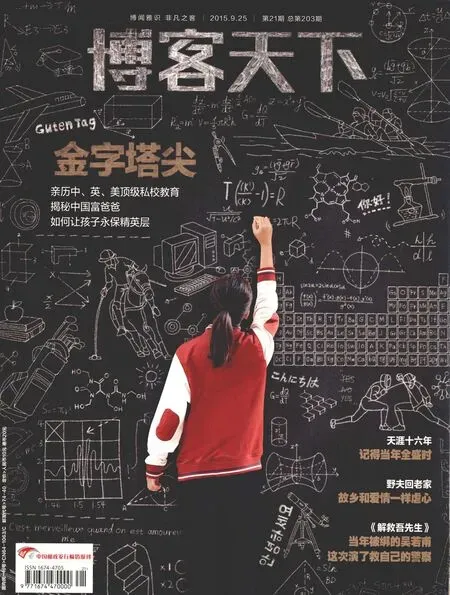野夫回老家,故鄉(xiāng)和愛(ài)情一樣虐心
文 徐雯 編輯 王波
野夫回老家,故鄉(xiāng)和愛(ài)情一樣虐心
文 徐雯 編輯 王波
站在1980年代愛(ài)情的發(fā)生地利川,野夫說(shuō),“其實(shí),故鄉(xiāng)是很多人的一個(gè)情感陷阱。”

作家野夫最近經(jīng)常在朋友圈刷屏,平均每天更新20多條狀態(tài)。
為了自己策劃和編劇的電影《1980年代的愛(ài)情》,這個(gè)53歲的男人放低了姿態(tài)吆喝:“慚愧,這幾天刷屏,大家理解一下,求生不易。”他的要求不高,只希望電影能和市場(chǎng)搏個(gè)平手。
這部以他為原型、在他家鄉(xiāng)湖北利川拍攝的電影,是他與故鄉(xiāng)跨越30年的隔空對(duì)話。
9月10日,在北京的首映式上,湖北省恩施州州委書(shū)記王海濤到現(xiàn)場(chǎng)致辭:“正像人們過(guò)去從沈從文的小說(shuō)、黃永玉的畫(huà)、宋祖英的歌中了解湘西,現(xiàn)在也會(huì)從野夫的小說(shuō)和電影中了解恩施。”
這幾乎是野夫受到的官方的最大禮遇,但他內(nèi)心清醒:“現(xiàn)在你成了名人,學(xué)問(wèn)比過(guò)去沒(méi)有增加,但是浮名多了。”
在電影的演職員表中,他用了真名:鄭世平。
致敬
“80年代初,人性已經(jīng)開(kāi)始松綁了,但還不能飛翔。那時(shí)候的愛(ài)情有一種純凈的美。”野夫坐在家鄉(xiāng)利川的茶室里,右手熟練地夾著一根煙,一字一句地說(shuō),“你可以用一切詞語(yǔ)形容這部電影,紀(jì)念、緬懷、祭奠,它是我對(duì)1980年代的致敬。”
電影講述的故事,野夫耿耿于懷了30年,這也正好是他離開(kāi)利川的時(shí)間。
因?yàn)檫@部電影,野夫的一幫朋友決定到利川看看。9月2日晚7點(diǎn),身著黑色上衣和亞麻色休閑褲的野夫飛快地走在前面,帶朋友到土家菜館雄起酒樓。大八仙桌上杵著煙囪,上來(lái)就是一壇52度的土家玉米酒和一鍋五花肉燉排骨,爐火嗤啦啦地響,野夫倒上酒,一飲而盡:“歡迎大家來(lái)到我的家鄉(xiāng)利川。”
這個(gè)留著平頭的中年男人步履矯健,手卻有點(diǎn)不易察覺(jué)的顫抖。“這是以前在監(jiān)獄留下的根。”與野夫相識(shí)50年的兄弟廖松告訴《博客天下》。
在野夫所有的文字作品中,這段經(jīng)歷和緣由都語(yǔ)焉不詳,在電影中也同樣被模糊處理,只剩下男主角胡子拉碴地走在燈紅酒綠的街道上,時(shí)代的痛感被肢解得七零八落。
電影片頭的本名鄭世平,則一直勾連著中年男人野夫人生的愛(ài)與痛。
廖松看了電影,說(shuō)女主角和野夫的初戀女友有幾分神似。詩(shī)人趙野也見(jiàn)過(guò)真人,稱之“雖然歲月滄桑,韶華已逝,眉宇間幾分英氣尚存”。

電影《1980年代的愛(ài)情》劇照
但野夫不愿意多談愛(ài)情,說(shuō)知天命的年齡已經(jīng)不提愛(ài)情了。“這種愛(ài),只是對(duì)已逝年代的一種找補(bǔ),它只是一種確認(rèn)而不是為了實(shí)現(xiàn)什么。”
1985年,野夫入學(xué)武漢大學(xué)作家班,從此遠(yuǎn)走高飛。大學(xué)畢業(yè)后,他被分配到海南當(dāng)警察。1989年,鄭世平選擇脫下警服,而后入獄5年。回歸社會(huì)后開(kāi)始了10年的北漂生活,成為名利雙收的書(shū)商野夫。
但骨子里他還是文人,覺(jué)得“人世虛無(wú),應(yīng)該對(duì)前半生的人與事有所交代”,于是回歸文學(xué)。以《江上的母親》始,野夫?qū)⒗ǖ娘L(fēng)物融進(jìn)50年的社會(huì)激變中,通過(guò)數(shù)量不多的散文就征服了讀者。
同是土家族的作家冉云飛與野夫相識(shí)近20年,他提前3天來(lái)到這座鄂西小城,參加電影在利川的首映。“毫不夸張地講,20年后野夫之于利川的意義,就是今天沈從文之于鳳凰的意義。”他說(shuō)。
如今在利川,“野夫”是一個(gè)比鄭世平更響亮的名字。“連我二姐都叫我‘老野’。”野夫說(shuō)。偶爾,只有年長(zhǎng)1歲的廖松會(huì)叫他世平。他倆都是在大饑荒的年代出生。
野夫現(xiàn)在生活在大理,但每年都會(huì)回利川,找老朋友喝酒。他習(xí)慣住在藍(lán)波灣大酒店,從窗口望出去,能看見(jiàn)外婆曾經(jīng)在山頭的孤墳。他用蕭紅在《呼蘭河傳》里寫(xiě)的一句話“呼蘭河這小城里邊,以前住著我的祖父,現(xiàn)在埋著我的祖父”來(lái)描述自己客居于此的安全感。
48歲那年,野夫出現(xiàn)老花眼,也開(kāi)始頻繁失眠,索性經(jīng)常半夜起來(lái)喝酒寫(xiě)文,在白紙上熬出一幫在歷史口徑上諱莫如深的小人物。
“我地理上的故鄉(xiāng)和精神上的故鄉(xiāng)都在利川。” 他說(shuō)。
尋找
但在老屋重建、塵土飛揚(yáng)的家鄉(xiāng)小城,人們已經(jīng)不太認(rèn)識(shí)這個(gè)在利川沒(méi)有房產(chǎn)的老鄉(xiāng)了。
“你不留在北京看閱兵?”出租車司機(jī)問(wèn)。
“我來(lái)找利川的作家野夫。”
“我們利川還有作家?”她反問(wèn)道。這也是接下來(lái)幾天里,其他幾位出租車司機(jī)的共同反應(yīng)。
9月3日,閱兵儀式開(kāi)始后,大大小小的電視屏幕前,坐滿了圍觀的人們,家具店門外的新藤椅和小板凳上,坐的不再是顧客,而是觀眾。
這條彌漫著愛(ài)國(guó)情懷的街道,曾經(jīng)是利川唯一的老街。青年野夫在這條街上威名赫赫。
有一次,恩施的女朋友來(lái)利川看他,剛下火車就被幾個(gè)小混混盯上,一路跟著到了野夫單位,才知道這是野哥的女朋友,嚇得直跑。
“我以前在恩施追女朋友還找他幫忙呢,我們是地方一霸。”廖松回憶,他們那個(gè)年代表達(dá)愛(ài)情的方式,通常就是兩個(gè)男人決斗,要么一對(duì)一,要么叫一幫兄弟群斗。野夫經(jīng)常為朋友而打架斗毆。
野夫的左眼上方還有當(dāng)年留下的一厘米傷疤。“我打架厲害,用現(xiàn)在流行的詞匯叫做古惑仔,對(duì)手不敢明著來(lái),就只能偷襲。”他說(shuō),有一次去醫(yī)院看朋友,黑燈瞎火,出門就被人埋伏,一刀子下去,就留下了一道疤。
他經(jīng)常和廖松在老街上喝酒。小縣城生活乏味,黃昏時(shí)候酒是必需品,“拜把子兄弟經(jīng)常一起喝”。有次有個(gè)同伴不想出來(lái),野夫和廖松拿著酒瓶去他床上灑酒,“被子濕了,沒(méi)辦法了,只能出來(lái)喝酒了”。
那時(shí)候,除了酒,他們還有詩(shī)歌。野夫和朋友成立地下詩(shī)社“剝棗詩(shī)社”,手抄、油印那些意氣風(fēng)發(fā)的詩(shī)句,熱火朝天地贊頌著青春、愛(ài)情和自由。他們會(huì)走兩天的路坐火車去還未被開(kāi)發(fā)的張家界,會(huì)在沒(méi)有任何探險(xiǎn)工具的情況下用十幾個(gè)小時(shí)徒步穿越原始的山洞,會(huì)拎著桿獵槍去樹(shù)林里打獵。
“沒(méi)有經(jīng)歷過(guò)的人真的沒(méi)辦法體會(huì)。”野夫說(shuō),“現(xiàn)在都還想回到那時(shí)候,太舒服了。”
但他也知道,離開(kāi)至今依然十分封閉的公母寨,是年輕人必然的選擇。“即便是今天,從這里走出去的人們基本都不愿意再回去。”
這幾乎可以解釋電影中女主角為何極力希望男主角能夠去遠(yuǎn)方追求理想。
兩人年輕時(shí)在公母寨分別的那個(gè)夜晚,低頭沉默代替了書(shū)中克制的麗雯突然的嚎啕大哭——這是策劃人、編劇野夫和導(dǎo)演霍建起分歧最大的一場(chǎng)戲。“這個(gè)情節(jié)是真的,我離開(kāi)公母寨的那天,她突然就撲到我懷里大哭,我想吻她,始終犟著不肯。她知道,如果吻到了,我們的最后一根心理防線就斷了。”野夫靠在公母寨溪邊的鐵索橋上,敘述著這個(gè)故事的真實(shí)版本。
如今的年輕人要比野夫幸運(yùn),他們可以從鐵路和高速公路離開(kāi)利川。30年前野夫“出峽”,到武漢用了4天時(shí)間,坐車去萬(wàn)州,然后在長(zhǎng)江上坐船順流而下。
公母寨的鄉(xiāng)民得知必須去縣里電影院才能看到野夫的電影,都訕訕地表示:“那看不成咯。”
看見(jiàn)老鄉(xiāng)民,野夫迎上去問(wèn):“有沒(méi)有人記得以前在鄉(xiāng)公所燒飯的老田?”鄉(xiāng)民想了很久,從記憶的故紙堆中挖掘出了這個(gè)人:“好像是有這么一個(gè)人。”旁邊有人說(shuō):“30年了,大概早去世了。”
老田也被野夫放進(jìn)了電影里。這個(gè)在鄉(xiāng)政府陪伴關(guān)雨波的老知識(shí)分子,因?yàn)闀?shū)法好,幫人抄了大字報(bào),“反右”清算時(shí),大家都不承認(rèn),鑒定筆跡后,全部賴在了老田身上。屈辱多年,妻離子散,平反后,也不過(guò)還剩殘年。六七年前,野夫回來(lái)過(guò)一次,但沒(méi)有找到這個(gè)人。
老田就像80年代野夫在利川小城留下的痕跡,消失得無(wú)影無(wú)蹤。
情誼
如今,代替他們?cè)诶h城露臉的是電影廣告招牌。
縣城大街上頗有山寨氣息的“周六福”和“周大生”等金器珠寶店門口,拉著“慶祝反法西斯戰(zhàn)爭(zhēng)勝利七十周年”的橫幅,工作人員散發(fā)著具有節(jié)日氣氛的促銷廣告。
與此交相輝映的,是“《1980年代的愛(ài)情》回鄉(xiāng)之旅”的大字烙在朦朧的山水畫(huà)上。主創(chuàng)野夫的名字理所當(dāng)然地出現(xiàn)在環(huán)繞舊城的牌子上。在利川唯一一家電影院門口,《1980年代的愛(ài)情》和《烈日灼心》的宣傳海報(bào)緊挨在一起。擺放海報(bào)的影院人員對(duì)野夫知之甚少,只說(shuō):“這是一部講利川的電影。”
房地產(chǎn)開(kāi)發(fā)商顯然更懂野夫的價(jià)值。在距離市區(qū)21公里的宜影古鎮(zhèn)度假村的新建樓盤上,開(kāi)發(fā)商掛著“野夫工作室”的大橫幅,圖片是電影中女主角仰望天空的臉龐。“施工時(shí)橫幅會(huì)取下來(lái),以后建成出售時(shí)會(huì)再掛上去。”工作人員說(shuō)。
對(duì)于度假村而言,野夫這樣具有“大理氣質(zhì)”的文人無(wú)疑是一種招牌。野夫不拒絕這些。他告訴《博客天下》,“未來(lái)如果想集中一段時(shí)間寫(xiě)作,也許會(huì)回到這里,過(guò)一段面山而居的日子。”
此外,他的名字也會(huì)被口頭提及。在利川騰龍洞景區(qū)的表演介紹中,野夫再次出現(xiàn)。三年前,他曾為利川民歌宣傳片《龍船調(diào)的故鄉(xiāng)》撰寫(xiě)解說(shuō)詞。他對(duì)土家族的民歌十分推崇,后來(lái)將哭嫁、跳喪等傳統(tǒng)習(xí)俗都融進(jìn)了電影。
不過(guò),廖松回憶,“拍攝《龍船調(diào)的故鄉(xiāng)》時(shí),老野很郁悶。”
那段時(shí)間,廖松幫忙盯這個(gè)項(xiàng)目。他直言利川和恩施官方對(duì)野夫不夠重視。
“這個(gè)是事實(shí)。”野夫坦言,“現(xiàn)在好多
“他們這代走出去的中年知識(shí)分子與故鄉(xiāng)都是‘隔’的,表面客氣,但無(wú)法親昵”了,每一任領(lǐng)導(dǎo)都不一樣,不能泛泛地講,畢竟因人而異。”
反倒在客居的地方,他獲得的尊重更多。“舉個(gè)庸俗的例子,大理去北京開(kāi)新聞發(fā)布會(huì),發(fā)言人會(huì)說(shuō)在我們這兒生活著土家野夫、葉永清,如數(shù)家珍,他覺(jué)得我們大理包容了這些人。但恩施這邊就不會(huì)說(shuō),甚至還怕我們這種有點(diǎn)敏感的人物會(huì)不會(huì)惹事兒。”野夫說(shuō),“當(dāng)然,我不介意這些,我是一個(gè)受歧視的人,你沒(méi)坐過(guò)牢,你不知道那種感受。”
1995年,減刑出獄的野夫在廖松家住了半個(gè)月。
多年以后,社會(huì)頭銜是作家的野夫回鄉(xiāng)和當(dāng)年的江湖兄弟喝酒,對(duì)方說(shuō):“嗨,什么作家不作家,不就是當(dāng)年街上經(jīng)常打架的兄弟嗎?”
有一次,他拉著好友蘇家橋參加飯局。飯桌上,朋友們出于好意,苦口婆心地勸野夫“改邪歸正”,換一種更柔和的姿態(tài)生活。野夫默不作聲,蘇家橋卻拍案而起:“你們根本不了解野夫!”
“我和大家沒(méi)有共同話題。”離家多年,敘舊變成了一種必須和無(wú)奈。所有人都只能跳過(guò)社會(huì)劇烈變化的30年,隔靴搔癢地聊著安全的話題。
即便如此,趙野還是覺(jué)得野夫比大多數(shù)人幸運(yùn)。“我們這一代中的大多數(shù),十六七歲就離家上大學(xué),從此和故鄉(xiāng)再?zèng)]有任何關(guān)系。‘鄉(xiāng)愁’這個(gè)詞,在我的生活中并無(wú)具體所指,只有形而上的意義。野哥則不然,他在家鄉(xiāng)有很多朋友,身份形形色色,卻都和他有一份山高水闊的情誼。”2006年,他跟野夫到利川后,在文章里這樣寫(xiě)道。
完成追溯記憶的小說(shuō)時(shí),野夫正在德國(guó)萊茵河畔。“隔得越遠(yuǎn),回望往事的時(shí)候,反而更加寧?kù)o,可以集中精力地來(lái)寫(xiě),形形色色的人。”寫(xiě)完的那天,他才覺(jué)得放下了一段前塵往事。
抵抗
這次帶著電影回鄉(xiāng),野夫特地跟朋友去了自己出生的村子。
原本是川鄂交界的繁華街道早已凋敝,一棟白色歐式小洋房是村里為數(shù)不多的現(xiàn)代標(biāo)志,另一個(gè)標(biāo)志是被隨意丟棄在小溪邊的紙尿片。“在農(nóng)村,這都是強(qiáng)勢(shì)文明的象征。”同路的冉云飛說(shuō)。
3歲前,野夫生活在這里,但他對(duì)此沒(méi)有記憶,已無(wú)法在那些破敗的吊腳樓中找到自己出生的屋子。他與這里唯一的牽連是早夭的哥哥—被一針不經(jīng)皮試的青霉素要了命,骨殖留于鄉(xiāng)野,孤墳不尋。
對(duì)這個(gè)哥哥,野夫感情復(fù)雜。那是他連結(jié)這片土地的血脈,但同時(shí)也讓他感覺(jué)自己是替代品:如果哥哥還活著,世界上就不會(huì)有鄭世平。
“貧瘠的年代,有一個(gè)兒子就夠了。”他說(shuō)。站在穿村而過(guò)的馬路上,他在煙雨迷蒙中回頭望了一眼,然后轉(zhuǎn)身背對(duì)村子,攤手笑道:“這就是故鄉(xiāng)。”
3歲后,野夫被父母帶到汪營(yíng)鎮(zhèn)生活了10年。每次回利川,野夫都會(huì)去汪營(yíng)鎮(zhèn)老街走一圈。
但這里還記得“老鄭家”的人已經(jīng)不多了。他的房東、一起長(zhǎng)大的熊九娃在街上開(kāi)鞋店,見(jiàn)野夫回去,熱情地握手。野夫覺(jué)得溫暖:“在大理,不會(huì)有人這樣問(wèn)你,即便它包容了你。”但他知道,能和熊九娃聊的內(nèi)容也不過(guò)是隔壁老王去哪兒了、街頭老張得了什么病。
野夫和街上一個(gè)老人聊起往事,提起曾經(jīng)一起長(zhǎng)大的樊家聲。“你是樊家聲嗎?”野夫轉(zhuǎn)頭問(wèn)不遠(yuǎn)處站著的一個(gè)男人,正要上去握手,卻見(jiàn)男人茫然地?fù)u頭,隔壁服裝店里一個(gè)女人走出來(lái)說(shuō),“樊家聲幾年前就死了。”她是樊家聲的老婆。
“他們這代走出去的中年知識(shí)分子與故鄉(xiāng)都是‘隔’的,表面客氣,但無(wú)法親昵。”冉云飛說(shuō)。
野夫?qū)⑦@種親近寄托在食物上。每次回汪營(yíng)鎮(zhèn),他都要吃幾碗酸辣涼粉。
這幾年,寫(xiě)作汪營(yíng)鎮(zhèn)故事的想法不斷在野夫的腦海里盤旋。他想去掉這種“隔”,近距離回憶這里發(fā)生過(guò)的事情。包括他和父親。野夫從小就看著父親在汪營(yíng)鎮(zhèn)街上被批斗,所有人都喊“打倒鄭麻子”。
“我爸出過(guò)天花,大家就攻擊他的生理缺陷。”野夫回憶。后來(lái)他買了個(gè)小步槍,裝了石灰,朝一米開(kāi)外一個(gè)喊口號(hào)的小孩直接打過(guò)去。小孩隨即被大人們送去醫(yī)院洗眼睛。野夫被從醫(yī)院回來(lái)的媽媽暴打一頓。父親從煤礦上回家后問(wèn):“你為什么敢在孩子眼里塞石灰?”得到的回答是,“他說(shuō)要打倒鄭麻子。”
父親一下子就沉默了,對(duì)正等待挨打的兒子說(shuō),“出去,吃飯。”
“若干年后,我理解了父親,那一刻,他理解了一個(gè)孩子受到的羞辱,理解了一個(gè)孩子的憤怒。”回憶起這些舊事,野夫眼圈有些發(fā)紅。
在小說(shuō)《1980年代的愛(ài)情》中,他借一個(gè)在各種政治斗爭(zhēng)中起起伏伏的老知識(shí)分子的口,說(shuō)了一句意味深長(zhǎng)的話:“哪里黃土不埋人啊?有什么故鄉(xiāng)他鄉(xiāng)的?”
“其實(shí),故鄉(xiāng)是很多人的一個(gè)情感陷阱。”野夫說(shuō),“這是命運(yùn)給我的提醒,是對(duì)故鄉(xiāng)清醒的態(tài)度。”
他要留存一份抵抗。“歷次的政治運(yùn)動(dòng)中間,回到故鄉(xiāng)的知識(shí)分子會(huì)被整得更狠,流落在外鄉(xiāng)的還可能僥幸求生。”野夫見(jiàn)到的很多長(zhǎng)輩的故事,都是如此。他慶幸落難的時(shí)候,還是有人對(duì)自己非常的好,隨即又話鋒一轉(zhuǎn)—“但每個(gè)人的故鄉(xiāng)都會(huì)有勢(shì)利的一面,所謂世態(tài)炎涼,你都會(huì)在你的人生中遭遇到。羅馬有句諺語(yǔ):村子里面無(wú)偉人,一是在村里人眼中你什么都不是,二是可能會(huì)嫉妒。”
因?yàn)樵谕饷嬗悬c(diǎn)名氣,很多老鄉(xiāng)會(huì)找野夫幫忙。“有些忙,你是幫還是不幫呢?可你算啥呢?一介布衣。”
野夫曾在博客上寫(xiě):“我的故鄉(xiāng)過(guò)去傳說(shuō)的趕尸佬,就是要把那些充滿鄉(xiāng)思而流落異鄉(xiāng)的游魂,千里迢迢地也要接回家山。”
但現(xiàn)在,野夫打算終老于大理蒼山之上。
他托命于早年認(rèn)識(shí)的一位白族兄弟,哪天自己長(zhǎng)醉不復(fù)醒,就埋到蒼山腳下,女兒多年后歸來(lái),就能問(wèn)白族兄弟,墳頭澆上三杯土家自釀的玉米酒,就算入了土,回了鄉(xiāng),完成了一個(gè)命運(yùn)流離的江湖文人回鄉(xiāng)的旅程。
“我的歸屬不在出生的地方,不在汪營(yíng)鎮(zhèn),也不在利川,其實(shí)你不知道在哪兒。懷鄉(xiāng)懷的是精神故鄉(xiāng),不代表他愿意回到故鄉(xiāng)生活,像沈從文離開(kāi)湘西,一輩子不回去。”野夫說(shuō),他要享受客居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