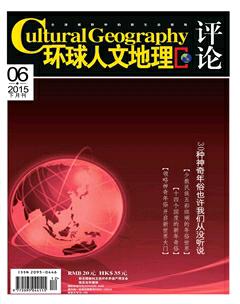近代京津社會與相聲藝術的成長
聶佳旭
中國傳統藝術中的相聲元素由來已久,可以溯及春秋戰國時期的俳優、唐朝的參軍戲、宋代的雜劇儺戲、清代的八角鼓等古代說唱藝術。然而正如馮不異先生所說,“可溯之源長,可證之史短”,現代意義上相聲藝術的真正形成則是在清代咸豐、同治年間,相聲藝術作為以說笑話或滑稽問答引起觀眾發笑為主要特征的曲藝形式,它源于社會生活,承擔了記憶近代京津社會的重要功能,分析相聲藝術的發展歷程是管窺其社會形態的一個獨特視角。相應地,近代京津社會的新陳演進同時也在相聲藝術成長中烙上了深深的時代印痕。
最初的相聲還談不上表演藝術,只是一門江湖生意罷了,其行業的規模在解放前一直還都是十分有限的。在這一相當長的時期內,相聲藝人的主要活動領域是京津地區的下層集市。相聲業內所謂的“北京是出處,天津是聚處”,說的就是相聲藝術起源于北京,發展于天津。其他城市如南京、濟南等個別娛樂場所零星也有相聲表演,但表演者大都是從北京天津流落去的藝人。所以相聲演出的集中地是不多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兩個,一是北京的“天橋”,一是天津的“三不管”。這兩個地方不僅是相聲的主要發源地、集中地,也是在相聲藝術發源發展史上關鍵之地。天橋,民間俗說其得名于“天子祭天祭農所行之橋”,位于北京南城的永定門內,是清末逐漸形成的民間藝人集中演出的地方,由于演出的紅火和商業的興盛,天橋的面積逐漸擴大。張次溪在《北平天橋志》中指出:至民國元年,天橋的界限已擴大三四倍,西北抵新世界,東北接金魚池,西南至禮拜寺,東南則達天壇壇門矣,地域擴張之大,可見其興盛之猛。天津的“三不管”位于南市一帶,因天津縣、法租界、日租界都不管而得名。規模不比天橋,也是重要的服務類游藝場所和商品集市。
清代的京城,人的身份地位與其住所位置是緊密相連的。而天橋所在的南城是平民區和貧民區,居住在那里的人大都是貧賤清苦出身,也包括外地涌入京城的趕考的、做生意的和其他游民。時至晚清,帝國政權日薄西山,旗人的鐵桿莊稼倒了,不少在旗的子弟也不得不紛紛從內城地帶搬離,他們中的一些下層民眾甚至流落街頭,幾乎無計活口。在那時,偌大的北京大概只有天橋能給他們一條活路。因而這一帶也就成為這一批新貧民的集中住所,最早的相聲藝人與其他民間藝人一道,都是在這種情形下來到天橋作藝為生的。其中著名的朱紹文,藝名“窮不怕”,是“天橋八大怪”之一。他生于1829 年,卒于1903 年,漢軍旗人。幼曾讀書,有個秀才的功名。后又曾習京劇,常靠演戲、教戲維持生活,因咸豐皇帝去世例行國葬,讓老百姓戴孝,并勒令一百天不準演戲、動樂,戲園子被迫關閉,并無隔夜之糧的朱紹文為了果腹充饑,流落天橋一帶,靠說笑話、唱小曲討幾個銅板,維持生活。他手里敲打的竹板上刻著:滿腹文章窮不怕,五車書史落地貧。就這樣相聲在北京落地生根。
作為京師門戶的天津地處交通要沖,歷史時期的傳統經濟貿易就已十分發達。晚清洋務派有在此興建了天津機器局,修筑了鐵路,開通了電報,設置了郵政,興辦了近代工礦和企業,城市經濟迅猛發展。尤其在《北京條約》簽訂后,開埠的天津九國租界并立,后來租界的總面積超過舊有的城區面積的8倍,可見城市發展之速。同時天津從歷史上附屬于北京的門戶城市逐漸轉變為溝通中外南北的外貿型工商業城市和華北經濟中心,在衣食住行等物質領域的近代科技和生活元素,到精神層面的社會文化元素,這些異質的進入和逐步深入,打破了傳統城市生活原有的平靜,改變了城市的格局和結構,也豐富了市民生活尤其是底層市民的文化生活。城市近代產業的興起吸引了大量的勞動力,也催生了一大批服務、餐飲、娛樂等行業。位于天津南市的“三不管”是河北山東等鄉下的販夫走卒進城的交通要道,一定程度上可說是天津的“天橋”。前來游逛“三不管的”的人更是是五行八作,多有城里的建筑、搬運、清潔、鐵路、煤炭等行業的工匠以及店員伙計、人力車夫、進城做工的莊稼人等等。詼諧的天津風情也是他們常常喜歡“苦中作樂”,結束了一天的辛苦勞作,一點點錢可以逛得高興快活。此處雖在規模上不及北京天橋,但在娛樂風氣的程度上則過之,因此成了又一塊容納相聲立足的寶地并令其風生水起。
進一步地說來,北京、天津的近代社會變遷這個大背景催生出一個低端市俗娛樂市場,相聲得以發展的機遇就源于很好的適應了這個市場。其一,天橋、“三不管”等地均屬貧民聚集地,但他們又不單是貧民,而是一群傳統文化意識影響下的“大家子”出來的人,有的甚至是破落的旗人貴族。他們雖然窮苦,但由于過去生活習慣的影響,卻有精神消費的需求。但如果讓他們請科班堂會,哪怕是到戲園子聽散戲,只怕都已財力不濟。相聲的演出成本低,向觀眾收取的費用也相對低廉很多。相聲憑借價格上的“制低點”,搶占了弱購買力娛樂市場的制高點。其二,云集在天橋、“三不管”的人們大都被主流社會及宗族排斥在外,這種情形下的人對于皇權、族權有一種逆反的附上心理。比如說單口相聲所用的醒木,藝人們常炫道該木天下只有七塊,分別是皇上的“龍膽”、娘娘的“鳳霞”、宰相的“運籌”等等,這種“七木同源”的說法相聲藝人通過這種方式進行自我標榜和抬高,這同時也是對受眾群體身份地位的拔擢與肯定,相聲的這種深含這傳統名分元素的說辭很符合其受眾的心理。其三,去游逛天橋、“三不管”的人大多是在城中做苦力,受勞役的鄉下人。他們的大多數時間在從事辛苦的體力勞作,沒有過多的空閑。在難得而短暫的休息時間里,一般能聽完整大部頭的大鼓、評書,而相聲小段恰如其分地滿足了以上情形。如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因素都從各自的方面共同起效,也從各自方面說明了相聲藝術在近代京津社會應運而生的必然性。
傳統相聲經歷了晚清民國社會新陳代謝的披瀝已有了長足的發展。作為一代之藝術,它必定是深深切中了當時社會狀態的發展特點和要求,與社會變遷都有著緊密的關聯。在那段灰色的年華里,相聲藝術以近代京津社會城市變遷的浪潮為溫床,實現了自己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