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熊:藝術要追求正大氣象
李懷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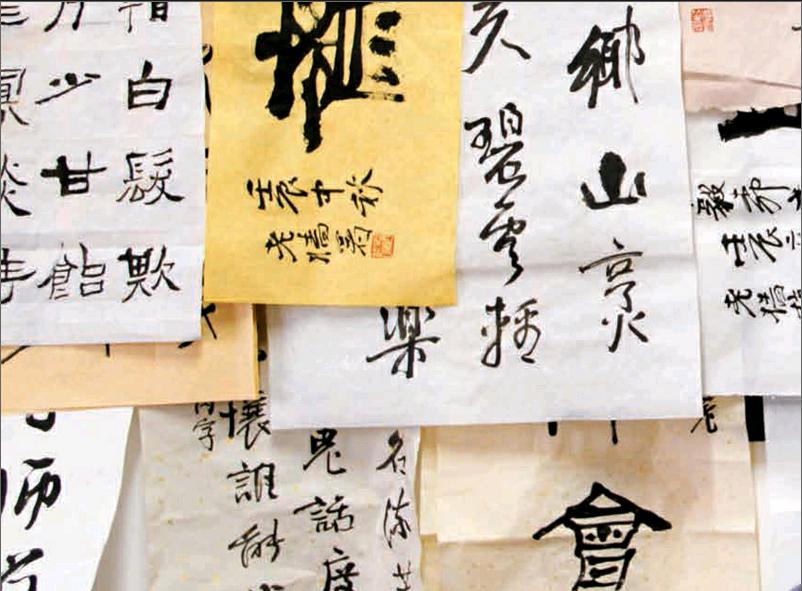

趙熊先生的書齋名為“風過耳堂”,每天刻印、寫字、畫畫,偶爾寫詩,與朋友唱和。他有和朋友詩云:“六十年來住舊京,紅塵慣看變流行。短長濃淡真人秀,榮辱浮沉假道情。聲色綿綿亡犬馬,江河滾滾損雄英。云煙未絕群峰亂,但眺青山不問名。”
1949年2月1日,趙熊生于西安。祖籍紹興,在道光年間,祖上考中進士到西安來當官,從此定居。趙熊的父親做了一輩子銀行工作,總是鼓勵兒子多去讀書。趙熊喜歡書畫,后來大伯帶他拜陳少默為師學習書法篆刻。
少時個性比較內向,趙熊常常一個人躲在家里,看看書,寫寫字,拿塊石頭刻刻印章,隨便畫一畫,家里人都說這個小孩在做正經事,不去打擾他。趙熊說:“書法如果有童子功當然最好。按我的理解,對當代人要講童子功,好像說天書一樣。因為現代生活的環境已經不是用毛筆書寫,而是一個硬筆時代甚至就是—個鍵盤時代,連硬筆都不愿意寫。但是,學書法相對來講越早越好,因為早一點的時候就相當于一張白紙,按照正式的法度,落的毛病比較少,上正路比較快。年紀越大,積習越深,自己有很多不好的書寫習慣,再要進入傳統的技法層面上學習,兩者經常要互相擰勁。從這一點講,童子功恐怕有意義。”
趙熊讀初中時,新來一位班主任,主張學生每個星期寫上幾張毛筆字,當作業一樣。這正好和趙熊當時的心態切合在一起,他開始比較自覺地臨習字帖,投入情感。1965年初中畢業,趙熊報考西安美院附中,專業課通過了,到最后綜合審查卻沒有通過,上面沒有任何解釋。“文化大革命”開始,趙熊應要求寫大字報、畫漫畫。他回憶:“我們當時就是披著馬列主義的外衣,用篆刻的形式,刻點毛主席詩詞,刻點豪言壯語,全都放到批判專欄上去。在陜西,“文化大革命”期間反倒是以革命的名義,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些藝術傳統。”
趙熊在小節上比較隨便,大節沒考驗過。從小學五六年級一直到初中,操行評語上經常是“不拘小節”。“文革”時興“忠字畫”,畫家向毛主席獻忠心,趙熊說:“對毛主席忠,要真正地忠在心里。”這種性格使他在一些事情上受過挫折,反倒刺激了他,使他將生活的重心放在喜歡的書法篆刻上,遠離政治。“文革”爆發不久,朋友送他一本《道德經》,他讀了,感覺很能安撫自己的心靈。他曾在一把扇子上寫了四個字:“居地心淵”,這是老子的話:“居善地,心善淵。”有一位原來的小學校長看了以后很吃驚,問他:“你敢寫這個東西,你真能做到這樣?”
趙熊學篆刻比書法稍晚,因為當年字帖比較好找,印譜比較難找。他從學習秦漢印開始,這可能也和性格有關系,他說:“秦漢印是正大氣象。學術界認為秦漢印是中國印章歷史上的第一個高峰,以前將古璽印排除在外,認為還不夠成熟。實際上,從當代的角度來看,秦漢印以前的古璽印里也有很多好作品,是另一種氣象,另一個高度。”
趙熊的印藝獨具一格,他是西安印壇最有影響的終南印社社長,卻與時風不太同流:“因為我不太和官場聯系,和企業家聯系也不太多。這是我性格中的一個缺點,所以這個印社的發展現在也有很多困惑。我一直有一個想法:文人雅事,好像也不宜跟錢和權離得太近。如果跟錢和權離得太近,人文的精神和風骨可能要受點影響。但是不跟錢和權離得太近,客觀上肯定影響這個社團的發展,得到的支持可能不夠。”
趙熊曾寫過《硯邊有思》:“濡朱染墨此生殘,換取霜絲意坦然。成敗丑妍皆幻象,人褒人貶是因緣。”他覺得在“風過耳堂”最好的狀態是沒人敲門,沒有電話,安安靜靜地沉浸在藝術世界里。他笑道:“如果中央臺來采訪我,問我幸福不幸福,我肯定要說幸福。我比較容易滿足,也沒有什么大志,所以感覺還是很幸福。”
《收藏·拍賣》:你最初喜歡印章是什么樣的因緣?
趙熊:和家里的影響有關系,因為家里有我祖父留的石頭,他是想刻來著,還沒來得及刻,有請別人刻的印章。他還買了一套刻刀,后來我們這些小弟兄都玩。刻得不好用砂紙沙沙沙磨了以后又可以從頭來,這也和十多歲的心智有關系。刻刀再往深里刻的時候,我就逐漸發現印章里是:方寸之間,氣象萬千。按照秦漢印就是寸印,基本上就是二到三公分。在一方很有限的尺寸里命題。因為刻的是人的名字,我不能給人家改名字,所以這個命題有限制,就像一個人在社會中一樣,不是純自由的,要受到人生、生活和社會的種種限制。在這個限制當中還要使自己相對自由,做到最大限度的精彩,實際上這和印章一模一樣。加上字與字之間要互相調配,講究和諧,但是在和諧的前提下怎么樣去生成很多的變化,這不是和人生完全是一回事嘛?現在來講相對自由一點,像過去我們那個時代不自由,找個工作分配到啥地方就是啥地方。這就跟刻印章一樣,就給你這么一塊石頭,軟也好硬也好,你都得刻。如果按照西方的美術理論來理解,中國的書法篆刻稱不上是一種純粹的藝術形式,因為它依靠的是漢字,而文字是工具。換句話說,這個藝術形式離不開工具性的制約,就不可能純粹自由,就是戴著腳鐐手銬在跳舞。它不像繪畫,繪畫里面有寫意畫,沒人去數你這朵花是多一瓣還是少一瓣,沒有人去注意你這片葉子是長了還是短了。但書法不行,必須在有限的條件下把這個東西做好。
《收藏·拍賣》:你從學秦漢印入手,后來有沒有專門學過哪幾家?
趙熊:說起來是學秦漢印,主要還是學漢印。因為當時秦印傳世得少,出土得少。最近二三十年,秦印出土比較多,看得比較多。秦印和漢印之間肯定有關系,但是秦印比漢印要活潑。西安是秦漢印的故鄉,這毫無疑問。從秦漢印以后,印章逐漸在走下坡路。一直到元明,有文人印之后才開始興盛起來。按我理解這是一種人文覺醒,它和過去工匠制印是兩回事。秦漢印是防偽辨奸的,是權力的象征。文人印更多的是閑文印,實際上和藝術相關。它有實用性,但更多是文人搞點藝術。文人印的大本營在江南,所以秦漢印以后一千年,如果以篆刻來說,在陜西是一片空白。后來像北方的齊白石,南方的吳昌碩這些大家,西安都沒有。所以,實際上我們學習篆刻的時候也很彷徨,沒有大家,就沒有老師。但是有一個好處,老師是一座高峰,但有時候也是一座圍墻,要辯證地看待。我們學篆刻有陳少默先生的指導,陳先生是人品最好,學問最好,接著下來是書法、鑒定、詩歌,但是他寫的詩歌也不是很多,現在我們收集到的詩也不過120多首。陳先生50多歲開始學篆刻,他有一方印:“少默年五十始好金石”,可以為自己做證。事實上,我們考證,他在此之前也刻過,可能沒有投入過多的精力。從50歲到70歲左右,大概前后有二十年,他才投入到治印。我從1971年跟陳先生學,要說刻印我可能比我老師學得還早,我是從1962年、1963年開始刻,但是他開始治印以后,和我們當時懵懵懂懂的小青年完全不是一回事。
《收藏·拍賣》:你早年如何學書法?
趙熊:我一開始比較感興趣的書法是漢隸,就是隸書。我也寫過唐楷,像顏真卿,寫后我就感覺有點法度森嚴,好像不太符合我的性情。隸書相較于楷書,給人感覺好像變化多一點,而且比楷書多一點古意。實際上,漢印的許多文字和隸書是非常相近的,所以這可能對我也有影響。后來還學過一段時間北魏,因為北魏的書法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是帶有很多民間書風的,所以形態上要別致一些,險一點,廟堂之氣不是那么重。行書上,我還是喜歡顏真卿一路的,我過去不太喜歡二王的東西,40多歲以后,覺得需要關注二王,學習二王。從書法流傳的發展史來講,王羲之是做得最好的,之后的米芾、王鐸,在行書方面寫得也很好。
《收藏·拍賣》:有一位先生告訴我說行書是最見功夫的。
趙熊:應該說行書最見性情,每個人寫出來的行書都有自己的風格。過去楷書最實用,但在今天書法創作中,行書應用最為廣泛,而草書則最能代表書法高度。
《收藏·拍賣》: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到現代,因為像鋼筆、圓珠筆、鉛筆等新的書寫方式普及之后,毛筆漸漸退出生活了,毛筆書法與現代生活的聯系不是很密切,會不會影響書法技藝的發展?
趙熊:從目前來看,好像還不會存在這樣的問題。像日本反倒是經濟特別發達的時候,保存了大量的手工藝作坊,給好多人提供了專門從事這種工作的機遇。當然這有一個前提,必須在吃飽喝足,生活無憂的情況下。這時候反倒有很多人來做這個事情,比搞群眾運動的效果還要好。時代的進步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以中間有一種經驗可以借鑒:于右任先生創造了標準草書,我認為這是兩個時代的誤會。最初的誤會是于右任先生做標準草書的背景,實際上是響應宋美齡和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正好于先生對書法有很深的研究,所以他從書寫角度和新生活運動相呼應。當然他本身也很喜愛書法,深入鉆研,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于先生沒有想到的就是硬筆逐漸地代替了軟筆,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于先生是一位大書法家,他把文字怎么樣寫都有書法意味,但是他把文字簡單地符號化了以后,一般沒有書法功力、沒有書法感悟的人寫出來的是啥東西?但是,從普及的角度是為了惜時省力,要改掉國民的陋習,提高生活的效率和質量。于先生百年以后,好多人又要把這個標準草書作為書法藝術來推薦,這是不是很奇怪?藝術何能標準,標準哪有藝術。弄了個標準草書,然后給它冠上藝術的名號,這肯定是限制藝術的。從社會進步、生活習慣的改變來看,對書法的影響肯定是有的。現在要求五六歲就必須要拿著毛筆去寫字,并且一直生活化地堅持下去,恐怕是不現實了。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可能會使有這方面天賦的人更集中、更精良地去做這件事情。
《收藏·拍賣》:于右任先生和沈尹默先生可能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書法家了。于右任先生是陜西人,書法中有蒼茫之氣,他對陜西的書法有沒有影響?
趙熊:有影響。但是相對來說,我感覺精神層面上的影響比較大。對具體的技法層面的影響不是很大,大家并不是趨之若鶩地都去學于右任的標準草書。
《收藏·拍賣》:于右任的書法氣象也很難學的。我在嵩山看過于右任的一幅書法“天地正氣”,寫得好極了。
趙熊:我自己的感受是,學習書法,學習篆刻,學習美術,你模擬學習的對象的風格如果太明顯反倒是壞事,你學進去以后,出不來。舉例來說,我比較反對喜歡書法的年輕朋友一上手就學柳公權。從歷史上看,學柳公權以后出來的也沒幾個人,這是客觀事實。不是柳公權的字寫得不好,他是寫得好,問題是他把字寫到極致了,沒有留下空間,你完全變成柳公權又不可能。從宋代到現代,總有人說顏真卿的字看起來有缺點,但是他的書法非常大氣,他留有空間,你進去之后還有可以挪身的地方,出來的余地大,所以從這一點來講,學顏真卿出來的人就多。
《收藏·拍賣》:于右任與沈尹默的書法完全是兩種風格,沈尹默是典型的江南氣韻,有溫潤的書生氣,寫得規規矩矩,書法是不是有地域的特性?
趙熊:過去一直有南人北人之說,也有南派北派之說。繪畫上有這種說法,書法上也有這種說法。特別是自從清代包世臣《藝舟雙楫》、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以后,崇尚碑學,所以對陜西的影響大,對南方肯定也有影響,但是對北方的影響比較大。最近我們在整理民國時期陜西的一些老前輩的書法作品和藝術經歷時,發現他們的書風真的有趨同之處,都是有寫北魏的經歷,好多面目出來之后都帶有北魏的特征,當然這跟包、康的倡導有關系,也可能跟人的地域性的性格有關系。陜西這個地方其實很好玩,我認為陜西是王道教化最早的一個地方,從周代下來十幾個朝代,王道教化比較早,所以長期的民風相對來講比較保守。當然,過去說“南人北相”,比如吳昌碩先生像個老太太,個子也不太大,寫出來的字,刻出來的印,很有金石味道,真是能力撥千斤。所以,不能想象從這么一個瘦老頭的手腕底下,能出來這樣的東西。當代,我也挺喜歡江南沙孟海的書法,包括他的印章。還有,像啟功先生胖胖的,寫出來的書法卻瘦瘦的。
《收藏·拍賣》:從西安來講,有碑林這樣的地方,對書法藝術的發展有沒有一個很好的借鑒作用?
趙熊:有,我們從小就去碑林,碑林那時又不收門票,隨便進去就玩,玩得高興就爬到石碑上蒙上一張紙,用鉛筆唰唰唰擦摹下來,拿回去玩。看哪幾個字好看可能回去專門照哪幾個字去寫,我這一代人恐怕都有這樣的學習過程,后來碑林收門票,進去不太方便了,這個學習過程就沒了。不過,在我們心中,碑林一直是書法的圣殿。
《收藏·拍賣》:近代的印家里面,你覺得誰比較有特點?
趙熊:近代的印家里邊有特點的很多,最有特點的應該是吳昌碩,他對篆刻的理解是最深刻的,技法是最豐富的。書法和篆刻實際上是一個人生命的外化現象。如果從生命的角度來講,一個民族在文化藝術方面要倡導的主旋律首先應該是光明正大。正大氣象,不排除花前月下,不排除小橋流水,但是正大光明符合生命生長的基本規律,如果大家整天都沉浸在小情調中,對生命是不能起到更正面更積極的作用的。所以,吳昌碩的東西是光明正大,于右任先生也是如此。
《收藏·拍賣》:以江南來說,像陳巨來、方介堪的印,你如何評價?
趙熊:方介堪是王福庵先生的學生。從藝術形態上說,王福庵和陳巨來達到了一個高度。精工印風雅致清蘊,具有雅俗共賞的特點,在社會上有著極強的生存空間,今天仍舊如此。比如篆刻中的藏書印是很儒雅的,而且書籍上面能容許你蓋印章的地方也不是太多,就很適合精工印的應用。雖然我自己刻寫意印比較多,但是碰到給朋友刻藏書印的時候,我還是盡量平和一點。
《收藏·拍賣》:印章漸漸地遠離了現代人的生活?
趙熊:拿書、畫、印三個門類相比較,篆刻肯定是屬于一種小眾藝術。造成小眾藝術的原因,最重要的恐怕是篆書的問題,因為什么文字都能拿來刻印,但是主流還是篆書。篆書從識讀上來講是一個障礙,好多人連繁體字都認不全,如何去認篆書。篆書在印章里還要做一些結構上的變化,這是一個難度。第二個從操作的角度上來講,篆刻不如書法那么方便,投入也比較大,做起來也比較辛苦。所以我現在非常憂慮喜歡篆刻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年輕人可以學可以玩的東西太多了,而且現在這個社會大家功利思想都比較明確,年輕人把大量的精力、時間、錢財投進去,還不知道這個東西有沒有回報。即便有回報,這個投入期也是很長的,這很影響篆刻藝術的發展。不過話說回來,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三十多年來篆刻的進步,真的要大于書法和繪畫的進步。
《收藏·拍賣》:為什么會這樣?
趙熊:主要是現在有大量的古代文字資料的發現。比方講,許慎在編《說文解字》的時候,他沒見過甲骨文。中國人到清朝年間才接觸到甲骨文,所以以前很少有人用甲骨文去入印的。到了近代,秦統一中國以前的戰國文字大量地出土,給書法和篆刻的學習與創作帶來了很大的沖擊,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收藏·拍賣》:印章的用石,有什么講究?
趙熊:從我自己的習慣,和純篆刻的角度來講,對浙江的青田石感覺最好。青田石就好像宣紙里的紅星宣紙一樣。當然,所謂青田石是一個寬泛的說法,青田石也有好壞。從比較高的品質上來說,青田石對刻刀的運動的表現是最到位、最可心的,是最好的。石頭的特點無非就是軟硬粗細,太軟了不受刀,線條不太容易塑造;硬了,用刀非常吃力,也不好塑造。青田石正好在中間,是不煤不膩,不硬不軟。所以,大家過去都最喜歡用青田石,但現在好石料越開越少。而且真正的好石料開出來以后價格越來越貴,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收藏·拍賣》:你覺得寫詩詞,對自己的書法和印章的修養,有沒有好處?
趙熊:絕對有好處。如果把書法精英化、專業化,實際上是把書法“矮化”掉了,把它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內涵抽掉了。大家整天都是寫“朝辭白帝彩云間”、“月落烏啼霜滿天”,如果不寫自己的東西,說明這個人沒有文心,或者沒有詩心。前人把“詩書畫印”這么一排列,表面上看好像只是順口,實際上也是很有道理的。詩肯定是第一,因為有文心詩心,才能牽扯到具體的藝術層面上來,然后才能講繪畫、書法、篆刻的問題。詩書畫印實際上是一個立體的東西。我退休以后時間比較充裕一點,所以就想在這方面綜合性地補一補。散文也在寫。有時候就是介乎散文和雜文之間的文章,也寫一寫。
《收藏·拍賣》:大變革的時代,藝術的發展有時候會有一種突變性,像詩書畫印的傳統在新的時代,會不會也有一些新的突破?
趙熊:這個比較難,現在這個社會的總體運行態勢是快,而中國傳統很多東西恰恰是慢。我有一個朋友說,在一個人生命里,很短的時間段,很有限的經歷,把一件事情做到頂端去,在前人的基礎上還想至少伸長那么一公分,都是很不容易。這種狀態是不符合現在社會運行的速度的。再加上更年輕的人,有工作的問題,房子的問題,孩子的問題,教育的問題,一大堆的問題,上邊有父母,年紀老了還有養老的問題,實際上壓力非常大的。身和心能夠進入一個都比較自由的狀態的時候,基本上也都到六十歲上下了。在這種社會環境狀態下,將全面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作為一種方向,對于他們來講實際上還是比較困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