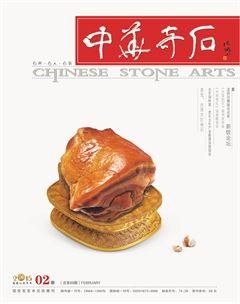把石頭賣給達·芬奇
黃永邊
外界看我們都是很淺的,沒什么文化,感覺你們表達不了什么深刻的主題,一旦拿到現代藝術的平臺上,卻上不了臺面,因為說不出更深層次的話。
把石頭賣給達·芬奇,不是別人,是達·芬奇。他是文藝復興的杰出人物,是藝術大佬。要想做大石頭事業,首先是要把石頭做成這個時代杰出的作品,這是我理解的做大。
但是,一般人很難獨立完成杰出作品,一定要讓藝術大佬摻和進來。所以,把石頭賣給達·芬奇是一種值得探索的路子。賣給達·芬奇的意思不一定是說從達·芬奇那里賺錢,而是與他發生關系的意思,關系越深越好。如果咱們能從習慣的“買賣”語境里逃脫出來,咱們可以將“賣”字換成“送”、“丟”、“借”、“當”、“訛”……
石界現在有幾種“做大”的方式。一是自我做大,拿單個的石頭去拼命宣傳炒作。第二是組織做大,熱衷于搞協會,把協會辦得規模很大,什么人都拉進來。
第三種是產業做大,是咱們需要的一個方向。關鍵是產業做大之后,我們似乎還缺了一些什么東西。
咱們一直不太重視石語體系,只重視單個石頭的解讀,把自己的一個石頭解讀的很好,文字配的很美,就認為已經做到很好了,但其實咱們只是做到了第一步,后面表現石頭的語言敘述與展示策劃都往往被忽略了。
咱們見到的許多展館其實是沒有策劃的,就是東西擺進去而已。咱們的石語體系建立起來之后要干嘛?就是建立石頭的人格形象,沒有人格形象的塑造,石頭的藝術是不成立的,它在社會上是不可能通行的,人家也不可能認識你,也不認同你,咱們經常是在石界自己說話,這個好,那個好,其實藝術界根本聽不懂,根本沒有進入他們的眼界,因為你的表述是沒有人格化形象的,人和石頭是分離的。你夸獎別人的孩子聰明可愛,其實是言不由衷的,夸獎了這一個,也可以用同樣的語言夸獎另外一個,不是自己有感情在里面。沒有人格力量。我們要把它們統一起來,就像夸獎自己的孩子一樣。你夸獎自己的孩子肯定帶有很深的情感,因為你將畢生夢想都寄托在自己孩子身上。咱們什么時候有人把畢生夢想都寄托在了石頭上?很少有人。我看到過很多人,都是很想急著告訴你,我這個石頭很好,急著賣給你,你不買,我想著這價是不是出高了,你買了,我惦記著是不是價錢出得夠高了。
塑造石頭人格形象,就要塑造有精神內涵的石頭人格形象。
我經常聽到講某個石友的故事,或者某塊石頭的故事,倒是很少從點連成線,沒有持續去關注,沒有去建立這種長久的內容。我舉個例子,說說“黃白黑”這個形象的深和淺。
從生活角度講,黃白黑其實走得很深,他走了很邊緣的地方,比如青藏高原的某個角落,一般人進不去的地方他會去,甚至很多人生感悟的東西,帶宗教色彩的東西,人與自然溝通的東西,甚至帶有詭異色彩的東西,他都感受到了。但是從人生意義角度,其實還是可以繼續深入挖掘的,挖出人生很普遍的意義,讓人一看到就感覺“黃白黑”與“我”的關系,看到“我”與石頭這樣建立的感情關系,如果能達到這樣一個層面,那么咱們石頭的人格形象就可以走向社會。整個社會也會像解讀一個很精彩的故事一樣,去解讀咱們石頭的人格形象。
所以說要用文學的手段。咱們現在沒有介入文學手段,最多就是停留在民俗手段上面,很多解讀都還是在重復解讀的層面上,達摩、觀音,沒有深入到更具體的地方,我們整個歷史人文那么豐富的東西為什么不能利用呢?因為自己首先沒有沉進去,所以外界看咱們都是很淺的,沒什么文化,感覺你們表達不了什么深刻的主題,一旦拿到現代藝術的平臺上,就上不了臺面,因為說不出更深層次的話。
咱們也可以在民俗的道路上走出文學性來,有這幾個人物可以做參考。
三毛,體現了命運與時代變遷,咱們解讀石頭的時候,我沒有發現有幾個人把他的命運和時代變遷解讀進去,你解讀的這個石頭有沒有命運感,有沒有時代背景?往往是沒有的。把整個中國文化當時代背景那往往是很籠統的。
一休,他有一些人性的沖突在里面,為什么大人愛看小孩也愛看,每看一集都會讓你感覺到這個小孩太智慧了,為什么智慧,因為人文歷史的東西都沉淀在這里面。
比如阿凡提,他是社會正義的化身,每一集故事都是很具體很形象的,因為他把很多民族文化的東西融合在了一起,而且那種幽默感,特別有阿拉伯文化的特點。
濟公,善惡糾纏,很有佛教文化的特點。
我的意思是,咱們可以把對奇石的解讀,跟文學作品聯系在一起,和這些文學形象進行一個對照。
好,現在回到正題。怎么把石頭賣給達·芬奇,怎么賣,走幾步路。
第一步,把石頭賣給他,你不要賣給別人,一百塊買來,三百塊賣給別人,沒什么意思的,沒有增值多少,那個石頭還是那個石頭。你如果把它賣個達·芬奇就不一樣了,事情變得一切皆有可能。
第二步,達·芬奇將石頭和《蒙娜麗莎》擺在一起,那么,達·芬奇擺的這個“攤”和一般的攤位是不一樣的。他在向社會暗示,你的這塊石頭和蒙娜麗莎是等價的。
第三步,讓石頭變成《蒙娜麗莎》,就是說你那個石頭,在達·芬奇的構思中,已經不是自然狀態中的石頭,而是藝術意味十足的藝術品。
第四步,跟達·芬奇的朋友們一起玩石頭。達·芬奇是那個時代的領軍人物,一大伙人都會和他玩在一起,所以你不要隨便捆人,捆綁名人要捆正宗的,要捆就捆達·芬奇,真正被人敬仰的,有代表性的,代表一個時代或者地域精神思潮的人,有文化向心力的人,你判斷對方是不是這樣的人,如果是,你義無反顧地把石頭賣給他,哪怕他不給你錢,你也賣給他。
《蒙娜麗莎》是一個時代的精品,而我們的很多精品石頭,是被當成一般的商品賣的,所以要有《蒙娜麗莎》的概念,以后每賣一塊石頭,你想想看這個可能是《蒙娜麗莎》,說不定就不會那么急著去賣,你能將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和你的石頭聯系在一起,你已經是一個藝術家了,你的展館就變為一個有時代精神價值的精品館,那就不是一般的東西了。
達·芬奇的這單“買賣”做成了,接下來就可以做這個“大作品”了。因為你有了文化“背景”。有了“蒙娜麗莎”這個藝術參照系,你就可以開始一般人沒有開始的“創作”了。
一個時代的大作品,需要什么呢?
首先,你要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咱們一般怎么做?就是羅列很多展品,和一個地方政府做業績報表一樣,做了什么,一個一個羅列出來。我們一般的展館也都是這樣做的,我這幾年買了什么石頭,賣了什么石頭,都擺在那里讓人家看,人家夸你,你也能滿足。
其實你就是把石頭拿回家了而已,并沒有與石頭建立什么聯系,更談不上感情。
其次,你要成為時代鏡像的表現者。掌握生活或者社會變化的一種規律,用情感去表達他,你喜歡這些石頭,外人只看到你的石頭不錯,卻沒有看到你與石頭發生了什么感情,你只是向外人證明這塊石頭不錯而已,所以要把感情帶出來。
再次,你要是時代真相的表現者。你的石頭展現要有明顯的精神上探索的特點。看完一個展館,咱們像看完一場電影一樣,你會去思考,到底為什么是這樣子的,它這樣拍,到底要告訴人們什么東西,如果一個展館讓人家覺得主人有認真思考,是按照藝術的方式來編排石頭,展演石頭,那就不會被人輕易的否定。
單獨幾個導演拍出好電影是不夠的,要有一群一流導演,電影才能讓我刮目相看。
達·芬奇的朋友們,都是一個時代里有文化創作實力的一個群體,咱們要找這樣的群體,比如你那個地方有一流的作家一流的畫家一流的書法家,你要把這些人聯合起來,進入奇石欣賞的領域里來,他們會共同產生一個文化效應,這個過程都需要這些人的介入,不是做好了請他們來看一下。看一下也沒看懂,夸你兩句走了,沒什么更深刻的關系。
這個創作群體有自己標志性的精神現象,在充分解讀的情況下從石頭中走出來。咱們經常沒有從石頭中走出來,沒有去表現社會生存狀態的內容,沒有藝術性,沒有標志性的精神現象,咱們經常很滿足于自己的石頭擺出來,而擺的怎么樣是真正考驗我們水平的,咱們有沒有后續創作力就看這個了。
什么叫標志性的精神現象?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精神現象。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報告文學,八十年代初的詩歌,八十年代中期的小說,九十年代后的書畫復興、持續多年的文物收藏熱,都構成了這個時代的精神文化現象,石頭文化也曾經幾次差點出現在風口浪尖,但因為都處在文化大佬們的視野邊沿,缺少評論界獨具深刻內涵的文化解讀,而一再喪失了它成為文化復興標識物的機緣。
咱們放松一點神經,不妨娛樂一下,沒有贏得引領風騷的時機,就回到文化生活的起跑線上,到路邊去等達·芬奇,在通往羅馬的必經路口,說不定就等來了文藝復興的那伙大師們,咱們搞個小小的聯歡,模仿評選什么最美某某,咱們評一組最美石頭來玩玩,讓大師們對著石頭說:這個石頭嘛,確實美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