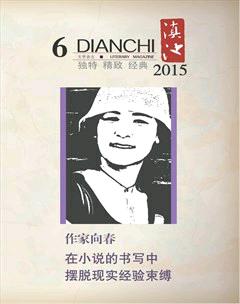再好的姑娘是人家的
向春
1
香夫人從一只麻袋里被抖出來,就嗅到了撲鼻的新鮮柏木的味道。她瞇著眼睛適應了一下光線,看到自己坐在一只柏木砌成的木頭房子里。她轉著圈看了一下四周,觸手可及的都是散發著松香的木頭,除了墻角的一只紅泥火盆和胡油燈的碗盞。看來這只胡油燈已經點了兩個時辰,或者可以說這盞燈等待了她兩個時辰,燈油盡了,火苗昏昏欲睡。香夫人給燈添了油,坐在火盆邊上烤身子,她被驚嚇得出了幾身冷汗,衣服濕漉漉的。
她回憶幾個時辰前,她和達拉特王爺在王府里吃肉喝酒。王爺醉眼惺忪地說,達拉特最好的馬奶酒就著義和隆最漂亮的女人,本王爺三生有幸啊。王爺的意思是香夫人秀色可餐,美酒就著佳人,真解饞呀。
香夫人說,跑馬地遭遇不測,愧對王爺的一片盛意,心中有欠呀。
王爺說,哎,夫人不要自責,跑馬地不長糧食那得怪跑馬地呀,母豬不下崽那得怪母豬呀。說到底是王爺的跑馬地不爭氣。夫人如果能陪本王爺共度良宵,跑馬地這一年的租銀就免了。
五千兩銀子免啦!五千兩啊,普通人家能娶一百個女人,王侯之家至少也能娶兩房夫人。香夫人的臉紅了,沒想到一個香夫人這么值錢。
可是香夫人是矜持的,她羞赧著繞過這個話題說,其實,我來王爺府是——
王爺說,哦,夫人有別的事?
香夫人看上去很為難,咬著下嘴唇,斟酌著。
王爺說,夫人,我們是親戚,有話不妨直說。
香夫人說,王爺人這么好,我實在是看不下去,我妹妹,你的小福晉——
王爺明白了,香夫人是為小福晉來的。一定是小福晉纓子在義和隆有什么丑事,瞞著王爺。他又想起了木篋里的馬糞,皺了皺眉頭。
香夫人說,她做閨女的時候,是喬家對她管教不嚴,現在貴為福晉,她還是不顧體面,這不,一到義和隆就和下人搞到一起,我們說不得問不得——
王爺從炕上站了起來。
這時外面有一點嘈雜的聲音,王爺說,進來!
進來的是小福晉的隨從,他風塵仆仆,用余光瞟了一眼香夫人,氣憤地對王爺說,小福晉在義和隆不守規矩,和下人來福明鋪暗蓋,特來告知王爺。
王爺又一次摔了奶茶壺。
香夫人嘆著氣說,王爺不要生氣。跑馬地的事你可能有所不知,是小福晉指使人給白歐柔種子調了包,致使跑馬地顆粒無收。她仇恨我們楊家,可她不能不顧達拉特的利益。還有,她派親信給狼山上的曾格林沁送糧草,結果王爺府遭到了第二次圍攻——
最后一句話點了死穴,王爺跳起來了。馬上派人到銀庫查賬,果然從小福晉手上支走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銀子——
就這樣王爺當著香夫人的面寫了休書。派人立刻召回小福晉,打入冷宮。
香夫人端起酒杯給王爺敬酒,一只玉手伸在王爺的面前竟有些發抖。
王爺并沒有用手去接酒杯,而是長滿胡子的嘴湊近酒杯,有聲有色地吸著馬奶酒,人先醉了。
之后他仰天大笑,重復了剛才的那句話,夫人如果能陪本王爺共度良宵,跑馬地一年的租銀
就免了。
香夫人笑而不答。
王爺說,夫人若有疑慮,立字據為證。
這是一筆愉快的交易,字據立好,各持一份,所有的仆人一揮而下。王爺提議喝交杯酒,香夫人知道機會來了,她半推半就端起酒杯,把提前放進水袖里的東西撒進酒杯里。可是聰明的香夫人做夢也沒有想到,達拉特王爺也用同樣的手段給她的酒杯里下了藥,不同的是下的不是蒙汗藥,而是春藥。他們分別喝了對方送上來的酒,達拉特王爺沒來得及寬衣解帶就拉起了二尺長的呼嚕,而香夫人臉色酡紅,意亂心迷,她到處找她的斗篷打算一走了之。可是她好像進了迷宮,轉了幾個來回沒找到出去的門。就在這時,所有的蠟燭都滅了,她聽到了風一般輕的腳步聲。接著有手伸出來,她被小心翼翼地捂了嘴,放進一只寬大的口袋里,抱在了一頂肥碩的馬背上。這個劫持者動作輕柔的程度,讓她以為是有人跟她開玩笑。接著她被帶上了路,根據身體的角度和馬蹄的力度,她知道他們在向高處走。風越來越大,空氣越來越涼,有人還在麻袋上披了一件棉襖。她明白,她被帶到了山上,就是義和隆背面屏障似的狼山。想到狼山,她就知道自己遭遇到了什么。狼山是土匪出沒的地方,她已經伏在了土匪的馬背上了。
那么香夫人此時是坐在狼山上土匪造的一只木頭房子里。這房子真是精巧,像她手里的一件女紅,精致而且舒服。土匪里還有這么手巧的人嗎,憑這一手好手藝還用得著當胡子?這里過早地點了火盆,暖和得像是義和隆清明時的春天。此時她的心定了下來,種種跡象表明,這不是一個不安全的地方。
一場虛驚之后,香夫人覺得累了。她摸到了一只木頭床想靠一會兒,床邊有一條木幾,上面是一盤奶食,有金黃的奶皮和雪白的奶豆腐,還有一壺奶茶,伸手一摸是熱的。難道這里的主人是個蒙古人?可憑著她女人的直覺,這房子是嶄新的,沒有人住過的。那么這奶食很可能是一個
蒙古人為她準備的。
她往床頭上一靠更是吃了一驚,床頭上有一只和他家里一模一樣的紅木算盤,這一發現揪緊了香夫人的心。這個人是認識她的,這個人是為了救她的。他把她帶到這里來,為她安排了這一切。此時的香夫人不是害怕,是好奇。究竟是誰這樣做呢,為什么要這樣做呢?
既然這樣了,那就等天亮再說。她上了床揭開被子,“喵”地一聲叫,嚇了她一跳,被子里鉆出一只貓來,毛色純白,天藍色的眼睛盯著她看。她伸手一摸被子,被子是熱乎的。她明白了,這只貓是給她焐被窩的。她鉆進被窩,把那只貓攬進懷里,心里竟有一絲被嬌寵了的喜悅。她一揮手扇滅了胡油燈,熄了的燈芯冒出熟胡油的香味,清白的圓月就從木頭窗格子里篩進來。
她聽到不遠處傳來馬頭琴的聲音,隨著風的吹向時輕時重,嗚嗚咽咽的。香夫人知道這首蒙古族民歌,叫作《再好的姑娘是別人的》。這首歌的曲調讓她心里變得安頓,也變得興奮。讓她想起那年義和隆的中秋節,樓下辦堂會,她和小酥在閣樓上相親。她看到叫苗麻錢的那個后生,器宇不凡眼睛發亮。他是妹妹小酥挑剩下的,可小香想嫁給他。可是,揭開蓋頭,她看到的不是他。她和妹妹都搞錯了,他們都看到了不想嫁的那個人。世界上可以有這樣的陰差陽錯,僅僅半個時辰,兩臺轎子從喬家一起動身,她和小酥長得一模一樣,在途中有人不小心調換一下就行了。可是沒有。永遠沒有了。她緊了緊被窩抱緊了貓。她的心開始等待,心情變得那么柔軟甚至是妖嬈。就這樣她枕著馬頭琴時斷時續的聲音睡著了。
早上推開門,是凈面的熱水和早飯。她麻利地拾掇好自己,專心地吃飯,她做的一切是那樣從容不迫。之后她走出院子,看到前面是一棵粗壯的柏樹。她站在柏樹的下面,看到木頭房子的四周是高高低低的房屋和帳篷,影影綽綽的人們在練兵,廝殺聲不斷。這是一座軍營,圍住了木頭房子,她可能是走不掉的。
可是誰說香夫人想走啊?
到了晚上,天空中掛著最圓的月亮,馬頭琴聲如期響起。她推開窗戶,看到了那棵柏樹,歌聲就從那棵柏樹下響起。
鴻雁展翅向南方
芳草低頭躲秋涼
含淚告別阿爸阿媽
再好的姑娘是人家的
這聲音在哪里聽過呢?這聲音太熟悉了,太好聽了,這聲音哪里聽到過呢?
香夫人的心亂了。她慢慢地解開一頭黑發,用一只木頭梳子細細地梳理,從頭頂到發梢一遍遍地梳理,直到頭發像一抹胡油一樣滑亮的時候,她想起了那個蒙古男人——達拉特王府的管家,騎著一匹高頭大馬到義和隆的喬家為纓子提親的蒙古胡達。
就是他,曾格林沁。
她想起了作為胡達的曾格林沁看她的眼神。
香夫人的心突然兔子一樣地跳了起來。這種心跳在她見到麻錢時沒有過,見到板凳時也沒有過。想起曾格林沁時心就這樣跳了。
第一次在喬家見到蒙古胡達時,香夫人看到了人才出眾的曾格林沁。可是因為他的身份是來給纓子提親的,對纓子的厭惡,香夫人自然對他產生了排斥。所以香夫人的表情是矜持的,她要用骨子里的高貴把她從纓子里區分出來。曾格林沁躲閃又熱辣的眼光讓她渾身有著說不出的舒坦,像陽光在她身上摸來摸去一樣,那個時候他覺得這個男人真好啊。
果然這個草原上真正的男人看上的是她小香,尊貴的香夫人。香夫人的嘴角露出了一絲笑容。
每天他可以聽到曾格林沁的歌聲。仿佛日子就要這么過下去了。晚上馬頭琴伴著水一般的月亮升起,香夫人的心已不能承受月色之重。木頭房子四周的人們磨槍擦彈,在為一件非常嚴峻的事情做準備。
天就這樣冷了,香夫人開始想義和隆想自己的孩子了。
這是一個太陽光芒四射的晌午,香夫人覺得自己應該離開了,應該走了。曾格林沁只是想救她,她不應該等待什么。
她把木頭房子里的東西按原來的樣子放好,她要走了。下了山坡,一匹馬正在悠閑地吃草。她看到這匹吃草的馬背上備著一副雕花的馬鞍。這副馬鞍刺得她眼睛有點疼。這個疼是一個暗示,她可以騎著這匹馬走了。于是她跨上了馬背。周圍的人都在磨刀霍霍,仿佛沒有人看見美麗的香夫人越馬而去。
下了山香夫人就聽到飛機在上空盤桓,一群群逃難的人哭天抹淚的,一打聽才知道日本人已經打到了西山嘴,五原縣的人已在屯墾隊的安排下轉移到了強家油坊,各個村子堅壁清野,恐怕連一只麻雀都找不著了。
太陽快下山的時候香夫人調轉了馬頭,她往狼山上奔馳,她為自己找到了返回狼山的充足的理由。她趕得很急,仿佛急著回家那樣揮動著馬鞭。夜色下她徑直走進那所木頭房子,松了口氣。房子里又燃起了火盆,一壺奶茶冒著氣,那只雪白的貓撲進她懷里。
這一夜馬頭琴聲沒有響起。外面似乎很嘈雜,人嘶馬鳴。黎明她聽到一個人在門口徘徊,像樹葉那樣輕輕地飄動。香夫人的眼里流出了眼淚。可是樹葉飄動得漸漸遠了。她推開門,看見門前的那棵柏樹上拴著一匹高頭大馬。這匹馬香夫人見過。她向柏樹走過去,馬嘶鳴起來。之后,天地是那么安靜,她聽到了柏樹下螞蟻搬家的聲音。
“夫人。”
聲音從柏樹后面發出來的。
“田野里的海納花開了有敗的時候,可是我的心發了芽就不會枯萎。草原上的駿馬飛馳千里都知道回家的路,我只把一個女人當成我的家。”
“夫人,我要下山干活了。窩子里有我的弟兄保護你。你等著我回來。要是我回不來了,我的弟兄會送你下山回家。夫人,我們分別向著相反的方向走,都不要回頭。如果我回不來,我不想讓你看到我是誰。”
香夫人背過身去往木房子走,那個男人牽了馬往山下走。他們都沒有回頭。香夫人聽這個男人的話。她走進木頭房,噼哩啪啦地打算盤。直到算盤珠子飛起來。
從此,香夫人站在柏樹下不停地向遠處張望,直到眼睛酸了淌下淚來。
就這樣狼山迎來了一個新的春天。曾格林沁帶著他的人馬回到了狼山。木頭房子外一片歡呼,殺羊宰牛猜拳喝酒,熱烈得空氣都要燃燒起來。二更以后狼山靜了下來。馬頭琴聲如期響起,那如泣如訴的聲音隨著一個男人的腳步近了。到這間木頭房子以后,香夫人第一次沒有拴門,她用一根青草挽住門拴,只要一個人伸出手用上比微風大一點點的力氣,這扇門就會打開。
香夫人的手里一直打著那只紅木算盤。
“夫人,我第一次見到你是在義和橋下。前一個晚上我做了一個夢,一枝海納花張開嘴對我說,我就在義和橋下。天不亮我就動身了,當我走到義和橋下時我就看見了你。”
香夫人手里的算盤頓了一下。
“你穿著一件蔥心綠的綢衫走進了大盛魁,你掏出碎銀子買了一把紅木算盤。轉過身你看見了我,看到我你是那么驚異,你張了一下嘴,露出了粉紅的舌尖。從那一刻起過去三十多年的曾格林沁死了,我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只想為一個女人活著的男人。我看見你慌亂地躲開我走了,從你的身上掉下一只繡帕,我趕忙塞進了我的懷里……”
香夫人站了起來。
香夫人開始全身發抖。算盤珠子全亂了。之后跌坐在木頭凳子上。但是手里的算盤沒有停。
這個男人愛上的是她的妹妹小酥。錯了。
“夫人,夫人,我曾格林沁這樣做讓你受苦了。我想讓你做我的女人,可別人說我是個土匪,腦袋別在褲腰上,說不定哪天就身首分家。你如果愿意就打開門。如果不愿意,義和隆的日本人已經全部殲滅了,我明天送你回家。”
算盤聲停了,天地一片岑寂。曾格林沁聽到里邊的女人拴上了門,動靜很大。
天不亮香夫人就跨上了那匹馬,她頭也不回地下了山。曾格林沁手下的一個叫狼山的漢子一直跟著她進了義和隆,他是曾格林沁派來給香夫人的家人證明香夫人的清白的。
香夫人直接到了順子所在的牛犋。她對倉皇迎上來的順子使了個眼色。順子又給牛犋上的幾個漢子使了個眼色,狼山束手就擒。
狼山被綁在五原縣衙門外,衙役放言,只有胡子頭子曾格林沁出面才能換回狼山的腦袋。當天晚上,曾格林沁騎著他的高頭大馬來到縣衙門前。狼山一聽到曾格林沁的馬蹄聲就喊,曾哥,那個女人是一匹母狼。你看錯她了。我要替你殺了她。
曾格林沁跳下馬,抖了抖身上的塵土,張開胳膊讓人捆綁他。他說,放了狼山,這事兒與他沒有關系。
狼山說,你們放過曾格林沁,他沒動那個女人一個指頭。你們放開他,消滅水川伊夫的那一仗是曾格林沁帶著弟兄們截斷他們的后路,把他們逼進兆河渠的泥淖里的。我們冒充是大青山的游擊隊,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放了他。
可是曾格林沁搖搖頭說,那是我手下的弟兄們干的,與我沒有關系。那時我正在狼山上守著一個心愛的女人。你們殺了我吧。
酥夫人跌跌撞撞地上了義和橋北,就在這時,她看見一片人黑壓壓地涌過來,一輛囚車開過義和橋,橋身不堪重負地吱呀呀地直響。
這可能是五原縣光復以后最熱鬧的一件事。
曾格林沁落馬后,五縣縣長審訓他:
黃羊木頭的那批煙土是你打劫的嗎?
是。
屯墾隊的東西你也敢下手?
倒騰大煙的人都是我的敵人。楊家的種子是你調的包?
是的。
楊家與你無怨無仇,為何下此黑手?
我不認識楊家。我只知道那批種子是要種在跑馬地上。跑馬地是蒙古人的牧場,我要它回到蒙古人的手里。
那香夫人也是你綁的票?
是的。
搶了東西還想搶人?
我們蒙古人以搶婚為榮。
那為什么又送她回來?
搶了她的人搶不來她的心。我不要一個沒有心的女人。
活捉水川伊夫那一仗是你冒充大青山游擊隊打的?
是弟兄們打的。我在山上的一個木頭房子里,天天喂我的馬,守著心愛的女人。
……
曾格林沁頂著一顆青皮大光頭,高大的身軀讓囚車顯得空間狹小。他迎著義和橋下的風走出去,他在義和渠渠背上高高在上地走著。像他上一年來到這里時一樣,他聞到這里的空氣真香,因為這里生長著他的女人。就是同一個季節。那一天他撿到了一只繡著一朵海納花的綢帕,此時正攥在他的手里。
曾格林沁他想死在義和隆。走出義和橋他回頭看一眼義和隆,他看見一個女人跟在看熱鬧的義和隆人們的后面,跑著,說著什么,跌倒,爬起來。
酥夫人一跌倒,曾格林沁的身子就要抖動一下。曾格林沁看到了她的女人,看到了他的女人的眼淚。這個女人瘦了,這么快就瘦了,他以為是為他曾格林沁瘦的,他的心揪緊了。他不會抱怨的,因為這是他心愛的女人,心上的女人,他愛她沒有條件。但他不知道這世界上有兩個一模一樣的人,這個女人不是他在狼山木房子里的女人。木房子里的女人不是他在義和橋下碰見的海納花一樣的女人——
他看到了他的兩個弟兄混在人群里,他看到那兩個弟兄在靠近他的女人,他的心一驚,這兩個弟兄是要報復他的女人。
酥夫人從地上爬起來,人們走得那么快,她沒有力氣趕上那輛囚車。她想說,不要死啊,不要痛心啊,那個女人不是這個女人啊,我要你活著啊。她張著嘴伸出手,在她又一次要跌倒的時候,兩個男人靠近她挾住了她,一把刀子在她眼前晃蕩。一個男人說,你這個蛇蝎心腸的女人,曾哥把心都掏給你了你還出賣他,你還有臉來這個地方?另一個說,把她兩個奶頭子剜下來給曾哥陪葬,讓曾哥到那邊去當下酒菜。這時他們聽到囚車上的曾格林沁發出狼一樣的嚎叫,這聲音凄涼、悲愴、哀怨、絕望,像一把把鈍刀戳在骨頭上。兩個弟兄一松手,酥夫人就蹲了下去。
鴻雁展翅向南方
芳草低頭躲秋涼
含淚告別阿爸阿媽
再好的姑娘是人家的
囚車拖著歌聲走遠了,酥夫人的眼前一片煙塵。緊接著另一隊人馬趕上來,向著囚車的方向馳去。酥夫人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那是她的男人苗麻錢,后面跟隨的還有王家的暢水、豐田和一些穿軍裝的人。
酥夫人開始往強家油坊的方向走,她要去看她的環環。太陽西斜時她撲在了環環小小的墳頭上。
當麻錢找到小酥時,她的棉衣蓋在環環的墳頭上,她趴在墳頭上雙臂抱緊了環環。她的血是從她的胸口流盡的。
楊板凳急匆匆地往義和隆趕,他要看看他的老柜,看他的香夫人有沒有奇跡般地出現在家里。他看到了一些陸續回家的難民,灰頭土臉的,但畢竟有了重返家園的喜悅。他腳底下就生了風,三腳兩腿就甩到了粉房圪旦,這是離義和隆最近的一個村子。這里空無一人,村里的人正在趕回來的路上。走近村口的一個茅草房,他餓了,圪蹴在門口吃干糧。這時他聽到了窸窸窣窣的聲音。他透過一張草簾朝里一看,乖乖,里邊一個女人的后背,雪白雪白的。她正在急匆匆地換衣裳。她好像很著急,胳膊抖抖索索的,咻咻地喘氣。板凳趕緊圪蹴下來,他不應該看人家女人換衣服。可是轉念一想,這個村子里沒有一個人,這個茅草房里是誰家的女人。他不由自主地又站起來,沒想到和正在撲出來的女人撞了個滿懷。
那個女人沒有看清撞在她身上的是誰,就撲通一聲跪下來,她嘴里嗚哩哇啦地說著什么,伴著響頭。
板凳退后一步說,你說甚?
這女人重復了剛才的動作和聲音。
板凳又退后了一步。他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日本女人,是一個漏網之魚。她整了一套中國女人的衣服換上想冒充中國女人。楊板凳恨透了日本人,日本人搶走了他的命根子香夫人,說不定早被他們糟蹋得稀松了。他們能日我的女人我不甚不能日他們的女人。他一個箭步上去拎起了這個女人,又摔下去,這個女人像一只皮球在楊板凳的手里起來又下去。日本人狗日的到我們后套來做強盜還帶上女人,要不是我們引水阻援,他們還在我們的鍋里吃飯哩,黑夜還在我們的炕頭上生娃哩。他越想越生氣。茅草房四周一看,正好有一口水窖,水是干了,可是有一個半人深的坑。他把這個女人扔進窖坑里,從茅草房里尋出一把銹敗了的鐵鍬,他開始活埋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不說話了,不作揖了,一鍬鍬的土撲在她身上,她不停地抖動著腦袋,好像怕臟。她先是坐著,后來站起來。先是背對著楊板凳,后來身子轉向楊板凳。先是低著頭,后來抬頭看著楊板凳。土馬上就齊胸了,她突然捉住楊板凳的眼睛,含情脈脈地看著他,眼淚吧嗒吧嗒地掉著,可嘴角輕輕提起來,笑,再笑。
楊板凳停下了手里的鐵鍬。他的心突然軟綿綿的。扔下鐵鍬,圪蹴在地上卷了一支旱煙。他聽得日本女人哽咽著叫了一聲“哥”。板凳的心水一樣的軟。扔掉旱煙,跪在地上拋土,把這個女人連根拔了出來。
從水窖里出來的女人跪在他的腳下,抱著他的雙腿,仰起臉,用很小的嘰哩咕嚕的日本話夾雜著中國話說,意思是,我是一個很年輕的女人,你是個男人,這里沒有一個人,你要了我再活埋我也不遲。之后她跪著挪著膝蓋把半身已經韁硬的楊板凳一點點推進了茅草房。這個女人脫光了衣服。
楊板凳的臉立刻像被扇了一巴掌一樣通紅。他轉身走出茅草房,靠著茅草房圪蹴下來,他不知道該怎么對付這個女人,他甚至后悔碰到了這個讓他棘手的女人。抽了一袋煙,對著里邊的女人說,你走吧,就當我沒碰見你。走出這里誰活埋你那是你的命。
這個女人能聽懂中國話,她點點頭。
楊板凳甩開大步離開這個女人,天將黑了,他要趕回義和隆。走開了五十多步,他的步子越來越慢。之后他往回折。他想回去告訴這個女人,她一定要裝成一個啞巴,隨便找個人家嫁了,但她保證一輩子不能說話。走回茅草房,發現這個女人伏在草堆上睡著了。他扯下他的老皮襖想輕輕地蓋在她的身上,讓她聽天由命吧。俯下的身子剛要直起來,他被一只手抓住了。這個女人徐徐地蹭到他懷里來,像一只吃奶的貓。她在他的腋下偎過來偎過去,仿佛他是她相濡以沫的心上人。
楊板凳被瓦解了。他跳起來抽掉了褲帶,大襠棉褲就掉在腳面上。嘴里惡狠狠地說,我操你個日本臭娘們兒。他縱身撲向她,懷著對日本人的痛恨,對自己牛犋的心疼以及對香夫人的思念,他要打垮這個日本人。就這樣他們在草堆上的一只老羊皮襖里翻滾,天亮時老皮襖濕透了。
楊板凳把這個女人當成一個啞巴“撿”回了義和隆的楊柜。
香夫人走進了楊柜,東家楊板凳揣著滿懷的喜悅和驚慌迎出來。楊板凳想接過她手上的包袱,香夫人皺了一下眉頭,閃開了。楊板凳尷尬地收回了伸出來的手,跟在香夫人的后面走。香夫人徑直走進自己的正房,關了門,沒有回頭。楊板凳在門口站了片刻,沒有聽到里邊的任何響動。無所適從的楊板凳給奶媽使了個眼色,奶媽端了熱湯走進了正房。
奶媽不敢看香夫人的眼睛,義和隆的人都說香夫人被胡子破了身,雖然九死一生可面子上比死都難受。可憐香夫人那么好強的一個人,怎么能經得住別人對她的蔑視。于是善解人意的奶媽避實就虛地說,哎呀,這仗打得家家妻離子散,好在一個個都回來了,我老婆子高興啊。來你喝口湯,我來抱抱寶貝疙瘩。
香夫人換了個姿勢把跑跑摟在懷里。她看著奶媽手里的湯說,這湯是誰做的?
奶媽挪了挪一雙小腳,乜著眼睛偷看了看香夫人的臉色說,東家在強家油坊撿了個啞巴,啞巴家里沒人了,求東家給碗飯吃,東家看我老了腰來腿不來不中用了,領回來幫我打個下手。
香夫人看了奶媽一眼,奶媽手里的碗就翻了。香夫人擺了擺手讓奶媽出去,說,以后茶飯還是你一個人來做,別人不要插手,外面的人不干凈。
回到楊柜的香夫人幾乎不說話,楊柜一下子住了兩個啞巴。其實她一進門就看到了那個啞巴,或者聞到了那個啞巴。她并沒有用眼睛看她。香夫人的眼睛不長在眼眶子里,是長在心上。所以她沒有看她,她用不著看她就能知道她是誰。
義和隆的人都說香夫人是從土匪窩子里逃回來的,早已被胡子頭破了身,所以讓聰明的香夫人說什么呢?楊板凳不敢看自己的老婆香夫人,他們再沒有彼此近身,很明顯楊板凳更怕香夫人了。夫人住在前院,他就住在后院,后院有一個很大的糧倉,總是黑洞洞的。糧倉的兩邊有兩個耳房,他和啞巴各住一屋。晚上月亮上來了,照得半炕通明,板凳的骨頭像被螞蟻啃酥了一般,欲望像決了口的水一浪一浪地嗆得他喘不過氣來,他開始絕望地呻吟。可是他不敢挪動身子,香夫人一直不睡,算盤珠子清脆的聲音滿院子回
蕩。終于有一夜楊板凳茅塞頓開,香夫人的算盤珠子不停說明香夫人沒有離開算盤,香夫人的算盤珠子響的時候是最安全的。于是他跳進另一間耳房把那個女人撂到糧倉里。
夜深人靜他們總是在這個糧倉里,鋪著麥子蓋著麥子,翻云覆雨。他可以那么放縱,像對待他的耬,想咋撒種由著他。像對待他的麥子,想咋捆就咋捆。像對待他的玉茭棒子,想咋揉就咋揉。想煮著吃烤著吃或者生著吃,他想咋地就咋地。他喜歡女人的聲音,就是在茅草房里老羊皮襖上的那種呢喃的聲音,他永遠沒有聽懂過,但他為那個聲音著了迷。他忘記了這是日本話,她是一個日本人。他已經深深地愛上了她的身體,一個男人愛上一個女人的身體才能愛上她的全部。他愛這個女人幾乎勝過了愛他的水和他的地。因為有了這個女人以后,他再沒有去看他的水和地。
他們像老鼠窩在糧倉里,身體像種子一樣飽滿而踏實。糧倉,糧倉,糧倉,楊板凳的天堂。
家里有糧食了,耗子就跟著進來了,肆無忌憚地前后院地竄。她偶然能聽到后院的那個女人被耗子嚇著了的聲音,那聲音是那么綿甜,像往她的胸口一針一針地扎。她貓著腰雙手頂在胸口上,無奈地呻吟。
香夫人把一只算盤扔出來,又把一只算盤扔出來,她扔完了家里所有的算盤,算盤珠子像羊糞蛋散了一院子。板凳趕緊貓下腰撿,嘴里嘶嘶地吸著,牙疼一般。
香夫人說,讓她過來侍候我。
板凳知道她說的是誰,嚇得撿在衣襟里的算盤珠子又撒在地上。他結巴著說,我來侍候你,她不會說話。
香夫人說,我不用她的嘴,叫她過來侍候我。
板凳只得去叫啞巴,他神色慌張地附在啞巴耳朵上說,千萬記住不能說話呀。啞巴神情鎮定,她用手勢對板凳說,永遠不會說話,即便暴露了日本人的身份,楊板凳并不知情。我只是板凳撿到的一個啞巴。這個手勢啞馬已給板凳打過無數次,板凳很熟悉了。無論發生什么樣的事情,板凳要一口咬定他不知道這個女人是日本人。
啞巴走進香夫人的正房,她沒有低頭,直視過去,笑。
香夫人看清了,這是一個很好看的人,牙齒細碎潔凈,臉是麥皮的黃中透白,細瓷的膩。這女人誰見誰稀罕呢,咋會是撿來的,這不是天上掉下金蓮花了嗎?
香夫人盤腿坐在炕上。她要繡花。她想她的妹妹小酥,她再不想打算盤了,她要繡花。她說,你上炕給我摘線,我要繡花。
啞巴垂著眼睛上了炕,她跪在炕上,不敢看香夫人。
香夫人聞到了一股很特殊的味道,這味道是從啞巴身上發出來的。這味道在哪里聞過,好像在哪家藥鋪子里或者趕廟會的粉樓里,香夫人皺了一下眉頭,一時想不起哪里聞過這種味道。香夫人說,你坐下吧,我可領受不起你給我跪著。
啞巴好像沒有聽懂,繼續跪著,雙手垂在兩只膝蓋前。
香夫人示意她盤腿坐下。
啞巴換了個姿勢坐下來。香夫人發現她不會盤腿,兩條腿僵著,一順兒拐著。香夫人撐好花繃子,啞巴開始摘線。香夫人看到了啞巴的兩只手,心突然被什么彈了一下。這雙手像十根蔥心兒,嫩的能冒出水來。這個女人的手不是河套平原女人的手。
香夫人說,你的家在哪里呢?
啞巴用手比劃著,在很遠的地方,來后套逃荒,家里人都死了,剩下她一個人。
香夫人手里的花針不動了,她想起來了,這個女人身上是麝香的味道。她想起來,那一年她到錦繡堂給母親抓藥,那藥里就有這味道,母親說這是麝香的味道。據說窯子里的姑娘都用麝香,是避免懷孕的。香夫人的手被扎破了。
香夫人抬起頭,想看出她臉上的風塵來。這個女人正用水晶樣透明的手指捻著絲線穿針呢。后晌午的太陽穿過潔白的窗紙照在她的臉上,她兩頰淡淡的絨毛像涂了一層薄金。她是那么專注,牙齒半咬著下唇又放開,嘴唇由淡漸紅。
她聽到門外焦躁的腳步聲。
絕望的香夫人兩只手捂在胸口上,一種疼從很遠的地方走近了,她咬緊了牙關。一個絕色的女人對任何女人都是傷害。她對啞巴擺擺手。啞巴悄然下了地。
啞巴拉開一扇門,聽得香夫人說,你不想嫁人嗎?
啞巴轉過身,半張著嘴。她半邊臉驚喜半邊臉恐慌,她不知道香夫人的意思,讓她嫁給板凳呢還是別人?
這時板凳從外面進來急促地說,就讓她做我們家的丫環吧,奶媽實在太老了。
香夫人沒有抬頭。自從從狼山下來她就沒有正眼看過自己的男人。她的嘴角掠過幾分鄙視,說,我看是我老了,你不想讓她做你的填房嗎?
板凳撲通一聲跪下了,女人沒有聽懂香夫人的話,看板凳跪下也就懵里懵懂地跪下了。
香夫人再次冷笑,她心想,這女人跟誰睡跟誰親啊。
板凳說,夫人調笑我吧,我不敢。
板凳低著頭,等待香夫人再次開口說話,或者表態。
香夫人并沒有接著這個話題。她的心口疼得厲害,擰著眉頭擺了擺手。
板凳雖然有點失望,但還是喜出望外,出門檻兒時竟跌了個跟頭。跟在后面的啞巴失聲“啊”了一聲。
到了后院,板凳蹲在糧倉前嘿嘿嘿嘿地笑個不停。啞巴聽不懂什么叫填房,她沒有聽懂香夫人的意思。但從板凳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一件好事情就要發生了。她從小接受的日本文化告訴她,一件事情要來臨的時候一定要內斂,像蒸一鍋饅頭寧可過一點頭也不能提前揭鍋蓋。眼前嫁給板凳這個老實巴交的男人是她最好的出路,一是她能活著,二是她能跟一個愛她的人活著。她什么都沒有問,繼續前晌的活計,雙腿一順兒坐著搖著小石磨,磨豆子。
板凳顯然膽子大多了,他蹭到啞巴跟前,摸她的腳,脫她的鞋。這雙腳真好看啊,圓潤無骨,腳趾像一串粉紅色的蓮苞。板凳把臉伏在她的腳上,身子就蜜一樣的稀了。他親著吻著,頭往上面磕,好像頭不想活了。
當最后一抹夕陽在糧倉的尖頂上消失,板凳就開始坐臥不安,他圍著糧倉轉,咻咻地喘氣,像有一只野獸要從身體里蹦出來。看到天有點陰,他就把一只木炭小火盆放在糧倉下,溫著。溫熱的麥子和溫熱的女人!
糧倉在楊柜是最雄偉的建筑物,這種造型還是板凳從口里帶來的。最下面用三個木頭樁子支起,上面交叉搭上粗壯的紅柳打底,再用葦子圍成圓柱狀,留個小門。框架做好了,麥草和了泥里外抹上,有心一點的人家還撿來一些碎瓷瓦片摁在上面,防雨雪防風蝕還好看。這樣的糧倉干爽透氣不積雨雪,放糧食十年不壞。夜靜更深時門拴了狗歇了,板凳像火苗一樣躥起來……
香夫人回到義和隆后,總是感覺到冷,其實天已經暖了,驚蜇了。尤其是妹妹小酥走了以后,她穿在身上的衣服像掛了霜,穿的越多越冷。奶媽說,叫錦繡堂的郎中看看吧,酥夫人給你做的棉襖絮的都是絲棉,不可能冷啊。奶媽的一句話提醒了香夫人。妹妹小酥她沒有走遠,她還附在這些衣物上,她恨她姐姐啊。香夫人不是不想救曾格林沁,曾格林沁是個好男人,是個好漢,可是曾格林沁活著她們姐倆就不安生,楊家和苗家就不安生。要想讓一切重歸平靜,她就不能出來為曾格林沁說話。可是讓香夫人料不到的是,她心地篤實的妹妹小酥走了,而曾格林沁卻活著。
老天總是和聰明的香夫人開玩笑。曾格林沁被麻錢率領的游擊隊和 35軍的人解救下來,和游擊隊的許多年輕人一起編入了正規軍,隨 35軍開拔到大同繼續打鬼子去了。一同去的還有她的兒子豐田和亮水。豐田和亮水崇拜曾格林沁,他們很快會熟絡起來。曾格林沁慢慢會知道義和隆有兩個一模一樣的女人,他會知道小酥的死。他會在思念一個女人的時候仇恨另一個女人。可是打完大同以后,豐田和亮水回到了五原駐地,這她當然高興,窩心的是曾格林沁也回來了,還當了什么長官,兵們一見了他就敬禮。她的胃里開始冒酸水兒,從她心底又浮起一種東西,那就是對曾格林沁的敬重。只有香夫人最清楚,他是一個多么好的男人,可是他愛的是她的妹妹小酥。
她開始羨慕她的妹妹小酥,有人愛她,得不到她的愛就為她放棄生命,這個人就是曾格林沁。小酥死得奢侈啊。
香夫人挑亮燈花,又披了一件衣服,這楊柜是多么清冷啊。一個女人沒了男人也就沒了熱氣。香夫人沒男人了嗎?有男人和喜歡一個男人是不一樣的,香夫人心里沒有這個男人。
黎明前,香夫人的窗前被一片火光照亮了。
可憐老實人楊板凳,只在糧倉下放了小火盆,小火盆里放了幾片牛糞,怎么就惹了天大的禍殃。糧倉的門本來是掩上的,可是用盡全身的力氣都跺不開。房后的順子是第一個來救火的人,接著附近的鄰居聞風而至,他們都聽到一個女人嗚哩哇啦地求救,仔細一聽,這個女人說的是日本話。
香夫人在現場看到,放牛糞的火盆里有一截幾乎燃盡的柏木木樁。
燒了楊柜的后院對香夫人來說幾乎是正中下懷。可啞巴是個日本女人,并且暴露給了義和隆,這楊家可就說不清了。
鐵錘鎮長的上任是被一把火點起來的。
首先到楊家救火的是楊家的渠頭順子。他看到東家楊板凳反穿著一條老棉襖,正在地上打滾兒壓滅身上的火苗。那個女人提著男人的大襠褲,她已經恢復了意識,不說話了,全身發抖。她的衣裳還冒著煙,像一截就要被風吹倒的破煙囪。
這時楊柜已經站了一院子的人。順子見狀上前對鄰居們說,謝謝鄰居們了,沒事了,大家回家吧,三更半夜的打擾大家了。
可是人們已經圍住了楊東家和那個女人。她說的是日本話,她是個日本女人!楊板凳窩藏這個女人,是想和日本人里應外
合!楊板凳是個漢奸!這時就有人揪住楊板凳的領子,你說,你為
甚要把一個日本女人藏在老柜,你想害死義和隆的人嗎?
啞巴女人向楊板凳打著手勢。這個手勢楊板凳很熟悉——無論發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我是日本人。
楊板凳說,大家誤會了,我從來不知道她是個日本女人。我是在回義和隆的路上發現了她,她打手勢給我說她無家可歸讓我收留她。我看她可憐,家里也缺人手,就當丫鬟用的。
她剛才給你打甚手勢?你說。楊板凳說,她意思是說,她對不起我,她騙
了我,連累了我。你胡說,她的表情不是這樣的。這時鐵鎮長身后跟著一幫人來了。鐵錘說,
好啊,沒想到義和隆還有沒來得及跑掉的日本
人。把她帶到二道橋活埋了。一個男人上來拎一只雞那樣把啞巴拎起來。楊板凳撲了上來。啞巴突然掙開那只手向楊板凳撲過來,她嘴
里惡狠狠地說著日本話,對楊板凳又扯又咬,做出抱怨他仇恨他的樣子。她咬楊板凳的時候,一根食指放在嘴唇上,她是在重復過去的手勢。
人們上來拉開黏在一起的他們,順子趁機把楊東家拽進旁邊的馬圈里。他把一直在掙扎著要出去的楊東家推倒在馬槽上,用一把馬料捂住了他的嘴。
鐵鎮長一上任就遇到了這么好的一件事,他要活埋一個窩藏下來的日本女人。他披著一件細葛布的新夾襖,站在二道橋的一道陽坡上。春風還有點刺骨,可是他身上熱氣騰騰,激動的心呯呯地跳。坡下的村民正在挖坑,他指手畫腳地指揮挖深一點。
啞巴的身體已經不再抖動,她偷偷地回望義和隆通向這里的那條羊腸小路,她想再看上板凳一眼,可是她更害怕板凳一時糊涂會出現在這條道上。她馬上就要死了,她希望埋她的坑挖的快一點,板凳千萬不要在這里出現啊。
坑終于挖好了,茍五蛋柱著鍬站在鐵錘對面說,鐵錘,這日本女人長得這么可喜,就這么埋了怪可惜了的。
這話說到鐵錘心坎兒里了。他站在陽坡上眼熱心跳的,是因為他看見了一個大盛魁賣的洋煙盒上才能看到的絕色女人。她與他見過的女人都不一樣,他揉搓揉搓自己的眼睛,他甚至懷疑這是不是一個血肉做成的人。這女人不知道撒不撒尿拉不拉屎,這女人是不是吃的不是五谷雜糧。
鐵錘說,這狗日的咋是個日本人,這狗日的日本沒男人了咋讓這樣的女人來我們中國打仗。
茍五蛋聽了鐵錘的話捂住嘴笑。他湊過身子貼在鐵錘耳朵上說著什么。
鐵錘終于聽明白了。他說,這狗日的日本男人腦袋掖在鞋幫子上了還帶著女人,想在咱大后套下崽子呀,這些狗日的想得還美。日本鬼子操過的女人再可喜的臉蛋子也跟腳后跟差不多。茍五蛋,把這個女人推進坑里去。鐵錘說這話時咬了咬后牙槽,腮幫子上鼓起了兩個包。
茍五蛋被鐵錘的氣概感染了,他沖到那個女人面前拽住了她的胳膊肘兒,他往前推搡的時候趁機抓了一把她的乳房。一種異樣的東西通過他的手傳到他的心窩上,他炮烙似地縮回手,這個女人閃電般地給了他一個響亮的耳光。
茍五蛋憤怒了,他扯著嗓子喊道,你這個臭婊子還敢打老子。日本鬼子糟蹋了那么多中國女人,把你這個臭婊子囫圇埋了便宜了你們日本鬼子。他一把把這個女人推進土坑里,自己也跳了進去。
坡上站著看熱鬧的幾個男人被茍五蛋說的話提醒了,他們也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褲腰帶。
他們看到茍五蛋扯下腰里的紅褲帶,在空中劃了一條紅弧線。接著又看到前面的小路上連滾帶爬過來一個人,他像叫春時受到驚嚇的一只老貓,聲音嘶啞、絕望地哀鳴。他從坡上一個跟頭就栽了下去,幾乎砸在茍五蛋和啞巴的身上。他拽著茍五蛋用異常低微的聲音說:她沒有殺過人沒有殺過我們中國人,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殺我們中國人。
楊板凳楊東家在乞求茍五蛋了,他的眼睛里要流出血來了。
茍五蛋太陽穴上暴出兩條青筋,說,你咋知道她沒殺過咱們中國人,你咋知道她是日本軍妓?
楊板凳說,她也是被日本男人扔掉了的一個可憐的女人,你不要埋她了,讓她走哇。能不能回了日本那是她的命,讓她走哇。
茍五蛋可憐的活了半輩子,還沒有人求過他。有一次一個口里來的要飯的到他家門口給他作揖,想討一口飯吃。茍五蛋說,你從鍋里盛哇。要飯的一揭鍋蓋,看見鍋底子都生銹了。再一揭米甕,只有一把耗子糞。這個要飯的生氣了,跳起來還把他捶了一頓。
茍五蛋掃興地提著褲腰帶上來了,這讓上面的幾個男人很失望,本來想著老光棍兒茍五蛋帶個頭,他們也能蹭點騷。現在看來沒戲了。大家咧著嘴用大黃牙笑他,說,哎,五蛋,燜在鍋里的老母雞飛了,下面的含水都流下來了哇。
光棍漢茍五蛋有些惱羞成怒,他一只手提著褲子直著脖子對鐵錘喊,鐵錘侄子,你沒看出來嗎?楊板凳和這個臭娘們兒有貓尿(貓膩)。楊板凳知道她是日本人才讓她裝啞巴的。大家記不記得,楊板凳早早就離開防空洞了,他趁著我們不注意就領一個日本女人回家,他辦下了天大的豬狗事,我們義和隆的人還不知道。這是一對狗男女。
大家看到,日本女人看見楊板凳來了,就頹然蹲下去,臉埋進雙臂里。之后她突然跳起來對楊板凳又抓又打,讓楊板凳上去。
鐵錘喊道,二爹,你上來,我問你話。
楊板凳流著眼淚從土坑里爬出來,圪蹴在了鐵錘的腳底下。
楊板凳是鐵錘的二爹,香夫人是鐵錘的大姨,她是吃大姨的糖麻葉長大的,他們是有親情的。鐵錘說,二爹你站起來,你這個水襠尿褲的慫樣子,不就應了人家說的閑話了嗎?
楊板凳不管這個,沒聽見一樣。
鐵錘看著二爹爛泥糊不上墻了,也就問了幾句不疼不癢的話。
你是咋碰到這個日本女人的?
楊板凳按照啞巴早教好他的話說了一遍。
她在楊柜做些啥,老實不老實?
板凳說,她推磨,洗衣裳,抱孩子。她沒說過一句話,香夫人讓她做甚她就做甚,能不老實么。
聽了楊板凳的話,鐵錘把身上的夾襖向肩頭上扯了扯,擺擺手,做出一副鎮長的樣子,意思是埋了哇。
人們提了鐵鍬往下走。
茍五蛋跳起來說,鐵錘,不能埋,讓縣里的人來斷一下這個事,看他們是不是穿一條褲子。
鐵錘說,茍五蛋,鐵錘的名字是你叫的嗎?縣長是你爺嗎?前幾天放的救濟糧和種子是鎮長給你放的還是縣長給你放的?我說埋就埋,埋!
茍五蛋氣得滿臉痛紅,這官大一級壓死人。可他還是有點不服氣,鐵錘分明是在包庇他二爹么。他說,那就讓楊板凳埋,你們不是說他們沒有甚貓尿么,就讓他埋。
這么一說把鐵錘將住了。他說,我二爹埋就我二爹埋,二爹你埋。
楊板凳接過鐵鍬,慢騰騰地小心翼翼地填了第一鍬土,土沒有撒在啞巴的身上。他低著頭不敢看啞巴,他轉著圈往啞巴的旁邊撒土。
茍五蛋搶過楊板凳手里的鐵鍬說,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就饒了你吧。他飛起鐵鍬嘩嘩地下土,人們也跟著下土,三下五除二,土到了日本女人胸上。
板凳圪蹴在一簇沙蓬后面,鼻涕抹在牛鼻子鞋上。他的兩只眼睛直直地看著義和隆,義和隆里的楊柜,楊柜里的糧倉。他的眼珠牛卵一樣地瞪著,癡著,仿佛先死掉了一樣。
啞巴一直甩著頭發,好像她沒想到死只想到臟。后來她沒有力氣了,臉白成一張麻紙,腦袋垂下來。
人們不約而同地住了手。
天空一下子安靜下來,連一只麻雀都沒有飛過。
日本女人突然抬起頭來,她用眼睛四處尋找著什么人。她盡量抬起已經虛弱了的手撥臉前的土。她說著日本話,配合手勢比劃,大家終于看明白了。
日本女人說她懷孕了,已經好幾個月了。
這對義和隆的男人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按照大后套的風俗,懷了孕的婦女是不能下葬的。當地的說法是,大人死了,孩子還沒死,這個沒死的孩子連同母親下葬后就會變成“墓虎”,會在一個大家都睡死的黑夜把全村的人和牲畜都吃了,連骨頭都不剩下。老年人還經常有鼻子有眼地給村里人講,哪年哪月哪村一個女人死了,大家不知道她懷孕就把她葬了。后來這個村里的活物連老鼠都讓墓虎吃了,這個村子變成了白骨灘,就在狼山腳下呢,現在人們黑夜路過白骨灘的時候,還能聽到墓虎吃肉吸血的聲音呢。
這下鐵錘可作難了,死人肚子里的娃都會變成墓虎,那活人肚子里的娃更是了得。他說,先揪出來揪出來。
板凳看見啞巴像蘿卜一樣被茍五蛋拔了出來。隨后香夫人和順子到了。
香夫人說,出了這樣的事我是有責任的。是我看著這個閨女人樣子好才收留了她。她比劃著說來后套逃荒遇上了打仗,家里人都沒有了,讓我們收留她。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因為她是個啞巴我們也就沒多想,思謀著先讓她給家里當丫鬟,再在義和隆挑個好人家嫁了。
茍五蛋說,她肚子里懷娃了,是在你楊柜懷上的哇?
香夫人說,這也怪我粗心,她住在我們楊柜我們用的是一個茅房,自打她來我就沒看見她來身上,我還想這閨女是不是身體有毛病,等閑下來給她看看郎中。這事隔過去也就忘了。
香夫人的意思是說啞巴女人在到楊柜之前就懷孕了。
香夫人怕別人不相信,就派順子回去叫錦繡堂的郎中來。
不一會兒錦繡堂的郎中到了。他仔細地把脈,之后慢條斯理地說,有喜了,三個月了。
大家心里算了一下日子,日本女人兩個月前到楊柜的。更何況人家楊板凳的老婆都說啞巴是來楊柜之前懷孕的,那又有什么可說呢?剩下來的事情是怎么處理這個懷孕的日本女人。
最后香夫人出了一個主意,她說,這個日本女人可能沒有直接殺過我們中國人,可她是一個軍妓,她幫助他們日本男人殺害我們中國人,同樣罪不可赦。她現在懷著身孕,孩子是無辜的。不如等她生下孩子我們把她交給駐軍,按照俘虜去處理她。家有家規國有國法,國事家辦是不合適的,大家說對不對?
香夫人說的話讓人心服口服。
鐵錘說,那讓她到哪里去生娃呢?
香夫人說,你要是信任我的話,讓啞巴還到楊柜去,我肯定不會虐待俘虜。等孩子生下來,讓駐軍帶人走。
事情解決了,大家鳥獸散。香夫人前面走,啞巴后面走。楊板凳跟在后面,心里嘀咕,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唱的哪一出,心里不落底兒。好在啞巴還能茍活下來,能多活一天算一天,楊板凳還是充滿了欣慰。
茍五蛋他們跟在后面,大家開他的玩笑說,五蛋啊,差點開個洋葷呀,時氣不好運氣低,騎上駱駝狗咬逼,以后沒事常到楊柜去,聞聞騷味兒也行呀。
茍五蛋自我解嘲說,我才不稀罕別人騎過的女人哩。要不是狗日的日本人進了義和隆,我都攢夠了娶親的錢了。要不是狗日的日本人我現在入洞房著哩。
大家笑著說,沒聽說光棍還能攢下錢,光棍的慫零流了,我看你攢下幾把清鼻涕。嘿嘿嘿嘿嘿嘿!
6
板凳甩開膀子走進鄉公所,接待他的還是上
次的那個后生。大叔,你咋又來了?板凳嘿嘿地笑了兩聲說,我心里不落底,我
再來靠實靠實。后生說,我已經給你說幾遍了,省上有政策,要寬大對待俘虜,我們是不會虐待俘虜的。板凳圪蹴下來,手抖著卷旱煙。他說,上次鐵鎮長他們把坑都挖好了。后生說,鐵鎮長也來過了,我們把政策也給他交代了。這只是一種抗日情緒,她不會被活埋的。板凳換了個圪蹴的姿勢說,那娃生下以后,她這個俘虜該咋辦呀?后生說,她是戰俘,長官處會把她送到國內交換俘虜的地方去的。板凳站起來了,手還是在抖著說,那她死不了了?在我們國家不會死,等她回去日本,應該也
不會死,可日本的事情我們就不太清楚了。哦,那她的娃,會死嗎?她是戰俘,她的娃不是戰俘,娃沒有罪。板凳手更抖了,說,那她把她的娃帶回日本
去,日本人也不會殺她的娃對嗎?不會。你說的話當真嗎?我傳達的是國家的政策。沒有假的。板凳抖抖索索地摸出一張卷煙紙來,讓后生
把國家的政策寫在紙上。
楊板凳往糧倉里裝糧食,他貓著腰干活,偷眼瞄著啞巴的動靜。啞巴的肚子太大了,像一口鍋放在身子上。她托著墻來回走動著。是香夫人讓她不停地走動的,說走開了才好生。啞巴心里明白,香夫人是想讓她早點生,這樣才能說明她肚子里的孩子與他們楊家沒有關系。
趁后院沒有人,板凳湊到啞巴跟前,把那張紙拿在手里,他知道啞巴不認識中國字,但這是一個證明。他給啞巴說,她和孩子都不會死,孩子生下后他們就到交換俘虜的地方去,之后回日本。
啞巴低著頭,她聽得懂板凳的話。
板凳看到她不說話,就又重復了一遍剛才的話。
啞巴抬起頭來,看著板凳。她的眼里慢慢地滲滿了淚水。她咬著牙關說,我哪里都不去,我只想在這里。
就在這時,疼痛開始了。啞巴抱著肚子貓下腰。
香夫人端了一盆煮雞蛋過來了,她說,多吃幾個雞蛋,有力氣。
香夫人一定在心里釋了口氣,終于要生了。
板凳的心卻燒焦了的皮子抽在了一起。他害怕這一天的到來,啞巴就要走了。
錦繡堂的接生婆來了,到產房里摸了啞巴。說,還得三個時辰。
接生婆隨著香夫人一起進了廂房,門敞開著。香夫人從箱子里揪出一塊料子,說,又讓您費心了,這塊料子是我孝敬您的。
接生婆作勢推辭著說,香夫人的事就是我老婆子的事,盡管吩咐就是了。
香夫人笑著說,大人孩子都要安全就行了。
接生婆看了一眼香夫人。香夫人接著說,這個女人挺可憐的,讓日本人輪番著糟蹋。這和我們眠春閣里的姑娘是一樣的,有辦法誰做這個營生。這個孩子生下來,長官處就把他們娘倆領走。她在義和隆在我們楊家住了大半年,我們沒虧著她,最后這一件營生了,我們也把它做好。我們義和隆的人厚道是出了名的嘛。
香夫人的話說得很在理,縱然有天大的過節,跟一個就要永遠離開了的可憐女人較什么真呢?接生婆和門外的板凳被香夫人的寬厚感動了。
板凳多次見過女人生孩子,隔著義和渠喊叫聲都能聽得見。可是啞巴的房子里沒有一點聲息,只有接生婆和打下手的奶媽出出進進的。板凳蹲在墻根下昏昏欲睡。
村里的幾條狗叫了,后來村里的所有狗都叫了。馬蹄聲從義和橋北踢踢踏踏地過來了。板凳聽到了敲門聲,香夫人匆匆忙忙從廂房里出來,聽到豐田喊娘。
板凳打開門,香夫人跟在后面。豐田拉著亮水閃進門來,拽著父母親進了正房。
豐田,出啥事了?香夫人把跑跑放進被窩里,壓著聲音說。
豐田抱著娘的一只胳膊說,娘,你不要急。國共合作破裂了,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翻臉了。重慶來的特務正在逮捕共產黨。傅將軍讓我們這些赤色青年馬上離開河套,讓長官部的人送我們到延安。爹,娘,我們是向二老道別的。
香夫人淚流滿面了,她捶著自己的胸口說,天呀,你啥時候成了赤色青年了呀?我以為你在公家那里做營生,跟著扛槍的最保險了,可你跟著什么共產黨起什么哄啊。
豐田跪下了,亮水也跪下了。
豐田說,娘,你們不要擔心我們,在延安都是我們這樣的人。我剛才找過麻錢爹了,他給我們備了最好的馬,他答應兩家互相照應,爹,娘,多保重吧。
亮水說,爹,娘,有我照顧豐田你們放心吧。
香夫人把兩個孩子扶起來。從躺柜里摸出一包東西塞進亮水懷里,說,快走吧,到了就捎信兒來。兩個人成個家吧,不要分開呀。
豐田和亮水又雙雙給爹娘磕了響頭。他們跳上高頭大馬沖進夜色里。
這時奶媽顫巍巍地跑過來說,哎呀,不好了,接生婆說沒見過這么大的胎兒,還是絞臍生。香夫人快拿主意,是保大人還是保孩子吧。
香夫人進了正房,板凳站在原地不動。香夫人說,板凳你進來。
板凳挪動著兩條腿進來,臉色土灰。
你都聽見了,拿個主意吧。
主意還是你拿吧。
別的主意我可以拿,這個事情必須你說話。
話說到這個份兒上了,板凳再不能推了。他說,大人孩子都要。說完就圪蹴在地下了。
香夫人眼睛里露出了十分的鄙夷,吃稀飯的拉的自然是稀屎。
她站在產房外,說,大人孩子都要,你盡力吧。
產房里始終沒有任何聲息,這真的讓人心慌,連香夫人的心都在敲鼓了。雞叫頭遍的時候,楊柜傳出了嬰兒的哭聲。
接生婆抱著孩子出來,臉色黯淡。她把孩子交給香夫人,對著圪蹴在糧倉邊上的板凳說,娃好著,大人出血過多,能到天亮就挺過來了。
香夫人接過孩子,吩咐黃米熱羊奶,讓奶媽帶接生婆到廂房歇息。她對板凳說,我們盡力了,剩下的看她的命了。
板凳看了一眼香夫人懷里的小包袱,香夫人抱這個孩子以前抱她自己的孩子姿勢是一樣的。孩子哭了,她趕忙輕輕晃蕩著胳膊,嘴里說著乖。
楊柜靜下來了。板凳蹲在糧倉旁邊,糧倉的墻頭都讓他靠熱乎了。他要等著,等著這個女人站起來從產房里走出來。哪怕他能聽到她的一點聲息,哪怕是一點輕微的喘息,他都相信她能活下來。
天麻麻亮的時候,他夢見啞巴了。啞巴坐在糧倉里對他說,板凳哥,我給你生了個女兒,我們就叫她麥子。
板凳睜開眼睛,看到產房的門開了,他的心跳起來,啞巴挺過來了。他站起來,看到一個腦袋,接著是半截身子,趴在門檻上。一只雪白的手向他伸出來。
板凳撲過去接住她的半個身子,門檻里的啞巴向門檻外的板凳笑了。
她的嘴貼在他的耳朵上,她的聲音像菟絲子那么細,纏在他的耳輪上——
板凳哥,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你把我當成一個人,愛我疼我。
懷胎的這十個月我是最幸福的女人。
我為你生了一個女兒,我走后,她陪伴你。
她的名字叫麥子。
就把我埋在已經挖好的那個坑里。那是一個高坡,我可以看見你。你不要送我,你在糧倉里想我。
你不要哭,一滴眼淚都不要流。記住我給你的那個手勢,永遠不要說出口……
啞巴掙扎著抬起兩只手,做了一個他們之間才懂的手勢。
啞巴走了。
板凳沒有哭。他躲進了糧倉里。
他聽見鄉公所的人來了,說,死了也好,鄉公所出棺材,就埋在坡上的那個坑里。可是孩子怎么辦呢?香夫人說,孩子的母親托付我收養這個孩子。
這是義和隆最安靜的一個出殯,板凳聽到,鐵鍬揚起的土撒在薄木棺材上,沙,沙,沙。
板凳在糧倉里睡了三天三夜,走出糧倉,他長長地伸了個懶腰,他看見義和隆的天是那么的藍。
他提起糧倉門口的一把鐵鍬,走向前院。他看見香夫人坐在一只蒲團上,靠著暖烘烘的墻,蒲團邊是一只空奶瓶。她露著半只乳房,懷里的嬰兒正吮吸著乳頭,那乳頭像一只櫻桃就要破了。名字叫麥子的嬰兒并不餓,她只是本能地在玩耍著乳頭。香夫人好像睡著了,她的臉皮不像過去那么白皙了,乳房下垂得像一只瓢。她的臉很安逸,像哺乳豐田增田和跑跑那樣,不溫不火不急不慢。
板凳的心頭哽住了。
他拄著鐵鍬跪下來,他摸了摸麥子的小臉蛋。他給她們磕了個頭。
他沿著義和渠一直往西走,一直走到太陽落山。他走進一片荒地里。他鏟一些直芨,搭了一個小茅房。他要從這里開荒了。
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個傍晚,他站在茅草房前,看到茅草房里一片金黃,他想起看見啞巴的那個后晌,啞巴背著身子急急了了地換一件中國女人的衣裳。
他突然想起,他從來沒有問過啞巴的名字。
啞巴叫什么名字呢?開完一畦地,板凳就這么想一下。
(長篇小說《河套平原》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