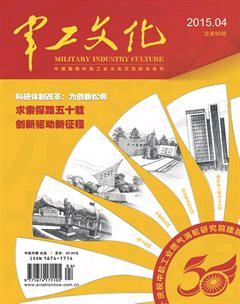李澤湘:打通創業最后一公里
談科研創新,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中國創業者跟美國的創業者的組成有哪些不同。我把美國這些年創辦的公司分了一下類,一類如蘋果和亞馬遜等,還有另外一類公司像HP、Microsoft這些,這兩類公司有共同點,但也有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類是從企業出來的人創辦的企業,而后一類人是直接從學校所學進行的應用研究做起,我們稱之為學院派。中國最近這些年創辦的企業可以關注草根企業家,一大堆的名字都非常響亮。學院派早期有方正、聯想,最近十幾年來這一類的創業企業幾乎消失了。
實際上這兩類企業,一類是“游擊隊”、八路軍,另外一類是“國軍”、正規軍。但很遺憾在過去十幾年中國的創業史上我們的“國軍”消失了,這可能引出來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國家這些年大部分的科研經費、教育經費實際上都投在“國軍”,這更是應該產生很多高科技的企業出來,但非常遺憾沒有達到我們所看到的效果,就像昨天我們都關注的環保問題,所以這是我一個問號。當然中國在今后10年、20年,如果要能夠達到實現“中國夢”,“國軍”應該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應該說會成為主力。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有沒有可能在教育科研的體制下,補上迷失的力量。所以就想從香港科技大學我的實驗室做起,看看有沒有可能做到。
我自己是在科技大學工學院電機系做了個很小的實驗室——自動化技術中心,我也把我們系跟美國最牛的一些學校比如MIT(麻省理工大學)等做了比較,我們的老師差不多,但我們的科研經費只有他們的1/4~1/5不到,這種數字是任何一所“985”學校都會超過的。我自己1992年加入到香港科技大學,我自己的科研經費在系里面也是低于平均數的。
我1992年去了科技大學,一直要做研究,期間有一個小的事情,引發了一些變革。有一天一個香港的老板在順德開了一家廠,買了一臺設備怎么都搞不定,最后他說李教授你能不能幫我把設備搞定,我說我只教課、做研究,你這個東西跟我沒有關系,老板很失望地走了。過了一會兒他又走過來放了一張空白支票說李教授你看著辦吧,那時候科大的科研經費還是不夠,我們就拿了一半控制卡,把他的設備修復了。通過這件事,我意識到學校的研究有可能對周邊的企業產生推動作用,但要做到這件事情必須大批量地復制,也必須創辦一家公司。
我們也知道,學校老師要創辦一家公司要具備三個因素:一個就是要與你的科研有關系。第二個,學校要有這么一個政策,有利于從學校的研究變成產業,我看到內地這么多學校實際上一直都沒有建立這個政策,其中也產生了很多糾紛。第三個,要有一個平臺,因為當時深圳要產業升級,深圳沒有大學,所以當時北大的書記、科大的校長還有深圳市市長開人大會的時候就有一個“借雞生蛋”的模式,政府提供土地、資源,讓兩所學校到深圳來辦一個大學,進行科學研究辦企業的方式。當時,深圳市領導到科大一個一個敲門,希望老師能夠來深圳做這個事情,啟動了深圳的創新模式。
我們看到珠三角的制造業,以前都是ODM的模式,這種模式找一個女工就干起來,一定的程度上它能賺錢,能滿足當時的需求。但這種模式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
中國發展到這個拐點的時候,一定需要自己的設計來支撐中國的制造業,設備機械可以山寨,但控制和軟件沒辦法山寨。
通過目標案例我學到了很多的東西,以前我招研究生都是從內地最好的學校招成績最好的學生,后來,發現這些學生的創新能力跟成績是不匹配的,而且我們原來的課程都是從美國MIT、伯克利拿過來的課程,最后就使得我思考應該怎么設計我們的課程,培養有創新能力的學生。
我的體會是,第一點是學生要有興趣、有理想、有激情來做事情。第二個,在學校創業不是商學院開一門創業課程,而是整個的創業文化氛圍,它的課程設計都是創業的課題,實際上像谷歌和雅虎都是這么起來的。第三,同門的師兄弟是最好的創業伙伴,學生跟老師在創業過程中是什么樣的關系,學生有激情有創新,但是他們缺少資源。在這方面學校的老師、學校政府應該是打造一個創新創業的平臺和體系,使得更多的年輕人能夠干起來。
科大以前在拼命地追求文章,現在也在進行反思。我們大學到底應該是怎么來定位的?所以我們也有了嘗試,就是成立了一個機器人研究所,把學習教學研究跟創業一體化集成起來。之后我們在松山湖打造了一個機器人產業基地,希望香港內地還有國外的機器人、智能硬件等從業的年輕人,能夠到一起來,我們把零部件和制造體系提供給他們,使得更多的企業能夠一個一個地走出去。
我講這么多,實際上我最后想總結一下,珠三角尤其是深港這一塊是世界上最好的創業樂園,硅谷有的我們都有,硅谷沒有的我們也都有。大家沒有意識到我們香港的幾所高校是香港最寶貴的資源,以前大家看香港就是你的海港、你的金融,但是我說錯了,香港最寶貴的是這幾所大學,高校跟珠三角的產業體系結合起來,是完全可以改變一個地區的經濟結構的,我希望政府、學校、老師把創業的最后一公里打通,只有通過引領中國機器人產業還有整個世界新硅谷的發展,香港的高校才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