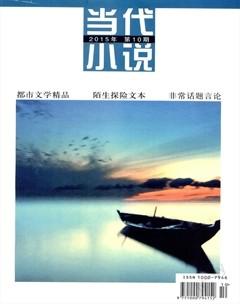請叫我鄭開顏
劉芬
當鄭開顏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她的名字常常遭人取笑。那會兒電視里正放映連續劇《霍元甲》,萬里長城永不倒的主題曲飄滿大街小巷。她的同學走過她身邊時總是故意唱道:睜開眼吧,小心看吧,這里是全國皆兵。唱完還對她促狹地擠擠眼睛。她的名字,鄭開顏諧同睜開眼,這讓多事的同學給她取了很多諢名,比如睜開眼、正開演什么的,反正都是不好聽的名字。鄭開顏哭著回去找父母,責怪父母不該給她起這么一個難聽的名字。鄭開顏的父親聽了哈哈大笑說,睜開眼有什么,說明你任何時候都有一雙銳利的眼睛比別人清醒。我當年給你起名字,是因為毛澤東的《長征》里有這么一句話,三軍過后盡開顏。看看,這句話多有革命主義英雄喜悅的氣息。鄭開顏不懂這些,只是委屈地叫道,爸你自私,你因為自己的喜歡就給我取這么個難聽的名字,你是一個自私的人。一點沒考慮給我帶來的感受。某些時候,小姑娘是個牙尖嘴利的人。
讀初中的時候,班主任黃老師是個幽默風趣喜歡搞怪的人。這從他對全班同學排的座位表中可見一斑。班上一個同學姓史,一個同學姓廖,黃老師貌似無意地把他們安排在一起,但其中的惡作劇大家一看便知。鄭開顏呢,她的同桌叫樊關容(樊同反),這名字與她的名字剛好形成反義結構,黃老師的用心昭然若揭。還有其它有說法的名字,黃老師也把這些同學安排坐在一起。這樣的座位排列順序,形成他們班的一景。
上了高中,倒是沒有人再取笑她的名字,也沒有其他與她名字對應的同學成為同桌。鄭開顏以為自己終于可以擺脫名字帶給她的小插曲了,卻不知,還是因為名字她又與一人結緣,并且還是個異性。這名字帶給她的衍生事件沒完沒了。鄭開顏想,我這具有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父親,可真是把我害慘了。
高一,班主任要班長鄭義登記全班同學的名字。因大家都是新生,鄭義對全班同學的名字不是很熟悉。在寫鄭開顏的名字時,無意中寫成了鄭開眼。鄭開顏非常氣憤,多年來因名字原因帶給她的各種感受讓她激憤難當,她生氣地去找鄭義,厲聲說道,作為一個班長,你連同學最起碼的名字都寫錯,請問你這班長是怎么當的?還鄭開眼,我看是你應該睜開眼才對吧?你看清楚,到底是我要開眼還是你要開眼?你這么做,也未免太不尊重同學了吧?你這是侮辱我的人格。我要你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向我道歉。鄭開顏的咄咄逼人讓鄭義倒吸一口涼氣,不就是名字寫錯了一個字么,犯得著這么認真較勁么?下次改正不就是了。還上升到侮辱人格的高度,這是上綱上線了。鄭義堅決不認錯,認為這純粹是女同學的小題大做及小肚雞腸。兩個人僵持不下,事情鬧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了解情況后把兩個人叫到一起笑著說,呦,兩個人都姓鄭呢,五百年前可是一家人。可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你們兩鄭,一鄭要在男生中起正面帶頭作用,一鄭要在女生中起正面帶頭作用。以后,班里的正能量就要靠你倆帶領了,握手言和吧。為了咱高一·三班的榮譽,你倆要并肩戰斗。
在老師巧妙的化解中,鄭開顏極不情愿地與鄭義握手,這算是消除表面的芥蒂了。但內心里,鄭開顏卻下定決心要與鄭義拼個高低。她就是要讓姓鄭的男生不能小瞧她,她可不只是言語上的巨人,在學習上,她同樣也要做個巨人。
鄭開顏鉚足了勁學習。人都說女孩子上了高中,學習都比男生要差。特別是理科方面。鄭開顏不信這個邪。她就要做領頭羊,讓全班所有男生都跟在她后面。特別是看到鄭義的名字出現在她后面,她就有說不出的喜悅。開顏,這意思不就是喜笑顏開的意思么?我就是要攜帶著這個暗語似的,表情符號般的名字橫行天下。鄭開顏心里的豪情壯志在心里像花朵般綻放。
鄭開顏與鄭義的成績都好,基本上都在前三名。班上還有一個叫李顧順的男孩子,也在他們三人集團的隊伍。每次考試,三個人的名次都是犬牙交錯,輪流領跑。他們三人基本上包攬了前三名,被同學們戲稱鐵三角。每次排名,鄭開顏要是排在第一就有一種獨占鰲頭我自橫刀向天笑的獨霸感,要是鄭義排在她前面,她就會在心里恨恨地說,哼,有什么了不起,你是班長,考第一是應該的。看我下次不考個第一氣死你。
其實這都是鄭開顏單方面的心思而已。真實的情況是:鄭義一方面專心學習,一方面盡職盡責地當好班干部。他是老師和同學們之前溝通的橋梁,也是同學們眼中的知心班長。不像鄭開顏,雖然因成績好擔任了英語課代表,但卻只限于收收本子發發作業,她刻意收斂自己的能量,為的是不過多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她要把大部分力量用在沖刺學習上。這是鄭開顏心里不為人知的一面。很多時候,鄭開顏是一個聰明機敏的女生,她保留了自己輕易不肯示人的一面。當然,關于鄭開顏心里那些女生獨有的小細膩小心思,鄭義是看不到的。
班主任每次把班干部留下來開會,鄭開顏總是與鄭義刻意保持距離,造成井水不犯河水的架勢。鄭義知道這些,鄭開顏的這些表面現象也做得太明顯了。如此說來,鄭開顏從來就沒有在心里放下過對他的芥蒂。但鄭義從不計較,他以好男不跟女斗的古語把自己的心安慰得妥妥帖帖,所以對鄭開顏暗地里的白眼、不屑等種種不友好的小動作,鄭義裝作視而不見。
這樣相安無事過了兩年。他們不過是普通同學中最普通的一對。甚至比普通同學的關系更糟糕。可是到了高三,這關鍵時刻,形勢卻是風云突變。
這年,大家都是十七八歲的大好青春年華。青春以霸道不可一世的強悍席卷了每個同學。男同學長高了,喉結變大了,嘴唇上冒起了小胡須;女同學明顯的胸部發育,每個人似乎都變得那么靦腆和害羞,更有甚者,怕自己發育的胸部讓人看出端倪,大熱天還穿著厚厚的外套,怎么都不愿意脫去。總之,這一年,同學們像被施了魔法似的,每個人都或多或少發生了改變,男生變得英俊,女生變得迷人。
千百年來困擾老師和家長的問題也出現了:早戀問題。這可是關鍵的一年啊,可是,身體里那些青春的細胞散發的力量是如此的洶涌,不是老師的警告和叮囑就能控制的。誰能阻擋得了青春的浪潮呢?它在每個人的心里面,就像一枚小小的原子彈,炸裂,散開。把青春的天空撕扯得五彩繽紛絢麗妖嬈。
鄭開顏,這個個性要強不服輸的女孩,她心里那些青春的花朵也慢慢開放了。她發現自己的心開始變得柔軟,尤其是對鄭義。她發現自己不討厭鄭義了,她喜歡聽他渾厚的男低音,喜歡看他跟男同學打打鬧鬧時揮舞著有力的手臂。更要命的是,她總是想著他,每時每刻,一堂課,不知多少次偷偷看他。
這真是件要命的事情。她被自己的改變嚇了一跳。一夜之間,她竟然喜歡上了一個讓自己討厭了兩年的男生,他們的關系人盡皆知,幾乎全班同學都認為他們是死對頭。他們一個是白天,一個是黑夜,永遠不可能有交匯的時候。這件事卻就這樣真真切切地在陽光底下出現了。
最初的驚嚇過后,鄭開顏陷入到一種幸福和緊張的情緒中。她發現思念一個人原來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想念一個人,隔著外衣,隔著距離,但卻聽著他的每一句話,看見他的每一個動作,他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她的心,她的心是為他跳著的。這是一件多么隱秘幸福的事情。
鄭開顏的心思,鄭義是有感應的。也許兩個人之前存在著某種相通的密碼,也許兩人之間確實有緣分。總之,鄭義也被青春之劍射中。當課堂上鄭開顏的目光隔著幾排同學的身影投射在他身上時,他立馬就能感應到,并用同樣熱辣辣的眼神迎上她的目光。但鄭開顏的眼神往往這時候就像受驚的小動物一樣馬上離開,她裝作看其他同學的樣子,回避了他的視線。
鄭義想,也許先前我們倆的芥蒂是緣分安排的一個鋪墊,它讓我們那么強烈地記住對方,卻是為了轉變成今天的思戀。
鄭開顏還是不與鄭義講話,旁人看不出兩個人心里的山呼海嘯。他們仍舊像冰山一樣沉默著,冷淡地對著對方。兩人心里明白,此時的冷漠與先前的冷漠是不一樣的,先前的冷漠,是對對方的否定,是對彼此關系的消極處理方式;現在的冷淡是一種偽裝過的外在的表現形式,是一種無法表述的欲蓋彌彰。
每天都有火辣辣的眼神對視,每天都看似漫不經心實際高度敏感地注視著對方的一舉一動……這些埋藏在心里的感情就像迷人的小蛇折騰著他們年輕的心。在感情的煎熬中,兩個人竟然都有相同的變化,那就是兩人都瘦了。
一天上完課后午飯時間,同學們都陸陸續續走得差不多了。鄭開顏磨磨蹭蹭地收拾著桌面上的書,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磨蹭什么。無意中她看到鄭義也在慢吞吞地收拾書本,她收拾得更慢了。她的心跳加快,滿街都能聽見。一個冒失的男生跟鄭義打招呼,大聲說班長你怎么還不下去吃飯,一會兒飯堂都沒有好菜了。咱們一塊兒走吧。鄭義回答說,你先走吧,我還有點事呢。男生一陣風似的走了。
終于,又有幾個慢動作的同學陸續起身離開了教室。教室里只剩下了鄭開顏和鄭義。鄭開顏的心似乎要跳出胸膛。她害怕著什么,又期待著什么。她期待著鄭義向她走來,又害怕他向她走來。在這甜蜜矛盾思想糾纏中,鄭開顏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做才好。
她把一本書放回抽屜,想了一下又拿到桌面上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該干什么。她用這些微小的動作,無非是想掩飾自己內心的慌亂。鄭開顏不敢抬頭,不敢看鄭義。
鄭義裝作是在清理桌面的樣子,其實無非把幾本書折騰來倒騰去。為了兩人能有機會單獨相處的這一刻,他其實已謀劃了很多次。可每次,鄭開顏不是與同桌一起走,就是與宿舍的女生一起結伴下樓,他沒有單獨見到她的時間。今天,老天開眼,兩人終有靈犀一起留在了教室里。可他不知道該走上前去對鄭開顏說什么。道歉么?說開學那天把你的名字叫錯了對不起,她那時不是強烈要求他向她道歉么?可事情都過去了幾年,現在再在找她說這件事明擺著是沒話找話說,再說自己當時態度那么強烈,認死也不向她道歉的。這個理由明擺著不行。說自己喜歡她么?不行不行。鄭義首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要說嚇著鄭開顏,自己也沒這分勇氣。再說,萬一鄭開顏拒絕了,那不是自討沒趣?鄭義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教室里很安靜,空氣中到處彌漫著焦灼的因子。某些不明原因的愛之細胞在空中飛舞,像精靈一樣穿梭在空氣中。兩個人彼此都感覺到對方輻射過來的力量,兩個人的氣場高壓、逼仄、纏繞、混合。
這貌似不相干的兩個人各自暗懷心事進行心靈的博弈。鄭開顏用輕輕拍打書本的方式掩飾著內心的慌亂。怎么辦怎么辦?他要是走過來向我表白我該如何是好?我該是答應還是不答應呢?鄭開顏在自己的假想問題中急得團團轉。不答應吧,怕失去了這個機會,答應吧,少女的嬌羞以及害怕東窗事發的擔心讓她心懷忐忑讓她絕對不敢正面接招。
一個想進不能進,一個想退不能退。兩個人的心事在燃燒的空氣中進行短兵相接。空氣中到處嘶啦嘶啦地冒著火花,仿佛一點就燃的樣子。這青春之火,燃燒起來竟是不管不顧的。
時間在流逝,吃飯的時間被拖延。天涯是咫尺,咫尺也是天涯。兩個表面上看來毫不相干的人,內心都在進行痛苦的煎熬。
不知道過了多久,兩個人都在遲疑著、較量著。這時,打飯較快的一個男生端著飯碗風一樣地沖進了教室。見了這兩個人夸張地大聲叫道,不是吧,你們倆還不快去吃飯。一會兒去到飯堂怕只剩下菜渣嘍。
鄭義扔下書本應了一聲,這就下去。他的聲音是驚慌的,變調的。打飯的男生以為他是為錯過了吃飯時間發出的本能的音調。鄭開顏沒有吱聲,內心卻在心里咒罵著這個男生,吃吃吃,吃你的大頭鬼,整天只知道自己吃,小心吃多了變成大肥豬。
鄭義走了,鄭開顏不得不收拾起錯亂的內心,慢悠悠地走出了教室,去打飯。
這么一趟美好的單獨相處的旅程,被一個無關緊要的男生無意中沖破。鄭開顏沒有等到鄭義的表白,她的心里委屈又難過,她怨恨那個男生,也怨恨鄭義。走到飯堂外邊的樹下時,她狠狠地揪了一片樹葉,把它握在手里捻得粉碎。仿佛對這片葉子有什么前世之仇似的。
把鄭開顏和鄭義聯系到一起的原因純屬偶然。
英語單元測試,鄭開顏的成績竟然一落千丈,大部分平時學習不太起眼的學生都跑到她前面去了。鄭義也是,第一次遭遇到學習上的滑鐵盧。英語老師是個剛從師范畢業不久分來的年輕老師,火氣很大,對這兩個人的學習一起下滑非常不滿意。
英語老師出了一道題在黑板上先是讓鄭義去做,鄭義做錯了。又讓鄭開顏上去做,鄭開顏也做錯了。老師又讓李顧順去做,李顧順做對了,這讓英語老師有了點顏面。否則,班上的前三名都做錯了,這不是說明他老師的教學水平是有問題的么?
年輕的英語老師非常生氣,對鄭義和鄭開顏一頓劈頭蓋臉毫不留情的指責:你們兩個,一個身為班長,一個身為英語課代表,看看你倆都在干什么。回頭你倆得給我好好檢討檢討,給我說清楚這次考試你們怎么會考成這樣!
停頓了一下,英語老師貌似還不解氣地對鄭義和鄭開顏說,你們兩個,還有李顧順,你們三人都到我宿舍里去,好好想想這次的考試。你們三人是班里的核心人物,我希望你們能以此為戒,這樣的成績下不為例。
到老師宿舍去思考,這是有點面壁思過的意思了。而李顧順,完全是被牽連的。只因他也是這三個核心成員的一部分。
三人在同學們幸災樂禍的笑聲和眼光中低著頭離開教室來到英語老師的單身宿舍。平常這三個人都是各課老師眼中的驕子,雖然明知道老師的這種處罰方式也是有傾向性的貌似嚴厲實則是另一種關愛,但同學們還是發出了笑聲。純粹是青春期的沖動和惡作劇。
英語老師和另一個班的物理老師共用一間房。兩人都是剛分來不久的年輕老師,學校宿舍不足,便安排他們共住一間約十多平米的房間。房間被一堵墻隔成了兩間,前面一間大的是另一個班的物理老師,英語老師的在后一間。房間很小,只夠擺一個單人床,一個辦公桌。老師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同學們的作業和書籍。
三個人都到了英語老師的辦公室卻并不說話,不愧都是各課老師都寵愛的尖子生。換作其他調皮的同學,早就珍惜這晚自習的自由打打鬧鬧起來了,這三個老師的寵兒都老老實實地站著,好像真是在檢討自己的過失似的。
晚自習是兩節課。上完第一節課中途休息,英語老師回宿舍來看他們三個。這當兒,可能是因為站的時間太久,也有可能是別的原因,李顧順一下子流鼻血了。年輕的英語老師沒有經驗,顯然是被突如其來的鮮血嚇到了,他驚慌地對李顧順說,快回教室去,弄點涼水洗洗。
李顧順被特赦回教室去了,英語老師要看著李顧順,又要上下一堂課,立馬也跟著去了。一著急忘了還有兩個人在他宿舍罰站呢。
這段單獨相處的時間簡直是老天刻意安排的。李顧順走了,狹窄的空間突然逼仄起來。兩個人身上散發的氣息像無數的圓圈在空氣中玩連環套。你的套著我的,我的套著你的。兩個人都局促起來,血流一下子加快。鄭開顏不由自主地挺直了一下背。
鄭。開。顏。鄭義仿佛用了很大力氣,一字一字地叫鄭開顏的名字。
嗯。鄭開毅小聲嗯了一聲,聲音小得像蚊子叫。她并不抬頭,卻只是看著自己的腳尖。
此后又是長時間的一段沉默。世界靜得只剩下兩個人的呼吸。
為了打破這份沉默,鄭開顏鼓起勇氣問,你叫我干什么?有什么好叫的?
鄭開顏的語氣看似很不友好,其實是一種色厲內荏的虛空,是一種假裝咄咄逼人的虛張聲勢。
鄭義當然是知道她的心思的。他順著她的話說,我叫你,是因為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這幾個多么艱難的字,竟然被鄭義這么順風順水地說了出來。竟然是自己給逼出來的。
盡管期待了很多次,鄭開顏還是被嚇了一跳。她設想過了無數次鄭義對她說出這幾個字的場景,不是在學校的櫻花樹下,就是在學校的湖邊,甚至在夢里她也聽見他這樣對她說。她千想萬想,惟獨沒想到他會在英語老師的宿舍中對她說這幾個字。尤其是在受罰的黑暗夜里,尤其是在一個并不浪漫的空間。可見命運的指引是有多大的牽引力啊,它只輕輕伸出個小指頭,這兩條年輕的小魚兒就上鉤了。
鄭開顏覺得自己應該給鄭義一個明白的表示,要不然鄭義一定會以為自己是一廂情愿的,那樣也許他會受到打擊,而自己也終將會錯失良機。她不能因為女生面子薄而拒絕這難得的機會。
鄭開顏想了想,低頭小聲地說,我也是。
僅此三個字,兩人之間的心門徹底打開,一道閃電連接起心之橋。
鄭開顏覺得這真是一個美好的夜晚。命運之眼突然在她眼前打開,她覺得這個夜晚變成了一只大白鵝,馱著她和鄭義在黑夜湖面上泛舟。
此后,兩個人沒有再講話,仿佛怕一說話,就有什么東西被打碎似的。
鄭義伸出手,輕輕地,小心地,試探般地接近鄭開顏的手。鄭開顏心里驚呼道,好你個鄭義,這都是在哪里,你竟然敢如此大膽。
但她的手明顯背叛了她的心。與她心里的想法相悖的是她的手,她的手沒有拒絕鄭義,而是半是掙扎半是愿意地接受了他的手。
剛開始兩人的手只是半握著,后來,兩只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似乎是在表演無聲的諾言。又似乎是某種堅強的暗示。兩人知道,從握住對方的手這一刻起,他們的關系不再是先前的猶抱琵琶半遮面了。從此以后,他們將是親密的戰友,忠誠的同盟。
兩個人就這樣緊握著手,甜蜜地、心無旁騖地享受這個突如其來的夜晚帶來的美好的意外。什么話也不用說。不知過了多久,傳來英語老師開門的聲音。兩個人像受驚似的放開手,片刻收斂起那份秘而不宣的心事。裝作沒事的樣子靜候英語老師的到來。
看得出來李顧順流鼻血給英語老師帶來的恐懼還在。英語老師沒有批評他們,只是問鄭義,想清楚了沒。鄭義回答,想清楚了。英語老師又問鄭開顏,你想清楚了沒?鄭開顏低著頭輕輕地說,想清楚了。英語老師說,那好,都想清楚了你們就回去了。下次考試,可不許再這樣了。
兩個人無意中對望了一眼。這一眼,是同盟,是防守,是秘密。這個夜晚的驚鴻一瞥,是一個故事的開端,是一對戀人拉開情愛的序幕。而英語老師,無意中扮演了月老的角色。這無疑是與他的初衷背道而馳的。
好了,就像對上了暗號接上了頭的兩個特工。鄭開顏與鄭義,這擁有同樣姓氏的男孩女孩并肩作戰,坐上了開往早戀班號的小船。
作為班長的鄭義有時要與女生說話,鄭開顏只看他一眼,他就不敢再理會人家了。一次,鄭義對文藝委員李茂花說,以后你教大家多唱些流行歌曲吧,別老是教那些老歌。同學們都有意見。
因為隔了幾個同學,李茂花沒聽清楚,反問道,鄭義你說什么?大聲點,我聽不見。
鄭義無意中看到鄭開顏射過來的眼光,像一柄清亮的明晃晃的小飛刀,他心里一緊,故意粗聲粗氣地對李茂花說,沒聽清楚算了。我不會再說第二遍了。
盡管被鄭開顏的目光無聲地制止,但鄭義心里還是非常甜蜜。鄭開顏這么在意他與其他女生講話,說明她吃醋,這是愛他的表現呀。
兩個人也寫字條。有次鄭義在字條上問她是否能去理個光頭,就像少林寺和尚那樣的。
鄭開顏對著字條兀自笑了半天,回過去一句,你要做了和尚那我怎么辦?這是要我也去當尼姑的節奏么。告訴你,你要是去當和尚,姑奶奶保證去踢廟,踢他個片甲不留。
鄭義笑岔了氣。
班上總共只有這么多人,大家都處于情竇初開的青春期,對異性關系特別敏感。哪對男生女生有好感,很快就能被另外的人識破。鄭開顏與鄭義的關系親密了沒多久,便被全班同學發現了。大家集體起哄,笑這兩個人早在五百年前就私定了終生。
消息傳到班主任黃老師那里。這可急壞了黃老師。他是從高一年級跟班帶上來了的,太熟悉這兩個學生了。這兩個學生可是寄托著他的希望呀。班主任與學校是簽訂了任務的,他的班上必須要有三個考上重點本科的學生,他就能拿全額的獎金。如今,這兩個人竟然談上了戀愛,哪里還有心情學習。難怪最近這兩個人的學習成績有所下滑。黃老師心急如焚。換作是其他學生,黃老師可能沒這么著急,偏偏這兩個人,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談戀愛的。黃老師是又急又氣。
黃老師先是分頭找兩個人談話,兩個人都答應得好好的。可答應只是嘴上的答應,被青春沖動控制住的男生女生,哪能說忘就忘呢。兩個人照樣卿卿我我。尤其是鄭義,還信誓旦旦地說要把這份感情轉化成學習的動力兩個人互相激勵鼓舞共同上進,爭取考上好學校。黃老師才不相信呢。以他多年的經驗,談戀愛是要分心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況且現在時間也緊急,兩個人談戀愛只是死路一條。
黃老師在班上安插了很多眼線,班上的其他班干部如體育委員宣傳委員都是暗中的監視者,他自己也留心鄭開顏和鄭義的一舉一動,從同學的匯報和他自己的觀察來看,很快他就氣餒地發現,這兩人根本沒有分手的跡象。他問宣傳委員,宣傳委員把兩個拇指對著彎了彎說,還是這樣子。
這可急怒了黃老師。他在心里狠狠地說道,好吧,你們兩個,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對你們說盡了好話,已經仁至義盡,你們兩個不吃軟的,那就吃硬的吧。也許硬的對你們有效。
應該說黃老師的處理方式是過激了的。青春期的男女,自尊心強,情感脆弱,又沒有抗壓能力,而早戀又是一塊非常不好處理的雷池,多少年來都是這樣。黃老師的行為,竟然把兩個人推向了無法回頭的境地。
周一是每周的班會時間,換作是平常,老師肯定是把班級后墻上大大的倒計時的日期撕掉一張,然后苦口婆心教育同學們時不我待,一定要加緊最后的時間沖刺等勵志的話,可這次的班會明顯不同尋常。黃老師鐵青著臉,臉上的表情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教師里肅靜的氣氛也說明了這次班會的不同尋常。
黃老師站在講臺上,直接點名并用手指著鄭開顏,你,給我站起來。又用同樣的方式讓鄭義也站了起來。眾目睽睽之下,鄭開顏和鄭義像被示眾般站了起來,接受同學們的注目禮,這令兩個人非常難堪,背后鋒芒刺背。
黃老師的發言更是不客氣。
他說,只有狗才開始在很小的時候談戀愛交配,幾個月就懂了。你們倆現在狗牙仔的年齡就開始談戀愛,那好,我現在就告訴你們的家長,讓他們幫你們買家具你們結婚算了。
這明顯是刺破了鄭開顏的底線。作為臉皮薄的女生,這番羞辱性的脫離實際的話語讓她連死的心都有。隨著撕心裂肺般的“啊”的一聲嚎叫,鄭開顏捂著臉奪門而逃,沖出了教室。鄭義反應快,連忙也跟著跑出了教室。其他同學有人想跟著追出去,黃老師說,別去,讓鄭義去追吧,他喜歡去就讓他去,正好讓他去表現。
黃老師滿以為鄭義是去追鄭開顏了。這兩個人此時此刻竟然還在他的眼皮底下表演愛情,是可忍,孰不可忍,黃老師氣得連連搖頭。
他不知道他的語言帶給兩個孩子的傷害程度是有多深。事情的發展遠遠地超乎了他的預判。
當天的晚自習后,他陸續接到鄭開顏宿舍和鄭義宿舍同學的消息,說他們倆都未回宿舍。
黃老師慌神了,這么晚了,這兩個人是要到哪里去了呢?黑燈瞎火的,也不知他們身上有錢沒?也不知他們在外面有沒有飯吃有沒有碰上壞人?如果不回來,這兩個孩子的一生就完了。黃老師急出了一身冷汗。
沒辦法,黃老師連夜通知雙方家長,家長又號召親友團,組成浩大的尋人隊伍,連夜展開搜尋。學校也組成緊急處理小組,加入到家長的搜尋隊伍中。
第二天,大家一無所獲。家長們著急,開始把矛頭指向黃老師,說他犯了教育的大忌,趕走了兩個孩子。盡管黃老師一再認錯,承認自己的方式方法有問題,但他的出發點是好的,焦躁的家長、學校的領導、甚至班上的同學都認為他處理此事的方式太過頭了。
第二天,大家報了警。電視臺、收音機都開始播報尋人啟事。街頭巷尾都被兩個孩子的家長貼滿了尋人啟事。聲勢浩大的尋人集團不停地擴大搜尋范圍,有車的用車,沒車的租車,大家紛紛尋思,這個城市就這么大,兩個孩子步行,又沒有多少錢,高考在即,他們又能走多遠呢?
一天、兩天、三天……時間像驚慌的葉子一天飄落一片。轉眼間已到每年一度的高考。兩個孩子仍然沒有出現。起先,家長們還抱著一線希望,認為兩個孩子會在考場上出現,可高考完了,孩子們也沒出現。這下,家長們不干了,紛紛跑到學校要人,要懲罰黃老師。黃老師絕望了。他沒想到自己無意間的一番話,竟然帶出這么大的一件事來。
孩子們的前程是徹底被自己耽誤了,不管他們日后是否回來,他們的人生都發生了不可逆轉的事件。帶著對孩子們的悔恨之情,帶著對家長們的謝罪之心,在高考剛考完后的第三天,考生的分數還沒來得及出來,黃老師飲恨自盡了。
此事很快在當地成為發酵性的大事件,引發了各學校對教育早戀學生問題的思考。各大媒體、報刊雜志針對此事發表大幅評論,信息劈天蓋地。茶余飯后的人們也都是議論此事。一時間,這件事情竟然超過了高考的溫度。黃老師用自己的死,推動了人們對教育的思考。
斯人已逝,無從追責。人們只能是惋惜和嘆息。時間流逝得很快,很快下一個高考又來臨了。很快下下個高考又過去了。人們早已忘了黃老師。在鄭開顏和鄭義兩家人的心中,孩子們的去向成謎,他們只能幻想著,兩個孩子也許在某個不知名的地方早已結婚生子過著平淡的日子。他們不希望人們打擾他們,所以一直沒回來。
而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鄭義確實追上了鄭開顏,兩個人相擁,抱頭痛哭了一陣。后來,鄭開顏提議說,她想去長江邊看看。長這么大,她就想看看長江。鄭義點頭同意。
兩個人來到了江邊,是在晚上的時候,遠處的江面上有星星點點的燈火。岸邊不時有江中心涌過來的浪。鄭開顏悲觀地說,我們就算回去,也沒有人會原諒我們,我們只會成為別人眼中的笑話。再說回去后,學習任務那么重,我們倆是肯定不能在一起了。我們還不如死了算了。這樣,我們就永遠在一起了。我們的殉情,讓他們難過一輩子。人們在說起我們的時候,也不會把我們當笑話。
鄭義想了想,覺得鄭開顏說得不是沒有道理。流落他鄉的無助,黑暗夜里的憂傷,心靈的創痛……種種感覺涌了上來。鄭義同意了鄭開顏的話。
兩個人手牽著手走向了江心深處。
很久很久以后,兩具腫脹的尸體被沖向了岸邊。一具朝上,一具朝下。他們被人打撈了上來。有經驗的人說,臉朝上的是女尸,臉朝下的是男尸。但人們已看不清他們的臉。很快他們被當做無主尸體被處理,進了焚燒爐。
而這一切,他們家鄉的人是不知道的。
某天,鄭開顏的父親想念女兒,便隨手翻開了女兒的一本書,那上面赫然寫著:請叫我鄭開顏。父親想起女兒曾經詰問他的關于名字的事,百感交集。愴然淚下。
可是他的女兒鄭開顏,卻是再也不會睜開眼了。
責任編輯: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