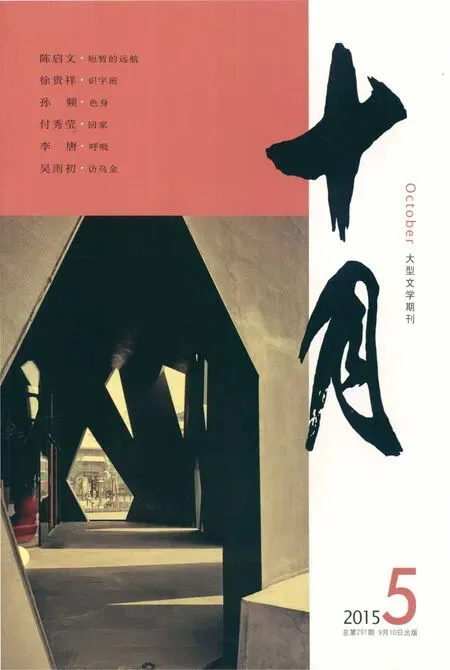窗內的凝視
王威廉
在現代文學中,孤獨的聲音是最迷人的。因為在這樣的時刻,歷史、社會與倫理的喧囂終于安靜了,一個豐富的生命個體凸顯出來了,他的傾訴從而極具存在本質的色彩。詩人阿多尼斯說:“孤獨是一座花園,但其中只有一棵樹。”我非常喜歡這首詩,在我看來,與其說孤獨的聲音是一種自言自語的循環式呢喃,不如說是精神主體步入那座大花園之后的回響:他試著描繪那棵唯一的樹。
讀青年作家李唐的小說,讓我在內心的花園里經歷了一次孤獨的跋涉之旅。他的小說,最重要的意象便是孤獨,虛無的孤獨聚攏了詞語,又如春蠶般緩慢地吐出了柔軟的絲線,編織成了語言的空間。讀完小說,那棵唯一的孤單的樹找到了嗎?那是一棵怎樣的樹?但這也許都是不重要的,如同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霧中風景》的結尾,那樣的一棵樹被濃重的霧氣包裹著,成為一個模糊的幻影,卻將我們感動得熱淚盈眶。
我仿佛也看到了李唐勾畫出的希望的幽影。他的希望遠遠不是廉價的,因為在那樣的幽影顯現之前,他在敘事上的緩慢與耐心令我暗自驚異。他對筆下出現的物件都有著撫摸般的全方位描寫,從而極大豐富了小說的視覺特征。請注意,這意味著這個極其年輕的作家已經懂得了藝術的克制。藝術的克制不是一味地少,同時也意味著在正確的方向上多。拋卻浮躁,像潛水艇那樣向黑暗的深海持續下潛,是寫作邁向精神縱深的絕佳隱喻。有太多的人,會因為怯懦、恐懼與平庸喪失下潛的勇氣,但是寫作的光榮,必定只能來自于朝向黑暗的勇氣。我毫不懷疑,李唐具備這樣的勇氣。
我和李唐認識于2012年夏。那一年,我三十周歲,他二十周歲,僅僅因為這兩個數字,那就應該算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對我而言,生命正在挺進一個通常被命名為“中年”的可怕的深廣區域;而對李唐來說,他的生命意識正如旭日東升一般,磅礴有力地照亮著青春的天空。我們站在佛山西樵山的大佛前聊了很多,基本上都是關于文學的,我們的價值、趣味與判斷多有共鳴之處,我心想這個年輕人是能寫出大作品的。他對我的作品的認可,也給我很大鼓舞,因為對于作家本人,長輩權威的認可非常關鍵,而對于作家的作品,下一代人的認可也許更加欣慰。當然,這其中有著復雜的辯證,但有一點是不需論證的,我和李唐成為了跨越年齡的朋友。
說起來,那次的見面,是緣自一次“90后”作家的活動,我讀了很多年輕人的文字,他們的才華、活躍與想象力都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李唐當時就已經是他們當中的佼佼者之一了。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他們更加全備的知識修養與思想訓練。按照現在流行的文學分類學,他們自然是“90后”作家,但我希望他們的文學不再被冠以“90后文學”這樣的字樣,因為他們很有可能寫出偉大的作品,很有可能誕生出偉大的作家。他們需要從代際的框架中跳出來,他們不再是一群人,他們中優秀的一個人便足以成為一群人——一個優秀的作家媲美一群人,甚至一個政府,這是那位偉大的索爾仁尼琴說的。
三年后的今天,李唐已從大學畢業并參加工作了,再讀他的小說,果然讓我驚喜。他現在的小說,已經完全沒有了青春期的稚嫩與躁動,扎實、克制、理性與思辨已經化入他的字里行間,也就是說,他的內心已經建立起了寫作的自覺性。我對他這么年輕就能具備這樣的意識,深感欽佩。他的兩篇小說《西伯利亞》和《呼吸》,對當代人的孤獨狀態有著細膩的呈示,小說的肌理纖毫畢現,詞語的節奏把控有度,在對小說主題的細致開掘中,抵達了存在哲學的高度。
在小說《西伯利亞》中,李唐實質上構造了一個噤聲的寂寞世界。那個叫陳眠的男人,夢中看到的景象與現實是一樣的,只是沒有聲音,這是富有意味的一筆。夢境往往是真實的另一種表現方式。陳眠是一個看監控的保安,瑣碎的日常生活和霧霾一樣,讓他看不清真實的事物。霧霾,構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氛圍,它的傷害是緩慢、持久和無解的,它早已不再局限于一個氣象學現象,甚至也不僅是某種政治或社會的隱喻,而是變成對人的存在本質的遮蔽。對一個生存于當代的中國人,霧霾幾乎就意味著存在困境本身。那么小說的題目與結尾所暗示的,那來自西伯利亞的凜冽的冷風,將會吹散霧霾,期間的意蘊便是很豐厚的了。
我們完全可以把小說《呼吸》看作是《西伯利亞》的姊妹篇,盡管它們的故事以及長度差別較大,但是它們就像是交響樂中對某個主題的變奏。小說中的入,呼吸系統出了問題(因為霧霾嗎),經常會突然間地窒息,接近瀕死狀態,但他處于絕對隔絕的狀態,沒有人理會他的生死,為了死后有個收尸的人,他遇到了一位打算跳樓的女人,他們之間先是極端占有后又極端排斥的愛情,是這篇小說的故事內核。這篇小說讓我想起韓國導演金基德的電影,那種孤獨、掙扎、思考以及長鏡頭一樣的絕望場景,完全挺進了人心深處的荒誕風景。這種在簡單關系中深入挖掘的寫作,是一種有難度的寫作,它考驗著作家對世界的認識程度。
兩篇小說都是以窗的意象開始的。窗,是一個具有強烈象征性的符號,無論是《西伯利亞》還是《呼吸》,我們都會記得那個臉貼著窗望向外邊的形象,這無疑是個體從靈魂內部向外邊世界的凝視。因此,小說的敘事一直是在“窗內”展開的,是一種遵循精神邏輯的迂回敘事,但小說又采用了第三人稱,拉遠了小說的景深,我們的閱讀更像是來自“窗外”的眼光,窺視到了“窗內”的掙扎之痛。我不免想到,窗,看起來是通透無阻的,但本質上卻是嚴密隔離的。這的確像極了個體存在的處境。不過,窗所劃定的這道界限,也讓小說的擬真性遭到了某種程度的破壞,從而有可能稀釋場景氛圍所帶來的感染力度。行文至此,我不禁要再一次提及李唐的敘事耐心,正是那些視覺化的描述,聚攏了閱讀的目光,抵御了封閉空間對閱讀的離心力,這就像是他遞給我們的一架望遠鏡,讓我們得以看清窗內的細節,仿佛置身其中。
李唐,真可謂是人少年而文老成。他是地道的北京人,卻避免在小說中提及北京,或是使用過于順溜的北京方言,我理解他,這是他對寫作的鄭重,他要在自我與現實之間,先建立起一個安全的過渡帶,以防止思想與語言的打滑。所以說,雖然他還有無限的變化可能,但他優秀的音質已經就此確證。毫不諱言,我非常喜歡他這種鮮明的現代主義品格,是的,沒有什么比看到更年輕的一代寫作者自覺承接起這樣的藝術意識更高興的了。因為只有將對生命的觀照聚焦于人的內在心靈,并以此為根基對這個世界進行思辨,才有可能真正清醒地認識到“現實”究竟意味著什么,而“真實”又是如何涌現的。這種獨一無二的內在體驗,是決定一個作家能否遠行的關鍵所在。在面對更加廣闊的現實生活時,我們不可能從自我的靈魂窗內逃逸出去,與其描述遙遠而縹緲的關于龐然大物的傳說,不如將更多的事物容納進窗內,從而擴大窗的邊界、突破窗的隔離。
畢竟,窗內的事物才是我們真正熟悉的事物。
責任編輯 季亞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