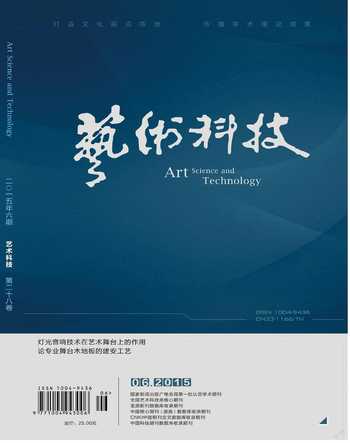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文本分析
王蓉
摘 要:本文對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從故事情節、舞劇細節、動作語言、舞劇結構及對電影鏡頭語言的挪用這五個部分進行分析,以期從理論上對中國芭蕾舞劇的創作實踐展開評述。
關鍵詞:《大紅燈籠高高掛》;張藝謀;中國芭蕾;戲劇結構;鏡頭語言
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由中央芭蕾舞團于2001年首演,總導演張藝謀,編舞王新鵬、王媛媛。這部舞劇改編自蘇童小說《妻妾成群》,導演張藝謀在執導電影版后,進行跨界嘗試,芭蕾舞劇版由此而生。這部舞劇以頌蓮為主線,描述了她在封建時代被強娶作姨太太后與舊愛偷情繼而被杖斃而亡的悲慘命運,是對封建制度的批判。張藝謀在劇情介紹中有詳細描述:
序幕
20世紀30年代,幽深的大宅院,一個年輕的女孩被強行塞進花轎,她是老爺新娶的三太太。上轎前,她想起青梅竹馬的戀人——戲班子里年輕的小生。
第一幕
迎親的喜慶氣氛中,大太太與二太太懷著復雜的心情接納這位新人。
洞房花燭夜,新來的三太太拼命抗爭,但終于沒能擺脫悲劇的命運。
第二幕
唱堂會,打麻將,老爺領著太太們終日消磨時光。
新來的三太太利用短暫的機會與昔日戀人相會,兩個年輕人的戀情被居心叵測的二太太發現了。
第三幕
年輕人繼續偷偷相愛相會,二太太告密。老爺當場捉拿了這對大膽越軌的戀人。
二太太想趁機恢復失去的寵愛,心情敗壞的老爺卻賞了她一記重重的耳光。
失落的二太太將滿院的紅燈撕得粉碎。
尾聲
那對年輕的戀人與二太太同時被帶到行刑現場,在死亡面前,他們盡釋前嫌,以寬容和愛彼此緊緊擁抱。
封建制度扼殺了年輕的生命和美麗的愛情。[1]
從故事情節看,這部舞劇描述了20世紀30年代的故事,與今相聚130余年。由于觀眾并未親涉其境,不能感同身受,但能在茶余飯后花時間去旁觀封建制度的一段畸形的情感故事。其實若從社會倫理角度來說,三太太嫁作人婦應遵守綱常倫理,偷情行為并不正確,但三太太的“嫁”本身是有違當今世道的。因此,作者仍在贊頌他們不正當的愛情,以混亂的情感糾葛批判封建制度。編創意圖源于文學作品,張藝謀的改編并不打算與原作進行內容上的交流,而是希望以不同媒介對同樣的故事進行敘說,以吸引觀眾眼球。因此,從內容上看,張藝謀并無新于原作的表達,只是根據舞劇特點將故事線索清晰化,這是因著芭蕾這一藝術形式而做的改動。此劇并未如原作般平鋪直敘地講述這個大家庭的千姿百態,而是選擇以三太太及戲班武生為主角展開敘事。這樣既可使故事線索更為簡單清晰,又便于編創雙人舞的舞段。這樣,如果觀眾對原作有了解,可將其作為背景而以三太太與戲班武生的愛情故事為焦點,若觀眾并不熟悉原作,也能明晰地理解舞劇的故事情節。但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對二太太的過度渲染,既然該劇已確定主線,那二太太的許多無關主線發展的行為亦不必交代,以避免舞劇結構稍顯混亂。
此外,張藝謀在面對媒體的訪問時,宣稱要將此做成一部“好看”的芭蕾舞劇,而通過其選擇性地對作品細節進行放大設置成舞段的行為,我們亦能查知,在編導眼中,哪些元素更易獲得觀眾視覺上的認可。首當其沖便是給人以視覺沖擊的那四十四只紅燈籠,從最初的點燈到最后二太太傷心地將燈籠撕碎,再加上舞劇之名及起初的紅燈籠舞,可見紅燈籠是本劇的核心象征。紅燈籠意味著封建家庭中女人的榮寵,也許對她們而言,暗無天日的日子里只能將紅燈籠作為虛幻的光源日夜期盼,實在可悲。再者,麻將舞也是張藝謀重描的細節,其實這一細節并不是非要不可,但在舞劇中卻有圍繞其而生的舞段,麻將舞段中的舞蹈設計并不精彩,或許編導認為麻將可以代表封建社會的糜爛生活,而麻將中的勾心斗角是男女主角偷情的合適背景。除此之外,還有洞房、堂會、花轎等細節具有濃重筆墨的敘說。通過對這些細節的分析,可見張藝謀在芭蕾舞劇的導演中非常注重中國元素的細節,這與電影中的選擇取向是如出一轍的。而通過舞美的華麗渲染,芭蕾舞劇版《大紅燈籠高高掛》確實是一部給人以視覺享受的作品。可見,在這部舞劇中,舞劇敘事節奏是在導演的傾向中信步而行的。
從動作語言看,此劇的導演與編舞是分離的,編舞在試圖表達導演的意圖。這樣,既可能在碰撞中擦出火花,也有可能出現編舞不能很好地貫徹導演意圖的情況。或許每人都愿意在自己能做的范疇中盡可能地做好,于是從最后呈現來看,這部舞劇的舞蹈語言要弱于“鏡頭”語言,這與導演與編舞的分開不無相關。例如,在三太太出嫁時,被四塊紅色木板所困以表達其不情愿的心情,這時,表達的方式并非以三太太的舞段,而是體現在她從紅色木板圍追堵截的逃跑中。這一方面可看作是舞蹈動作語言的失語失色,又可看作是舞劇呈現中表達方式的多元化。王新鵬和王媛媛均是現代舞和當代芭蕾創作的新銳編導。因此,《大紅燈籠高高掛》有大量現代舞的表現手法,使芭蕾語匯更為豐富,但遺憾在于并沒有非常出彩的芭蕾舞段。戲曲元素僅在堂會出現,是插入到舞劇中的,而堂會過后的全府學戲時,稍顯冗長,舞者們得其動作而不得其神韻,男女主角的偷情戲也沒有得到明顯的發展。
本劇結構仍然是延續了“戲劇結構”的模式,就是用芭蕾語匯按照戲劇的方式講述故事,但在此基礎上有所精進。例如,在第二幕堂會戲中戲里,在舞臺中又設有一小舞臺,京劇演員在唱念做打,而劇中人也如觀眾般在看戲,當三太太看到舊日情人在飾演武生時,以音樂的驟變與燈光的驟暗體現了三太太的心理活動。而后,三太太離開座席,與武生一同將小舞臺的鏤花木門關上,在燈光與音樂的配合下,營造出后臺這個空間。這時整個舞臺被隔成三個空間,舞臺上的觀眾與演員成了背景,而男女主角則吸引了臺下觀眾的眼球,這是三太太出嫁后與戲子武生的初次相會。而后二太太從木門走出出現在觀眾視野中,這樣不言而喻地說明二太太已洞悉奸情。而后,該到武生上臺時,木門重被打開,武生開始表演,三太太回座,舞臺回到了兩個空間的狀態。因此,在戲劇結構的基礎上,對時空處理的方式已較先前豐富許多。
現今,舞臺藝術離不開觀眾,而觀眾亦不再滿足于被填鴨式地灌入編導的主體思想,而希望能介入其中,鏡頭語言的使用給觀眾留足空間,這也許是該劇“好看”的原因之一。比如說,在結尾處,二太太、三太太及武生被杖斃之時,家丁拿著大粗紅棒敲擊在舞臺后側的白布,每敲一次便在白布上留下紅色印記,三人在舞臺前側痛苦不堪,這樣,觀眾觸目驚心地看到白布上的血跡,以自己的想象力進行“代入”,便能最大限度地感受到三人之痛。這是強而有力舞臺語言描述。又如在老爺與三太太的洞房花燭夜時,張藝謀在舞臺后側安置一排紙糊的背景,而在老爺追三太太時二人沖破紙幕前后穿越,暗示三太太的驚惶之感,最后舞臺鋪滿紅布暗喻三太太的失身,在這段情節中,觀眾并不會關注其中是否舞蹈占的比重過微,而是會震撼于整體舞臺效果之余為三太太而神傷。這難道不是舞臺語言的勝利?諸如此類的例子并不在少數,《大紅燈籠高高掛》對舞臺綜合元素的運用對其他芭蕾舞劇的表現方式可以說有啟發意義。如何四兩撥千斤地用適合的方式去敘述,或許是張藝謀導演在進行此番跨界嘗試中給舞界從業人員的啟示,其中鏡頭語言的使用突破了舞劇慣用的表達方式,有助開拓舞劇創作思維。
參考文獻:
[1] 張藝謀.新浪網[DB/OL]. http://ent.sina.com.cn/h/2003-07-03/17431656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