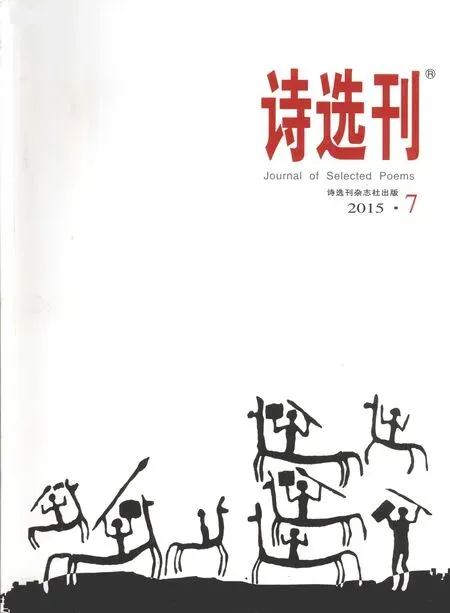移民的后代
姜華
右臂上的胎記
一塊鮮紅的胎記,刻在我的右臂上,現在,它已長成我家族的風水,成為秦嶺上空的火燒云,漢江之畔的圖騰。
一塊龍紋的胎記,從我的掌心一直延伸到小臂,像一個家族的路線圖。事實上,這塊誕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一個秋天,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的磨難,伴隨我身體慢慢長大,變紅、變深的胎記,就是一塊記錄著一個家族興衰的標本或活化石。它也是伴著四季輪回,印在我身體上父母的骨血。
在我的故鄉,神造的陜南,沿著這塊胎記,渴望的目光還在延伸。越過秦嶺以北的北方,秦嶺以南的水鄉,然后返回到我的臂紋,抵達秦嶺山地的阡陌。這塊在我身上生長了近半個世紀的胎記,傳承著家族的血統,也沾滿了塵世風沙。它帶著父親的囑托,母親的疼痛和一顆年少張狂的夢想,伴我行走江湖。
今夜月到中秋,坐在異鄉的天空下,看月光下手臂上的胎記,忽明忽暗,就像老家那個叫桑樹灣村子的燈光。現在,這塊卑微、溫暖的胎記,突然令人心痛,和牽掛。
月光下,一塊普通的胎記,泛著微光。它像一首詩坐在我的手臂上,站立或行走,一言不發。移民的后代
人到中年的時候,大多開始懷古。我多么想乘一葉小舟,沿著三千里漢江,順流而下,去尋找三百年前湖北麻城,一個叫姜家灣的地方,那里是我的故土我的根。
那時候,中原戰火正盛,天災不斷。失去了糧食、土地、和安寧,爺爺的曾祖父,于清末一個無月之夜,用擔子,把一個家族的種子,挑到了陜南,在漢江邊一個叫旬陽的縣城,他們停下了腳步。
被稱著移民的人,是我的家人,一群骨子里不安分的人。種桑、養蠶、織布、種棉,最初的農業文明,在這塊秦頭楚尾的土地扎下根來。扎下根來的,還有我們這些兒孫。五百多年過去了,家族發達的根系,已遍及漢水流域。
只是在雨季,夢一樣的漢江,伴著潮聲,把我們的懷念一次次帶遠,帶向下游,那塊叫故土的江漢大平原。我們的心情,就這樣伴著漢水低下去,低下去,一直低到對故鄉仰望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