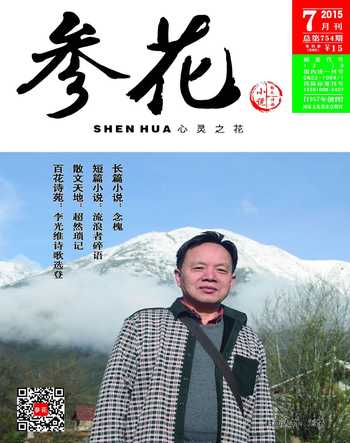小橋舊夢
蒲江濤
巴山夜雨潮如雷,老家小石橋又該淹沒在洪流中了吧!
那是一座平板橋,兩條丈余長的青石板,一頭分隔兩岸河沿,一頭緊扣河心巨石,嵌置三塊巨石間。遠遠望去,小橋就像一只石公雞,橫跨峽谷底,繡身小河間,俯身綠波上,仰臥云天下,一頭叼起河沿一曲徑,一頭系著石壁一古道,兩岸人家叫它雞公橋。
奶奶在世時,常對我們說,這座小橋建成時間有多長,她的年齡也就有多長。她還告訴我們,小石橋能建成,多虧嫁到對岸的老前輩。當時連接河沿的,只是一座小木橋,每逢山洪暴發(fā),滾滾洪流常把橋面兒給沖走,成了兩岸人家的傷心橋。后來一位蒲家女省吃儉用,拿出半生積蓄開山劈石,于光緒二十四年最終搭成這座石板橋。兩岸人家,從此不再為繞道出行而苦惱。
記憶中的雞公橋,宛如一張老琵琶,奏出時光小夜曲,泄露山民多少彷徨,抖落老家多少落寞。
那些年,雞公橋的脊背上,不時晃過一個個身材高大、行色匆匆的身影。他們踏過青石板,趕到集市里,或是去山外,將一些稻谷小麥雞蛋小菜呀什么的帶出去,換回幾包食鹽或是幾張可憐的小鈔票。更多時候,他們板著一臉菜青色的老面頰,背挎一簍風和雨,拖著疲憊的雙腿,順著河沿小路匆匆往家趕。他們偶爾也會停留在小橋邊,抬頭望望天,看看山,發(fā)發(fā)呆,一盯小河流水就是老半天。要么就是三個一群,兩個一伙,斜靠橋身歇歇腳,掏出煙斗吸袋煙,閑聊幾句,長嘆一氣,然后繼續(xù)趕路。
時逢山雨來臨,那些飛落峽谷,宛如滾龍的山洪,便會沖進小河谷,一齊暴漲,一路咆哮,很快淹沒雞公橋。如有家人未歸,村里便會趕緊派人把守橋頭,生怕有人過河落水,出門要辦事的,也得多繞山路十余里。面對掙扎洪浪中的雞公橋,兩岸人家除了揪心,只能滿臉無奈。
更多斜風細雨的老時光,雞公橋苦撐一輪老光陰;或是寂寥無助的慢時光,不是閑瞅淺底小魚小蝦,就是顧影自憐。間或一只水鳥掠翼擦水,驚起一圈圈波紋,總把它的倒影弄得搖搖晃晃,或是歪歪斜斜。此時的小石橋,唯有死盯河面,一面哀嘆自己身不由己,一面靜待水面平靜,恢復身板固有的直挺。宛如我那老奶奶,終其一生持鐮把鋤,仍然為“婦難為無米之炊”而愁悶,只好拿出“書中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古訓,教育我們這些子孫走過小橋,搬到大山外。
小小雞公橋,由此種下我們信手涂鴉的憧憬,也撒落我們童年那些滿地落英。
多少風輕云淡的早晨,我們這些小不點,晃著小書包,沿著小山路,踏上小石橋,跑向河對面。彎曲小路上,時常撒落我們滿地童歌童謠;兩岸小河谷,不時回蕩著銀鈴般清脆的歡笑。時逢放學歸來,我們路過橋頭,丟下小書包,脫掉小褲衩,跳進清溪里,玩起了打水仗。撲打在小伙伴兒臉上的水花,招來滿河嬉逐,驚出淺底魚兒,惹得大家急忙拋開小淘氣,和魚兒玩起了小機智。
晚霞滿天的黃昏,雞公橋成了我們課外習作的大課堂。我們這些學生娃,作業(yè)沒完成的,抓過同窗練習本,趴在橋頭上,亂抄一氣;對課文還不熟悉的,獨坐石橋上,手捧小課本,蕩著小腳丫,一邊背誦唐詩宋詞,一邊留心橋下斜擺魚尾的小驚喜。那些早早做完功課的,拿出連環(huán)畫,或是故事書,趴在石碾上,看得如癡如醉。那份兒專注與癡迷,就連小小的雞公橋也不忍心打擾。那些年,我們多想沿著小橋流水走出古老的大山,步入詩書鋪開的世外桃源。
那些年,同村小伙伴大都在草地上追風做游戲,在橋下嬉戲浪條和流水,而我時常爬巖攀壁,流連小橋四周,只因喜歡清凈。小小青石橋,兩岸石壁上,那些不同年代鑿刻的文字,讓我觸摸到了先輩躬耕這方山水的蛛絲馬跡。鑿成于成化四年的“路志銘”,讓我不由得對五百多年前修建這條山路的祖先肅然起敬。橋頭石壁那塊“通橋功德碑”,讓我心懷感恩搭建這座小橋的先輩;那些恍如利劍刺空的“打土豪,分田地”等標語,既是我對那段彌漫經卷的紅色革命的初識,也飽含著我對二爺加入紅軍隊伍的敬意……小小雞公橋,就像一部傳承家族歷史的小百科,豐盈著我對小石橋愈發(fā)彌堅的敬畏。
感謝雞公橋,養(yǎng)育出了一個個值得我們效仿的老前輩。我那加入紅四軍的老二爺,定居蓉城的二爸,匯入三線建設大浪潮的祿才哥,曾任省府機關某部委的金志老晚輩,定居滬上的堂哥們……他們踏過雞公橋,走出大巴山,除了將一頂頂“人才輩出”的高帽子送回老家小山村,也給津津樂道的老家人丟下一道道高山仰止的背影和一家家暗自發(fā)奮、送讀子女的虔誠。那些年,一家家,一戶戶,大家起早貪黑,不辭艱辛,將勞苦所得變成紙幣,換來我們朝夕往返雞公橋,安坐對岸學堂瑯瑯的讀書聲;呵護我們奮筆黃昏,挑燈夜幕的小身影,度過寒暑相伴的小時光;激勵我們這些不甘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家娃,扎根詩書禮樂慢時光,生出“好男兒志在四方”的壯志凌云。
十七年前的那個夏天,我那穿越百年風雨的奶奶,在一個傾盆大雨的清晨撒手紅塵。當我轉車換道十余次,終于趕上送她最后一程。看著奶奶滿面紅光,一臉祥和,宛如安睡的遺容,我知道,她是想告訴我們這些子孫:能夠走過雞公橋,回不回家,告不告別,其實不重要,只要紅塵安好,就好!
二十年來,我們這些子孫陸續(xù)搬出大山,唯有小橋依然在,也已早就淪荒老家小河灘,淡出我們視線,成了我心中難舍的斷魂橋。
今夜,又是山洪暴發(fā)的雨季!我的雞公橋,你在老家可安好?
(責任編輯 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