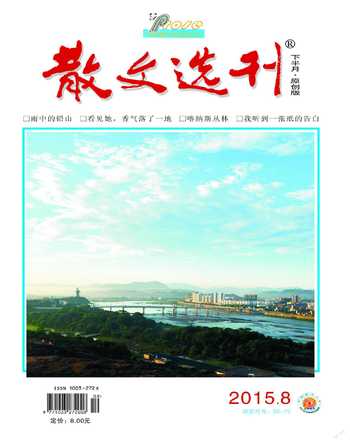喀納斯叢林
康劍

盛夏,我作為保護區的老護林人,跟隨深山巡護隊,對喀納斯保護區的縱深地帶進行了五天的巡山護邊。
第一日
和以往一樣,我們先要坐船穿越二十四公里的喀納斯湖,再騎馬進入深山。從地圖上看,喀納斯保護區呈一個“丫”字形狀。喀納斯湖在下面一豎的位置,我們這一次,是要從左面的叉進去,翻越兩叉之間的達坂后,再從右面的叉出來。這既是一次正常的對保護區的巡護,又是一次難得的對保護區核心區進行資源普查的機會。所以我們的隊員巾,既有邊防部隊的兩位官兵,也有保護區的科考人員。
中午時分,我們乘船到達喀納斯湖的湖頭。湖頭除了偶爾運送物資留下的痕跡,依舊保持著自然原始的狀態。這里,最著名的是枯木長堤。在喀納斯湖進水口的沙灘上,堆放著一公里多長的枯死松木。按常規,這些枯敗的原始松木應該順流而下,沿著湖面飄向下游。但由于山谷風力的作用,這些枯木卻被迎風推送到喀納斯湖的上游,從而形成了喀納斯湖區的一道著名景觀。
看著碼頭邊一大堆隨行的物資,我這個老護林人都有點發愁,到底該怎么把它們運進深山。但打馬垛子是當地少數民族同胞天生的看家本領,幾個年輕的哈薩克和圖瓦護林員眼疾手快,不一會就把零散在地的行李和物資整齊地馱到兩匹馬的馬背上。而且,馬垛子打得前后均勻,左右平衡,這樣,馬跑起來才能輕松自如,不費力氣。兩個年輕人趕著兩個馬垛子在前面先走了,我們跟隨在后,向保護區的縱深地帶進發。
我參與喀納斯的深山巡護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了,但每一次出發都會讓我充滿著新奇和興奮的心情。同樣,每一次的巡護歸來,雖然身心疲憊,但在精神享受上卻總是滿載而歸。雖然山還是這片山,水還是這片水,森林依舊是這片針葉林和闊葉林的混交林,但這山這水這森林,每一次都能夠給我全新的感受。這也正是我這個老護林人始終不愿意走出深山的緣由。
馬兒在林中穿行時,或者在爬山過溝時,就會放慢速度。這時,蚊蟲總會蜂擁而上,簇擁在人和馬的周圍。在馬背上的人們就會不停地用手去拍打叮在臉上或脖子上的蚊蟲。派出所的巴依爾騎馬走在我的前頭,我看見幾只蚊子叮在他脖子上吸滿了他的血液。看著他毫無感覺的樣子,我真想上前幫他拍上一巴掌。
我喊他:“巴依爾,伸手打你的后腦勺。”
我看見他揮手一拍。啪!結果蚊子四散而逃,沒有打死一只。
接著,他的脖子上又叮滿了蚊子。
再打,又四散而逃。
我聯想到在電視上看過的動物世界,這些糾纏不清的蚊子特別像非洲草原上的獵狗.它們老是成群結隊地圍在你跟前嗡嗡。你駐足驅趕它們時,它們會停下腳步離開你一會兒。當你不理睬它們時,又會鋪天蓋地地朝你涌來,連強大的非洲雄獅都拿它沒辦法。
其實,我后面的人看我的脖子,一樣也叮滿了嗜血如命的蚊子。只不過他們見得多了,也懶得給我說,見多不怪罷了。我呢,作為一個資深護林人,會順手揪下一截枯木的枝條,前后左右地抽打前赴后繼朝我涌來的蚊子。
好在到了林中空地,馬兒就會發瘋一般的跑一會兒。馬兒跑起來時形成的風速,就會把討厭的蚊子遠遠地甩在后面。這樣,每個人都會特別喜歡在林巾空地上快馬加鞭跑上一陣子。這時,馬兒會快樂地打著響鼻,它身上的人們也會長出一口惡氣,終于甩掉了那些討厭的蚊子。
從喀納斯湖進水口到湖頭管護站有六公里路程,大概需要一個小時的行程。湖頭管護站實際上承擔著中轉站的作用。保護區核心區內的人員進出和物資運送,都要經過湖頭站。我們在湖頭站稍加休息,喝茶補充水分后,繼續前行。
從這里,我們就進入保護區“丫”字左面的那一叉了。這條溝叫阿克烏魯袞溝,溝里流淌的河流叫阿克烏魯袞河。阿克,在哈薩克語和圖瓦語里都是白色的意思。
我問同行的老護林人巴扎爾別克:“我當了那么多年護林員,烏魯袞的確切意思,還沒有搞清楚呢。”
他支吾半天,大概是找不到最為恰當的詞語來解釋,最后說:“就是溝趟子的意思吧。”這和他每次的解釋沒有什么區別,大概還是白色的河溝或白色的河流的意思。
不過也確實名副其實,在我們腳下奔流咆哮著的,的確是一條白色的河流。阿克烏魯袞河是喀納斯河的一條最大支流,它發源于巾國和哈薩克斯坦的界山加格爾雪山。白色的河水,就來自加格爾雪山下的眾多冰川。
阿克烏魯袞山谷要比喀納斯河谷窄許多,河谷中間沒有特別開闊的谷地和大片的森林。由于河水經常會使河岸的山體塌方,馬道不得不一次次向高處轉移,行走起來也就更加崎嶇艱難。我們經常會為過一個塌方地段,騎馬爬上超過70°的大坡,然后再沿70°的大坡下來。雖然路段不長,但卻耗時很久。我們有時還會在半山腰上穿越一片巨大的石頭灘,這些大小不等的碎石,都是幾千乃至幾萬年前地質運動帶來的結果。在喀納斯河谷區域,這樣的塌方泥石流隨處可見。我時常在想,如果當時這些地質運動再大點,從山頂滾落而下的石頭就會阻擋住河流,在它的上游就有可能形成一個新的堰塞湖。那么,喀納斯區域的景觀或許比現在更加豐富多彩。實際上,現在的喀納斯湖以及河道上的許多湖泊,就是當年冰川運動和地質運動的結果。
我進而在想,當今人類在發生了大大小小的地質災害后,人們總是急于疏通河床巾形成的堰塞湖,這到底是否科學和必要?試想,如果當年喀納斯周圍大大小小的湖泊形成時也有人類存在,而那時的人們和現在的人們一樣,及時清除了形成這些湖泊的堰塞體,那么,我們今天還能看到如此美妙的山河湖泊嗎?其實,我們人類經常會犯一些白以為是、白作聰明的毛病,動不動要和大自然做一番戰天斗地的抗爭。當自然界發生災難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大自然的事交給大自然自己去辦,讓它自我修復和完善,或許不失為最佳選擇。
前面一條溪流擋住了我們的去路。溪流不大,但流水淙淙。我抬眼向上看去,溪流上方不遠處有一個秀麗的飛瀑。我們棄馬徒步,踩著長滿苔蘚的石塊攀登而上。看著不遠,我們卻足足攀爬了半個小時。瀑布實際是溪流的一處跌水,溪流在流經一段舒緩的草地后,遇到一塊凸顯的山崖,它們來不及放慢速度,就順勢跳下了山崖。巖石將瀑布梳理成扇狀,在周圍綠草鮮花的映襯下顯得格外耀眼。
滿足了好奇心,我們幾人順著溪流返回原路。這時,天空開始下起了小雨,馬隊也把我們幾人遠遠地拋在了后面。在小雨巾騎馬穿越叢林,更加感覺無人區的幽靜和神秘。漸漸地,山谷也變得開闊起來,河床更加舒展,馬兒也可以快步小跑了。
我們從一段開闊的河段過河,馬隊從河的左岸轉移到右岸繼續前行。這里的森林開始變得茂密,絕大部分是西伯利亞云杉和冷杉組成的巾幼林。越往里走,森林越密,樹干和松枝上長滿了松蘿。
松蘿是一種寄生植物,它靠吸收雨露和空氣中的潮氣就能生存。過去我們曾經錯誤地認為,松樹上長松蘿是因為空氣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結果。但當我走過許多無人區后卻驚訝地發現,空氣越是純凈和濕潤,樹木上越是容易寄生松蘿。松蘿生長的多少,恰恰證明了一個區域生態環境的優劣。當然,任何事物都是雙刃劍。松蘿生長多了,也必定會影響樹木本身的生長。在森林巾,我們常常會看到周身纏滿松蘿的高大云杉已經沒有幾片綠枝,甚至連生命都奄奄一息了。
想起了一個故事。前些年,針對松蘿影響樹木生長這一情況,有人建議從云南引進滇金絲猴,因為它們是松蘿的天敵。但有人針鋒相對地提出質疑,請你首先解決它們的過冬問題,因為滇金絲猴根本無法抵御喀納斯區域冬季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這個故事成為保護區內當時廣為流傳的一則笑話。
在夜幕降臨前,我們到達阿克烏魯袞管護站。天色陰沉,氣溫驟然下降。看來,今夜會有一場大雨普降山林。說不定,明天早晨遠處的山頭上還能看到皚皚白雪呢。
第二日
朦朧中,我們是在噼噼啪啪的燒柴聲中醒來的。
昨晚,喀猴硬纏著把我的新睡袋換走。結果,他半夜凍得睡不著覺,而我在厚厚的舊睡袋里一覺睡到了天亮。喀猴感慨說:“看來,新的東西不一定就好,舊的東西不一定就不好。”我說:“不管舊的還是新的,關鍵要看效果。就像我和巴扎爾別克這樣的老護林員,關鍵的時候,年輕人還不一定能比得上我們呢。”
起床到木屋外洗漱,一絲寒意襲上周身。經過一夜的雨水洗禮,山林在晨靄中泛著幽藍。薄霧從河谷中輕輕升起,眼看要彌漫開來,卻又緩緩收起。如此反復幾次,最終還是沒有霧漫山巒。山里的氣候就是這樣,有時候水汽太大,因為氣溫太低,反而拉不起濃霧。太陽從云縫中射出,照亮對面的山頭,金光燦燦,昨晚果然雪蓋山尖。
阿克烏魯袞管護站是兩座新蓋的木屋,木屋的炊煙在晨曦巾飄向空巾,奶茶的香味從房門里四溢開來。年輕的護林員忙著燒茶做飯,綁馬背鞍。這一切,使得這片原始山林有了些許人間煙火的味道。
早晨九點我們上馬出發,沿河北上。今天,我們要從阿克烏魯袞管護站趕到阿克吐魯袞管護站。兩個地名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卻要跋山涉水,翻越達坂,穿越叢林。也就是說,我們要從“丫”字左面的叉,跨越到右面的又。
天空慢慢放晴,山谷巾開始霧氣升騰。馬隊行走在泥濘的山路上,泥水會隨著馬蹄的踩踏四處飛濺。穿越叢林時,露水會像雨點一樣打在人的身上。但不管怎樣,森林巾的清新空氣總是讓人周身都能充滿愉悅的情緒。
我們來到卡拉迪爾山谷,阿克烏魯袞河在此由兩條河流匯合而成。向西,是歐勒袞河。向北,是卡拉迪爾河。我們今天要沿著卡拉迪爾河北上,然后翻越卡拉迪爾達坂,最后沿著阿克吐魯袞河谷進入到喀納斯河谷。
進入卡拉迪爾河谷,河水明顯小了許多。山路崎嶇不平,一會兒是石頭灘,一會兒是沼澤地。老護林員巴扎爾別克騎馬走在我的前頭,不時回過頭來跟我說以往巡護時的奇聞逸事。他似乎更加信任他的馬和他一樣會老馬識途,干脆松開韁繩扭頭和我聊天。但讓他意料不到的是,他的馬在經過一個泥潭時由于選錯了路線,連馬帶人陷入了泥潭巾。馬掙扎了幾下跳出了泥潭,巴扎爾別克表現還算靈敏,及時將雙腳從馬鐙中抽出,仰面摔在泥潭中。幾個年輕護林員將他從泥潭中拉出來,他的下半身已經滿是黑泥。
好在離河水不遠,將馬和人都弄到河邊,很快都洗干凈了。
巴扎爾別克有一點不好意思:“我騎了一輩子馬,還從來沒有掉下來過。”
我說:“今天這叫陰溝里面翻大船啦!”
中午十二時許,我們來到卡拉迪爾河溝的深處。這里,山勢已經不同于阿爾泰山前山地段那般平緩無奇,山體開始變得陡峭挺拔。越往深處,越是層巒疊嶂,山頂之上奇峰突起,白雪皚皚,霧氣彌漫在雪峰之上,雄性的阿爾泰山從這里開始盡情展現它的風姿。
在綠草如茵的河邊搭鍋起灶,不失為絕佳的選擇。巡護隊員們下馬休整,開始準備今天的午餐。
小河對岸的原始森林一直生長到半山腰上,再往上,是茂密的灌木林和夾雜生長著的稀疏松林。在一片巨大的碎石灘的上方,一條瀑布從山頂傾瀉而下。瀑布來自何方,為何出現在碎石灘的上方,其中的奧秘吸引著我們要去一探究竟。
商議之后,決定留下大部分隊員在河邊做飯休整,我和巴依爾、喀猴三人組成小分隊前去瀑布。我們三人騎馬過河,在密林巾爬至亂石灘的底部,馬已經無法再往前邁出一步。于是,我們開始棄馬爬山。從河谷對岸看,亂石堆的石頭并沒有多大,好像從一塊石頭踩著另一塊石頭很輕易的就可以上去。但真正到了跟前才發現,亂石堆上的石頭大小不等,大的足有一間房子那么大,小的也不亞于一張桌子大小。要想從一塊石頭爬上另一塊石頭,必須要手足并用。有幾塊特大的石頭,我們不得不用繩索做工具,一個一個地攀爬上去。這讓我想起了在這樣的環境下,為什么棕熊始終是爬行動物而沒有進化到直立行走的階段,爬行對于它們太有現實意義了。此時,我們這些早已進化到直立行走的人類,在這樣的環境下也不得不重溫我們祖先的行走模樣。越往上走,瀑布的聲音越大。快要接近瀑布時,我們向河谷看去,我們穿越過的森林在我們的腳下足有五六百米遠,蹚過的河流更像一條雋永的溪流,而馬隊和我們的其他隊員則像螞蟻一樣,星星點點地在河邊玩擺家家的游戲呢!
那么現在,讓我來說說眼前這條壯美的瀑布吧。這條瀑布,是從一塊巨大無比的花崗巖石上飛瀉而下的。當然,這塊花崗巖一定不是齊頭齊腦的那樣一塊規整的石頭,如若那樣,這個瀑布一定稱不上是一條好看壯觀的瀑布。想當年,這里的山體絕大部分是白色的花崗巖體,劇烈的冰川運動使這些堅硬的石頭被切割成大小不等的碎塊。冰川運動的力量足以將一座山頭削為山谷,它們將花崗巖體源源不斷地運送到現在喀納斯的巾山地帶。冰川退縮后,遺留下來的,是我們腳底這些被冰川遺落的碎石。好在冰川帶走的,是當年阻礙它自由行走的山體。而這些悄無聲息的無名之輩卻得以幸存,而今,它們儼然成為這一帶的高山雪峰。我們眼前的這條瀑布,正是從這些前世殘留的雪峰之上蜿蜒而下,滴水成河,百川匯集,最后在這塊當年殘存的巖石上攢足了氣力,然后傾瀉而下。
我們目測這條瀑布,上下足有四層樓房那么高,寬度足有四五十米。現在,正是枯水季節,如果是豐水期,它的壯觀程度,無須述說也可想而知了。但不管怎樣,現在的這條瀑布已經足以證明它是喀納斯區域最大的瀑布。叫它瀑布之王,實至名歸。
喀猴感慨說:“原來喀納斯也有大瀑布啊。”我說:“只是它藏在深山人未知呀!”
我們從瀑布的左方,艱難地移動到右方。隨著視角的變換,瀑布也在變換著它的形狀。但不管怎么變化,這條瀑布始終不變的,是它的大氣磅礴和雍容華貴。在這樣的瀑布面前,沒有人會舍得扭頭離去。
當我們再次像哈熊一樣手腳并用攀下山崖時,已經整整耗去了三個小時。匆匆用過午飯,抬頭看見河谷對岸的山頭已經堆滿了黑云。巴扎爾別克說:“看來又要下雨,我們得趕快走。”老天爺很給面子,在我們攀登山崖探尋瀑布時,它始終在用藍天白云眷顧著我們。
騎馬繼續行進,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極具西伯利亞特征的山水油畫。大花柳葉菜開滿在河床邊。乳白色的河水舒緩地流淌在河谷的灌木林間。松林從溝底茂密地鋪展向峽谷兩側的山腰。兩岸的青山巍峨挺拔高聳云間。谷口的正北方是加格爾雪山下高大磅礴的卡拉迪爾達坂。
我們此刻,正是要去翻越那雪山之下的卡拉迪爾達坂。
深山里的天氣變化無常,河谷對岸山頂的烏云隨著風勢向我們擠壓過來,把剛才還藍天白云的北方天空涂抹得灰蒙蒙一片。應了剛才巴扎爾別克的話,是要下雨了。細雨伴隨著寒風很快就追上了我們的馬隊,所有人都將能穿的衣物全都穿裹在身上。越往北上,海拔越高,氣溫也就越低,細雨漸漸變成了雨夾雪。繼續向北已經無路可走,風雪之中隱約可見的冰山擋住了我們的去路。現在,我們要向東翻越卡拉迪爾達坂,這是通往喀納斯河谷的唯一通道。
卡拉迪爾達坂不像果戈西蓋達坂那樣險峻,但它卻高大得似乎永遠都爬不到山頂。天空巾紛揚著鵝毛大雪,腳底下是雪水泥濘的草地,馬隊在爬完一個坡梁后前方又會出現一個望不到盡頭的坡梁。連續幾天的降水,高山草甸已經被浸泡成了雨雪交融的沼澤地。這里,竟有一處牧人的氈房。一白一黑兩只大狗狂叫著遠遠地迎接我們,氈房前站著兩個年輕的牧人。由于環境嚴酷,這一家只留有這兩兄弟在這里放牧。海拔過高,這里不長樹木,甚至連灌木都不生長。幾截從溝底拉來的松木被兩兄弟高高地供在氈房門口,生怕被雪水打濕了,那是他們用來生火做飯的唯一燃料。還有棕熊,兩兄弟告訴我們,棕熊常常前來騷擾他們的生活。他們經常眼睜睜地看著體態肥大的棕熊大搖大擺地走進羊群,然后扛起一只肥羊向后山揚長而去。我們順著牧人兄弟給我們指的道路繼續往前走。他們告訴我們,爬到前方的那個坡頂,有一個圖瓦人堆起的敖包,那里就是下山的道路了。在敖包處,我們仿佛站在了天上。
都說上山容易下山難,不光徒步如此,騎馬同樣如此。而且,上山爬多少的坡,下山也要走多少的路。天空不再風雪交加,但云霧遮擋住下山的道路,我只感覺眼前是一個巨大的山谷。馬兒在幾近垂直的山道上謹慎下行,馬蹄不時會在濕滑的草地上打幾個趔趄。隔著云霧,我隱約看到腳下的山谷巾有一道蜿蜒的白色河流,起初我以為是喀納斯河,但隨著云開霧散,發現山谷巾沒有幾棵樹,河流也是發源于不遠處的幾座冰山。猜測這一定就是阿克吐魯袞河了,它和阿克烏魯袞河并行流入喀納斯河的上游。也就是說,我們昨天從阿克烏魯袞河流入喀納斯河的出口進入,繞了一個巨大的彎子后,現在即將從阿克吐魯袞河匯入喀納斯河的出水口出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喀納斯河是一面旗幟的旗桿,那么我們這兩天行走的路線,就是這面向左面飄揚的旗幟的邊沿。
但前方,仍有漫長的下山道等待著我們去艱難地走。
第三日
早晨,醒來時我才斷定自己確實是睡在阿克吐魯袞管護站的木屋里。因為,我做了一晚上的噩夢。在夢里,我一會兒是睡在蓋滿厚厚白雪的卡拉迪爾達坂上,一會兒我們還在漆黑的夜里騎馬走在陡峭的山崖上,一會兒又是阿克吐魯袞管護站的護林員在晚霞巾迎接我們。我確定不了這些夢境的真假,我多么希望醒來時自己是真實地睡在管護站的木板床上。
昨天,我們確實走了太多的路程,經歷了風霜雨雪,也經歷了藍天白云,最后,還看到了晚霞照映雪山的景致。下阿克吐魯袞河谷時,喀猴的馬開始拒絕下山了。無奈,喀猴只好徒步牽馬下山。我們下到阿克吐魯袞溝底,喀猴和他的那匹可憐的老馬還在半山腰上。我們在溝底下馬休息,等待喀猴和他的馬慢慢下到河谷。天空開始放晴,從溝口向喀納斯河谷對岸的層層雪峰看去,朵朵白云正從山尖升起。夕陽從我們下來的大山的另一面斜照到山谷對面的山頭,條條溪流像白色的玉帶從冰雪末端緩緩流向山谷。阿克吐魯袞河像歡快的小馬駒奔向喀納斯河谷,河邊盛開著大片紫色的大花柳葉菜。漸漸地,天色變暗,西天涂抹了幾片橘紅色的晚霞。我問巴扎爾別克:“大概還有多長時間下到阿克吐魯袞管護站。”他說:“大概兩個半小時吧。”聽了他的話,嚇得我們全都伸長了舌頭。難怪,我們昨晚到達阿克吐魯袞管護站時,早已空山寂靜,夜幕降臨。
今天,是巴依爾和巴爾斯的節日。起床后,大家都非常紳士地向他們表達了祝福。大學生軍官巴爾斯說,能在巡邊途巾過一個節日,還真有意義。巴依爾和巴爾斯都是當地土生土長的圖瓦人。巴依爾是白哈巴村人,應征入伍后,作風和軍事素質過硬,現在已經擔當了喀納斯邊防派出所的副所長。巴爾斯是喀納斯村人,是個80后,大學畢業后入伍提干,現在已經成為派出所的業務骨干。從這兩個年輕人身上不難看出,當地人通過自身努力,不僅融入了現代社會,并且已經成為了保護和建設家鄉的重要成員。
昨夜又下了一場大雨,空氣巾充滿了雨水和青草的味道。巴依爾和巴爾斯幫助年輕的護林員在馬背上捆綁行囊,看得出,他們從小就練就了這些在山里必須熟練掌握的生活技藝。
今天我們將沿著喀納斯河谷前往白湖,沿途大多是較為平緩的原始森林和林中空地。用巴扎爾別克的話說,和昨天的路途相比,我們今天走的將是高速公路。這也就使我們有了足夠的時間來探討一些平時感覺好奇的問題。
我一直弄不明白,阿克烏魯袞和阿克吐魯袞兩條河流的名字如此相似,但這一字之差究竟蘊含著什么意義。按照巴扎爾別克的解釋,應該都是白色的溝趟子或白色的河流的意思。我就對此有異議,如果真是一個意思,為什么兩者非要差一個字呢?喀猴卻有他獨到的見解:“阿克烏魯袞因為河谷較小但河水流量大且水流湍急,翻譯成白色的河流應該沒有問題;而阿克吐魯袞卻主要說的是這條峽谷的幽深和幽靜,那么翻譯成漢語的標準意思應該是,流淌著白色河流的幽深峽谷。”一條說的是河流,一條說的是峽谷。這樣解釋似乎很有道理,小的河谷流淌著一條白色的大河自然是白色的溝趟子,高深的峽谷中間流淌著一條白色的小河白然是流淌著白色河流的幽深峽谷。
巴扎爾別克說:“從現在開始到白湖,途巾還要經歷十個溝趟子。”大家都說:“我們經歷了阿克烏魯袞和阿克吐魯袞兩個那么大的溝趟子,你的這十個小溝趟子還能算得上是溝趟子嗎?”
馬兒和騎在它身上的人們今天心情都很愉快,密林巾不時傳出馬兒快樂的響鼻和人們歡快的笑聲。
巴扎爾別克更是來了興致,他說:“我給你們講一個故事吧:從前,有一個老漢,在他快要離世的時候,看著自己的老伴想說什么話又不好意思說出來。老伴給他說,老頭子你有什么話你就說吧,我受得了。老漢從他睡的氈子底下摸出了五個羊髀石,含著眼淚說,老婆子,我對不起你,我這一輩子嘛背著你有過五個相好。老伴聽后走出門去,回來的時候圍裙里兜了二十八個羊髀石。”
我們全都在馬背上笑翻了。喀猴說:“你的這個故事嘛,我們都聽你講了二十八遍啦!”
我說:“老巴下一次再講這個故事,就是二十九個羊髀石啦!”
自然,我們接下來經過的十個溝趟子,就像十個小渠溝,在我們的歡聲笑語巾,輕而易舉地被我們的馬蹄甩在了后面。
從阿克吐魯袞管護站到白湖管護站,正常速度要用三個小時,而我們今天只用了兩個小時多一點就到了。白湖管護站是喀納斯保護區內最遠的管護站,距離中俄邊境不足十公里。在這里,由于是保護區的核心區,至今沒有人類生產生活的痕跡,因此它保存著喀納斯區域最為完整的自然生態體系。
中午,我們在白湖管護站吃過午飯,接著騎馬趕往七公里外的白湖。今晚,我們要露營在白湖湖邊。明天,我們將利用一整天時間,對白湖周邊進行巡護和野生動植物普查。
我們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到達白湖的西岸。湖邊青草沒過膝蓋,在我們到來之前,這里沒有一絲人類活動的跡象。柳蘭、穿葉柴胡和聚花風鈴草成片地開放在湖邊的草地里。幾棵當歸孤零零地生長在湖邊的石頭縫隙巾,愈加顯得玲瓏妖媚。湖北坡的果戈習蓋達坂高聳入云,看不到山頭。湖南岸的別迪爾套山層巒疊嶂、雪峰連綿。正前方的群峰上升起大朵的白云,乳白色的湖面在下午陽光的照耀下顯得格外明亮。置身于這樣的環境中,三天的馬背顛簸勞累頓時化為烏有。我們每個人,像打了雞血,興奮異常。
在天黑以前,我們要做好兩件事。一是搭建好晚上睡覺用的帳篷,二是利用風倒木做一個明天過湖用的木筏。我們分為兩組,巴依爾和巴爾斯帶一組負責搭建帳篷和做晚飯,巴扎爾別克和喀猴帶一組負責找木頭做木筏。我這個老護林員負責給兩個組的人拍照留念,紀錄他們的工作過程。很快,五頂帳篷搭建好了,巴依爾和巴爾斯開始給我們做晚上吃的抓飯。而做木筏子就沒有那么簡單了,首先要找來不粗不細的幾根風倒木(太粗了會很重,太細了又承載不住六個人的重量),然后截成五根差不多四米長的木筏原材料,巾間再用四根小木棍把五根木頭用釘子和鐵絲連接牢固,木筏子就基本做成了。光有木筏子還不行,還得有劃木筏用的槳。于是再找來六根干木棍,用斧頭砍成木槳。
木筏子完全做好放在湖邊時,太陽離西邊的山頭還有一丈多高。抓飯的香味開始從帳篷邊飄過來,一下午的體力勞動,這時大家確實都感覺到真的餓了。
吃過晚飯,太陽還沒有落到西面的山頭。我來到湖邊,欣賞這人跡罕至的湖光山色。白湖本來的名字叫阿克庫勒,直譯成漢語就是白色的湖泊,因此人們通常就叫它白湖。白湖因湖水終年呈白色而得名。白色的湖水,來自于友誼峰西南側的喀納斯冰川以及白湖周圍大大小小的眾多冰川。在冰川運動中,白色花崗巖相互擠壓,在冰層巾夾雜著大量花崗巖粉末,冰川融化時,這些白色粉末被河水攜帶著流入白湖。從空中看,白湖是一個倒寫的“人”字。人頭是…水口,兩條又是進水口,靠北邊的一條進水口來自友誼峰下的喀納斯冰川,靠南邊的一條進水口來白發源于友誼峰南坡的布的烏喀納斯達坂。當然,這只是H湖的兩條主要水源補給地,白湖周圍的眾多冰川也在為它源源不斷地輸送著水源。
就在我把自己的思緒放在空巾,盡情描繪著白湖周圍的山川河流時,一陣山風吹過,從果戈習蓋達坂的山頂涌來一片黑云,接著天空下起了小雨。我在想,如果過一會兒雨過天晴,太陽還沒有下山,在白湖的上空很有可能會出現彩虹。因為下雨的地方只是我們的頭頂和靠近我們這一邊的H湖的上空,白湖對岸的天空依舊是藍天H云。很快,山風將頭頂的烏云吹散,太陽從西面的山頭向白湖照射過來。這時,我們所期盼的奇跡果真發生了。我們看見一道彩虹漸漸出現在白湖的上方,而且,這道彩虹愈來愈清楚,最后竟然變成了兩道七色的彩虹。在喀納斯區域,由于特殊的自然環境,雨后經常能看到漂亮的彩虹。能在白湖之上看到橫跨兩岸的雙道彩虹,而且它的背景是潔白的湖面、兩岸的群山和對岸的雪峰以及雪峰之上的藍天白云,這真的有一點像在夢境中看到的景象。但同伴們的歡叫聲告訴我,這一切的確真實地發生在現實之中。巡護隊員們全都簇擁到湖邊,驚嘆這在人世間看到的只有在夢巾才有可能出現的美輪美奐的奇特畫面。雙道彩虹在湖面上足足持續了十幾分鐘,最后,圓弧慢慢開始變淡,而插入靠近右岸湖水巾的那兩根弧柱,卻越來越清晰地倒映在白色的湖面上。
我們全都肅立在湖邊,面朝東方,向這個神圣的景致行注目禮。
當太陽被西邊的山頭遮擋住光芒,我們剛才看到的一切立刻不復存在。巡護隊員們相互擁抱,互致問候,祝賀大家看到了剛才那難得一見的絕美景色。但熱鬧間忽然發現人群里多了兩個年輕人,這著實嚇了我們一跳。喀猴最先認出他們。兩個年輕人分別是小崔和小陳,他們是巾科院派來的研究生,專門調查白湖區域野生動物的種類和分布情況。他們已經在白湖周圍的高山森林和湖區安裝了三十多臺紅外感應自動攝像機,每天都要在這深山老林巾徒步行走十幾公里。小陳手巾拿著一個紙袋,他告訴我們,他們剛才在湖邊采集了棕熊的糞便,從糞便的新舊程度看,棕熊應該在昨天來過這里。
小崔和小陳還要趕到七公里外的白湖管護站,他們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暮靄里。
我們提醒他們:“走夜路,注意安全,明晚我們也返回白湖站。”
“明晚白湖站見。”叢林里傳出他們稍顯稚嫩的聲音。
第四日
昨晚,我們的馬就散放在我們睡覺的帳篷周圍吃草。俗話說,馬不吃夜草不肥,馬全靠在夜間吃草補充能量。而且馬是直腸子,可以一天到晚站在那兒不停地吃草。在草原上,你看不到一匹馬是臥在那兒或是躺在那兒的。如果有一匹馬躺在了地上,那它一定是一匹生病的馬或者是一匹即將死去的可憐的老馬。
馬吃草的聲音陪伴著我們睡去又醒來。在這樣的聲音中睡覺,人會感覺到極度的安全。馬是極有靈性的動物,有馬陪伴在身旁睡覺,就不用擔心夜間會有棕熊或是其他野生動物侵擾我們。馬雖然斗不過棕熊,但它在緊急情況下會嘶鳴和揚蹄,它會提醒熟睡的人們將有危險到來。自然,野生動物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愿讓自己處在任何危險之巾,通常它們會轉身離去,不會做無畏的冒險。
我穿好衣服,拉開帳篷的拉鏈鉆出來,帳篷的外層防雨布結上了一層寒霜。天空晴朗,山林寂靜,白湖沉醉在一層淡淡的晨曦巾。巴依爾已經在生火做飯,火苗從石頭壘砌的爐灶底歡快地舔著茶壺的周身。一縷青煙先是在松林間繚繞,然后慢慢飄向湖面,最后和湖面上輕輕的晨霧融為一體。太陽還被東方的山頭遮擋在背后,但它早已把南岸雪山冰峰的尖頂照亮。光線從山頂逐漸向山下移動,等到移動到山腰之下,陽光從東方的山尖處猛然躍出,我們所在的湖岸被朝陽完全普照了。
早餐后,我們巡護隊分為兩組,一組由巴扎爾別克帶隊,留守在駐地,就地查看巡護。我和另外五人組成一組,劃昨天做好的木筏沿白湖的周邊巡護。這另外五個人是:巴依爾,巴爾斯,喀猴,恰特克,木拉提汗。
剛出發時我們幾個人劃槳的動作很不協調,木筏要么原地不動,要么就地打轉。后來,巴依爾像訓練軍人那樣給大家做示范,喊口號,不厭其煩地給大家講基本動作要領。最后,經過突擊訓練的六個人終于做到動作一致,用力均衡,木筏才向著湖心慢慢移動。
這是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海拔1900多米的白湖上劃槳前行。要知道,白湖最深處達137米,平均水深也達到45米。在這樣一個深水冰湖巾劃木筏度湖,稍不留神后果將不堪設想。因此,我們選擇沿湖邊劃行的線路,始終和湖岸保持著二三十米的距離。這樣,一旦遇有不測,很快就可以靠到岸上。
我們是從白湖“人”字形的湖頭向里進發的,現在我們將沿著“人”字形的一捺進到喀納斯河流入白湖的入湖口,再拐到“人”字形的一撇劃行到白湖的另一個入水口布的烏喀納斯河,然后,從那里登上別迪爾套山,考察那里的冰川凍土和野生動植物資源情況。
在面積達9.5平方公里的白湖上不靠機械動力,全憑人力劃槳來沿湖考察,在用力劃槳的時候認真想一想這件事,我們這些人的膽子還真夠大的。要知道,白湖的面積雖然是不到十平方公里,但它的湖面是不規則的,它是一個“人”字形的湖泊。而且,我們的劃行將是沿著這個“人”字的周邊劃行一圈,這一圈,少說也有十幾公里。
就在我們的木筏拐入喀納斯河谷方向的時候,喀猴興奮地壓低聲音喊道:“快看,那個入水口的岸邊有一只棕熊。”我們迅速將木筏劃行靠岸,借助岸上的石頭做掩護,觀看入水口那邊的情況。
在喀納斯河流入白湖的白色沙灘上,我們清楚地看到一只體型龐大的棕熊獨自在那里戲耍。它一會兒低頭喝水,一會兒抬頭向四周張望。我們想用望遠鏡搜尋還有沒有它的同伴,但周圍沒有任何動靜。喀猴說:“這是一只公熊。”沒錯,在這個季節,正是幼熊的成長期,母熊都會帶著它們的孩子在自己的領地四處覓食。這些年,我們巡護巾看到的母熊一般都會帶著一到兩只小熊,最多時我們看到過一只母熊帶著三只小熊在山坡上玩耍。而公熊就不同了,公熊在山林巾往往都是獨來獨往,如同孤家寡人一般。母熊只有在發情期才會允許公熊在身邊存在,它們一旦懷孕生子,就會遠離公熊,愛子如命,全身心地養育自己的孩子。因為公熊為了占有母熊,往往會不擇手段地殺害幼熊,所以母熊在哺乳期間絕不會讓公熊靠近身邊半步。在公熊面前,母熊會顯示出極強的護子本能。
我們想要把木筏再往前劃一點,以便更清楚地觀察公熊的活動跡象。但公熊似乎覺察到了我們的存在,快速向入水口對岸的密林跳躍著跑去。公熊跑幾步還要停下來,回過頭來向我們這邊張望一下,顯得極不情愿的樣子。
我們繼續劃著木筏,從“人”字的一捺劃向“人”字的一撇。但這一捺到一撇,足足耗費了我們三個小時。
臨近午時,我們才把木筏劃行到布的烏喀納斯河流入白湖的入水口。我們真正體驗到了什么叫作“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從喀納斯河入水口劃向人字的拐彎處,基本上是順風順水,使大家節省了不少的體力。但一過拐彎處開始往布的烏喀納斯河的這條溝劃行的時候,即逆風又逆水,人累得半死,卻感覺不到木筏是否在前進。我們索性把木筏靠近湖的岸邊劃行,這樣既可以遠離河道的主流,又可以借助山勢阻擋風速對木筏的阻力。
我們進入白湖的這一條入水口,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涉足這里的沙灘。為了減輕木筏的負荷,我們只帶了一小袋干糧和一只燒水的茶壺。巴依爾的野外生存能力非常強,他找來一根胳膊粗細的木棍,斜插在沙灘上,用刀子在離地五六十公分的地方刻了一個深槽,將打上水的茶壺掛在木桿上,然后在茶壺底下點起一堆火。很快,我們就喝上了熱氣騰騰的茶水。
就在巴依爾做著這些的時候,喀猴和巴爾斯也沒有閑著。喀猴在河谷沙灘的灌木林里發現了許多大小不等的棕熊的腳印,他把它們一一拍照并記錄下這些腳印的特征。巴爾斯在認真地擦拭著他一路背來的半自動步槍,他的任務是在野生動物襲擊我們的時候開槍嚇走它們。恰特克和木拉提汗卻在那兒爭論不休,他倆到底誰留下來看護木筏。喀猴做完他的工作回來決定說,恰特克腿長爬山快,還是木拉提汗留下來看護木筏。實際上,在這樣的環境里,沒有人愿意一個人待在一個地方,集體行動是最安全的選擇。
喝完巴依爾燒的熱茶,我們現在開始創造一項類似于人類登月的歷史紀錄,攀登白湖南岸的別迪爾套山。的確,這里是名副其實的無人區。無論是從東西南北,無論騎馬和徒步,都無法進入到這個區域。東面,是白雪皚皚、高大巍峨的友誼群峰。南面,是連綿的雪域高原和亙古冰川。西北面,則有崇山峻嶺下的白湖和洶涌冰冷的幾條大河阻擋。用木筏做交通工具并成功橫渡了白湖,這在白湖上還是首創。
從第一步開始,我們已經切實感受到,今天要攀登的這座山,不僅僅是陡峭的,并且是高大的。我們選擇從一處山脊登山。首先,我們要穿越五百米左右幾近在垂直山體上生長的密林,這里主要生長著西伯利亞云杉、冷杉和很小一部分五針松,林下多為柳屬喬木以及其他交錯生長的灌木。在這樣的叢林中登山的難度可想而知。我們選擇沿山脊攀登,就是為了能很好地觀察地形,避免在密林巾迷失方向。
在這樣的原始密林中穿行,尤其要防范野生動物的偷襲。這一區域,正是棕熊活動的領地。巴依爾從巴爾斯手巾接過半自動步槍走在前面,剩余幾人緊隨其后。越往上攀登,山勢越陡峭,森林就長在巖石之上。我們腳下是長期積累的厚厚的腐殖質和潮濕的苔蘚,稍不留神雙腳就會陷進石縫當巾。忽然,巴依爾在前面示意我們停下腳步。我們全都躲在巖石下,屏住呼吸,不敢發出任何聲響。山林寂靜,空氣凝重。我們這時最害怕聽到的是巴依爾的槍聲,畢竟,和棕熊狹路相逢,是大家都不愿碰到的事。過了一會兒,巴依爾又打手勢叫我們過去。他指著地上的一堆棕熊糞便說:“看,應該是棕熊昨天從這里走過留下的。”我們愈發感覺到棕熊隨時都有可能會忽然出現在我們面前,身邊隨時都可能發生危險,大家都緊緊跟在巴依爾身后,生怕自己掉隊后成為棕熊的口中美餐。
終于,我們手腳并用地攀登到林子的盡頭。我們站在山脊的一塊凸出的巖石上,腳下是一條深深的“U”型谷,河谷巾流淌著一條蜿蜒的河流。河谷的最上方,是連綿的雪山。雪山之下是一條冰舌嚴重萎縮的冰川,小河正是發源于這條冰川之下,喀猴說,這條冰川名字叫48號冰川,今天終于能夠近距離看到它了。這是喀納斯湖區域內兩百多條冰川中的一條,實際上,這些冰川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喀納斯河的上游區域,喀納斯河包括它下游的喀納斯湖,正是這每一條冰川融化后形成的涓涓細流匯集而成。冰川融化后形成了河流和湖泊,流向下游,滋潤著廣袤的大地。而冰川本身,卻像耗盡了血液的軀體,不斷向后萎縮。我們眼前的這條冰川,就足以證實喀納斯現有冰川向后加速退縮的嚴重性。
天空中開始涌起朵朵白云,對面雪山的輪廓時而清晰,時而模糊。這幾天的氣候很有規律,早晨是碧藍的晴空,巾午大朵的云彩布滿天空,到了下午就變得黑云壓頂,免不了有一場或大或小的雨水。看來今天也不會例外,我們必須要加緊后面的行程。
好不容易才將密林甩在了腳下,前面又是大片的石礫堆滿山腰。接下來的路程和我們第二天去看瀑布的艱辛程度差不了多少,我們必須要從一塊石頭跳向另一塊石頭往前行走。這些石礫都是數千年前地質運動從山頂上滾落下來的,石礫上的石蘚足以能夠證明它們的年代。我們向山下看去,白湖已經開始呈現在我們面前。但現在我們看到的白湖,只是細長的一條白色湖面,因為我們現在的高度還不足以看到它的全貌。
那么我們要看清白湖的全貌,就必須向上攀登到足夠的高度。當我們跋涉過漫長的石礫堆,緊接著阻擋我們的是濃密的灌叢,這些灌叢是清一色的高山小葉樺。它們應該是疣枝樺的變種,因為海拔太高,它們不得不變異成為低矮的灌叢,在這里匍匐著生長。也正因為如此,小葉樺枝干交錯,長得極為稠密。而且這里山勢陡峭,我們每邁出一步,都要用手拽住上方的灌叢,手腳并用向前跋涉,否則我們只能是舉步維艱。在這高高的山巔之上,在低矮灌叢的碎石堆巾,大花柳葉菜和西伯利亞耬斗菜正嬌艷地開放。
就這樣,白湖在我們的腳下,一寸一寸展現在我們面前。起初,它只是一道細長的湖面,隨著我們一步步登高,它一點點將它的面貌變寬變長。當我們攀登到超過海拔3000米的高山草甸處,我們的腳下幾乎已經沒有了可供站立的土地。這里是超過70°的陡坡,每走一步,都會帶動無數的碎石向山下滾落。再向上攀登,已經不再可能。我們決定停下腳步,終止這次用生命換取的賭博。我們依著山勢坐下來,平心靜氣地面朝山谷,內心不由肅然起敬。在我們的眼前,在崇山峻嶺之中,分明是一座呈“人”字形狀的乳白色的湖泊。這座湖泊,最初我們看不到它的形狀,但隨著一步步登高,它愈來愈神形并茂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看著眼前這座像牛奶一樣潔白的湖泊,我們既興奮又自豪。在這個從來沒有人類涉足的高山之上,我們是用雙腳,一步一步地將眼前的這個湖泊丈量成了“人”字的形狀。
白湖的上空布滿了陰暗的烏云,我們必須要趕在天黑之前返回白湖管護站。我們后面的路還長著呢,要連滾帶爬地下山,要將木筏從湖尾再劃回湖頭,還要將湖頭的帳篷收起,騎馬回到白湖管護站。當做完這一切,不到夜幕降臨,那才怪呢!
第五日
本來我們是下決心要睡到自然醒再起床的,但這個白然醒卻來得過早。也許是因為昨天我們都付出了太多的體力使得我們夜晚的睡眠質量過高,也許這山林之巾的負氧離子過于充分讓我們在最短的時間就恢復了體力。總之,這幾天我們雖然睡得晚,但卻都能早早地醒來。而且,過量的體力付出并沒有讓我們感覺到絲毫的身心疲憊,相反,我們每個人都變得精神倍增并且身輕如燕。
我走出爐火正旺的木屋,室外的遍地野草鋪滿寒霜。今天又是一個好天氣,峽谷上方的窄長天空上沒有一絲云彩。白湖管護站所處的位置是整個喀納斯河谷中最為狹窄的地段,西面是陡峻的山坡,東面是滔滔奔流的喀納斯河。河谷的寬度不足兩百米,是一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要通道。正因為如此,這個管護站也成為阻擋非法采挖人員越境采挖的最后屏障。它在喀納斯保護區所承擔的作用是別的管護站無法替代的,我們戲稱它是我們這個區域最后的一道國門。
一只星鴉像箭一般從管護站前的小樹林飛向河邊的叢林,我跟隨而去。星鴉在飛行時總會發出“嘎”的叫聲,不同于其他的鳥類,它嗚叫的聲音直接而干啞,就像它飛行的速度,聲到身到,直來直往。我在叢林里找到它的身影時,這個可愛的小家伙正在一棵紅松上啄食松籽。星鴉是針葉林中的精靈,每年在松籽成熟的季節,它都會采摘大量的松籽埋在樹根底下。到了冬季和春季,它就會在林巾尋找自己貯藏的食物。當然,它們找到的往往不一定是自己埋在地下的食物,它們有可能吃到的是它的同類偷藏的食物。但不管怎樣,星鴉們享受著彼此的勞動成果,同時也在做著給森林更新育種的工作。這只星鴉似乎也發現我對它觀察太久,不等吃完一個松塔上的松籽,又箭一樣地在密林中飛走了。
我回到管護站,巡護隊員和管護站的小伙子們也三三兩兩起床了。直到這時我才看到小崔和小陳的身影,他們倆昨天出去收取安裝在各個點上的紅外感應自動攝像機,晚上比我們回來的還晚。
小崔打開他的電腦,讓我們觀看從攝像機上下載的照片和錄像。他們昨天總共取回了七臺自動攝像機,但攝取的內容已經足夠讓我們興奮不已。這些攝像機白天工作是靠捕捉到動物移動的目標,晚上工作是靠動物活動帶來的熱感應。而且攝像機捕捉到拍攝目標后先是連拍兩張照片,緊接著開始錄像。攝像機記錄下來的有棕熊、馬鹿、貂熊、雪兔等珍稀動物,而黑琴雞、花尾榛雞、松鼠以及鼠兔等就更是鏡頭中的常客了。其中一個鏡頭特別有意思,一只成年母熊帶著兩只幼熊來到攝像機前,母熊對著攝像機研究了半天,最后像是要嘗嘗攝像機的味道,伸出舌頭把鏡頭添得模糊不清,似乎是感覺味道不好,然后揚長而去,小熊尾隨其后像躲避瘟神似的狼狽逃竄。小崔和小陳告訴我們,等一個月后三十多臺攝像機全部取回后,一定會有更多珍貴的動物和它們活動的畫面呈現給大家。僅從目前這幾臺獲取的資料來看,對喀納斯實行保護并禁獵二十多年來,保護區內的野生動物,無論在種類上,還是在種群上,都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恢復,這著實令人欣慰。
吃完早飯,我們開始返程。今天,我們的任務就是返回喀納斯湖下湖口區。還記得我前面說過,我們這次行程是一個向西飄揚的旗幟的形狀吧?是的,我們今天就是要從旗桿的桿頂返回到旗桿的底部。雖然行程單一,但卻要騎馬整整走八個小時。
告別白湖站,我的內心隱隱生出一絲悲涼的情緒。當了那么多年的護林人,也算是走遍了喀納斯的山山水水,僅白湖我就來過五次。如今,自己的頭發已經變得花白,體力也明顯感覺不如從前。像這樣的巡護,不知道自己還能再來幾次。在大自然面前,一個人就像一只小蟲子那樣弱小和無助。短短的幾十年時間,人從出生到逐漸老去,仿佛是一瞬間的事情。當回過頭來看看自己經歷過的一切,頓感人生苦短,生命如梭。但讓我們慶幸的,是身邊的自然還青山依舊,流水如常。
我們騎馬在叢林中穿行,返程的馬兒總是情緒高漲,健步如飛。這是一片成年林,樹干粗大,樹冠參天。五針松是這片森林巾的佼佼者,堪稱林中之王。五針松挺拔俊美的身姿,一直以來總是讓我嘆為觀止。它筆直粗壯的腰身,娟秀婆娑的樹冠,讓同林中的其他樹種白慚形穢。也正因為這是一片成年林,林中的倒木也大多是參天的古木。一棵樹,它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只不過它的輪回要大過我們每個人的幾倍甚至十幾倍。通常,我們看不到一棵樹從生長到死去的整個過程,就像一棵樹無法證實冰川消融的整個過程一樣。實際上,大自然和我們人類一樣,也在進行著生老病死的演變過程。只是我們每個人的一生太短暫,以至于根本看不到大自然從有到無的周期變化。
早些年,冰川學家崔之久教授告訴我,我們現在正在行走的這條喀納斯河谷,在兩萬年前,這里還被幾百米厚的冰川覆蓋著。那時,喀納斯區域大部分山川河谷都覆蓋著冰川。而在更早期的十二萬年前,喀納斯的冰川甚至長達一百多公里,一直延伸到現在的駝頸灣區域。這還都是現代冰川,至于古冰川,那都是二十萬年以前的事了。比如地球兩極周圍所覆蓋的冰層,它們的壽命都可以追溯到二十萬年以前。我記得我追問教授:“那么我們眼前的冰川徹底消融之后,我們人類該怎么辦?”教授顯得非常樂觀:“還會有一個冰期要到來。”我再問:“在那個冰期到來之前我們怎么辦?”教授顯得很嚴肅:“所以我們經常提醒,人類最好不要人為加速眼前這些冰川的消融。”我記得當時我們都沉默很久。
現在,騎馬走在深深的河谷里,我努力地展開想象,想象教授所說的古時的冰川,會是何等的綺麗壯觀和不可一世。那時的冰川應該像一只巨大的冰蓋,把阿爾泰山的崇山峻嶺覆蓋得白茫茫一片,它們在陽光的照射下放射出晶瑩剔透的藍色光芒。壯麗磅礴的冰川為每一條河流提供著豐沛的水源,額爾齊斯河一定寬闊得茫茫無邊,奔騰的河水使得兩岸的廣袤大地綠意盎然,生機勃勃。
但這些年,我們又的確看到了大自然加速演變的另一面。氣候在變暖,冰川在消融,河水在變小,草原在退化。這一切,與自然本身的演變周期有關,但我們人類對自然的過分貪婪和索取也加劇了它惡化的速度。在大自然演變進程的這一出大戲里,我們人類往往充當不好主角,也飾演不好配角,我們經常扮演的是遭人唾棄的丑角。我們既然沒有能力演好主角和配角,我們能否盡量少去扮演可惡的丑角。更多的時候,我們只需靜靜地躲在一邊,老老實實地充當大自然的觀眾,少去人為地去招惹它,而是努力地去適應它,去順應它,去呵護它,去欣賞它,更不要做什么人定勝天的所謂大事。就像我們面前的這些冰川、河流和湖泊,人為地稍微觸碰,可能就會帶來巨大的災難。
這正如湖泊來源于河流,河流來源于冰川,那么,當這些日益萎縮的冰川最終化為烏有的時候,我們眼前的河流和湖泊中流淌著的,還會是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生命之水嗎!那時在大地上流動的,一定只有黃沙、亂石和干裂的土地。真正到了那時,我們人類只能是欲哭無淚,走到了盡頭。
那么,讓我們守護好自己身邊的這塊自然山水吧!如果你身邊有一棵小樹,請常常用水把它澆灌,讓生命之樹向著太陽快樂生長;如果你身邊有一條小河,請不要隨意修筑堤壩,讓河流曲曲彎彎自由流淌;如果你身邊有一座高山,請常常為它投去仰望的目光,讓雪山和冰川永駐生機和希望;如果你身邊有一片大海,請時刻保持敬畏的距離,讓海水永遠碧波蕩漾蔚藍如常。
想到這些,我的內心忽然感到豁然開朗。我仿佛不是騎馬走在喀納斯的河谷里,而是騎著一匹騰云駕霧的飛馬,行走在高高的阿爾泰山的山嶺之上。原來,我的內心并沒有變老,作為一個老護林人,我仍然還保留著一顆年輕的心。我之所以能保留著一顆年輕的心,正因為像處女一樣年輕的喀納斯,給了我無限愛它的理由和動力。想著這些,我就會心情愉悅地揚鞭策馬,穿越一片又一片森林,趟過一條又一條河溝。八個小時的騎馬行程,對一個心態年輕的老護林人來說,根本不在話下。
當馬隊穿越最后一片森林,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夕陽斜照下波光粼粼的喀納斯湖。而二十四公里的湖外,那里有我的親人和同事正守候著我的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