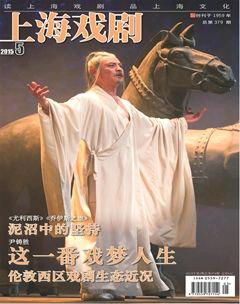身體敘述生命之思
孫韻豐
肢體劇《1971》改編自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莫言的作品《蛙》,以出生在高密東北鄉(xiāng)的“我”作為主線敘述人,向觀眾講述“我的姑姑”萬心的故事。七十分鐘的作品,緊扣“姑姑”作為一名鄉(xiāng)村女醫(yī)生從幫人接生到追人“計生”的經(jīng)歷,將上世紀(jì)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國生育史展現(xiàn)在了舞臺上。
用肢體劇的形式來展現(xiàn)《1971》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身體,在這里成為了全能的敘事者。舞臺以黑色幕墻為底,劇中所有演員都身著黑色中性演出服裝,這樣的設(shè)置為演員預(yù)留了最大表現(xiàn)空間。這部讓觀眾時而笑不能止,時而默默流淚的戲,在多處細(xì)節(jié)的處理與表現(xiàn)方面讓觀眾驚嘆導(dǎo)演的想象力以及演員們的身體表現(xiàn)力。比如,開場的群蛙出場,點(diǎn)出“蛙”這個劇中最重要的象征符號,所有演員都用身體模擬青蛙彈跳入場,鼓起腮幫子惟妙惟肖。在描述“姑姑”的出身背景時,表現(xiàn) “姑姑”過世的父親,演員巧妙運(yùn)用身體造型表現(xiàn)出逝者的遺像、祭臺,使得舞臺充滿意象。當(dāng)“姑姑”成為鄉(xiāng)里有名的接生女醫(yī)生后,她騎著自行車接生了一名又一名新生兒,在這一情節(jié)的表現(xiàn)過程中,所有演員通過各自身體的組合與造型,活靈活現(xiàn)地擺出了一臺“自行車”,“姑姑”坐在這輛“組裝”的自行車上奔波鄉(xiāng)里去迎接新生命,這也著實(shí)讓臺下觀眾眼前一亮不得不佩服導(dǎo)演與演員們的舞臺智慧。再如,在張仁美與小跑洞房之夜,那根不愿被吹滅、帶著窺視欲望的蠟燭,用了擬人化的手法去展現(xiàn),反而將“窺探房事”這樣抽象的欲望演活了。而當(dāng)“姑姑”由接生醫(yī)生變?yōu)椤坝嬌贬t(yī)生追堵張拳老婆時,身體不再是造型工具,而是成為戲劇情境中有血有肉的人物角色,此時,身體所表達(dá)出來的情感張力使得臺下觀眾感動落淚。在《1971》這部肢體劇中,身體是什么?身體是全能的載體,是不同層面的敘事者。它既是打破了“第四堵墻”跳出舞臺同觀眾交流的故事敘述者;它又是舞臺上故事內(nèi)的人物角色,有靈魂、有個性的敘述者;它還可以是舞臺上任何道具、布景的非人敘述者。身體的全能性與靈活性使得舞臺上的時空能夠自由轉(zhuǎn)換,節(jié)奏亦快亦慢,牢牢抓住觀眾眼球。
不得不提的是,舞臺上的全能身體與演員的身體基本功分不開。而這些演員平日里都要針對不同肌肉進(jìn)行形體訓(xùn)練,任何身體運(yùn)動,形體技巧的掌握,都要依靠知覺與肌肉運(yùn)動間的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具備了形體動作的基本素質(zhì),演員的形體器官就會變得像雕塑家手中的粘土一樣,能夠聽從創(chuàng)作意志的支配,用它塑造出多姿多彩的形象來。就如導(dǎo)演唐劍威談到的身體:“我覺得身體原本是厚重的、封閉的,保護(hù)我們,卻也是阻礙我們情感表達(dá)的壁壘。但經(jīng)過訓(xùn)練以后,身體就是演員表達(dá)自我,呈現(xiàn)自我靈魂的載體。”
《1971》中的身體是具有多義性的。從戲劇表現(xiàn)形式來看,肢體劇自由靈活的身體展現(xiàn),似乎與故事主旨中對于原始生命的自由追求形成呼應(yīng)。從舞臺敘事的層面來說,《1971》中的身體作為全能敘事者,形象而流暢地完成了敘述與抒情的功能。以故事文本層面來說,身體是生命的載體,在莫言原著中,人物也都以身體器官來命名,比如“姑姑”萬心、陳耳、王膽等,這本身是對生命崇拜的一種隱喻,對生命的扼殺即意味著身體的毀滅。
《1971》是一部帶領(lǐng)觀眾進(jìn)入生命思考的作品,引人回味,通過身體將觀眾帶入情境之中,它將個人置身于那個年代,展現(xiàn)那個時代下的生命境遇,體驗(yàn)身體之殤,思考生命之初。該劇正是從微觀的角度進(jìn)入到生育生命的情境之中,比如開場的孕婦生產(chǎn),是震撼卻諷刺的,男人們緊緊圍繞著臨產(chǎn)的女人轉(zhuǎn)圈,使生產(chǎn)的儀式感中又透露出封建傳統(tǒng)倫理觀念的偏執(zhí)愚昧。劇中另一處對于1975年高密東北鄉(xiāng)人口大幅增長的描述也是通過婦女生產(chǎn)來表現(xiàn),由高大的男演員鼓著肚子來扮演多產(chǎn)孕婦,臀部一蹲腿一張,一個娃躍入臺前,來來回回六個娃排成一列搶粥喝,這滑稽夸張卻又承擔(dān)著遞進(jìn)轉(zhuǎn)折敘事功能的一場戲?qū)ⅰ叭丝趧≡觥彼淖衷溨C具象地表現(xiàn)出來。在導(dǎo)演唐劍威看來,“姑姑”是時代的縮影,是中國特有的時代下產(chǎn)生的人以及這些人的生活狀態(tài),具有典型性,從她的身上又可以看到我們生活的縮影。當(dāng)“姑姑”在手術(shù)臺上親手將自己的侄媳婦兒張仁美以及肚中孩子“送走”時,全劇情節(jié)已致高潮,此時的“姑姑”身披紅圍布上場,這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形象。自此,“姑姑”開始反思,面對赤裸的生命,她矛盾、糾結(jié),此時舞臺上用肢體形式外化表現(xiàn)了“姑姑”自我矛盾、糾結(jié)的心理過程,出現(xiàn)了“面具”。在這之后的一次追堵超生孕婦王膽時,“姑姑”徹底卸下了這枚令人顫抖的面具,又用她曾經(jīng)溫暖的雙手迎來了一個新的生命。
可以說,戲的前半部分在展現(xiàn)人物外部行動時,是高效且令人意想不到的,但這部戲后半部分的人物抒情方面,尤其是張拳老婆被“姑姑”追堵時,胎死腹中,而作為母親對孩子瘋狂幻想的行動外化,從表現(xiàn)效果來說,是稍有牽強(qiáng)的。運(yùn)用身體直接地展現(xiàn)一個行動、表達(dá)一種夸張的情緒,不難,但若要運(yùn)用身體去精準(zhǔn)地傳達(dá)一種細(xì)膩的感情,也許這對導(dǎo)演和演員的功力要求就更高了。戲劇藝術(shù)中,時空的不可復(fù)制,使每一次演出都是全新的開始,每一次演出都可以去創(chuàng)新與突破,而舞臺藝術(shù)的魅力不正于此嗎?因此,期待它會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