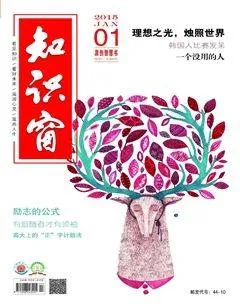謙卑的灰灰菜
姚秦川
一日,在讀徐光啟《農政全書》之《荒政》篇時,驚喜地發現,他曾寫了一段描寫灰灰菜的文字:“灰灰菜是列為人們救饑時可食用的野蔬。除了莖、苗可食外,穗成熟時,采子搗為米,磨面作餅蒸食皆可。”短短的兩句話,讀起來親切、樸實、貼心,也一下勾引起了我對灰灰菜的無限念想。
在我的家鄉,人們一直將灰灰菜叫成“灰灰草”。小時候,我最先認識的一種草,便是灰灰草。倒不是它長得多么好看,多么讓人過目不忘,也不是它的名字叫起來多么順溜,只是因為它能當菜吃。在當時那個蔬菜貧乏的年代,如果每天都有幸能吃上一頓菜,并且口感還不錯,那確實是一件讓人做夢都能發笑的高興事。
若非要我說出灰灰菜的不足,那我只能從雞蛋里挑骨頭,從它的長相上發揮了。灰灰菜的確長得忒不起眼,忒不好看。首先,它的顏色黃不黃綠不綠的,給人一種說不出的衰敗感;其次,它的身姿也不那么風姿綽約、楚楚動人,有些粗枝大葉、粗糙焦暗。特別是在它的成熟期,這種感覺愈顯強烈,在片片葉子上,有無數日光銹蝕的白色斑塊,像殘破的蛛網,讓人不忍目睹。
如果說,在野菜之中,薺菜為不食周粟、避世全節的隱士逸民;苦菜為不墮青云之志、抱殘守缺的仁人寒士;那么,灰灰菜則當是隨遇而安、自生自息、生命力勃郁的底層貧民了。你看,不管在田間地頭,還是在荒山野嶺,都能看到它隨意生長的身姿。
放眼望去,那么多的灰灰菜,一片片,一蓬蓬,努力地張開它那并不受青睞的粗糙葉片,遮蓋著污穢的溝沿和寂寥的路邊。它們一根根迎著風,挺著身,一幅“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架勢,真是讓人忽生幾分敬畏之心。
小時候,我總覺得,母親身上有一種驚人的本領,那就是,不管長在地里的什么野菜,只要被母親挖回家,它們都會立刻變成好吃又美味的涼拌菜。當然,灰灰菜也不例外,而且備受歡迎。我們從不在吃飯的時候做其他事,因為我們擔心,一轉身的功夫,灰灰菜就被其他人吃個精光。
聽村里的老人講,灰灰菜不光能吃,還有其他用處。比如,很早以前是沒有洗衣粉的,由于灰灰菜吸堿,所以人們便把灰灰菜曬干,燒成灰,并儲存起來,稱為“儲冬灰”。冬灰不僅能用于洗衣除垢,同時還能食用,當面堿用。現今,新疆拉面中的蓬草灰就是同類的東西,而考古界、古玩界清理舊瓷器、青銅器時至今亦使用“冬灰”。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總以為,吃灰灰菜只有在貧困年代的困難家庭才能見到。直至長大,讀了一些書后才發現,富貴人家竟然也吃灰灰菜。《紅樓夢》第四十二回里,劉姥姥要回家去了,平兒吩咐她,“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干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蘆條兒各樣干菜帶些來,我們這里上上下下都愛吃。”看,富貴如賈府人,不也吃這個嗎?由此可見,灰灰菜當時的身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樣低,甚至還有些高貴呢。
灰灰菜是生長在春天里的植物,那些在春風里驚醒的灰灰菜,撲棱棱抖落一身薄薄的輕霧,接著,伸展一下那三五片沉默寡言的葉子,探頭探腦地打量著這個春天。
在春風的吹拂下,謙卑的灰灰菜,亦有了美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