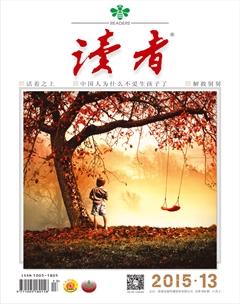解救舅舅
葉三

我舅舅原本是個老實人。
我的老家離北京不遠,但估計你們沒聽說過。那個地方其實不算窮,但很小,很土,很無聊。我爸,我媽,我爸的爸和我媽的媽,全是本地人。
我媽今年55歲。她只有一個弟弟,比她小6歲。小時候我對這個舅舅的印象不深,每年只有過春節的時候,才會見到他。我記得他長得濃眉大眼,算得上英俊。回想起來,別的親戚聊天或者搶著干活時,他總是自己坐在一邊,一聲不吭。我幾乎沒跟他說過話。
上大學那幾年我春節回家,沒見到舅舅。聽我媽說,他那幾年在國外打黑工——先去越南,然后去非洲。他是干裝修的,小學畢業,沒什么文化,只有力氣。在國外打黑工每年能掙幾萬塊,但他又很倒霉,每次不是被騙,就是受傷,折騰幾年下來沒發財,也干不動了,就只好在老家混著。大學畢業那年,我回老家見到了他,覺得他曬得很黑,也老了。我對他的印象,就是個老實本分的人。
我舅舅只有一個兒子,1989年出生的。在北京的公司開起來之后,我把這個表弟帶了出來。他說他崇拜我。他就在公司里干活,我忙得也很少見他。上個月,表弟給我打電話說:“我爸去搞傳銷了。”
我沒當回事,這種蠢事不是誰家都有嗎?去年春節后,舅舅說他去外地接工程,先去了北海,又到了武漢,他跟家里說不想再打工了,要自己做工程,家里人覺得這是好事兒,于是舅媽把這些年攢的10萬塊錢家底匯給了他,我媽也給他打了5萬塊錢。
去年年底,舅舅把他堂弟叫到武漢,拉他加入一個所謂的資本運作工程。他堂弟到了一看,就是傳銷。堂弟拉他回家,死勸活勸,他不回,還對他堂弟說:“你們自己沒志氣,就不要攔著我掙錢!我老婆不同意,她可以改嫁,兒子也大了,我管不著他,他也別管我。”一個老實人說出這么狠的話……那十幾萬已經被他全扔進去了。這點錢是他們家一輩子的積蓄。我媽急,我表弟也急,老家親戚一個接一個地給我打電話。
警察管不過來這么多。現在的傳銷組織也進化了,不限制人身自由,全靠洗腦,告也沒法告。表弟跟我說完,我上網查資料,我舅舅參與的這個傳銷組織以前在北海叫“1040陽光工程”,號稱是政府秘密支持的財政項目,忽悠人加入,入會后先交一筆6萬多的會費,然后發展下線,層層升級,最后發展了36個下線后“出局”,賺1040萬——他們有一套嚴密而復雜的算法。后來北海的組織被取締了,它就換到其他地方,改名為“資本運作工程”。舅舅堅信他靠這個工程,幾年后能賺到一千多萬。
按我和表弟計劃好的,表弟假裝生了肺病。畢竟是自己的兒子,舅舅馬上買了機票飛到了北京。在機場見到他時,我有點驚訝。舅舅穿黑色羽絨服、黑西褲、黑皮鞋,背著一個雙肩包,干凈利索,精神很不錯,看起來倒有些生意人的模樣,跟我記憶里那個木訥的工人完全不一樣。接他上了我的車,我告訴他,現在去找我的一個醫生朋友談談表弟的病,就往“反傳銷別墅”開。路遠,開了一個多小時,一路上舅舅很健談,跟我聊國家經濟政策,聊創業、掙錢、人脈,聊得頭頭是道……我開著車,心想:旁邊這個人是我舅舅嗎?
“反傳銷別墅”的三層有好幾個房間,里面設了茶盤和沙發,很舒服。舅舅、我和表弟,還有反傳銷組織的一位志愿者老師就在其中一個房間里喝茶聊天。志愿者老師很有經驗,先假裝談表弟的病,慢慢地把話題往資本運作上引。
聽說老師也在那個工程里干過,舅舅立刻來精神了。“你干到第幾層啊?”他兩眼放光地問。他馬上忘掉了表弟的病,開始滿懷期待地與眼前這個人說工程模式,說幾年后的回報,無數專業術語從他的嘴里冒出來。我插不上話,就聽著。老師拿了紙筆,按照他們的項目形式給舅舅算錢。“你不是交了69800元嗎,”老師說,“我們來看看這些錢到哪里去了。”我舅舅小學文化程度,這些,我估計他看不懂。算了一個多小時,老師說:“實話跟你說,這是假的,我以前做到過‘上總,就出局了,沒有出局證,一分錢也沒拿到。”
舅舅愣住了。然后,他轉向我大吼:“你們是來看病的嗎?”他指著表弟的鼻子破口大罵,我們老家的臟話滾滾而來。我從來沒想到這個老實人能變得這么兇狠——我們還沒反應過來時,舅舅一邊罵,一邊奪門而出,直沖向一樓的大門。
我和表弟追上去拉他,他回身就是一頓拳打腳踢。表弟撲上去抱著他爸,這時老師和反傳銷協會會長一同出現在大門口,還有另一個反傳銷老師也來了,女的。女老師比舅舅還兇,劈頭罵他野蠻,威脅要扭送他去附近的派出所,其他人好言相勸,連哄帶嚇,只是不放他走。其實真讓他走,他又能到哪兒去?一幫人在別墅門口鬧了一個小時,好說歹說,總算又把他拉回三樓。
那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大腿上挨了一腳,挺疼。我覺得舅舅已經瘋了。
回到房間,舅舅像變了一個人。茶不喝了,煙一根接一根地抽,低著頭,無論別人說什么,就是不接話。老師掰開揉碎地給他講,所謂的國家秘密政策、媒體宣傳、回報模式,統統是騙人的。老師講他的親身經歷,如何把自己的親朋好友害得傾家蕩產,如何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場。老師聲淚俱下,但就像水潑在水泥地上,舅舅一點反應也沒有。就這樣,說了四五個小時。
那時候是晚上10點左右,誰也沒想起吃晚飯。那個充滿煙霧的房間幾乎讓我窒息。我實在忍不住,站起來走出了那個別墅。在小區門口的小賣部,我買了兩條最貴的煙打算送給志愿者老師。走到別墅門口,我媽打來電話問情況。匯報完,我拆了一盒煙點上一支——兒子出生后我有兩年沒抽煙了。
抽完一根煙剛要上樓,別墅門口來了輛車,下來一家人。我上前問問,了解到這是從內蒙古某地剛解救出來的,情況跟我舅舅差不多。我跟他們一起上樓,回到那個烏煙瘴氣的房間,老師一看,站起來說:“正好,你倆是一個工程的,那你們聊聊,哪個是真的?”
老師說完吃飯去了。我、舅舅、表弟和那一家人,默默無言地坐著。那家人中有男有女,時不時傳過來一陣抽泣。就這樣,耗著。屋里沒有鐘,我也不想看表。我跟舅舅一起抽著煙,慢慢地,我對時間失去了感覺,我只覺得那個房間里的荒謬已經超乎了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