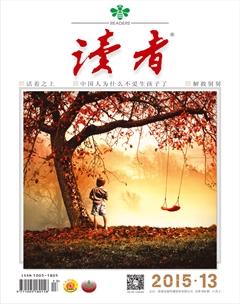一只鳥
沈柯

窗外的樹上有一只鳥。
我停下手上的工作,將目光凝聚在那只鳥身上。我猜那是一只烏鴉,它全身烏黑而有光澤,我仿佛還可以看到它那雙明亮黝黑的眸子。是烏鴉嗎?我只知道烏鴉才會長得這么黑卻不顯得丑陋。管他呢,它只是一只鳥。
我的目光,在這只鳥身上停留了許久。看得越久我越覺得它親切。我熟悉它的身形,它的毛色,它的明亮黝黑的眸子。我是不是在哪里遇見過這只鳥?我記得,幾年前,樓下確實經常飛來一些鳥,我還給它們拍過照片。它是其中的一只嗎?遠方的天空飛來一群麻雀,零零散散地落在了不遠處的電線桿上。我能感覺到它們在嘰嘰喳喳地開著沒有主題的會議。幾乎每一天,我都能夠看到一群麻雀從天空中飛過,或者悠閑地停落在人類活動的地界上。我從不特意去觀察那群麻雀,因為在我生命中飛過的那些麻雀仿佛永遠都是同一群麻雀,灰色、褐色、黑色、雜毛,飛著、叫著、生長著,永遠都是這樣,不曾改變過。我看不出我5歲那年看到的一群從電線桿上揮動翅膀飛向遠方的麻雀,和我現在看到的這群停留在電線桿上的麻雀有什么不一樣。但事實上,多少萬年以來,多少代麻雀像人類一樣死亡,繁衍,又死亡,一代接一代。想來若麻雀也有思想,它看我們,必定和我們看它們無異。
想起小時候的某個傍晚,我和父親走在家鄉昏暗的街道上,頭頂飛過一群麻雀,父親吟起一首打油詩:
人站在地上
抬頭望著天上的鳥
問道
鳥啊鳥
你在天上瞎飛瞎飛
做什么呢
鳥飛在天上
低頭瞧著地上的人
問道
人啊人
你在地上瞎跑瞎跑
做什么呢
上帝看了
輕蔑地嘀咕
鳥啊,人啊
你們在那兒瞎想瞎想
是何苦呢
我無法知道父親吟起這首打油詩時的心境,當時只覺得這么一首打油詩從一向嚴肅的父親嘴中以方言說出來,別有一番趣味。現在突然想起十幾年前的這首打油詩,竟然覺得其中蘊含了一個非常嚴肅而又說不清楚的問題。我們和麻雀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卻又生活在多么不同的兩個世界中。我們不解麻雀幾萬年來在天空中飛來飛去永不停歇的宿命,麻雀想必也不會明白人類在地上四處奔波交付歲月的命運吧。難道正因為如此,我才會覺得多少年來仿佛是同一群麻雀在陪伴著我?我分不清它們大同小異的面孔,是因為它們同樣無法區分我和路人甲的不同。我是路人乙,或者,我也是路人甲。鳥兒疑惑那個在地上瞎走瞎走的我,一如我看天空中瞎飛瞎飛的一群麻雀。我們都無法擺脫時間,跳出命運,我看麻雀如同麻雀看我。
我又將目光轉移到了那只烏鴉——就當它是只烏鴉吧——身上。它還在原來的那根枝丫上,保持著原來的姿勢,像尊雕像。我在我短暫的生命中遇到了它,它在它更短暫的生命中闖進了我的世界,但它渾然不覺。多年以后,我是否還能記得,在一個冬日的中午,我悄無聲息地邂逅了一只烏鴉?如果我能夠跳出我的軀體,以第三者的角度看到我和烏鴉的邂逅——這樣的場景,是否會很有意思呢?我想不出詞匯和語言去形容那種感覺,就像我可以像鳥一樣在空中,然后看到在陌生的人流中穿行的自己,就和一只陌生的烏鴉沒有區別。那種感覺肯定是奇妙的。
人的一生要遇到多少陌生的人和物?我時常感嘆命運真是一個奇妙玄幻的東西。命運讓我遇到了這個陌生人而不是那個陌生人,而我又恰好記住了某張陌生的面孔。這能算緣分嗎?也許在某個時候,我腦海中還會一閃而過曾經在某個街頭擦身而過的美麗女子,閃過一個曾經賣給我報紙的報刊亭主人,他們渾然不知他們就這樣闖入了我的世界,并在我記憶深處占據了一席之地。我也會成為別人記憶中隱秘的一部分,因為我必定也會莫名地闖入一個陌生生命的世界,一個我從未謀面的人的世界。命運是多么隱秘和奇幻!它讓無數生命無形中交織在一起,卻讓生命的所有者對此一無所知。一個遠在大洋彼岸的白人小孩,永遠不會知道,只因一個新聞畫面,就足夠讓他在我腦海深處存活一輩子了。任何偉大的作家都無法訴說和表達這種命運的隱秘性,因為我們都糾纏在這種混亂卻有條不紊的關系之中——隱秘而偉大。
那我到底是否曾經遇見過這只鳥呢?我覺得我肯定是見過它的,我覺得它是那么親切。我在多年以后竟然和同一只鳥相遇?生活竟會如此有趣和充滿巧合嗎?
我記起以前小區里的一只貓。
我覺得那只貓會笑,因為我看到它慵懶的貓臉就不自覺聯想到我以前的物理老師——太像了。我的那位物理老師和這只貓有什么聯系嗎?為何命運讓他們在我的記憶中產生了如此大的交集?我長這么大也不過記住了那么幾只貓,它是其中一只。它是幸運的,作為一只流浪貓,它在我的記憶中永久地存活下來。但我記住這只貓,難道不是因為它獨特的長相和那個物理老師驚人地相似嗎?但它不會認識我的那位物理老師,它只能認得我,倘若它能夠像我們這樣記憶和思考的話。誰讓我那么多次俯身去觸摸它臃腫的身體呢?我摸著流浪貓的腦袋,想的卻是我的那位物理老師。
枝丫猛烈地搖晃起來,那只烏鴉厭倦了原有的姿勢,起身飛走了,飛到我看不見的遠方。它就這樣離開了,自始至終不知道它竟長久地成為一個人眼中的風景。它沉醉于自己眼中的風景,殊不知自己成了我眼中的風景。那首《斷章》是怎么寫的?“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這是我最欽佩和喜愛的新詩。分歧、聯系、矛盾、悲哀,還有無盡的未知與永恒。我覺得詩中表達的就是命運——感嘆時間和空間給人的局限和無奈。仔細思忖,我們擁有的竟然是如此混亂不堪、令人費解的命運。它存在那么多不確定性,冥冥中卻又像是早就已經安排好的存在。
多年前父親打趣說:“上帝說,人啊、鳥啊,瞎想什么呢?”難道當時年近不惑的他已經感受到這種命運的關聯和矛盾了?幾句詼諧的打油詩,感慨的又何嘗不是閱世漸深后驚覺的無奈呢?可惜我當年太小,模仿著父親,操一口方言念叨著那幾句詩,只覺得有趣,而已。
那群麻雀飛走了,窗外變得空曠。何時我能夠再次遇見這群麻雀呢?或許,再也遇不到了。
或許,它們多少年來,就從未離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