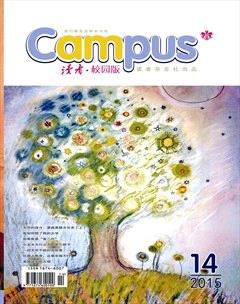一本書只能是一個人的生命
2015-05-14 13:11:44約瑟夫·布羅茨基
讀者·校園版 2015年14期
約瑟夫·布羅茨基
就整體而言,書籍的確比我們自己更能實現無窮。甚至連那些糟糕的書也能比它們的作者活得更長—這主要是因為,較之于它們的寫作者,它們占據著較小的物理空間。往往是,在作者本人早已變成了一抔塵土之后,它們還披著塵土立在書架上。然而,這種形式的未來,仍勝過幾個健在的親戚或幾個不能指望的朋友的懷念。常常促使一個人拿起筆來寫作的,正是這種對身后意義的渴望。
因此,當我們將這些長方形的東西,這些四開、八開、十六開的東西傳來傳去的時候,如果我們設想我們是在用雙手撫摸我們實在的或潛在的骨灰盒,我們是不會出大錯的。但說到底,用來寫作一本書—一部小說,一篇哲學論文,一本詩集,一部傳記,或是一本驚險讀物的東西,最終仍只能是一個人的生命:無論好壞,它永遠是有限的。有人說,理性的思考就是死亡的練習,這話是有些道理的,因為,沒有任何人能借助寫作而變得更年輕一些。
(雪茹摘自上海譯文出版社《悲傷與理智》一書,Getty Images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