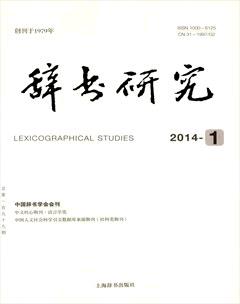《集韻校本》序
趙振鐸
《集韻》是宋代繼《廣韻》之后的又一部大型官修韻書。根據(jù)卷首《韻例》,它在收字、注音、釋義各個方面都盡量要求完備,這和陸法言《切韻》以來的韻書“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捃選精切,削除疏緩”的旨趣有所不同。正因為如此,有人認為它是一個“大雜燴”,用途不大。其實這部書收字三萬以上,大大超過了《廣韻》;收錄字的讀音也比《廣韻》多,有的字的讀音多達十個以上;字義的解釋也比較豐富,收錄的義項不少。這部書除了音韻學上的價值外,在文字學和訓詁學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只要運用得當,它對研究古音,探索詞義,考察字形結構都有很大的好處。除此以外,《集韻》注音將切語的類隔切改為音和切,每個韻內部的小韻按照聲母的發(fā)音部位和發(fā)音方法類聚在一起,開宋代韻書革命的先河,也是值得注意的。
根據(jù)文獻記載,《集韻》由丁度、李淑與宋祁、鄭戩、王洙、賈昌朝等同定。在編纂中丁度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一些公私書目只著錄丁度的名字。書成于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九月,慶歷三年(1043)八月十七日雕成。兩宋時期各地陸續(xù)有一些刻本。從元朝到明朝四百年間,這部書沒有重刻過,宋代的刻本也漸漸稀少,到了明末清初,見過這部書的人已經(jīng)不多,博學多聞如顧炎武,也因為沒有看到而認為它已經(jīng)亡佚。
康熙年間,朱彝尊從汲古閣毛扆處借得一部影宋抄本,交給曹寅鏤版印行,以廣流傳。康熙四十五年(1706)在揚州刻成,就是通常所說的曹楝亭本,簡稱“曹本”。《集韻》又有了刻本在世上傳播。嘉慶十九年(1814)顧廣圻重修本、光緒二年(1876)的姚覲元“姚刻三種”本都是用它作底本的。
《集韻》是一部官修書,官修書粗疏之處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錯訛的地方不少。姚覲元說“《集韻》觸處皆誤”,不是夸張之辭。曹寅刻書的時候,按照自己所定的統(tǒng)一格式重新編排抄寫,又出現(xiàn)一些新的錯訛。正如姚覲元所評論,這個本子“版刻精工,而校讎未善,識者之所弗取”。
早在宋朝《集韻》編纂的同時,司馬光等人修纂《類篇》,就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集韻》的錯訛,并有所糾正。到了清代,由于有了刻本,見到《集韻》的人多了起來,人們發(fā)現(xiàn)這個本子的一些錯訛,對它進行校理,段玉裁、王念孫等學者都有過整理這部書的打算,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都沒有成功。除了段玉裁有校本流傳外,他們對《集韻》的見解,散見于他們的著作中。
清代校理《集韻》的學者不少,如余蕭客、汪道謙、吳騫、許克勤、韓泰華、陳鳣、鈕樹玉、汪遠孫、嚴杰、陳慶鏞、許翰、董文煥、湯裕、周壽昌、馬釗、丁士涵、衛(wèi)天鵬、顧廣圻、呂賢基、凌曙、黃彭年等,他們大多數(shù)是用當時能夠看到的汲古閣影宋本來校《集韻》的,也有用傳世典籍校《集韻》的,這些校本藏在國內的一些圖書館中,已經(jīng)屬于善本書了。
方成珪的《集韻考正》是清道光年間寫成的,后來由孫詒讓編入《永嘉叢書》。這部書對《集韻》做了全面的整理,用功最勤。書中用的宋本是汲古閣影宋鈔本,不是原書,而是傳抄本,還僅是部分引用,此外還用了汪遠孫、嚴杰、陳慶鏞的校語。雖然他沒有更多地利用宋本,但是所得的結論,卻和宋本相合,這是難能可貴的。但是他引用的嚴杰校語有的是段玉裁的,可能嚴杰過錄段校沒有標明,所以出現(xiàn)這個誤會。不管怎么說,這是今天能夠利用的整理《集韻》的好本子。
陸心源也曾經(jīng)用汲古閣影宋鈔本校《集韻》,寫了一些校語,書名《校集韻》,在他的《潛園總集》中。
以上是兩部刊印出的研究《集韻》著作。
清朝同治年間,常熟龐鴻文、鴻書兄弟曾經(jīng)從同鄉(xiāng)翁同龢家中借得南宋明州刻本《集韻》,用它和曹本對校,作了校記。這是開始利用了南宋刻明州本《集韻》來校曹本。光緒年間朱一新邀約黃國瑾、濮子潼、錢振常和他的兒子錢洵等人也用明州本校曹本,世間還有明州本《集韻》才為人知曉。
姚覲元的《集韻校會編》,利用了明州本和汲古閣影宋鈔本,并錄有余蕭客、段玉裁、鈕樹玉、韓泰華、呂賢基等人的校語,應該是晚清整理《集韻》的重要著作,但是存書不到四卷,而且僅是稿本。
清末錢洵對《集韻》也下過一番功夫。他除了參加用明州本《集韻》校曹本外,還做了其他一些工作。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有他校《集韻》的三種本子。一種是前面提到的朱一新等五人的校本,另一種是他過錄的余蕭客、韓泰華校語和自己校明州本的校記,再有就是將各種字書材料過錄在《集韻》上的一個本子,其中五家校本更接近原校本,最為寶貴。
以前要看到宋本《集韻》,那是一件難事。顧廣圻就因為明知有一部宋本在揚州某氏家,就是無法看到而發(fā)出感嘆。今天我們的條件比前人好得多,所知的三個宋本都已經(jīng)影印出版:前清內府藏南宋潭州本《集韻》已經(jīng)編入《古逸叢書》三編,于上世紀末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翁同龢家所藏南宋明州本《集韻》已經(jīng)編入《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叢書》,一九九三年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最難見到藏于日本宮內廳的南宋淳熙金州刻本《集韻》,也于二〇〇一年編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出版,各大圖書館庋藏的清人批校本也可以借閱。這在前代是不可想象的。
筆者有心研究這部書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當時我還是剛上講臺的青年教師,上級號召我們向科學進軍,要大家擬訂科研項目。我心想祖父的《廣韻疏證》已經(jīng)寫成,我就照他研究的路子,把《集韻》作為研究對象,訂了一個整理《集韻》的科研項目。那時教學任務比較重,除了應付日常的教學,所剩時間非常少。而那個時代,你在教學任務之外去搞科研,還會受到有些人的指責,說你在“搞私貨”。但是我還是堅持下來了。一九六四年起,先是下鄉(xiāng)搞“四清”,回學校后,又參加了學校的“四清運動”,接著就是那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幾年的光陰就這樣白白浪費掉了。
整理《集韻》舊事重提是在一九七五年參加《漢語大字典》編纂工作時,工作中接觸到許多有關《集韻》的資料,就留心抄錄,幾年下來收集到的資料已經(jīng)不少。于是利用《漢語大字典》的稿本制作了一套《集韻》的工作底本,將《集韻》分字剪貼在上面。把收集到的資料抄錄在相關字頭下。又把方成珪的《考正》和陸心源的《校集韻》也錄下來。
一九九〇年,《漢語大字典》編纂工作告一段落,我閑了下來,就和發(fā)妻鄢先覺外出訪書,在北京、上海、杭州、寧波、南京等地的圖書館,由于朋友的幫助,能夠看到不少以前沒有看到的資料。第二年就開始進行整理工作。采用前人編寫長編的辦法,將資料錄入工作本。這里既有校勘的文字,也有詞語的疏通證明。將近二十年,全部工作基本完成。然后把文字校勘材料匯總到一起,編成這個校本,希望能夠為使用《集韻》的讀者提供一個可以利用的本子。
校本以嘉慶十九年顧廣圻重修本為底本,因為這個本子在曹本的基礎上對一些錯訛有所改正,上世紀末中國書店又曾經(jīng)影印過,流傳較廣,容易得到。將文字的衍訛缺倒注在有關字的書眉,并按韻標號,校記附在全書之末。
整理《集韻》是一項非常繁重的工作,論自己的學識和功力,還不敢說就做得很好,對清人的校語還有一些無緣看到,但是既然已經(jīng)寫成,還是想將它刊布于世,希望得到讀者的批評指正。
(四川大學中文系 成都 510064)
(責任編輯 郎晶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