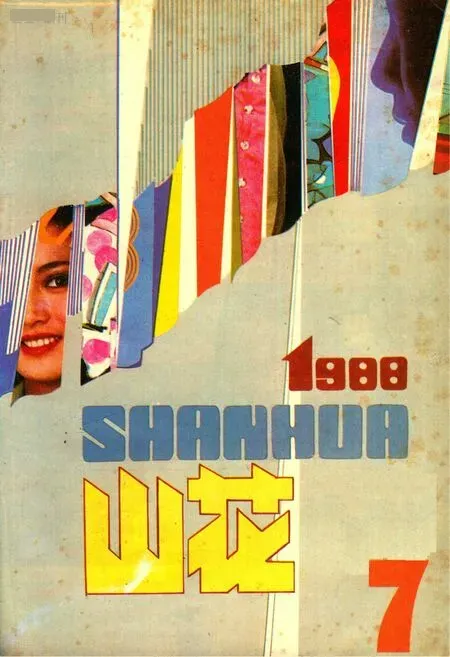清唱
姬中憲



馬哲讀中學了,父母去外地做生意,把他遺棄在一座陰涼的老宅子里。那宅子在底樓,由于樓外地面不斷墊高,這宅子越來越像地下室。馬哲每晚蟄居在這里,感覺那張大而無當的床正一寸一寸陷進地下。他半夜起來上廁所,馬桶上方高懸著一個小天窗,正對著外面的樓梯間,三樓啞巴嗓子老劉家那兩位花枝招展的妙齡女兒和她們的流氓男友們此時正在樓梯上打情罵俏,那興奮而壓抑的小嗓門,有時是大女兒的,有時是二女兒的,有時分不出是誰的。女孩的脂粉氣和流氓男友的酒氣透過天窗溢進來,把馬哲牢牢困在馬桶上,為他的性幻想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
又一場漫長卻跑題的如廁,馬哲常常把腿都坐麻了。
啞巴嗓子老劉的兩個女兒――姑且稱為大劉和二劉吧――都是廠里的文藝骨干,元旦職工聯歡會上和廠長一起唱過歌的。老劉一生和一口濃痰斗爭,嗓子始終不清不楚,據說他剛生下來的第一聲就哭得不利索,多年以后,他竟生出這樣鶯歌燕舞的女兒,還一下生了兩個,這一度讓啞巴嗓子老劉相當自豪。但是有一天晚上,老劉發了火,先是向樓梯間咳一口濃痰,接下來便趿著一雙拖鞋,揮舞著一根拖把,把一個臭流氓從樓梯間里追出去,追過家屬區的大門,追過廠辦后面的籃球場,追過市武裝部門前“歡度春節”的橫幅,追了大半夜。全市的流氓都嚇得不敢出門。事后,有個把月的時間,一直到元宵節之后,這一帶的治安和風氣都為之一振。
整個春節期間,大劉和二劉都被鎖在家里。可是,年輕女歌手的心可不是一把鎖就能鎖得住的,很快,北面小臥室的窗戶里就放出她們的女聲二重唱,再后來,歌聲不見了,大劉和二劉已經逃出來,前赴后繼跑去了南方的一個大城市。半年后老劉啞著嗓子發布消息,說她們被“總政”歌舞團招去了,和董文華一起唱歌去了,算是暫時堵住了鄰居們的嘴。“總政”真是一份有前途的職業,當年就見效,下一個春節前,老劉已經收到兩個女兒寄來的錢,多得數不過來,多得不像話。錢不斷寄過來,卻遲遲不見女兒們成名,收音機上聽不到她們的歌聲,春晚上見不到她們的身影,連董文華本人都不見了,老劉數錢的手,開始抖了。有機會去南方的人們回到家屬院,為大家帶來了改革開放的新鮮熱辣消息,鄰居們的嘴也重新活躍起來,言語間時常提及大劉二劉,不小心傳到啞巴嗓子老劉耳朵里。老劉黑著臉,重重撂下一口痰,腳不沾地地離開。大家期待老劉再宣布條消息,隨便什么消息都行,但這一次,老劉什么也沒宣布。有七八年的時間,他一直緊閉著嘴,從不在人前停留。只是每晚后半夜,三樓北面小臥室里的咳嗽聲更動情了。
錢還是不斷寄過來,七八年后老劉攢夠了錢,在郊區買了新房子,一舉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此刻,在那間地牢一樣的廁所里,大劉或是二劉的脂粉氣還混在馬桶的尿騷味中,馬哲躲在黑暗中,吸毒一般貪婪地吸食那味道。就在前一天,馬哲在鍋爐房前打熱水時,一個女人從背后捉住了他,他惶恐地回頭,大劉或是二劉高聳著胸脯,長輩一樣指點他。
女人說:早晨六點鐘的歌,是你唱的嗎?
馬哲說:嗯?嗯。
女人說:唱的還不錯。
馬哲說:哦,哦哦。
女人說:高音部分不大穩,還有顫音,要這樣唱,看,像我這樣,噢——
水房前打水的人都回頭看他們,馬哲羞愧難當,只剩下點頭。大劉或二劉滿足了,像個真正的大師一樣點頭笑笑,竟然還拍拍馬哲的頭表示贊許,事實上,她們得踮起腳尖才夠得到他的頭。這時,女人好像發現了什么,拿手擺弄馬哲的衣領,說:哎喲,這件襯衣很漂亮嘛,你媽媽給你買的?那手不老實,借著這話題的掩護,已經繞進馬哲光光的后脖梗。馬哲覺得女人的手像一枚圓潤的冰塊融化進去,驚得他后背起了一層雞皮疙瘩,仿佛被當眾剝光了衣服。大劉或二劉的手卻突然停住,觸電一般縮回去,用鄙夷的眼神盯著他。
女人說:你——很久沒洗澡了吧?
哦,女人啊,女人,此刻你仍然是干凈的,盡管已沾了臭流氓的酒氣,但你仍是干凈的,純白的。這是你最后一個干凈的時刻,你向我伸出了手,而我卻臟得像個沒來得及卸妝的小丑。
一直到成年以后,馬哲還會夢到冰塊。根據夢境不容置疑和不證自明的原則,馬哲確定那是冰塊,卻有手的形狀,那深刻的觸感,介于冰涼和滾燙之間,每一次都讓他自慚形穢,讓他措手不及,又讓他迫不急待地進入高潮。如同一支沒有前奏沒有過門的歌。
噢——噢——
女人在他耳邊叫,用氣聲唱法。那一刻,她的聲音仍是干凈的。
她還留給馬哲一個好名字,她隨口就把它說出來:早晨六點鐘的歌。
老宅子里住進來一對陌生男女。男人手臉發白,一身的文弱,據說卻是個逃犯,身上背了兩條人命,打外地逃亡到這里。馬哲的爸媽在外做生意,錢沒有賺到,亂七八糟的朋友倒認識了一堆,有一天深夜,爸爸把這對男女護送到這里,說是要暫住一段,還可以幫助照顧一下馬哲。得了吧,馬哲想,他自身還難保呢。不過又據說,男人并沒有殺人,是誤會,是錯判,是冤案,一時又解釋不清,只好拉家帶口逃亡,避過風頭再說。算了吧,別解釋了,馬哲一眼看穿了男人文弱外表下的殺伐之氣,當時就代表司法部門判了他的死刑:他就是個殺手,而且是職業的。
再看那女人,職業殺手的老婆,倒生得一臉慈悲,又瘦,像觀音菩薩減肥后顯形了。她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確保馬哲看到的每一眼她都是清醒的,絕不以昏睡示人。她在廚房做早飯,煮玉米面粥煮西紅柿雞蛋面,總有一份是給馬哲的。她動作小心,從不發出任何聲音――自己不出聲,也不讓手里的鍋碗瓢盆互相碰出聲――倒有十足的逃犯家屬的做派,好像稍有動靜警察就會破門而入一樣。女人一站到男人身旁,立刻柔順了,像男人的一個附屬,隨男人的聲調起伏。男人則眉頭緊鎖,眼縮著,像有無限心事。
總之,一男一女住進馬哲家里,擺開家當,拉開架式,好像一部電視劇就要開拍了。
不對,還有一個人,最關鍵的角色——女人大著肚子。
馬哲很快補齊了這部電視劇的另一條線索:兩人沒有領證,孩子是不允許被生出來的,生出來也上不了戶口,是黑孩子。
那時候《超生游擊隊》這個小品已經紅遍大江南北,一個男人帶著一個大肚子女人四處躲藏,眼前這對男女正是這樣一組原形。馬哲想起他們剛到的那個深夜,身前身后背的各種蛇皮袋,正是游擊隊員的裝備。
就這樣,一個男職業殺手,一個女游擊隊員,加一個黑孩子,一家子不法分子和馬哲住到同一屋檐下。每天早晨六點鐘,馬哲為他們唱歌。
馬哲不是有意唱給他們聽,他其實每天早晨都喜歡唱歌,只是過去沒有聽眾。過去他獨自住在那個沉靜的老宅子里,總是努力弄出各種聲響,一個人營造出一家人的氣氛。每天早晨六點他都要蹲一個漫長的廁所,實質性的內容早結束了,他還不肯起來,總覺得意猶未盡,像某種生理障礙。正是在這段百無聊賴的時間里,他開始唱歌,像國家一級演員那樣,每天早晨準時吊嗓子。廁所小,四壁又光,門一關,就是個大音箱。馬哲處在這音箱的聲源,震中,黃金分割點,一開口就有混響。混響充實了馬哲年輕稚嫩的嗓音,使他的歌聲變得雄渾,回蕩,還環繞,是真正的家庭影院效果。他每天早晨把廁所門關得嚴嚴的,放聲唱起來,那歌聲有時暢快,有時憋屈,有時帶著釋放后的快感,有時又有爆發前的醞釀,聲線非常多樣,情緒也異常飽滿。更妙的是,班上的壞小子,濤子,再也別想偷聽然后取笑他唱歌了。
事實上,大家都聽到了。老房子的隔音本來就差,早晨六點又是全世界最安靜的時候,城南發電廠敲鐘的聲音都能傳進每家人的耳朵,何況廁所上方還有一扇小天窗。于是,早起的人有幸耳聞了馬哲最旁若無人的歌聲,濤子的爸爸四哥聽到了,大劉二劉聽到了,一家子不法分子也聽到了。
有一天下午,馬哲放學回家,黑孩子降生了,一身白,像那對男女憑空捏造的。老宅子門窗緊閉,一屋子血腥,像殺人現場。
女游擊隊員首度開口了,似乎之前的一切事情都不值得她開口,現在,她作為一名媽媽被激活了。她指著馬哲對黑孩子說:娃啊,你可是聽著他的歌生下的。
馬哲聽說過胎教這回事,據說最好的辦法是聽莫扎特,長大了準成才,實在沒有聽馬勒也行。黑孩子沒福氣,不但沒戶口,也沒機會聽莫扎特,甚至沒聽過馬勒,只聽過馬哲。馬哲頓覺責任重大,黑孩子能成才嗎?
家里一下有了生氣,一股野生的氣。原本沉默的三個人,現在被一個黑孩子鬧得不安生。女游擊隊員不準人開門窗,一股野味全憋在房間里。馬哲懷疑他們巴不得這老宅子全陷下去,成為真正的地下室,這樣就沒人來戳穿他們一家子黑暗的秘密。但是有一天,男殺手從外面回來,不知道從哪里弄來一把六弦琴,陰暗的房間里,和著黑孩子的哭聲,叮叮咚咚彈了起來。黑孩子不愧是他爸生的,哭著哭著哭出了節奏,于是,男殺手用已經不太熟練的琴聲,伴著黑孩子越來越熟練的哭聲,上演了一出地下童謠。很快,女游擊隊員也加入了,她不但開口,而且開罵了。有了女人的罵聲,這個老宅子,開始有點家的味道了。
馬哲倒成了局外人。
每天早晨六點鐘,他仍然蹲在馬桶上唱他的歌,把天窗也關上,回聲鼓動著他的耳膜。他想,他才上中學,什么時候才能輪到他逃亡?他自己的那部電視劇,何時才開演?
這部電視劇的結局是這樣的:一家不法分子離開了馬哲家,繼續東躲西藏的日子,幾年后,男殺手實踐了眾人的傳言,他殺了人。他殺了女游擊隊員。女人的嘴被刀劃開,尸體丟進一個魚塘里。真相永沉水底,案件卻一目了然,他幾乎連個像樣的公審都沒機會參加,直接被拉到了刑場。男殺手跪在地上,慘白的臉第一次有了血色,他對天狂喊:素琴啊!我終于還清了!我還清了!我——警察可沒空聽他表白,一槍斃了他。
這些都是馬哲聽別人講的。馬哲聽到這結局時,結局早就發生過了。仍然是一個標準的電視劇式的結局。
他總是不小心窺見一部電視劇的某個片斷,聽到別人談論它的結局,至于中間每晚準時上映的那些日復一日的情節,則被他略過了。
馬哲想,他判斷沒錯,男人果然是殺手,只不過不是職業的,是業余的。他一生只殺了一個人,然后就被殺了。“身上背了兩條人命”,這個說法并不過分,只不過在當時,一條還沒有出生,一條還沒有被殺。他和她,殺人的和被殺的,都曾聽過馬哲早晨六點鐘的歌聲,在他們短暫而卑微的一生中,那歌聲草率得連一首電視劇插曲都稱不上。
現在,馬哲穿過人群,走向自己的舞臺,預備平生最重要的這次演出。
黑孩子沒有戶口,也沒了爹娘。一個真正的孤兒,真正的局外人。
稍微有點意外的是,馬哲在很多很多年以后,迎來了這部電視劇的真正結局。他在另一個城市遇到了黑孩子。他早就不是黑孩子了,還像剛出生時一樣白。他連考了七年,考上了公務員,當月就學會了打官腔,一副出人頭地的樣子。馬哲想起曾給他做的胎教,覺得該欣慰一下,卻欣慰不起來。
馬哲覺得,那也是他的孩子。
廣廣的藍天,映在綠水
美麗的春天的孩子,寵愛你的是誰?
茫茫的眼珠,望穿秋水
流浪的大地的孩子,長大將會像誰?
馬哲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曾有過一段堪稱奇怪的經歷,日后經過家人的層層轉述和渲染,那經歷更帶了神奇的色彩。馬哲曾向米小奇講過一次,講得繪聲繪色,像在講別人的故事。但他越是講得生動,那故事就越像是假的。馬哲幾次停下來,說:是真的。小奇搖搖頭,說:如果你寫出來,它就像是真的,如果你說出來,它就是假的。
那一年,米小奇14歲,馬哲也14歲,她比他小5天。用她的話說:小一個星期,不算雙休。一個星期后,馬哲把那故事寫進了作文。他的語文老師一手扶著黑框眼鏡,一手捧著作文本,為班里同學朗讀了其中的幾段。但最后,語文老師的評語是:不真實。那三個字,用紅色墨水寫在正文的下面,看上去無比真實,后面還墜著一個大大的感嘆號,像一錘定音。
馬哲氣鼓鼓地把作文本拿給小奇看,她笑得合不攏嘴,她說:因為老師把它讀出來了,所以它就成了假的。
馬哲被小女孩奇怪的邏輯弄得很惱火,他說:是真的,真的是真的!
女孩想了一會兒,說:那好吧,如果真的是真的,那總有一天,你會再次成為啞巴。
一直到三歲,馬哲都是一個成功的啞巴,三年里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一歲的時候,爸媽已經有點著急,同齡的甚至更小的孩子都已經牙牙學語,唯獨小馬哲金口難開。他們逗他,教他,嚇唬他,只為他能叫出一聲媽媽或爸爸。他卻發不出任何有形的音節,只會哭,唱歌一樣的哭。兩歲的時候,馬哲作為一個啞巴的事實得到進一步鞏固,因為他已經掌握了另一種語言:啞語。他開始向別人打手勢,配上一些含混不清的口音,來表達他餓了,困了,或是高興了。他的啞語已經相當熟練,連他的小姐姐都能讀懂。鄰居們安慰馬哲的爸媽,說這是貴人話遲,爸媽心里卻是一天比一天急,帶小馬哲去見各種醫生,各種民間高人。高人們撐開馬哲的嘴巴,拿手電筒向里照,像在查電表,或者捏捏馬哲的喉嚨,拍拍馬哲的后背,耳朵貼在馬哲的胸口上聽,像在檢查一臺短路的收音機。最后,他們無一例外攤開雙手,從理論上再次肯定了馬哲作為一個啞巴的事實。爸媽的絕望轉為憤怒,互相怨恨起來,爸爸說:讓你懷孕的時候亂吃東西!好像啞巴是可以按照一定配方吃出來的一樣。媽媽說:讓你整天亂說,話都讓你說盡了!好像他們家的話是按人頭定量分配的似的。小馬哲樂呵呵看著他們倆,一言不發。
三歲那年,院里來了一個外地人賣燒餅,大家不喜歡外地人,外地人長得怪,口音怪,燒餅口味也怪,沒人買他的燒餅。外地人卻不急不惱,每天準時把燒餅燒好,一張張碼齊了擱竹筐里,身前身后各背起一個,走街串巷的唱起來:
燒餅來——燒餅來——
大家聽得心煩,二樓四哥剛喝完啤酒,正午睡,此時開了窗,先放出一個飽嗝,再猛吼一聲:吼什么吼!
外地人聽了還不惱,咧嘴朝四哥笑,笑出一口小白牙,說:燒餅來——燒餅來——
還是那個調子,卻唱出了討好和呼應,好像要和四哥對情歌,聽得四哥都笑出來,再留下一個飽嗝,回屋繼續睡了。
大家仍然不買外地人的燒餅,卻逐漸容忍了他的唱。每天中午,大家聽到外地人的唱腔,條件反射一樣收緊了胃,心想:要開飯了。
有一天中午,馬哲的爸媽正在廚房做飯,馬哲獨自從床上醒過來,很不耐煩地打完一個呵欠,朗聲唱道:燒餅來——!
爸媽愣了一下,對望一眼,迅速丟掉手里的盆子鏟子沖到臥室。馬哲的首場演出開始了。小姐姐在床前歡呼雀躍:噢――馬哲會說話了!馬哲會說話了!好像他們家那臺接觸不良的14寸黑白電視機終于調出了聲音。很多年后媽媽仍然記得馬哲那一嗓子,她常常套用京劇里的話來形容兒子的第一次出聲:字正腔圓。
外地人走了,永遠消失了,沒人記得他是什么時候走的,直到有一天有人突然說起:賣燒餅的怎么今天沒唱?大家才想起來,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唱聲了。
只有馬哲的爸媽堅持認為,正是在馬哲開腔的那一天,外地人走了。那個好心又神秘的異鄉人,打著燒餅的幌子,竟是來傳授歌聲。
三班的米小奇,以她那個年紀所不該有的理智態度,拒絕相信這個故事,即使它已經寫進了作文。她留給馬哲的那句話,成為一句無心的詛咒。
又過了14年,米小奇28歲,馬哲也28歲,她仍然比他小五天。米小奇嫁給了冶煉廠采購二科的科長,婚禮前一天早晨,她在做頭發的時候突然有了一個可怕的想法,頭發做得很慢,使她有時間對那想法進行周密計劃,她想如果她現在逃走的話,至少有五種可行的方案。這時濤子打來電話向她請假,他原本要來參加婚禮,但當天早晨四哥因為腦梗住進了醫院。掛了電話,那個想法突然變得可笑,五種方案也像是五個更深不可測的陷阱。她開始在腦子里一遍遍輸入一個名字,又一遍遍刪掉。她永遠不知道的是,幾乎就在同時,在遙遠的另一個城市,馬哲正在電腦的搜索欄中輸入“米小奇”三個字,這是他自從學會輸入法以來,第一次在電腦上打出這樣三個字,奇怪它竟然如此容易。問題是,叫米小奇的太多了,有16萬8千多條,甚至一種袋裝膨化食品也叫這個名字。他想,如果有足夠的時間,他愿意一條一條查看下去,總有一個是屬于他的。他并不知道,留給他的時間,只有不到一天了。
兩年后一個冬天的早晨,米小奇的兒子又發燒了,采購科長還在外地采購,她一個人在收費取藥處排隊,那時她仍然記得那個日子,心里默默提醒自己不要忘記,但五分鐘后她就忘記了,輸液室混亂的床位和護士粗暴的態度讓她憤怒,她奮不顧身地投入到她的生活中去。事后她安慰自己,即使沒有忘記,她又能做什么?想起,偶爾想起,已經是她能做的全部。同一天的早晨,馬哲還在被窩里,早早編輯好了一條短信,卻沒有發送的號碼。他想,他有五天的時間,不算雙休的話,還有一個星期的工作日,如果他爭分奪秒,這并非沒有可能。當天晚上,朋友們趕來為他慶祝,一輪一輪跟他干杯,第一輪過后他開始不停說話,酒店很吵,他不得不抬高聲調,話里多少有些得意;第二輪過后他開始唱歌,已經有點聲嘶力竭;第三輪過后,他的歌聲里帶上了哭腔,起哄的人此時也小心停下來,那歌聲有些不倫不類。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
第二天,三十歲后的第一個早晨,馬哲從宿醉中醒來,感覺到嗓子里的異物,仿佛無聲吞下一記悶雷。那顆大號的膠囊,潛在里面很多年,這時開始發揮藥力。一個開關已在他喉嚨間安裝調適成功,他幾乎聽到了那一聲“吧嗒”,隨后,開關關上了。他試著發出一個最簡單的音節,并且認為已經發出來了,只是耳朵暫時失聰。但他很快否定了自己:窗外不遠處的工地上,一個打樁機正鏗鏘有力地打出節奏,關于冬季防火的廣播正在小區里一遍遍播報,他其實正是被這些聲音吵醒的――那他自己的聲音呢?
他去了醫院,三歲以后,他的嘴巴被再次撐開,醫生裝扮得像個礦工,額頭上的探照燈深深射進馬哲的喉嚨,他幾乎能在胃或肺里感覺到那束強光。那光將他黑暗的內部照得通明,他像一座早已枯竭的礦井,被一眼看穿了,看透了。醫生診斷為急性咽炎,開了幾百塊錢的藥,又說藥只是輔助性的,關鍵要禁聲。
五天之內,不要講話,醫生說:其實,你想講也講不出來。
好吧,五天,再加上雙休的話,也不過一個星期。
他回到家里,開始了無聲的生活。默默地起床,默默地吃飯,默默地喜怒哀樂。他做得很自然,仿佛本該如此。他去了一趟單位,手里捏著一張假條,不假解釋地請了五天假。他把自己鎖在家里,公然不接電話,任何人的電話都被他按掉。他甚至有些洋洋自得,看吧,聲音并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我并不一定非得向你們說些什么。
大概從第二天晚上開始,那幾百塊錢的藥開始發揮作用,很快,副作用超過了正作用,他開始不停打嗝。他并沒有在意,認為可能是喝水吃藥時岔了氣,他有一整套方案來對付它。他含一大口水,屏住呼吸,待到忍無可忍時再將水吞下,剛吞下就打了一個嗝。他閉上眼睛,集中精力轉眼球,左三圈右三圈,睜開眼,還是打。他在椅子上坐定,收集口腔內的所有口水,連續吞咽三次,這并不容易,第三次的時候他幾乎是在忍氣吞聲,但是沒用,還是打。他用了各種方法,就差冷不丁打自己一個耳光了,那響亮的嗝,還是一個個不請自來。他被折騰得筋疲力盡,試圖以睡覺來息事寧人,那嗝卻不困,越晚越精神,一聲聲將他從睡夢中拖出來,接受活生生的拷打。第三天起,那嗝養大了,越來越有力,越來越頻繁,馬哲的整個身體都繃起來,迎接一次次的痙攣。打嗝像打槍,而且是后座力很強的那種槍,每一槍都把馬哲的身子頂起來。遠處看去,他好像剛經歷了驚動天地的一場大哭,現在只剩下一具默默抽泣的軀體。他甚至沒有辦法求助,他開不了口,又羞于見人。猶豫再三,他開始發短信,向所有能開得了口的人發短信,用冗長的形容詞和修飾語來描述他目前的狀態。他得到了一些安慰,一些應對打嗝的陳舊的小伎倆,和一些不合時宜的玩笑,還有人一遍遍打他電話,完全不顧及他現在不能說話的現狀,執意要向他面授機宜。他知道這里面至少有一多半人是真心的善意的,但他還是被激怒了,如同一個絕癥患者不合人情的過激反應,他編了更長的短信,用更冗長的修飾來咒罵他們,咒罵那些膽敢關心他的人。而在這期間,那揪心的嗝,一次也沒有放過他,分分秒秒地折磨他,把他的身體一次次頂起來,再放下,再頂起來,毫不通融。第三天的晚上,他關了手機,站在衛生間的鏡子前,開始抽自己耳光,一下一下,毫不留情地抽,有時候他剛抽完一個耳光,一個嗝就緊跟著頂上來,使他的臉在鏡子里顯得很狼狽。他一下一下地抽,抽得很客觀,像代表另一個人在抽。終于,當第一千四百六十七個嗝像體內一桿長矛將他戳穿時,他哭了出來。眼淚頃刻間淹沒了他的臉。
第四天的時候,他想到了死。
他不再試圖想任何辦法,他冷冷地看著他打,看他能把他打成什么樣。他和他,開始變成兩個人,現在,他是幸災樂禍的那一個。有時候,他會覺得自己軟弱,丟人現眼,一個大男人被一個嗝打死,再怎么說理由也不夠充分。但很快,另一個他站出來,用更雄辯的聲音告訴他,死,并不是那么羞于選擇的。他想到了老舍,那么幽默那么會開玩笑的一個人,卻不能容忍別人開他的玩笑,當別人合起伙來堅持要開他的玩笑并且這玩笑越開越大時,他果斷地跳了湖。
寧可死,也不讓自己的身體成為笑柄。
現在,他不正是這樣一個可笑的小丑嗎?如果不是,那誰會把自己的身子一次次頂起來,誰會發出那一聲聲丑陋的無意義的聲音?那么就死了吧,再也沒有比這更恰當的時機了:他以一個啞巴的身份出生,以一個啞巴的形象死去,誰也不能否認,這還算是一個圓滿的回合。
他并不知道,這一天,在世界的另一端,采購科長回家了,為他的妻子采購回了三十歲的生日禮物。他的妻子卻高興不起來。她忍到晚上,上床熄燈后,第一滴眼淚就奪眶而出。科長問她為什么哭,是不是太久沒給她買禮物了,高興成這樣?她也不知道,但她可以肯定和禮物沒關系。她想一個人默默地哭一會兒,但科長不允許,手伸過來,帶著煙酒氣和廉價牙膏味的鼻息湊過來,她又淹沒在現實生活的黑暗中。
膈肌痙攣又稱呃逆,是由于膈肌、膈神經、迷走神經或中樞神經等受到刺激后引起一側或雙側膈肌的陣發性痙攣,伴有吸氣期聲門突然關閉,發出短促響亮的特別聲音。如果持續痙攣超過48小時未停止者,稱頑固性膈肌痙攣,也叫頑固性呃逆……
唐米說:小齊是誰?
馬哲說:一個同事吧,姓齊,大家都叫他小齊。
唐米說:男的女的?
馬哲說:男的。
唐米說:怎么他的電話號碼是空的?
馬哲說:……那把他刪了吧。
第五天早晨,打嗝停止了,他小心坐起來,花十分鐘來確認這件事,不相信,再花十分鐘來確認。確實停止了,不負責任地停止了,像個負心的情人將他的身心折磨殆盡,卻一句話也沒留下,天不亮就走了,像沒來過一樣。馬哲安撫他的身體,那剛剛遭遇了一場毒打的身體,表面上竟看不出一點痕跡。只有他自己知道,此刻他的身體正像一座內爆的建筑物,他將完整地倒下,所有的傷都在里面。
這是他禁聲的第五天,他把這五天時間都花在和自己身體的搏斗上了,現在,他開了手機,那個號碼欄仍然是空的,看樣子要一直空下去,直到某一天被隨手刪掉。在禁聲的最后一天,他開始反復修改那條短信。如果你把它說出來,它就是假的,如果你把它寫出來,它就是真的。
如果我寫出來,但永遠不發給你,那它是真的嗎?
第五天的傍晚他做了一個決定。一百多塊錢的藥,現在還剩下一多半,他把它們打包丟掉。他想找一張白紙,翻遍整個房間卻找不到,這時候,一本病歷不知怎么到了他的手上,真是可笑,可還有比這更恰到好處的嗎?“禁聲5天”,醫生的結論還在上面,馬哲拿出筆,把那個決定寫在后面,像立遺囑一般煞有介事。
就這樣,他在最后一天的沉默中做出了這個決定:永遠沉默下去。
他去了單位,手里捏著一張辭職書,不加解釋地辭掉了工作。退工證明上寫著:2009年,因身體原因辭職。
2009年,墨西哥爆發甲型H1N1型流感,很快就在全球蔓延,央視新大樓發生火災,英國航空公司開始向乘客收取如廁費,來自湖南的20頭豬使廣州的70個人瘦肉精中毒,瑞典當局焚燒了3000只兔子當作取暖的燃料,新聞聯播主持人去世,劉德華在紅館連開17場演唱會,“大提琴陰囊癥”在一番爭論后被證明是一場笑話……2009年,世界仍然喧鬧,馬哲卻一聲不吭。
只要不說話,他立刻就退出舞臺,隱身成為聽眾。有一次在公交車上,他目睹了一場漫長的、沒有終點站的爭吵,全車人都加入進去,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個陣營,他卻一言不發,像身懷利器的高手,或手握終極答案的高人,默默審判著眼前的一切。還有一次他去補交逾期的電費,排隊時不小心頂翻了身后老太太手里的一包綠豆,那一窩綠眼的小精靈歡快地蹦跳著,頃刻間占領了整個收費大廳,害得整個大廳的人都彎腰撿豆子,馬哲默默承受了眾人的埋怨,內心里卻是一片歡騰。在一次電話中,他得知了父母的最近一次爭吵,與三十年來的每一次都雷同,父母卻沒能從他這里聽到哪怕一聲呼吸,他無聲的樣子讓父母覺得既陌生,又熟悉。而在他那一眾熱愛鬧騰的朋友們看來,他等于消失了,隱形了。他回憶他和她的每一次甜言蜜語,每一次爭吵,似乎每一次都說盡了一生的幸福或悲傷,從此再沒有開口的理由。他想起語文老師的紅色批語,不真實。
樓下新開了一家快餐店,中午十二點他掀簾子進來,拿手指點,吃這個,吃那個。他點頭或是搖頭,表示飯多了,或是少了。酒足飯飽后他會朝老板豎大拇指,或者拿兩個食指和兩個拇指在空中劃出一個四方,表示他需要餐巾紙。老板從第一天起就對他笑臉相迎,從沒有另眼相看,但是一年后,當馬哲走進快餐店急匆匆說出“老樣子,飯多一點”時,老板卻瞪大了眼,左右尋找聲源,最后看著馬哲說:原來你不是啞巴!
一年后,馬哲重新開口說話時,嗓子里多了一個聲音。那聲音有些渾濁,但并不陌生。此后,他說出的每一句話都像是和聲。
現在,馬哲穿過人群,走向自己的舞臺,平生最重要的這次演出即將開始。
唐米說:嗓子沒事吧,我看你不停咳。
這是他們認識的第728天。馬哲說:沒事。
唐米說:一定要唱嗎?
馬哲說:當然。
唐米說:唱什么?還不告訴我?
馬哲說:馬上就能聽到了。
臺下的人群已經有些騷亂,心急的人已經招呼身旁的人吃起來,叮叮當當的碰杯聲不時響起。多少次,馬哲也曾坐在他們中間安心吃喝,笑看他人。現在,輪到他自己上場了。
司儀湊到他身邊,把一支話筒塞到他手里,叮囑他說:話筒已經開好,上臺后不要按開關,也不要喂喂喂地試,直接唱!馬哲說:好的。司儀說:真的不需要伴奏?馬哲說:不需要。
大廳的燈滅了,眾人一片輕嘆,紛紛收起手中的刀叉和酒杯,把最后一句玩笑說完。一條紅毯鋪展在馬哲眼前,通向大廳另一頭的舞臺,黑暗中那紅色失去了色彩,像一條黑色的不歸路。馬哲走上去,多少顯得有些鬼鬼祟祟。他上了臺,臺下是黑壓壓的寂靜,司儀的叮囑還在耳邊,但他還是把話筒關了。緊接著,司儀夸張的聲調在黑暗中響起:下面有請新郎為大家演唱!掌聲響起來,他溜到舞臺一側,轉過頭,借著掌聲的掩蓋,把一口痰吐進垃圾桶。那痰凝重,完整,如同全副的內臟,一口吐出,他感到全身通透,體內再沒有什么。他空蕩蕩地回到臺上,一束追光將他圈在舞臺中央,臺下,新娘的婚紗隱沒在暗處,他覺得有眼淚要流出來。他把話筒舉到嘴前,深吸一口氣,手指悄悄按下開關。提示燈一閃,話筒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