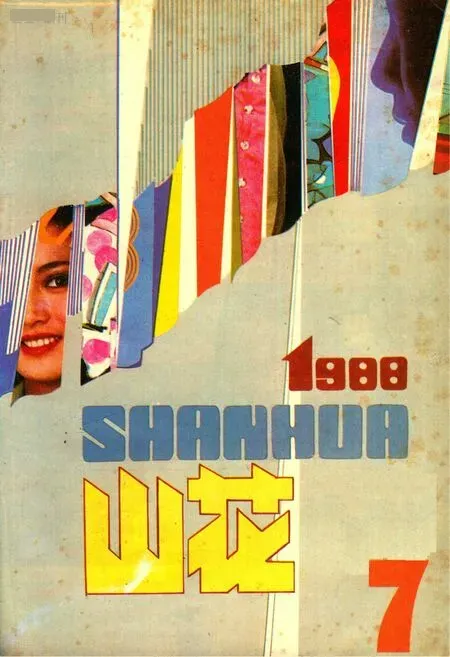一個人的中國故事
張頤雯


直至今天,胡雪梅依然算不上一個廣為人知的作家,但胡雪梅作為一位并無特殊寫作背景的作者,已經寫出了大量的有其自身意義和特質的作品,吸引了眾多讀者的目光。她不是這個年代作家中常見的學院派,也沒有刻意運用她出眾的故事能力去取悅讀者,但她用獨異的視角,飽滿的情節和多樣的題材,誠懇地表現著我們這個紛亂、多樣的時代,勇敢地面對自己經歷的生活。
一、現實中國的旁觀者
《北京文學》2011年發表的小說《花朵》是我第一次看到胡雪梅的作品,被作者的文字所吸引,得知小說的作者是一位職業記者,在小說里,故事也是由一個女記者的角度開始和終結,所以讀小說之余,這一文字以外的職業和文本中主人公職業的一致性不可避免地讓我對小說與作者的關系有了興趣,有意無意地開始關注小說的二元視角,即文本視覺和作者視角。
小說寫了一個記者、殺手、被害人和警察同時在場的兇殺案,各方人物糾纏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作為第一主人公的女記者發現了她工作的獵物,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男的舉著刀,女的在前面跑,作為一名盡職的記者,她記下了這個驚心動魄的瘋狂的時刻,同時是自己記者生涯最驚險卻也是輝煌的時刻。她記錄下了一名失職警察逃避案犯那個瞬間的影像,她盡到了責任。失職警察在人性的拷問下最后跳樓自盡,環環相扣的故事之中,“我”的道德正義一直成竹在胸,“記者”這個職業雖然曾經風光無限,它的道德光環在這些年也消失殆盡,但在小說中,一位有“理想”的記者在心理上從未失去過道德優勢,正是她的這種道德優勢讓她成功,并擊敗一個被她視為道德淪喪的警察最后的生存根基,直至警察自殺,記者和警察作為兩個具有道德光環的職業,在這里互為影射,在批判一個失職警察的最后,這位女記者再次見到警察的妻子,才意識到她自己的缺失。
胡雪梅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故事高手,在小說中,各方人物的人性本質在最為激烈的故事沖突里得到了充分的表達,強烈的情緒通過節制、從容的敘事傳遞出來,直至小說結尾那冷峻的一筆。最為吸引我的不是故事里環環相扣的兇殺案,也不是這位失職警察的進退兩難的生存困境,而是兇殺案的目擊者——小說的主人公女記者,她扮演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她的行為動機。她為了自己的職業正義和可能帶來的榮譽而放棄了什么?小說里作者對自我職業的批判和對社會的關照,這雙重矛盾構成了小說最奇妙和閃光的一面。
作者并非僅僅利用了記者觀察眾生的便利,對社會對他人進行批判,而是將自己這一身份放入自己的小說之中,在觀察他人和社會的同時,不斷反躬自問,對自己進行反省和剖析。她反思當事的每一方,更是在刻薄自己的職業,正因為是反省,所以更兇狠,小說中作者用這樣的口吻提到了她自己的職業:“記者嘛,巴不得天天都有人行兇殺人,飛機撞大樓,漲大水,發大火,還有就是公務員毆打小市民,農民集體上訪告村官,大街上群毆,跳樓自殺,丈夫出走,或者妹妹打哥淚花流也不錯。總之,不出事記者就得餓肚子。”
我以為,這個女記者的形象是當代小說中全新的,這個人物的職業似乎決定了她觀察者的身份,但是,她的光榮,她的矛盾,她的自我懷疑,她作為一個記者和作為一個人的行動和思想在今天都有新的意義。面對種種社會問題,輕易地下結論幾乎成了這個時代的通病,這種通病在媒體圈也許更嚴重,但是,當代的文學作品似乎甚少表現這一時代通病。
必須有強大的理解力,表達力和感受能力,作者才可以在各種人與人之間,人與事,精神與物質之間進行反思和語言的游戲。毛姆說過“聰明人的刻薄是世間的鹽。”在當今的許多作品中,或許因為不夠智慧,或許缺少力量,這種能力已被遺失,胡雪梅卻做到了這一點。與小說《花朵》相似的,胡雪梅的另一部小說《心靈診所》同樣以一位女記者為主人公,作為各種不幸故事和事故的旁觀者,她是智者,旁觀世事百態,同時作者對這樣一位旁觀者——也許就是作為作者的自己的身份進行了無情的剖析和尖刻的自嘲。這樣一位對她的采訪者來說全知全能的人物,在面對自身的問題時,仍然無力作出有效的行動。這自嘲和剖析解構了她在小說中觀看人間百態的居高臨下的姿態。于是,包括作者在內的所有人都被輕松扯平了,“上帝死了”,作者消失了,成了小說中的人物,成了與這個社會艱難相處又被這個世界所裹挾所包圍的故事中的人。
二、復雜中國的講述者
胡雪梅描寫記者這個職業時充滿自嘲,自嘲也是她面對現實的力量,但是除去以上那些帶有對自己身份自嘲意味的小說,拋開胡雪梅的記者身份,她更多的小說資源來自講述另一個場景,另一段歷史。在《一豆的春天》《公安局長當保安》《賠我的愛人》《去天堂的路上》《母親在遠行》這幾篇小說中,她的小說從鄉村中來,在小鎮中生根發芽。從舊時代直至最為切近的今天,她筆下的主人公成了小鎮青年,民辦教師,派出所退休所長,過氣妓女,失去兩個孩子的母親等等,她會直接表達對這些筆下人物的深刻的同情,表達她質樸的愛,她的反諷和自嘲竟消失了。
小說《賠我的愛人》里,派出所退休所長遇到妓女安小曲,在偶然的事件中,派出所長被認為破壞了妓女唯一的從良機會,從此所長被認為對改變妓女的未來前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妓女則幾乎變成了另一個人,她要盡力成為一個“正經人”而不可得。這不僅表現了作者的寫實能力,更表現出她對這樣一群人的理解和同情。在細節的層層推進中顯現了一個中國南方當代小城的真實畫卷,一群艱難生活的中國人的不屈不撓。他們都不是人生贏家,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灰色人生之中,正是他們最樸素的情感和最真實的生活讓他們相互理解和溫暖。
小說《公安局長當保安》也是寫一位退休公安局長的際遇。退休公安局長遇到了他退休后的競爭者—— 一位一心想當小區保安主任的老保安,于是產生了匪夷所思的保安主任之爭。這本是一個喜劇的開始,但在抓竊賊的過程中,老保安竟犧牲了,喜劇成了悲劇。這是當代社會小人物的悲喜劇。
《母親在遠行》同樣在寫行進中的中國,一位母親遭遇兩個兒子的意外死亡。一個在八十年代的嚴打過程中被匆忙判了死刑,另一個在自衛反擊戰中成了烈士。這是中國人在國家前進過程中的命運之一,胡雪梅也只是從母親的角度去表現它,她如何去面對這樣的命運,她的絕望,她的尋找,她解決自己如何生活下去的方式……
這些小說就是胡雪梅的中國現實,是她看到和發現的中國人。處在今天的現實之中,小說的作者想要對此時此地進行想像和虛構最為艱難,每個人都會受制于自己的時代,而時代又不可避免地給予我們力量。今天的小說如何處理復雜的當下經驗和焦慮?胡雪梅的方式是:回到了現實主義的傳統之中,回到最經典同時也最長久和有力的細節、語言、故事和情感之中,在鄉村、在縣城,在大城市的邊緣找到人們的命運,并勇敢地直面這些命運,直面這些在巨大變動中的具體生命,讓平凡人物在自己的痛苦和快樂中獲得意義。在這些中國的最深處,我們才可能看到真正的中國,一個更樸素,更精準,也更本質的中國。胡雪梅沒有用技巧將這樣具體生命的困境回避掉,在今天的小說創作中,特別是在年青一代作家中,這尤其寶貴。
三、過去中國的回望者
作家對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看法,這看法構建了他們的想象世界。本期《山花》發表的胡雪梅的《團頭魴》,就是作者構建的一個過去的世界。這篇小說不同于之前的作品,之前的小說都是和我們當下生活離得更近的作品,而這一篇,年代、背景都有了很大的距離。小說回到了過去。所謂回到過去,其實與我們相隔并不遙遠,卻被認為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個時代。這意味著回到我們成為現在的我們之前,那時的人們如何生活和思考,決定著我們的今天和未來。
小說的題目“團頭魴”,是武漢當地盛產的魚類,因為獨特,因為鮮美,更因為毛主席曾經品嘗過,于是成了當時人們追逐養殖的品種,甚至成了珍稀品種。圍繞著團頭魴,人們展開爭奪,對名譽和利益的爭奪,對生存的爭奪,因為這爭奪發生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與今天隔著幾十年的時間,所以讓人感覺尤其強烈、尤其分明。
小說《團頭魴》是一個近于傳奇的故事,也是作者對我們歷史的描述。文革年代,在這個非同一般甚至黑暗的年代之中,有關孩子,女人和魚的故事。孩子、女人和動物,是今天被大家所公認的弱者,那么,小說就是在講述弱者在一個強力年代還能夠做些什么的故事。團頭魴就是小說中的精靈,孩子和女人因為它而生存,也因為它受到傷害,最后,是團頭魴讓他們得到精神上的救贖。在回到過去的故事里,作者的筆調變得單純,細節變得清楚明快,沒有對世界和自我的嘲弄,也沒有無解的困惑,有的是清清楚楚的好人與壞人,是善惡報應,是黑白電影一般的一個時代——在我們的記憶里,它應該就是這個顏色。
在作者的筆下,這個年代的人們有著自己的生長方式,女人因其神性而得到救贖;孩子則脫胎換骨,獲得成長;而團頭魴則更像是一個精靈,在這個年代搭救深陷迷途的人們。荒謬的年代里,人們是怎么生活的,是怎么走出困境達到今天,小說給了我們一種答案。
如何進入歷史,如何進入文革的歷史記憶,胡雪梅有自己的方式。小說有種簡單的力量,其中的每一種情感都真實,濃烈,黑白分明,與她之前的小說——那些與現實很近,特別是與她職業很近的小說,形成了鮮明對比。這是作者心中兩個時代的對比,同時也是對自己的今天與昨天的對比,是對我們自己過去的青春年代的記憶和想象。《團頭魴》中人物的精神譜系,那些正義、果斷、善良的品質曾經并且正在維系著我們社會,這些常被今天遺忘的品質有別于今天對物質,對欲望的狂熱,更多的呈現是對自然、對家庭、對倫理的忠誠,它們的摧毀和重建的過程今天還在不斷地進行著。
在之前的那些小說中,她表達了今天的自己,在作者目力所及之處,再沒有如此純粹的鄉村和村里的人們了。人們的面孔,人們的形象變得模糊、含混,他們也不再是種田、打漁的人,他們走在街頭,成了城里的各色人等,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在出走和回歸之間,展現著它的復雜性,鄉村已經消失或者凋零,早已不是浪漫的精神家園,而城市也遠非《團頭魴》中那個遙遠的夢想之地。人們在名與利與正義感之間徘徊游走,對社會百態的有情或無情的反諷與揭示,都發生在今天,已經回不到過去。
但這篇小說里的鄉村是經典意義上的鄉村,人們種田、打漁,并以此為生,這呈現了另一個想象的世界,那里有英雄氣概,有落難英雄,有正義與邪惡之爭,讓人們相信正義終會戰勝邪惡,那里有對過去的想像,也有對今天的期待,這是作者自己的精神烏托邦。
八十年代之后,中國的小說已很少見到這樣的風格。今天的多數小說,是懷疑的、細膩的、小的。虛無主義的故事,對意義的刻意消解成了主流。而這篇小說中,有種特別的真誠和坦白,有鮮明的善和惡,英雄主義的故事在用新的方式,通過舊的時代回到我們身邊,這在今天特別的珍貴。
我不知道幾十年之前的人們是否如此單純,如此堅定,如此的在道德上站在了我們的高處。《山花》發表的這篇小說,與其說是在胡雪梅發表的一眾小說之后的裂變,不如說是它們的前傳,與其說是講了一個過去時代的故事,不如說是在講述我們的過去。在歷史的圖景之中,團頭魴的故事,看似在寫作我們的上一代人,上一代歷史,某種意義上,它更是我們自己個人歷史的縮影,因為它的簡潔、單純、有力,這要求我們自己必須在是非之間,而不是在利益之間進行明確的選擇,所以,它也像是我們的年輕時代,是對這一代人的過去的描摹。
一位評論家在談到這個時代的年輕作家時提到:“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受到負面的現代主義影響,作品充滿文藝腔,內容空洞,完全不被市場邏輯左右。”與此不同,胡雪梅的這一系列小說,來自她最刻骨的生存經驗,來自中國最普通的城市與鄉村。將這些小說放置在一起,在諸多的詞語、物件、人物之間,構成了胡雪梅的一個人的歷史,而這些語言、故事、細節和主題也構成了這一代人精神世界的一個獨特注釋。胡雪梅的力量就在于,她是講故事的高手,她用最為經典和傳統的講故事的方式,用通俗的,好看的語言,沖突性的人物關系,出人意料的結尾,表達了最貼切和最真實的生存經驗。她貼著生活,沉浸在生活之中,在這一代作家里顯示出值得珍惜的能力,但她的小說絕不僅僅停留于故事,她的故事之間和故事之外有冷靜、有諷刺,也有這一代人難得的和足夠的熱情,她在故事之中努力揭示時代的本質和意義,抵達當代歷史的精神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