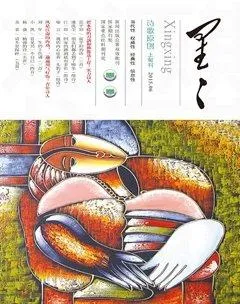孤 獨(外一首)
2015-04-29 00:00:00小西
星星·詩歌原創 2015年6期
有時它是一片葉子
脈絡的走向十分清晰
有時它是小心爬行的壁虎
眼睛里閃著狡黠的光
或者它是寒冬的杯子里,越來越堅硬的水
但它更像深夜里,一只飛蛾
用翅膀拍打著窗戶,而玻璃正輕輕
裂開細縫。又仿佛從裂縫里
擠進來的風聲。
當它不約而至時
我躺下來,在你躺過的地方。
拿過你的桃木梳,給沮喪的玩偶
梳理頭發。
又從你雜亂的書本里
找到卡佛的詩歌,讀到《悲傷》時
我用你的被子蒙住了頭
那里一片黑暗,什么都不是我的
除了洗發水的香氣和碩大的淚滴
我很久都沒有這么溫柔了
你從未像現在這樣乖。
在白色的房間里,被一種叫“腦血栓”的東西
拴在床上。你任兒女和醫生擺布。
就如你曾經任意擺弄的蔬菜和莊稼。
只是,你再也無法開出花朵,結出果實。
大腦里那些管道
沒有被饑餓,貧窮所堵塞
沒有被擔心和勞累所堵塞
但在這個初夏,薔薇開得最喧鬧的時候
它和你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
你的嘆息像一棵樹那么高,傷心的葉子日漸肥大。
我細心地喂你,用嬰兒的勺子。
輕聲地和你說話,如對待初戀的情人。
我小心擦去你眼角的淚水
講一些不著邊際的趣事。
母親,我很久沒這么近距離看著你,握住你粗糙的手了
很久沒有停下這雙奔波的腳,為你洗腳了
也很久沒把頭靠在你的白發上了
是的,母親
我很久都沒有這么溫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