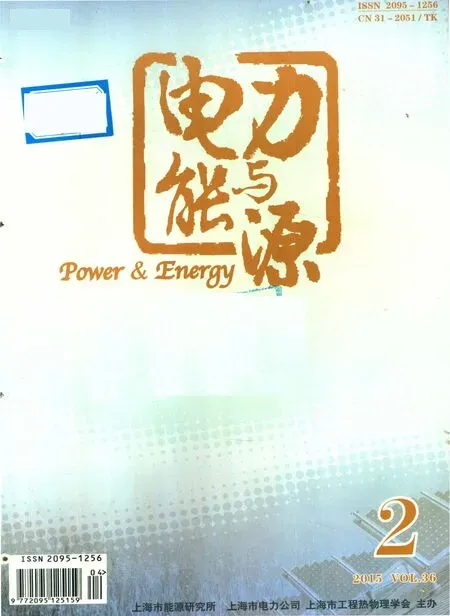基于STIRPAT模型驅動建筑能耗增長影響因素的研究
褚智亮,楊永標,王旭東,黃 莉,王 冬
(1.國電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210000;2.國網天津市電力公司電力科學研究院,天津 300384;3.南京理工大學,南京 210000)
如今中國城鎮化進程大大加快、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建筑能耗呈現出快速的增長趨勢。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和交通領域節能策略的實施,使得工業和交通的節能潛力空間越來越小,如何減小建筑領域能耗的工作成為重點。為此中國制定了“十二五”節能減排規劃,計劃到2015年,全國萬元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到0.869噸標準煤,比2010年的1.034噸標準煤下降16%。“十二五”期間,實現節約能源6.7億噸標準煤。完成此目標的重中之重是在建筑節能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目前,國內對驅動建筑能耗增加影響因素的研究集中在影響因素的定性分析研究,并沒有定量的分析影響因素的大小。周大地運用LEAP軟件情景預測2020年中國的建筑能耗,研究表明政策的執行力度對建筑能耗影響很大,居民采暖能耗和公共建筑能耗就可造成2億噸標準煤的能源消費差距[1]。清華大學建筑節能中心通過CBEM模型對2030年中國建筑能耗進行了情景分析,主要研究了生活方式、技術水平、建筑面積三個關鍵驅動因素,結果顯示:當建筑面積穩定緩慢增長、人們保持自然和諧的生活方式、先進技術得到大范圍推廣,2030年建筑能耗僅比2006年增加14%[2]。楊嘉等人認為未來建筑能耗變化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城市化進程的推進、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人口的增長、能源價格和科技水平的提高[3]。
本文以天津市智能電網園區的建設為案例,創新的采用STIRPAT模型來分析研究驅動智能電網園區建筑能耗增長的影響因素。在之前的研究中STIRPAT模型常被用來解決能源環境中遇到的問題,國內對該模型的應用主要集中在研究碳排放的問題上。本文對智能電網園區能耗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及其影響程度的大小進行了研究,在此基礎上運用嶺回歸分析方法建立了能耗增長驅動因素的回歸模型,為智能電網園區制定建筑節能戰略提供了相關依據。
2 STIRPAT模型及其相關理論基礎
隨著工業領域革命的發生、科技的日新月異、人口的迅猛增長、經濟的不斷發展,資源和環境給全球帶來的壓力也日益加劇。專家學者展開了大量研究關于人口、經濟、科技對環境的影響,并提出了相關的數學模型。
2.1 IPAT模型及相關理論基礎
Ehrlich和Holden首次提出建立“IPAT”方程來定量反映人口、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對環境的影響,其中I是環境壓力(Impact),P是人口數量(Population),A是富裕度(Affluence),T為技術(Technology)[4,5]。學術界對該模型廣泛認可,并將其用于分析影響環境的關鍵因素。此后,有學者對該模型進行了改進,提出了不同形式的擴展模型。Schulze把人的行為因素B(Behavior)引入到IPAT模型中,提出“I=PBAT”,他認為人類不僅可以通過使用有效的技術手段來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之外,還有更為有效的方式,如自身行為[6]。Waggoner和Ausube提出了IMPACT模型,把“I=PAT”中的T分解成單位GDP的消費(C)和單位消費產生的影響(T)[7]。
2.2 STIRPAT模型及相關理論基礎
“I=PAT”模型、“I=PBAT”和“I=PACT”模型,都是通過改變一個影響因素,并保持其它影響因素不變來分析問題,這種情況下得到的結果是變量的等比例變化,是這類模型最大的局限性。
為了更好的彌補IPAT的不足,York等人通過建立隨機模型來分析人口、經濟、科技對環境的非比例影響。在IPAT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STIRPAT模型[8],即:

式中 I——環境;P——人口;A——財富;T——技術;a——模型系數;b——人口影響指數;c——財富影響指數;d——技術驅動力的影響指數;e——模型的誤差。
IPAT模型事實上是STRIPAT模型的一種特殊形式,當a=b=c=d=e=l時,STRIPAT模型就轉化為IPAT模型了。STIRPAT模型是一個非線性的多自變量模型,對等式兩邊進行對數化處理后:

STIRPAT模型的優勢在于在保留了IPAT等式乘法結構的基礎上,通過引入指數來填補各影響因素等比例變化的缺陷,更為關鍵的是,STIRPAT模型不僅允許將各個系數作為參數來進行估計,而且也允許對各個影響因素進行適當的分解,從而彌補了難以定量分析各個因素對環境產生影響的不足[9]。
3 針對智能電網園區建立相應的STIRPAT模型
推動園區建筑能耗增長的影響因素眾多,通過調研大體上可分為:人口因素包括園區人口總量、人口分布結構、年齡結構等;經濟因素包括人均GDP、建筑行業總產值等;居民生活因素包括人均居住面積、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費水平等;園區建設水平因素包括房屋建筑面積、集中供暖面積等。
3.1 園區建筑能耗影響因素的定性分析
園區建筑能耗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人口總量,人口的增長必然會增加能源的消耗,因此可以假定人口總量與建筑能耗存在著正向關系。
導致建筑能耗增長的直接因素是迅速增長的園區建筑總面積。從技術角度分析,隨著建筑面積的增加,用能設備的負荷隨之增加。例如采暖系統、空調系統、照明系統的負荷設計依據之一就是建筑面積,建筑面積越大,用能負荷越大。以采暖為例,北方城鎮的平均采暖能耗為20 kg標煤/m2年,也就是說當建筑面積每增加1 m2,年采暖能耗就多消耗20 kg的標準煤。
首先我們觀察混合數據(pooled data)中各變量與主觀幸福度的相關性。由于OLS和Ordered model得到的結果并無實質性差異(Ferrer-i-Carbonell and Frijters, 2004),本文采用OLS方法得到混合回歸結果。從表2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健康、婚姻狀況、教育、工作、性別和年齡等人口學變量都對主觀幸福度有顯著影響。這一研究結論與幸福經濟學文獻(如Easterlin,2002,溫曉亮等,2011)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
園區的城鎮化建設對建筑能耗的影響并不是單一的,一是由于城鎮建設的大規模開展,導致園區的建筑面積迅速增長;二是農村居民人均能源消費相比城鎮要低得多,城鎮化進程必將導致大量農民進城,建筑能耗會因此增長;三是加速城鎮化進程必將推動第三產業發展,公共建筑的能耗也因此增長。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會導致園區建筑能耗的快速增長。我國小康社會2020年住宅居住目標:北方地區冬季供暖將得到全面普及,供暖覆蓋率達到99%以上;南方冬季寒冷地區的家庭擁有健全的取暖設施,冬季的居住舒適度得到保障。因此暖通空調能耗等建筑能耗所占的比例也會相應上升,建筑能耗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10]。
公共建筑能耗的最大組成部分就是第三產業能耗,第三產業經濟活動的頻繁發生導致公共建筑能耗隨之增長。因此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也是推動園區建筑能耗的增長因素之一。
3.2 模型擴展及模型變量的說明
根據3.1對智能電網園區建筑能耗增長驅動因素的定性研究分析,為了能夠更準確的定量分析驅動因素的影響程度,將初始IPAT模型中的各因素進行進一步擴展,其中人口因素可被分解為人口總量和城鎮化率兩個因素,富裕程度可被分解為第三產業增加值指數、建筑總面積、居民消費水平指數三個因素。技術因素應歸結為單位面積建筑能耗,居民生活水平和建筑能耗水平是單位面積建筑能耗的直接影響因素,兩者并不能準確反映技術因素的影響程度大小。本文分析的著力點是建筑能耗增長的驅動因素,技術因素反而是促進建筑能耗下降的因素。基于上述分析,在此模型中技術因素不予考慮。
根據以上分析,得到的最終智能電網園區驅動建筑能耗增長影響因素STIRPAT分析模型如式(3)所示,具體模型變量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中各變量的說明
3.3 模型數據來源
STIRPAT模型中所需的社會與經濟數據來自《2011年天津統計年鑒》,GDP換算成2005年標準,時間序列選擇的區間為1985~2010年,其中城鎮化水平只有1996~2010年的數據,對其進行指數式(4)擬合,R2為0.996,進而可以推算以前的城鎮化水平。

4 驗證與分析
4.1 最小二乘法回歸分析結果
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簡稱OLS)對STIRPAT模型進行線性回歸擬合時,變量之間不能存在高度的線性關系是重要前提之一[11]。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矩陣形式為Y=Xβ+ε,其中參數β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計為:

當X中的變量完全相關時,(XTX)為不可逆矩陣。因此,不能用公式求出回歸系數。
當X中變量高度相關時,此時幾乎為0,此時求(XTX)的逆矩陣會產生嚴重的舍入誤差。因此,該模型的回歸系數極易受到舍入誤差的影響,其估計值的抽樣變異性大大增加。所以當模型的變量存在多重共線性時,采用OLS建立的回歸模型存在的缺陷是回歸系數參數估計的標準誤差變大,估計值的穩定性下降,置信區間寬度變大,系數t檢驗不能達到要求或得不到正確的系數估計值[10]。
因此,當利用OLS法對模型進行線性回歸擬合時,首先要考慮的是診斷變量的多重共線性。由3.1分析可知,智能電網園區建筑能耗的影響因素為人口、第三產業的發展、建筑總面積、城鎮化、居民消費水平,4個因素在時間序列上有著共同的趨勢。其中建筑總面積、城鎮化、第三產業的發展、居民消費水平都與經濟發展存在正相關的關系。
依據收集到的各項數據指標,以擴展后的STIRPAT方程為模型,運用SPSS18.0對模型(3)做OLS多元回歸分析和多重共線性VIF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VIF檢驗的結果顯示,模型中5個自變量的VIF值均大于10,因此模型(3)的自變量之間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由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P、U、A的系數均為負數,不能滿足研究分析的要求。故模型(3)不能采用普通OLS進行回歸擬合。

表2 OLS回歸分析及多重共線性VIF檢驗
4.2 嶺回歸分析結果
為了更好的克服自變量之間嚴重的多重共線性,本文采用嶺回歸(Ridge Regression)估計對模型進行擬合。Ridge estimate是由Hoerl和Kennard于1970年提出的。嶺回歸分析是一種修正改良后的的最小二乘估計法,當自變量之間存在嚴重的多重相關性時,該方法比OLS有著更為穩定的估計,并且最終的回歸系數的標準差也比OLS要要小的多[12]。
該方法的基本原理是當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相關性時,Ridge estimate會在自變量標準化矩陣XTX的基礎上加上一個正常數矩陣k I,則存在k>0,使|XTX+k I|盡可能不等于0,此時嶺回歸參數估計為:

利用SPSS18.0軟件自帶的嶺回歸函數對方程(5)進行線性擬合,并設置嶺回歸系數k的區間為(0,1),步長為0.01。當k≥0.06時,該方程的回歸系數慢慢趨于穩定,當k≥0.12時,所有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值,滿足分析的要求。因此選擇嶺回歸系數為0.12,嶺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嶺回歸模型擬合結果
由方差分析結果可知,F顯著性檢驗p<0.000 01,各自變量標準回歸系數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值均小于1.08,并且回歸系數的符號滿足經濟學的要求。由模型的顯著性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可決系數大于0.94,因此該模型有較高的擬合度。綜上所述,模型(3)的擬合方程為:

根據該模型的嶺回歸估計結果可以得出,該模型下天津市近25年來驅動建筑能耗增加的影響因素按其影響程度的大小依次為:居民消費水平(26.9%)、第三產業發展(23.8%)、建筑總面積(18.5%)、城鎮化率(14.7%)、總人口(1%)。如圖1所示。

圖1 驅動因素影響程度大小圖
由表3可知,模型中各自變量所對應的回歸系數,即各驅動因素變化1%所對應的建筑能耗變化量。其中總人口的變化量為0.057,城鎮化率的變化量為0.326,建筑總面積的變化量為0.276,居民消費水平的變化量為0.214,第三產業發展的變化量為0.151。
5 結語
在人口因素中主要從人口總量和城鎮化率這兩個角度進行分析,對建筑能耗的影響程度分別為14.7%和1%,人口結構因素對建筑能耗增長的影響程度大于人口總量因素。造成這樣的結果其原因是多樣化的。城鎮化對智能電網園區的建筑能耗的影響效應是多重的,主要體現在由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居民消費行為的變化。相比而言,由于計劃生育和觀念的改變,人口總量因素對建筑能耗的驅動作用十分有限[13]。
消費水平的提高是五個因素中對建筑能耗驅動作用最為明顯的,高達26.9%。衡量國家富裕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居民消費水平,其對建筑能耗的影響方式主要體現在:(1)消費水平提高導致家用電器擁有量和使用時間上升;(2)消費水平提高導致人們更注重生活的舒適度,其中供熱供冷的暖通空調系統的能源消耗也將大大增加[14]。
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建筑能耗的驅動作用也是十分明顯的。主要原因是公共建筑能耗的最大組成部分就是第三產業能耗,第三產業經濟活動的頻繁發生導致公共建筑能耗隨之增長[15]。
建筑總面積的增加是驅動建筑能耗增長的直接因素,建筑面積增加必然帶來照明系統、空調系統、動力系統用能的增長。
政府在建筑節能中的處于主導地位,充分發揮政策的優勢。抓住戰略機遇,引導生態城區建設與發展。積極引導市場,促進建筑行業節能的健康發展。抓緊基礎研究工作、完善建筑節能技術和服務保障體系。
[1] 周大地.2020中國可持續能源情景[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 清華大學建筑節能中心.中國建筑節能年度發展研究報告(2009)[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3.
[3] 楊 嘉,吳祥生,張敏琦.神經網絡在建筑能耗宏觀預測模型中的應用[C].全國暖通空調制冷2002年學術年會論文集/下冊,廣州,2002.
[4] EHRLICH P R,HOLDEN JP.Impact of population growth[J].Science,1971,171:1212-1217.
[5]EHRLICH P R,HOLDEN J P.One dimensional economy[J].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1972,16:18-27.
[6] WAGGONER P E,AUSUBEL J H.A framework for sustainability science:a renovated IPAT identity[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2002(99):7860-7885.
[7]SCHULZE P C.I=PBAT[J].Ecological Economics,2002(40):149-150.
[8]DIETZ T,ROSA E A.Rethink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population,affluence and technology[J].Human Ecology Review 1994(1):277-300.
[9]YORK R,ROSA E A,DIETA T.STIRPAT,IPAT and Impact:analytic tools for unpacking the driv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J].Ecological economics,2003(46):351-365.
[10] 王惠文.變量多重相關性對主成分分析的危害[J].北京航空航大大學學報,1996,22(1):65-70.
WANG Hui-wen.Elementary introduetion to mutiple correlation causing harm to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J].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1996,22(1):65-70.
[11] 王惠文,吳載斌,孟 潔.偏最小二乘回歸的線性與非線性方法[M].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6.
[12]HOERL A E,KENNARD R W.Ridge regression biased estimation for non-orthogonal problems[J].Techometrics,1970(12):55-68.
[13] 何 強,呂光明.基于IPAT模型的生態環境影響分析—以北京市為例[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8(12):83-88.
HE Qiang,LV Guang-ming.Analysi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mpact based on IPAT model--A case study of Beijing[J].Journal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2008(12):83-88.
[14] 盧 娜,曲福田,瑪淑怡,等.基于STIRPAT模型的能源消費碳足變化及影響因素—以江蘇省蘇錫常地區為例[J].自然源學報,2011,26(5):814-824.
LU Na,QU Fu-tian,FENG Shu-yi,et al.Trends and determining factors of energy consumption carbon footprint-An analysis for Suzhou-Wuxi-Changzhou region based on STIRPAT model[J].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2011,26(5):814-824.
[15] 燕 華,郭運功,林逢春.基于STIRPAT模型分析CO2控制下上海城市發展模式[J].地理學報,2010,65(8):983-990.
YAN Hua,GUO Yun-gong,LIN Feng-chun.Analyzing the developing model of Chinese cities under the control of CO2 emissions using the STIRPAT model:A case study of Shanghai[J].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10,65(8):983-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