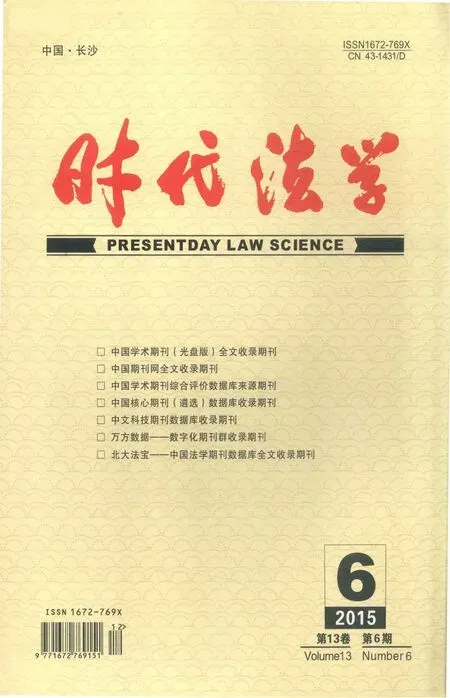日本“情況證據(jù)”理論及其借鑒*
帥清華,郭小亮
(1.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江西南昌 330029;2.江西警察學院,江西南昌 330100)
證據(jù)的審查判斷,是審判權(quán)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審判實踐中,運用間接證據(jù)來認定案件事實要比直接證據(jù)更為復雜,也更具研究價值。間接證據(jù)在日本亦稱為情況證據(jù),其理論來源于英美法,但又有別于英美法,具有鮮明的特色。通過研究日本的情況證據(jù)理論,發(fā)現(xiàn)和甄別其中可以為我國所借鑒的地方,對于完善我國證據(jù)制度、規(guī)范審判權(quán)的運行,庶幾可以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一、日本“情況證據(jù)”理論概觀
(一)情況證據(jù)中的“情況”
情況證據(jù)(Circumstantial Evidence)又稱情勢證據(jù)、環(huán)境證據(jù),指的是“間接證據(jù)以及由此認定的間接事實合在一起的總稱”〔1〕[日]松尾浩也.刑事訴訟法的爭點[M].東京:有斐閣,2002.156.。按照這一定義,情況證據(jù)與間接證據(jù)是有一定區(qū)別的。但是,日本的司法實務并不嚴格區(qū)分兩者,情況證據(jù)與間接證據(jù)是在同一含義上使用的,兩者僅具有語源上的差別,即:“間接證據(jù)”來源于德國法,“情況證據(jù)”來源于英美法〔2〕[日]石丸俊彥.刑事訴訟實務(下)[M].名古屋:新日本法規(guī)出版株式會社,2005.41.。
情況證據(jù)一詞,在英美法上是來自于“情況不會說謊(Circumstances don't lie)”的格言〔3〕[日]植村立郎.實踐的刑事事實認定與情況證據(jù)[M].東京:立花書房,2008.35.40.。按照這一格言,情況證據(jù)中的“情況”是指可以證明案件事實的事物性質(zhì)、痕跡、環(huán)境以及人的行為等客觀資料和信息。這些客觀資料和信息的存在具有客觀實在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故云“不會說謊”。但客觀資料和信息并不能直接地證明犯罪構(gòu)成要件事實存在與否,只能證明某些間接事實,然后才能根據(jù)間接事實推導出犯罪構(gòu)成要件事實。所以,日本刑事證據(jù)法一般將情況證據(jù)中的“情況”理解為不屬于待證事實,但又與待證事實具有密切聯(lián)系的事實,這些事實可以間接地推認待證事實的存在或不存在〔4〕[日]平野龍一.刑事訴訟法概說[M].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201.。在這一意義上,“情況”就是間接事實,因此將情況證據(jù)等同于間接證據(jù)也就不難理解了。
(二)情況證據(jù)的存在形態(tài)
1.情況證據(jù)的常規(guī)形態(tài)
日本的刑事證據(jù)理論一般把情況證據(jù)的常規(guī)形態(tài)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實物依存型,一種是非實物依存型。
所謂實物依存型,就是以實物形態(tài)表現(xiàn)出來的情況證據(jù)。如兇器、藥物、現(xiàn)場遺留的碎片、鑰匙孔的破損、各種痕跡、指紋、腳印、筆跡、賬簿、會議記錄等。實物依存型的情況證據(jù)相當于我國的物證和書證,比較容易理解。
所謂非實物依存型,指的是以實物之外的形態(tài)表現(xiàn)出來的情況證據(jù)。最常見的是各種言辭,如證人陳述被告人于某一時間不在現(xiàn)場的證言(日本司法實務一般套用英美法用語稱為「アリバイ」,即Alibi)。此外,人的生理、心理變化、行為、狀態(tài)等,也可以成為情況證據(jù)。例如哭泣、哀叫、性格、疾病、可能用于犯罪的知識和經(jīng)驗、財產(chǎn)的轉(zhuǎn)移和處分、工作變動、社會交往關系等。日本法院的判例還明確指出,說話的聲調(diào)、語氣、發(fā)抖、出汗等表現(xiàn)人的心理變化的情況,也可以通過錄音、錄像、檢驗筆錄等形式固定化為情況證據(jù)〔5〕[日]植村立郎.實踐的刑事事實認定與情況證據(jù)[M].東京:立花書房,2008.35.40.。
2.情況證據(jù)的特殊形態(tài)
情況證據(jù)的特殊形態(tài),主要有四種。
一是作為輔助證據(jù)的情況證據(jù)。這種情況證據(jù)要證明的對象不是待證事實,而是其他證據(jù)的證明力,即所謂“證據(jù)的證據(jù)”。例如,會議記錄記載董事長甲在公司董事會上暗示要挪用和侵占客戶資金的發(fā)言,該會議記錄是一種情況證據(jù),而證人乙作證陳述甲當天在美國旅游,不可能出席該次會議,乙的證言不能證明甲是否實施了侵占行為,但能夠間接地證明會議記錄的可信度,此時乙的證言就是一種作為輔助證據(jù)的情況證據(jù)。
二是關于可能性的情況證據(jù)。這種情況證據(jù)不能確實證明待證事實的有無,只能證明有無該事實的可能性。例如案發(fā)現(xiàn)場的環(huán)境、構(gòu)造、通風、采光等情況,只可證明被告人是否有作案條件或證人是否有目擊條件,其證明的結(jié)果僅為一定程度的可能性。大阪高等法院2001年10月24日的判例指出,被害人尸體無法找到,不能確實查明其年齡,但從其案發(fā)前不久的照片上的容貌、體格、發(fā)育情況等,可以認定其系未成年人的可能性較大,此時,該照片可作為情況證據(jù)使用。
三是關于被告人作案后實施特定行為的情況證據(jù)。即通過被告人在作案后的毀滅隱匿證據(jù)、栽贓嫁禍、整容、逃亡等異常表現(xiàn),推認其就是實施犯罪行為的人。例如,東京高等法院2000年8月17日的判例認為,被告人在其女友失蹤之后,立即搬家到外地、不與女友家人聯(lián)系、不去參與尋找、將報紙上的相關報道剪下來收藏、不出席葬禮和法事,這些異常的間接事實可以作為推認被告人殺死其女友的情況證據(jù)〔6〕[日]植村立郎.實踐的刑事事實認定與情況證據(jù)[M].東京:立花書房,2008.35.43.61.。
四是控辯雙方當事人特定的訴訟行為也可能成為情況證據(jù)。例如,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指出,在檢察官初步證明了待證事實后,被告人可以提出反駁,如果被告人提不出證據(jù)進行反駁,就可以認定檢察官指控的事實成立。此時,被告人提不出證據(jù)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情況證據(jù),法院可以據(jù)此認定對被告人不利的事實。同樣,對于被告人的反駁,檢察官可以提出再反駁,如果檢察官無法提出再反駁,也可以作為情況證據(jù)認定對檢察官不利的事實〔7〕[日]石丸俊彥.刑事訴訟實務(下)[M].名古屋:新日本法規(guī)出版株式會社,2005.55.。
(三)情況證據(jù)的分類
情況證據(jù)有多種分類,實務中常用的是兩種。一是分為肯定指控內(nèi)容的積極情況證據(jù)和否定指控內(nèi)容的消極情況證據(jù)。二是分為并存的情況證據(jù)、預見的情況證據(jù)、溯及的情況證據(jù)。
并存的情況證據(jù),指的是產(chǎn)生于犯罪行為實施過程中的情況證據(jù)。最常見的如現(xiàn)場殘留的被告人指紋、腳印、血痕等。此外,日本法院的判例認為,Alibi以及被告人提出的犯罪行為系第三人實施的主張,也屬于并存的情況證據(jù)。
預見的情況證據(jù),指的是產(chǎn)生于犯罪行為實施之前,可以證明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情況證據(jù)。日本法院明確認定的預見的情況證據(jù)有:被告人具有制造毒品的知識和經(jīng)驗、向他人購買用于印制假鈔的機器、與被害人的矛盾糾紛、對藏有銀行金條的特殊隱密場所的認知、業(yè)務侵占行為被揭發(fā)前經(jīng)營不善而出現(xiàn)資金緊缺的情況等。
溯及的情況證據(jù),指的是產(chǎn)生于犯罪行為實施之后,可以證明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情況證據(jù)。前述情況證據(jù)的特殊形態(tài)已涉及到溯及的情況證據(jù)。此外,溯及的情況證據(jù)還包括:犯罪發(fā)生后第二天,被告人持有作案用的工具;被害人財物被盜竊后,被告人的銀行卡上忽然多出與被盜金額相近的存款,并在數(shù)天之內(nèi)揮霍一空;殺人現(xiàn)場留有被告人血跡,而被告人在案發(fā)當晚曾到醫(yī)院治療傷口〔8〕[日]植村立郎.實踐的刑事事實認定與情況證據(jù)[M].東京:立花書房,2008.35.43.61.。
(四)情況證據(jù)認定的構(gòu)造
1.實體性構(gòu)造
按照前述的定義,情況證據(jù)是間接證據(jù)以及根據(jù)間接證據(jù)認定的間接事實的總稱。據(jù)此,運用情況證據(jù)認定案件事實的基本構(gòu)造,也就包括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根據(jù)間接證據(jù)認定間接事實,第二步是根據(jù)間接事實推認出待證事實。日本證據(jù)法理論上說的“情況證據(jù)認定的構(gòu)造”,指的主要就是根據(jù)間接事實推認出待證事實的過程和方法。
曾任東京高等法院法官的木谷明教授把情況證據(jù)認定的構(gòu)造概括為三個關鍵詞,即“分別檢討、綜合評價、過程說明”〔9〕[日]木谷明.刑事事實認定的基本問題[M].東京:成文堂,2008.259.。分別檢討,指的是對每一個間接證據(jù)和每一項間接事實都要單獨拿出來進行分析,判斷其與待證事實的邏輯關系,重點審查其證據(jù)能力(關聯(lián)性)。綜合評價,指的是在肯定情況證據(jù)關聯(lián)性的基礎上,將全案的情況證據(jù)作為一個整體,判斷其對待證事實的推認能否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過程說明,指的是要求法官在判決書中詳盡地說明推理過程。從間接事實到待證事實,需要在判決書中有意識地展示推理過程。如果推理過程的說明不能排除被告人辯解提出的合理假說,就需要對認定的事實進行重新審視〔10〕[日]木谷明.刑事事實認定的基本問題[M].東京:成文堂,2008.259-261.。
2.程序性構(gòu)造
按照日本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刑事案件一審開庭之前要進行庭前整理程序,目的是交換和開示證據(jù),在盡量早期的階段明確爭議焦點,以便庭審時集中進行證據(jù)調(diào)查和法庭辯論。在庭前整理程序中,檢察官應提出記載預定證明事實的書面材料,在充分進行證據(jù)開示的基礎上,向被告方表明主張。這要求檢察官在書面材料中明確提示情況證據(jù)的運用以及舉證計劃。另一方面,對于被告人的防御而言,一般可以從排除情況證據(jù)本身、主張相反的間接事實、反駁推理過程這三個方面著手,這些主張應在庭前整理程序中明確提出,需要提交證據(jù)的,應充分開示。如果被告人認為檢察官開示的證據(jù)和舉證計劃有不夠清晰的地方,可以通過法院要求檢察官釋明。對法官而言,應“準確地把握檢察官舉證構(gòu)造的整體狀況,對照著斟酌被告方的主張,在此基礎上整理爭議焦點,確定審理思路。”〔11〕[日]木谷明.刑事事實認定的基本問題[M].東京:成文堂,2008.259-261.
(五)日本法院判例中情況證據(jù)的運用
在日本法院的歷代判例中,情況證據(jù)的運用非常廣泛,最常見的是用于對被告人同一性和對故意、目的等主觀要件事實的認定〔12〕[日]最高法院司法研修所.從情況證據(jù)的觀點看事實認定[M].東京:法曹會,1994.3.。
檢察官指控被告人犯罪,首先要證明被告人與作案人的同一性,即犯罪行為系被告人所實施。在日本,運用情況證據(jù)來證明被告人與作案人同一性的著名判例是最高法院2000年2月21日關于“烏頭堿殺人事件”的判決。在該案中,檢察官以殺人罪、詐騙未遂罪起訴被告人神谷某,指控其于1986年5月20日與妻子神谷佐利子(被害人)及女友二人一起到?jīng)_繩縣石垣島旅游,期間被告人將一枚含有烏頭堿的膠囊交給被害人服下,被害人于當晚出現(xiàn)不適,在送往醫(yī)院的途中因心肌梗塞而死亡。被告人堅決否認自己下毒殺人,因此沒有口供或其他直接證據(jù)。檢察官提交的情況證據(jù)主要通過動機、作案條件、被告人的專業(yè)特長、行為習慣、在短期內(nèi)為被害人購買巨額人身保險、曾購買烏頭草和河豚等間接事實來證明被告人的同一性。與此相對,被告人提出的辯解是:烏頭堿為急性劇毒,5毫克左右可立即致命,而被害人出現(xiàn)不適癥狀時,自己已離開被害人3個多小時,因此否認檢察官的指控。檢察官對此進行反駁,認為被告人所用的毒藥是烏頭堿與河豚毒的混合物,河豚毒是慢性毒物,可緩解烏頭堿毒發(fā)的時間。本案由東京地方法院一審,經(jīng)綜合考慮認為檢察官提出的假說具有較高的蓋然性,且足以否定被告人的辯解假說,遂認定被告人構(gòu)成殺人罪和詐騙未遂罪,判處無期懲役。案件經(jīng)東京高等法院二審、最高法院三審,均維持原判。此判例沒有明確指出被告人實施犯罪的事實達到了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而是從具體時空條件下殺害被害人的可能性的角度來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從而認定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這被認為是沒有直接證據(jù)的場合完全依靠情況證據(jù)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較為成功的典型判例〔13〕[日]石井一正著.刑事事實認定入門[M].東京:判例時代社,2005.117.。
在殺人案件中,被告人經(jīng)常以沒有殺人意圖作為辯解理由。為此,能否運用情況證據(jù)來證明殺人的故意,是事實認定的關鍵。按照日本法院的判例,認定殺人意圖的存在,主要是從兇器、創(chuàng)口、行為形態(tài)、動機這四個方面來著手。東京高等法院1994年11月16日判決中對根據(jù)兇器來認定殺人故意的做法作了較為全面的總結(jié)。在該案中,被告人用華麗的錦盒裝住一把刃長68厘米的忍者刀,偽裝成禮品,進入被害人的辦公室,將被害人砍傷,對此,被告人辯解稱自己僅有傷害的故意,沒有殺人意圖。法院認為,在使用刃物殺人的案件中,刃部的長度、形狀、攻擊的部位、角度、方法等,均可成為認定殺人意圖的積極要素或消極要素,關鍵是看兇器及其使用是否具有致命的危險性,根據(jù)本案案情,兇器忍者刀為精煉花紋鋼材質(zhì),刃口較長而且十分鋒利,被害人受傷的幾處部位均足以致命,被告人將兇器精心偽裝,則表現(xiàn)出計劃性,因此可以認定被告人具有殺人的直接故意。另一方面,正如上述判例指出,兇器的性狀也可以成為消極的情況證據(jù),例如福岡地方法院宮崎分院的一個判例認為,被告人使用刃長僅4.5厘米的水果刀捅被害人腰部,最多只能在傷害的程度上認定犯罪故意〔14〕[日]植村立郎.實踐的刑事事實認定與情況證據(jù)[M].東京:立花書房,2008.124.。
根據(jù)兇器來認定殺人故意,還要考慮被告人的認知,在這一點上與過失犯罪相區(qū)別。例如,對于藥物、爆炸物、機械、弓弩等具有一定技術含量的物品,其本身雖有高度危險性,但如果被告人不可能認識到危險性,則不應認定被告人具有殺人故意,根據(jù)案情應認定為過失或無罪〔15〕[日]植村立郎.實踐的刑事事實認定與情況證據(jù)[M].東京:立花書房,2008.132.。
二、日本“情況證據(jù)”的若干特色
與我國的間接證據(jù)理論相比,日本的情況證據(jù)理論更是具有鮮明的特色,大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淵源判例,具有顯著的實踐性
日本的判例制度十分獨特,一方面它堅持成文法主義,另一方面,它又規(guī)定法院的判例具有事實上的拘束力,法官在審判案件時有遵循判例的規(guī)范性義務〔16〕[日]團藤重光.法學的基礎[M].東京:有斐閣,2007.167.。日本刑事訴訟法典對情況證據(jù)的規(guī)定很少,學者的教科書和專著中對情況證據(jù)的論述大多也很簡略。但由于情況證據(jù)在審判實務中的重要性,很多法官都非常注重對情況證據(jù)的研究和實踐,由此形成了很多經(jīng)典判例。自1947年日本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修改以來,通過數(shù)十年的判例積累,形成了一套體系龐大、內(nèi)容豐富的情況證據(jù)理論。情況證據(jù)理論的大部分內(nèi)容,可以說主要不是依靠純粹的學者,而是依靠法官,尤其是學者型法官來完成總結(jié)和表述的任務的。前面論及的研究者,石丸俊彥、植村立郎、石井一正、木谷明等皆是享譽司法界的學者型法官,他們的論述常常大量引用各級法院的判例,使得情況證據(jù)理論的很多內(nèi)容與具體案情直接相關。
(二)分類獨特,具有廣泛運用性
日本將情況證據(jù)按時間序列區(qū)分為并存的、預見的、溯及的三種,這種分類未見于英美法,為日本所特有。一般來說,并存的情況證據(jù)產(chǎn)生于犯罪過程中,與犯罪行為有密切的因果聯(lián)系,證明力相對較強。預見的情況證據(jù)和溯及的情況證據(jù),其證明力則十分微妙:一是其結(jié)論的或然性也比較低;二是其不能單獨定案。對此,日本最高法院的中川武隆法官把預見的情況證據(jù)和溯及的情況證據(jù)稱為“危險的證據(jù)”,并指出,“對于這些情況證據(jù),法官往往容易過度地肯定其可信度和推定力,因此,在判斷這些情況證據(jù)的時候,應當慎重地分析其含義和相互聯(lián)系,在適當?shù)姆秶鷥?nèi)認定其證明力。”〔17〕[日]最高法院司法研修所.從情況證據(jù)的觀點看事實認定[M].東京:法曹會,1994.36.在日本的刑事判例中,因為沒有直接證據(jù)而完全依靠情況證據(jù)定罪的案件非常多,前述的“烏頭堿殺人事件”就是近年來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此類案件之一。同時,運用情況證據(jù)判決被告人無罪的案件也占無罪案件的多數(shù)〔18〕[日]法務省法務綜合研究所.平成21年版犯罪白皮書[EB/OL].http://www.moj.go.jp/content/000010214.pdf.。
(三)恪守程序,存疑有利于被告人
日本刑事訴訟法明確規(guī)定了自由心證原則,證據(jù)的證明力主要由法官依據(jù)自己的心證裁量。但基于情況證據(jù)需經(jīng)過推理這一特殊性,為了防止自由裁量權(quán)行使超越應有邊界,法律和判例確定了一系列制約性程序。值得一提的是疑罪從無原則的適用。情況證據(jù)只能得出或然性的結(jié)論,雖然允許被告人提出反駁,但實踐中仍難以避免因判斷失誤造成冤案的情況。為此,曾任東京高等法院院長的石丸俊彥法官在其著作中深有感觸地寫道:“由于法官的過于自信,情況證據(jù)往往變成危險的證據(jù)。有了情況證據(jù)后,法官在面對各種壓力時,就容易傾向于考慮報應感情的滿足和社會秩序的維持,通過處罰被告人來緩和被害人與輿論的指責。對此,情況證據(jù)最重要的注意規(guī)則,莫過于堅持‘存疑則有利于被告’這一刑事審判的鐵的法則。”〔19〕[日]石丸俊彥.刑事訴訟實務(下)[M].名古屋:新日本法規(guī)出版株式會社,2005.90.
(四)公開心證,展示事實認定過程
自由心證主義在現(xiàn)代被要求具備可檢驗性,而可檢驗的前提正是法官將心證形成的過程予以公開。木谷明教授認為,“裁判文書的制作是事實認定過程的一種反饋。將事實認定過程包含的各種信息完整地傳達給受眾,是裁判文書的基本功能。”還有法官指出,“裁判文書不是訴訟檔案,不應該要求裁判文書能夠詳細到可以獨立于案卷和證據(jù)而存在的程度。”因此,詳盡的說明并不等于冗長的文字,就判決書的寫作而言,日本法官也反對單純地羅列間接事實而使文書顯得繁瑣,“說明的詳略程度,應視案情而定,在全面的基礎上兼顧精練。過于簡略或過于冗長,都會使判決喪失說服力。”〔20〕[日]最高法院司法研修所.從情況證據(jù)的觀點看事實認定[M].東京:法曹會,1994.127.
三、我國刑事審判對間接證據(jù)的運用:以日本“情況證據(jù)”理論為借鑒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我國的法律制度和司法體制與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別,日本的刑事訴訟和刑事證據(jù)理論的很多內(nèi)容,對于我們來說僅具有參考意義,不宜直接移植。例如日本法院根據(jù)傳聞規(guī)則通常否認偵查筆錄和庭外書面證言的證據(jù)能力,與我國司法實踐的做法大不相同。但是,由于審判權(quán)運行的普遍規(guī)律和證據(jù)運用規(guī)則所具有的共性,中日兩國的刑事訴訟和刑事證據(jù)理論還是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鑒之處的。在以下幾個問題上,我國刑事審判對間接證據(jù)的運用可以借鑒日本情況證據(jù)理論的有益經(jīng)驗和做法。
(一)總結(jié)經(jīng)驗,確立間接證據(jù)運用規(guī)則
日本的情況證據(jù)理論在總體上給我們一個啟示:證據(jù)法具有濃厚的實踐性色彩,光靠單純的理論思辨和哲學玄想很難在證據(jù)法研究上有所作為。判例的積累和法官的思考,是證據(jù)法理論發(fā)展和完善不可缺少的路徑。目前我國關于間接證據(jù)的研究,有幾個值得商榷的傾向:一是介紹英美國家法律的多,結(jié)合本土資源的少;二是研究立法規(guī)定的多,關注司法運用的少;三是抽象論述的多,個案實證研究的少。要改變此種現(xiàn)狀,唯有以廣大法官為研究主體,以典型案件為研究素材,以實證分析為研究方法,不斷總結(jié)審判實踐運用間接證據(jù)的經(jīng)驗,上升到理論高度,既要切合司法實踐,也要防止就案論案,使司法審判中法官的智慧和經(jīng)驗轉(zhuǎn)化為普適性的原則和規(guī)范。期待我國盡早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案例指導制度,為審判實踐運用間接證據(jù)的經(jīng)驗總結(jié)提供制度支持。
(二)謹慎判斷,發(fā)揮間接證據(jù)的獨立定罪機能
日本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經(jīng)濟發(fā)達國家之一,這種情況被歸結(jié)于其刑事司法制度的成功運作,同時,法院審判刑事案件的有罪率很高,一般都維持在99.8%左右。由于存在沉默權(quán),實踐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沒有口供和直接證據(jù)的案件,可見日本法官對運用情況證據(jù)定罪是非常“大膽”的。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明確規(guī)定了自由心證主義,法官對證據(jù)證明力擁有較大的裁量余地,另一方面,日本法官享有良好的職業(yè)保障和社會威望,在作出裁判時面臨的案外壓力相對較小。
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理論雖然也承認可以完全運用間接證據(jù)證明案件事實〔21〕徐靜村.刑事訴訟法(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68.,但在司法實踐中,單憑間接證據(jù)就定罪的案件可謂少之又少,而大量地取得直接證據(jù)在很多案件中是不可能的。這種二律背反已經(jīng)演變?yōu)樗痉▽崉盏囊环N困境,有學者稱之為刑事訴訟的“證明危機”〔22〕龍宗智.印證與自由心證——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模式[J].法學研究,2004,(2).。出現(xiàn)這種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1)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標準過于理想化,要求證明結(jié)論具有唯一性,并“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23〕陳光中.刑事訴訟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66.,而間接證據(jù)必須經(jīng)過推理,推理結(jié)論僅具有或然性,不可能絕對地“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2)“口供情結(jié)”在很多法官的觀念中仍然根深蒂固,未能克服傳統(tǒng)司法“罪從供定”的思維模式,對沒有口供的案件不敢作出判斷;(3)我國偵查機關技術落后,偵查人員素質(zhì)不高,很多間接證據(jù)未能及時收集、固定,或存在嚴重瑕疵,影響了證明力;(4)我國實行嚴厲的錯案追究責任制度,法官在作出判決的時候常常不得不有所保留;(5)我國法官的司法能力和社會公信力仍有待提高,法官在審判時面臨的社會壓力較大,缺乏運用間接證據(jù)定案的底氣和自信;(6)司法體制有待改正,我國實際行使審判權(quán)的往往是審判委員會,真正審案法官往往只是將自己的意見交由審判委員會裁決,審判委員會成員由于不是實際的審判經(jīng)歷者,而只是根據(jù)法官報告來形成意見,在只有間接證據(jù)的場合,難以形成明確意見。
2010年6月,我國的“兩高三部”聯(lián)合發(fā)布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jù)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該規(guī)定第33條放棄了“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理論標準,代之以“排除一切合理懷疑”,此“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被新《刑事訴訟法》第53條再次確認,為獨立運用間接證據(jù)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據(jù)。但關于合理懷疑以及如何排除存在紛爭,且現(xiàn)今正處于司法體制階段,要解決解決間接證據(jù)司法困境和證明危機,還有待于實踐的繼續(xù)探索和司法環(huán)境的根本改善。
(三)疑罪從無,尊重和保障被告人權(quán)利
日本司法機關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曾標榜“精密司法”,即通過嚴密的社會管理機制和細致的偵查手段來追究和指控犯罪,大量運用科學化的證據(jù)準確認定犯罪。但是,80年代以來,日本連續(xù)出現(xiàn)了財田川事件、白鳥事件等著名的冤案,通過媒體的放大宣傳,導致“精密司法”的神話成為歷史,曾經(jīng)得到國民高度信任的法官威望面臨空前挑戰(zhàn)。這促使日本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反復強調(diào)“必須堅持‘存疑則有利于被告’這一刑事審判的鐵的法則”。還有法官明確主張“刑事審判中第一重要的不是追究和懲罰犯罪,而是阻止冤案的發(fā)生,保障無辜者不受處罰。”〔24〕[日]木谷明.刑事事實認定的基本問題[M].東京:成文堂,2008.2.
我國媒體高度關注內(nèi)蒙古呼格吉勒圖案強奸殺人案、浙江張高平和張輝叔侄強奸案、安徽于英生故意殺人案等近年改判的刑事案件,這些冤錯案件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嚴重影響國民心中尚未樹立牢固的司法權(quán)威。我國與日本的司法體制大相徑庭,造成冤案的原因也不盡相同,但間接證據(jù)運用不當應是共同原因。對于間接證據(jù)的運用,應當以證據(jù)鏈的真實、完整、協(xié)調(diào)為標準,在極其謹慎的基礎上進行縝密的邏輯推理。當公訴機關提出的證據(jù)不能使推定達到高度蓋然性的程度時,應當嚴格依照程序,從保障人權(quán),維護被告人權(quán)利的角度出發(fā),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
(四)詳盡說理,明確裁判文書證據(jù)推認過程
過去我國法院的裁判文書長期流于簡略,事實和理由均以數(shù)筆概括,曾被學者詬為“簡單歸攝模式”〔25〕張志銘.法律解釋操作分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25.。近年來此種狀況得到較大改善,洋洋萬言的判決書已是司空見慣。但是仔細考察這些篇幅較長的裁判文書,其大部分篇幅并非用于說理,而是用于羅列證據(jù),這些證據(jù)已載于案卷,法官在裁判文書中概括轉(zhuǎn)述,不僅顯得重復,而且可能存在人為剪裁、斷章取義的危險。在證據(jù)的分析和說明方面,目前我國的裁判文書較為注重證據(jù)個別分析,即在羅列證據(jù)的同時說明每個證據(jù)的來源、證明對象、是否采信等事項,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對于運用間接證據(jù)得出待證事實的推理過程,仍鮮見詳盡的論述,往往是在大量羅列證據(jù)之后,直接得出最后的整體結(jié)論,其思維和推理過程如何則不得而知,給人印象十分唐突。裁判文書缺乏推理過程,也就無法進行有效的事后檢驗,在上訴和再審程序中容易造成上下級法院的認識分歧,導致案件被改判或發(fā)回重審。
對此,應該借鑒日本的“裁判文書不是訴訟檔案”、“不要求裁判文書能夠獨立于案卷”的觀點,即裁判文書不必將大量的篇幅用于重復敘述證據(jù)的內(nèi)容,而應將重點置于“說理”,公開展示對證據(jù)的評價和推理過程。為此,法官在運用間接證據(jù)進行的推理中,最好能夠詳細地分析每一個推理步驟,層層展開,使證據(jù)鏈中的空隙都得到填補,形成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完整的邏輯思維過程。法官對于推理所使用的經(jīng)驗法則、邏輯規(guī)則、生活知識、專業(yè)知識等,都應大膽予以明確的揭示,通過裁判文書的文字載體,盡量公開自己形成心證和內(nèi)心確信的全部過程,以接受上級法院和社會公眾的事后檢驗和監(jiān)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