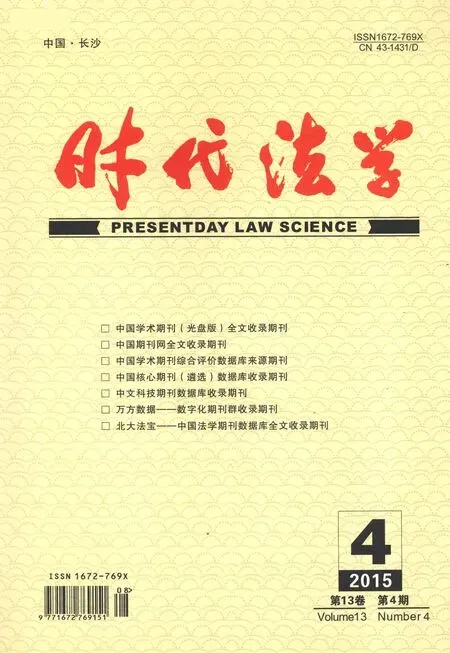洗錢罪的故意與明知
許克軍,秦 策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
洗錢罪的故意與明知
許克軍,秦 策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洗錢罪故意與明知的認定一直是理論界與實務界爭議較大的問題。從語義分析、實施效果和犯罪防控的角度看,間接故意也應構成洗錢罪的故意類型。對于明知的性質,采“概括的七類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說”更為合理;對于明知的判斷標準,應采“主客觀相統一說”,并根據洗錢罪的不同主體有所側重;對于明知的程度,采“確定或可能說”更符合司法實踐需求。關于明知的證明過程,運用嚴格證明和法律推定相結合的方法較為可取;至于有學者提出用舉證責任轉移,使被告人承擔“不明知”的證明責任的觀點,有違無罪推定原則,因而不可取。
洗錢罪;故意;明知;嚴格證明;推定
洗錢罪,是在現代經濟高速發展,毒品、走私、黑社會等有組織犯罪猖獗泛濫,犯罪分子通過各種非法手段聚斂了大量黑錢而無法在正常經濟領域流通的背景下產生的,其本質在于掩飾、隱藏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非法收益。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洗錢犯罪在我國各地頻發,呈現出日益擴散的趨勢,嚴重侵犯了我國金融管理秩序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繁榮穩定。在理論界與實務界,洗錢罪故意與明知的認定一直是個難點問題,直接影響到對這種犯罪的查處和懲治。本文對此展開研究,希望對司法實踐有所助益。
一、故意的類型
洗錢罪以故意為主觀要件,行為人以直接故意的主觀心態實施洗錢行為成立洗錢罪學界并無爭議,關鍵是間接故意能否成立洗錢犯罪。對此問題,分歧在于如何理解《刑法》第191條中“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的含義。通說以為,“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而實施洗錢行為,就表明行為人在主觀上存在犯罪目的,而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中。依此觀點,《刑法》條文中已徹底排除了本罪由間接故意構成的可能性,因而洗錢罪的主觀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王作富.刑法分則實務研究[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586.。
但是,通說對于洗錢罪故意類型的理解是偏狹的,與國際公約以及發達國家的規定存在差異。《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歐洲反洗錢公約》、《聯合國禁毒署反洗錢示范法》等國際刑事司法準則均認可間接故意構成洗錢罪的規定。德國、瑞士等國在其立法上也明確規定了洗錢罪可由間接故意構成。美國法規定了與一般明知不同的“故意不知”也可能構成洗錢罪的情況,其中亦包含著間接故意的放任因素。可見,僅依直接故意方可成立洗錢罪的觀點是不恰當的,間接故意也可成為洗錢罪的故意類型,理由如下:
首先,從語義分析的角度看,“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的表述并不能充分表明洗錢罪的目的犯性質。應該說,這一表述在內涵上具有主客觀上的多樣性,我們不能想當然的把它認為是對目的要素的規定。筆者認為,“掩飾、隱瞞”一句強調的是洗錢罪在客觀行為方面的特征,并非強調構成本罪必須具備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目的,它實際是對刑法列舉洗錢行為方式所加的限制,不能等同于刑法理論上的目的犯,因而“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不是關于犯罪目的的規定*陳興良.協助他人掩飾毒品犯罪所得行為之定性研究——以汪照洗錢案為例的分析[J].北方法學,2009,(4).。行為人實施洗錢行為時,當然也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在掩飾、隱瞞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03.。不能僅憑“為……”的立法表述,就認為洗錢罪是目的犯。既然洗錢罪不是目的犯,則其罪過形式由間接故意構成并無不當之處。
其次,從實施效果來看,完全排除間接故意成立洗錢罪會出現法網的疏漏。實踐中的洗錢行為并非都是以“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為目的,如實踐中某些金融機構為了獲得資金或增加交易數量等,雖明知系洗錢行為而對“黑錢”被清洗的后果聽之任之,采取放任的態度。這是一種“故意視而不見”的行為,客觀上阻礙了司法機關對犯罪的追究,且對金融秩序造成了相應的危害。就此情形,如果僅以洗錢者沒有特定的目的,而將其排除在洗錢罪的范圍之外,顯然是對犯罪分子的放縱,導致參與或介入洗錢的行為不受刑事追究,不利于刑法保護社會目的的實現。
再次,從犯罪防控的角度來看,完全承認間接故意不成立洗錢罪,不利于強化金融機構的監管責任,容易導致其工作人員忽視自身的職業義務。如今,洗錢已發展成為高度復雜的專門行業,它往往需要行為人對國內外復雜的金融、法律制度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絕非一般的犯罪分子可以做到,惟有那些精通國內外金融、法律制度的專業人士才能勝任。所以犯罪分子才愿意給這些專業人士支付的高額費用以換取他們的服務。正因為如此,一些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投資專家、高級律師等就成了大量洗錢犯罪的實際操盤手。鑒于此,自2003年起,中國人民銀行推出《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定》等金融法律規范,以加強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反洗錢義務,堅決杜絕對于洗錢的放任行為。如果對以間接故意實施的洗錢行為網開一面,顯然不利于強化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職業義務,也不能消除洗錢罪滋生的土壤。
二、明知的實體定位
(一)明知的性質
根據《刑法》第191條規定,行為人“明知”的對象是法條規定的七種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是在理解過程中,學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即“具體的七類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說”和“概括的七類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說”。前者是指,行為人必須明確認識到是七類犯罪中的某一具體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才能構成洗錢罪中的明知。而后者是指,行為人對屬于七類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具有概括性認識即可,無需知道是具體哪一個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就可成立明知。兩相比較,“具體的七類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說”過于機械地理解了《刑法》條文,不利于司法實踐中對于“明知”的認定,要知道洗錢行為的上游犯罪是多種多樣的,即使在刑法中列舉的七類犯罪中,其具體的犯罪性質與特征亦各不相同,而要認定行為人明知其所經手的或者投資到某一商業活動中的或者在某一銀行帳戶內存入的資金來源是某項特定犯罪的犯罪所得是非常困難的,尤其對于那些專業的犯罪集團所建構的龐大洗錢網絡來說,要弄清其資金的非法性質和具體來源更是難上加難,甚至有時候實施洗錢的行為人自己也未必知道上游犯罪的種類。而且,“具體的七類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說”還違背了刑法關于主觀認識錯誤的理論。這種學理解釋已經被最高人民法院所采納*2009年11月1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3款規定:“被告人將刑法第191條規定的某一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誤認為刑法第191條規定的上游犯罪范圍內的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不影響刑法第191條規定的‘明知’的認定。”。
(二)明知的判斷標準
關于洗錢罪明知標準的判斷,我國刑法學界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是主觀說,該說認為行為人對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是否明知,應當以行為人自身的認知能力為依據,根據其年齡、生活閱歷、知識水平等主觀能力進行判斷,在當時條件下,如果行為人完全能夠認識的,就認為具有明知。第二種是客觀說,該說著眼于犯罪人所處的客觀環境,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根據一般的經驗、邏輯和常識,社會普通人能夠確切認識到違法所得及產生的收益的性質和來源的,就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明知,而無需考慮行為人的自身實際情況。第三種是主客觀相統一說,該說認為對于洗錢罪明知的判斷既要考慮案件發生時的客觀實際情況,也要考慮行為人自身的認識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克服主觀說和客觀說的片面性*趙廷光.中國刑法原理(各論卷)[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98.。《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明知”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換、轉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進行認定。實際上是采納了主客觀相統一說來作為判斷明知的標準。
盡管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能夠兼顧行為人的認識能力和事實發生時的客觀情況,避免淪為單純的主觀歸罪或客觀歸罪。但是,筆者認為,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把握不能采取完全均衡的方式,而應當根據洗錢罪的不同主體有所側重。我國洗錢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應當區分金融機構與自然人、其他非金融性組織。對于前者,應當以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認識能力為主要標準,兼顧事實發生時的客觀情況。這是因為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對于反洗錢負有更多的職業義務,并具有更高的注意能力。對于后者,則應當以事實發生時的客觀情況為主要標準,而將行為人的認識能力作為次要因素,即根據一般的經驗和常識,通常的人能夠確切認識到違法所得及產生的收益的性質和來源的,可以認定是行為人具有明知,對行為人自身實際認識能力只進行附帶的考慮。因為普通的自然人及非金融性組織與金融機構在認識能力上存在較大差異,所以針對不同主體,以區別對待的方式來考慮明知的判斷標準是符合實際的。
(三)明知的程度
刑法學界對明知的程度大致有三種觀點,分別是“確定說”、“可能說”、“確定或可能說”。“確定說”認為,“明知”就是行為人確切的知道是刑法規定的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對刑法規定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認識不確定或不明了的,不能視為“明知”。“可能說”認為,“明知”只要求行為人認識到可能是刑法規定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即可,即不要求達到“確知”的程度。“確定或可能說”認為,“明知”包括“確知”和“可知”,“確知”就是行為人明確的知道他人的財產就是特定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可知”就是行為人雖然不是確切的知道,但是他人的財產可能是刑法規定的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李希慧.論洗錢罪的幾個問題.法商研究[J].1998,(2).。目前司法實務主要采綜合性的“確定或可能說”,即“明知”不意味著確實知道,確定性認識和可能性認識均應納入“明知”范疇,即只要行為人在當時確實知道或可能知道對于所經手的財產系七類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都可以成立明知。
但筆者認為,在此仍然存在著類型劃分的必要,同樣應當將自然人、其他非金融性組織與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區分開來,因為這兩類主體在注意義務與注意能力方面是存在顯著差異的。如果刑法規范要求只有行為人對特定構成要件要素達到“確知”狀態的才構成犯罪,那么就表明這類犯罪弱化行為人的注意義務,更注重對人權和自由的保障*王林林.刑法分則語境中“明知”的認定[J].天津法學,2014,(1).。對于不承擔特定職業義務的自然人或非金融性組織而言,要求行為人明確地知道是刑法規定的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是恰當的;而對于具有專業能力、承擔注意義務的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而言,明知的程度則應當降低為“可能”即可,甚至還應當擴展至“應當知道”的層次。行為人主觀認識的降低導致入罪可能性的增加,其目的在于嚴格金融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注意義務,防止其利用職業能力與職業便利為他人洗錢暗渡陳倉,進一步消除洗錢罪滋生的土壤。
三、明知的證明
作為一項犯罪構成要件,犯罪的主觀方面屬于與定罪有關的事實,自然成為刑事案件中的證明對象。洗錢罪的認定離不開明知要素的證明。在犯罪構成要件諸要素中,客觀行為和結果等要素容易得到證明,但主觀的故意、目的等要素則較難認定,明知要素的證明也就成為洗錢罪認定的一個難點。作為一種非物質性的心理活動,明知要素屬于內界事實,他人很難通過感官直接認知,其取證與認證難度不言而喻。但是,這一內界事實并非不可證明,其具體的證明方式或途徑有以下幾種:
(一)運用證據的嚴格證明
1.獲取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否具有“明知”的心理狀態,通過訊問獲取其口供無疑是最為便捷的方式。口供是一種直接證據,往往能夠全面反映案件事實情況,但是口供也存在與生俱來的缺陷。口供的內容具有復雜性,存在著較大的虛假可能性;口供內容具有反復性和不穩定性,經常出現反復或翻供的情形,從而影響到口供的證明效力。與此同時,為了防止司法實踐過于依賴口供,甚至導致刑訊逼供的發生,刑事訴訟法對訊問程序進行了嚴格的約束,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權利的方式取得的口供將會作為非法證據而加以排除。而且,根據口供補強規則,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換言之,即便存在著有效的口供,同樣需要其他證據的印證與補足。如此看來,被告人口供在其證明效用方面雖然有其優勢,但它的獲取及運用比其他證據而言存在著更多的約束。因此,口供對于“明知”要素的證明功用雖然不可忽視,但又不能過分依賴。
2.借助間接證據。間接證據是指不能獨立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據,由于它無法單獨證明案件主要事實,需要諸多具有關聯性的間接證據形成一個“證據鏈鎖”來發揮證明作用。在缺乏口供或者口供失去證明效力的情況下,使用間接證據形成證據體系同樣可以證明被告人的“明知”。“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這主要指的就是使用間接證據證明的情況。一般認為,使用間接證據認定案件事實,除了單個證據本身要具有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之外,還需要符合充分性、協調性和排他性的要求,這里的充分性是指必須達到能夠證明案件全部事實所需要的量。筆者認為,由于“明知”只是定罪構成要件中的一個要素,有關證據只能是完整證明體系的一個環節,因此無須拘泥于充分性這個要求。但是,需要重視的是協調性和排他性的要求,即所使用間接證據之間以及間接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必須協調一致,沒有矛盾;同時,所取得的結論應當是唯一的,能夠排除合理的懷疑。當然,要將作為事實片斷的間接證據粘接起來,還需要法官依據邏輯法則與經驗法則所進行的推理活動,這是法官自由心證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運用推定的證明
推定涉及兩個事實(基本事實和推定事實)之間的關系,即在基礎事實得以確立的情況下,如果沒有遇到相反證據,事實審理者就應當或者可以認定推定事實的存在。作為一種事實認定方式,推定所要解決的是推定事實的認定問題。由于通過尋常的證明方式,推定事實的認定往往比較困難或者成本過高,因此使用較易證明的基礎事實來加以推斷。作為一種推理類型,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存在著客觀存在的常態聯系,這種常態聯系盡管并非絕對的確定,但是,它所達到的蓋然性程度應足以使一個普通的理性人完成由基礎事實到推定事實之間的推理過程。作為一種程序機制,推定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即基礎事實一旦得以認定,在缺乏必要反證的前提下,可以直接認定推定事實;同時,關于推定事實的證明責任也會發生全部或部分的轉移,影響當事人訴訟權利和義務的分配。
為方便司法實務的操作,《刑法》第191條規定了五種應當定罪的行為方式:提供資金帳戶的;協助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的;通過轉帳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的;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的;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這表明,只要存在上述客觀行為,就可以推定行為主觀方面的“明知”的成立。《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進一步規定了認定“明知”的一般性原則:“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接觸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換、轉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進行認定”。還結合實踐中的具體個案情況列舉了六種推定“明知”的具體情形,即(1)知道他人從事犯罪活動,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2)沒有正當理由,通過非法途徑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3)沒有正當理由,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收購財物的;(4)沒有正當理由,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于市場的“手續費”的;(5)沒有正當理由,協助他人將巨額現金散存于多個銀行賬戶或者在不同銀行賬戶之間頻繁劃轉的;(6)協助近親屬或者其他關系密切的人轉換或者轉移與其職業或者財產狀況明顯不符的財物的。對于該六種情形,除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之外,均可以認定行為人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具有主觀“明知”。值得指出的是,《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均有規定,根據本公約確立的犯罪所需具備的明知、故意或目的等要素,可以根據客觀實際情況予以推斷(inferred)。這里所指的是運用間接證據或事實推定認定事實的情況*公約的原文是:Knowledge, intent or purpose required as an element of an offence...may be inferred from objective factual circumstances. 所使用的詞語是inferred,不是presumption(推定),兩者之間不可混淆。,與我國刑法及司法解釋中所確立的法律推定是不同的。
運用推定來證明行為人的“明知”具有一定的優勢。首先,推定能夠大致準確地認定案件事實,彌補證據裁判的不足。明知作為主觀心理狀態,屬于較難證明的事項,如果一味追求證據的全面證明,無謂地加重了辦案機關的負擔,甚至使訴訟陷入僵局。推定依托事物的常態聯系,能夠保證事實認定的大致準確性,同時還緩解了證明上的困難。其次,推定可以體現刑事政策與立法價值。刑法設定洗錢罪的政策意圖在于通過堵塞非法收益被清洗的途徑而使得“上游犯罪”的行為人不能享受到犯罪的巨額利潤,以減弱驅使其犯罪的原動力,最終達到減少“上游犯罪”的目的。我國當前對洗錢罪的懲處尚顯不足,在合理的范圍內加大打擊力度是今后的政策發展趨向,通過推定來證明洗錢罪的明知有助于體現這種政策趨向。同時,使用推定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舉證,這有助于控制舉證成本,增進訴訟效率。再次,推定可以推進訴訟程序,通過舉證責任的轉移來發掘案件真相。推定程序功能之一在于,一旦基礎事實確立,推定事實的部分舉證責任會轉移給辯方,這樣可以迫使辯方提供有力的反證來進行抗辯。這推動了訴訟過程的向前發展,實質上啟動了是否明知的真實性的調查程序。
相對于嚴格的證據裁判,推定是一種比較靈活的證明方式,在證明程度上也要略低一些。但值得說明的是,利用推定證明犯罪有其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點:一是推定與刑事訴訟一貫主張的控方負完全證明責任的原則相沖突;二是增加了被控方的證明負擔;三是推定的結論并不具有絕對的必然性*沈丙友.訴訟證明的困境與金融詐騙罪之重構[J].法學研究,2003,(3).。因此,利用推定來證明洗錢罪的“明知”應當遵循一定的規則:首先,應當貫徹證據裁判優先,推定證明輔助的原則。案件事實如果依證據能夠得到嚴格證明,則無需適用推定。只有在為避免舉證困難或舉證不能,并且符合推定各項要件的前提下,才予以適用。其次,必須保證基礎事實的可靠性與真實性。推定事實的證明來源于基礎事實的真實性,只有基礎事實是真實的,據以推出的推定事實才有可能是可靠的。再次,應當給予被告人反駁的機會。較之證據證明的事實,推定事實存在著更多的錯誤或虛假可能,如果不允許被告人提出反駁顯然是不公平的。推定的反駁一般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對基礎事實進行反駁,例如,被告人否認所指控的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行為,并提供反證。二是直接用證據對推定事實進行反駁,例如,被告人雖然承認存在著刑法及司法解釋所規定的行為,但實際上仍然屬于非明知的情況。
(三)被告人證明責任問題
有學者主張通過重新分配證明責任來化解證明洗錢罪“明知”的難題,即控方不承擔證明洗錢行為明知的責任,而由該行為人承擔自己“不明知”的證明責任*王樂龍.洗錢罪主觀方面之證明[J].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5).。國外立法亦有類似規定,如菲律賓《1995 年洗錢控制法》第 9 條就規定:政府不負責證明被告人知道有關錢財來源于非法行為,提供相反證明的責任由被告人承擔。但筆者認為,通過立法將“不明知”的證明責任分配給被告人并不妥當,根本的原因在于這種做法能會不適當地加強被告人的舉證負擔,與無罪推定原則相悖離。如前所述,我國刑法及司法解釋已經規定了若干推定明知的情形。作為一種特殊的證明方法,推定之中內在地包含著某種舉證責任的轉移機制*秦策.美國證據法上推定的學說與規則的發展[J].法學家,2004,(4).,這種機制在功能與效果上已實質性地迫使辯方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證明自己在主觀心理上的“不明知”。這意味著,在立法上進一步將證明責任分配給被告人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必要性。況且,推定的效力比較有限,它所轉移的只能是提供證據的行為責任,而證明被告人有罪的最終責任仍然由控方承擔,這樣對于無罪推定原則的侵蝕作用尚不算太強。而如果在立法中直接規定由被告人對自己主觀心態之“明知”存在與否承擔證明責任,這意味著被告人的證明能力成為罪與非罪的關鍵因素。被告人的舉證負擔會被放大,導致對無罪推定原則的實質性違反。
Intention and Clear Knowledge of Money Laundering Crime
XU Ke-jun, QIN Ce
(SchoolofLaw,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23,China)
Intention and clear knowledge of money laundering crime is disputed issu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direct intention shall be covered in the intention category of money laundering crime in perspectives of plain meaning, implemental effect and crime control. It is reasonable to take the nature of clear knowledge as the generalized seven upstream crimes and their gains. The criterion of clear knowledge shall combine the subjective theory and the objective theory. The certainty or possibility theory concerning the degree of clear knowledge is suitable to the needs of judicial practice. To prove the clear knowledge, methods combining strict proof and legal presumption are preferable. Some scholars argued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of shall be shifted and that it is the duty for the defendant to prove that he has no clear knowledge. But this opinions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should be dismissed.
money laundering crime; intention; clear knowledge; strict proof; presumption
2015-03-15
201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課題(GJ2013D12)、2013年江蘇省法學會項目(SFH2013B09)研究成果。
許克軍,男,南京師范大學“江蘇高校區域法治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人員,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訴訟法學;秦策,男,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刑事法學。
DF611
A
1672-769X(2015)04-0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