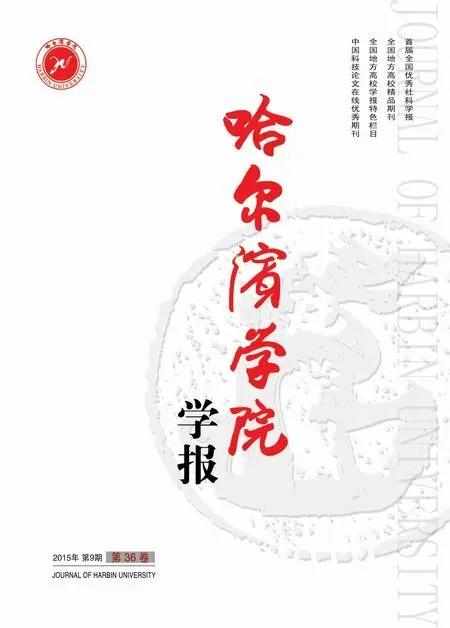王桐齡的日本觀研究
霍耀林
(井岡山大學外國語學院,江西吉安 3 43009)
民國時期的日本研究,我們耳熟能詳?shù)挠写骷咎铡⒅茏魅说热耍鴮ν跬g等知之甚少。王桐齡作為京師大學堂首批官費留學生,分別在20世紀10~30年代東渡日本留學考察,對日本有詳細的考察記錄,而這三個年代恰好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重要發(fā)展階段。王桐齡作為民國時期中國史學界舉足輕重的歷史學學者,通過對他及他的日本觀的研究,對全面透視民國時期中國的日本觀有著重要作用。
一、王桐齡及其赴日經(jīng)歷
王桐齡,我國現(xiàn)代著名歷史學家,字嶧山,號碧梧,1878年出生于河北省任丘縣趙北口村,清末考取秀才,于1900年考入直隸大學堂肄業(yè)。此時,由于義和團運動興起以及八國聯(lián)軍的入侵,北京陷入混亂。《辛丑條約》簽訂后,清政府迫于時變,于1902年1月下令停辦的京師大學堂復校。責成張百熙為管學大臣,負責擬定學堂章程,章程歷經(jīng)多次修改于當年8月奏定頒行,即《欽定學堂章程》,章程頒布實施后,京師大學堂也馬上著手招生開學事宜。經(jīng)過兩次招考,大學堂于1902年12月17日正式開學。
王桐齡通過兩次考試于1902年底進入京師大學堂師范館。據(jù)《速成師范館考選入學章程》,[1](P315)考選的方法分為八門:有修身倫理大義、教育學大義、中外史學、中外地理學、數(shù)學、物理及化學、英論、日本文論。考試十分之六以上者方為合格,英、日文及代數(shù)可從寬錄取。王桐齡能夠順利通過考試,表明此前他接受的教育已經(jīng)不僅僅是傳統(tǒng)的科舉教育,涉獵的新學應(yīng)該對他幫助不小。
1903年底,張百熙等向朝廷上奏,稱派遣學生出洋留學乃不可緩之事,而教育乃基礎(chǔ),應(yīng)當從培養(yǎng)教員入手,及早儲備大學堂教習。“現(xiàn)就速成科學生中選得余棨昌、曾儀進、張耀曾、杜福垣、王桐齡……陳治安等共三十一人,派往日本游學,定于年內(nèi)啟程。”[2](P20)能夠順利入選赴日游學隊伍,可見,王桐齡在京師大學堂一年的學習成績應(yīng)該是非常出色的。這批學生“志趣純正,于中學均有根柢,外國語言文字及各種普通科學亦能通曉。大凡置之莊岳,假以歲時,決其必有成就”。可見,在出國之前,都已經(jīng)學習了外語,對于各種普通科學也都已經(jīng)有所了解,為出國留學打下了很好的基礎(chǔ)。這批學生于1903年底順利出發(fā),張百熙親自送行,由教習章宗祥護送前往日本。
1904年,《東方雜志》刊登文章,對于這批留學日本的學生的分科情況做了介紹,王桐齡被分到哲學科,以教育學為主。王桐齡隨后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第一部文科,第一高等學校被視為是東京大學的預(yù)科,修學年限為三年,這里畢業(yè)的學生大部分進入東京大學,王桐齡也于1908年順利升入東京大學史學科,于1912年畢業(yè)。在東大留學期間,他曾受清政府之命,赴日本京都調(diào)查,其調(diào)查的結(jié)果提交給了留學生監(jiān)督處,并隨后以《日本東西兩京之比較》之名,在1910年的《中國地學雜志》和《教育雜志》上刊發(fā)。
1912年1月,孫中山領(lǐng)導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4月,臨時政府遷都北京,袁世凱任大總統(tǒng),蔡元培為總長的教育部也隨之北遷。7月,蔡元培辭職,由范源濂接替教育部總長職位。范源濂曾任清末京師大學堂東文分教習、正教習服部宇之吉的翻譯助教,王桐齡應(yīng)該在京師大學堂時便與之相識,他也正是由范源濂電召而回到北京,并入教育部,任參事。11月,兼任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課。范源濂于次年1月辭職,王桐齡也隨之辭教育部之職,專任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課。
五四以后,中國文化學界風潮不斷,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也新增了一批教授,校園內(nèi)各種思想非常活躍。1919年冬,校長陳寶泉被派赴歐洲考察教育,翌年歸國后調(diào)往教育部任職。在此情況下,1921年春,由陳寶泉推薦,經(jīng)教育部批準,王桐齡被再次派往日本留學,《東游雜感》正是記述了他這次赴日途中耳聞目見及到達日本后的感想。1922年7月,王桐齡從東京返回北京,結(jié)束了在日本東京大學一年零四個月的留學生活。這一年多,他收獲很大,除了《東游雜感》之外,另作成《中國歷代黨爭史》《女真興亡略史》《儒墨之異同》等著作。
回國后,王桐齡繼續(xù)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任教員,此時,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正在申請將師范學校改為師范大學。1923年7月,國立北京師范大學校正式成立,范源濂于11月1日出任第一任校長。王桐齡撰寫了《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過去十二年間之回顧》,回顧了他自入校以來的點點滴滴,表現(xiàn)出了對學校深厚的感情。
1934年9月,中國國內(nèi)紛爭不斷,王桐齡借機請假赴日考察,在兩年的考察中,他旅行足跡遍及日本南北,對日本人文、社會、教育、經(jīng)濟等方面都有很深刻的考察和體驗,并且和自己之前兩次在日經(jīng)驗進行對比,展示出日本社會各個方面的變遷史。他身在日本,不忘祖國,時常將兩國文化相比較,指出中日間文化上的差異。除此之外,他還于1935年5月21日至6月6日以教授的名義陪同北平師范大學畢業(yè)生團體參觀學校及教育機關(guān)(主要在東京市內(nèi)外);1936年4月8日至4月20日陪同河北同鄉(xiāng)康迪安參觀產(chǎn)業(yè)組合,分別為:群馬、新瀉、石川、福井、滋賀、三重、愛知、靜岡等。
1936年,《留東學報》第五號刊載有《本社社員王桐齡先生》簡介的文字,其中說道:“前后四次渡日,在日本生活前后約十四年、對日本社會狀況有明確的觀察……任師范大學教授之職。”由此可見,王桐齡在日本生活應(yīng)該有十四年之多。根據(jù)《東游雜感》的記述,1919年暑假,王桐齡曾應(yīng)邀參加廣島高等師范學校夏季地理講習會。由于史料原因,此次赴日詳細不明。
二、20世紀10年代的日本觀
1910年,王桐齡受清政府委派去日本京都視察。關(guān)于視察的目的尚不明確,但是他為留學生監(jiān)督處提交的考察報告書《日本東西兩京之比較》后來發(fā)表在《教育雜志》1910年第12期上。從他的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他的日本觀。
據(jù)文章載,這一時期,王桐齡一直居住在東京。1910年的京都視察也許是他第一次京都之行。他發(fā)現(xiàn)東京和京都完全不同,東京的建筑樣式都是洋式或者和洋折衷式,而京都則都是和式。京都的裁判所、小學、古寺都是古代建筑,由此而感嘆日本人善于守舊。東京的工廠機器皆由煤氣運轉(zhuǎn),而京都則是由水力運轉(zhuǎn)。東京屬文明開化之中心,男子著洋服者多,而京都則很少。東京的女性勞動者多,而京都的女性則從事藝妓者多。東京的勞動者勤而奢,京都的勞動者儉而惰。東京的電車往返便利,而京都的電車遲滯。凡此種種,皆可看出東京之氣象與京都不同,“東京處處振作長足捷步直追從西歐,而京都處處因循泄泄沓沓萎靡不振,猶有我國陳后主南唐李后主元順帝明神宗時代之遺風”。[3]
以上是王桐齡初次在日本留學時所寫,文章整體著眼于維新后東京之“新”與京都之“舊”,在他看來,東京活力四射,儼然已經(jīng)成為維新的中心,成為了日本文明開化的代表,成為了現(xiàn)代化的都市。
從該文章的前記來看,他受政府之命利用學校假期赴京都考察。由此可以推測,他所著眼的東京與京都的“新”“舊”有可能不是他自己的決定,也有可能是政府的命令。和他后期的旅行記相比較,這一時期的日本觀稍微有些主觀,但是在清末,作為中國人,這應(yīng)當是首次對日本東西兩京進行的比較。
三、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觀
1921年3月,王桐齡第二次赴日本留學,到翌年7月歸國之前,他在日本實際生活一年半左右。《東游雜感》是他第二次赴日時所寫的游記。據(jù)載,他是為《地學雜志》而寫,發(fā)表后,被國內(nèi)許多雜志轉(zhuǎn)載,興起一陣熱潮。1922年,《東游雜感》的單行本由北京文化學社出版,1928年再版時改為《日本視察記》。該書詳細記載了王桐齡第二次赴日的經(jīng)過,以及他在日本留學期間的各種經(jīng)歷。
1.20年代的朝鮮觀
王桐齡第二次赴日經(jīng)由朝鮮到達。此時距離朝鮮被日本合并已經(jīng)過去了十多年,朝鮮半島對他來說是怎樣的存在,他對于朝鮮人又有怎么樣的認識?以此為參照,他的日本觀或許會更加凸顯。在他的論述中,日本作為朝鮮半島的統(tǒng)治者,民族意氣奮發(fā),而朝鮮民族則相反,作為弱者,甚至每個朝鮮人身上都富于了弱者的氣質(zhì)。從這些看法不難看出他對日本人的感情。他并沒有對作為弱者的朝鮮民族表示同情,相反對于列強日本卻表示了贊賞。
鴨綠江是中國到達朝鮮半島的必經(jīng)之路。那時,已經(jīng)建橋,但日本人卻在橋兩邊設(shè)置警察署,檢查過往行人。對于中國人的檢查并不嚴格,但是朝鮮人則必須獲得警察署的出入許可,即使持有許可,也要進行盤問,如有任何出入,則沒收許可,本人也被拘留。
當時,朝鮮三一運動已經(jīng)過去兩年,但日本對于朝鮮半島的嚴格統(tǒng)治由此可見一斑。日本人滿面精明氣,朝鮮人滿面忠厚氣,日本民氣發(fā)揚,朝鮮民氣則相反。由此他認為征服之國與被征服之國,性格也不同。“朝鮮人富于猜疑心,陰險心,此亦弱者之恒有性也。……日本人好勞動,得錢即花。”[4](P26)王桐齡之所見或許為實,但他的日本認識卻明顯傾向日本,充滿了對弱者朝鮮的批判。他在東京時,經(jīng)過歌舞伎,看到了朝鮮藝者表演,他用劉禹錫的“凄涼蜀故伎,來舞魏宮前”慨嘆朝鮮人國土被日本侵占,卻無一點救國意識。
1921年5月,王桐齡遷居到東京黑川家,其中住有兩個中國人和三個朝鮮人。據(jù)他記述,中國留學生皆胸懷大志,按時上課,夜里也學習到很晚。而朝鮮人不論何時皆窩在家中,幾乎不出門,白天用朝鮮語大聲喧嘩,晚上則與日本情婦幽會,他用“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來批判朝鮮人不知亡國之恨。
2.日本民族特性
《東游雜感》也寫到了日本人的國民性,但是在文中,并沒有使用“國民性”一詞,而是用了“民族之特性”,由此也可得知他是從民族這一視角出發(fā)來探索日本人特性的。他認為日本民族是由通古斯族、馬來族、朝鮮族、漢民族等四大民族構(gòu)成,特別是漢民族給日本帶來了中國文化,對于教化日本人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最早和大和民族相融合。
實際上,日本民族特性、民族性、國民精神抑或是國民性等詞均是從日本傳來。甲午戰(zhàn)爭后,大批中國人先后渡日,派遣至日本的留學生也不斷增多,關(guān)于民族性的研究也漸漸增多。20世紀10年代后期,中國的日本民族性研究已經(jīng)受到極大的關(guān)注,先后有戴季陶、王桐齡、許藻镕、謝晉青等中國知識分子對日本的民族性進行了大量相關(guān)研究。王桐齡作為先行中的一人,其所起的作用當然不容忽視。
他首先認為民族性如同人的個性一樣存在,而造成民族性產(chǎn)生的原因也有兩點。一是遺傳;二是后天的環(huán)境教育。而日本本土由三個大島組成,所謂的島國根性當然也就會存在,但日本島又不同于其他的島嶼:首先,地理氣候不同;其次,日本自古受到中國儒家、道教和印度佛教影響;最后,日本人種由多數(shù)民族融合,其遺傳性也不同。由此,三個原因?qū)е氯毡久褡逍砸卜浅碗s,盡管如此,他還是從歷史的考察和實際體驗出發(fā),認為日本民族具有以下特性:
第一,模仿性與沒創(chuàng)造性;第二,服從性與妥協(xié)性;第三,敢死性與殘忍性;第四,易感性與浮薄性;第五,淡泊性與孤僻性;第六,細密性與褊小性;第七,愛美性與浪漫性;第八,沉默性與現(xiàn)實性。[4](P38-76)
他認為日本民族所具有的這八個特性都包含了正反兩個方面。因為世界萬物均有兩面性,這種兩面性或許恰好就是王桐齡日本民族性研究的特征。
3.日本家族制度
王桐齡認為家族的起源始于農(nóng)業(yè)時代的互助。他在承認進化論的同時,也接受了傳統(tǒng)的夫婦是人倫之始的觀念,認為家族制度是夫婦關(guān)系的開始。他認為日本的家族中也存在著男尊女卑,夫婦不平等現(xiàn)象。并認為日本的家庭主婦在家庭內(nèi)實際上以主婦資格,兼領(lǐng)廚子、裁縫、打雜、買辦、招待、會計、庶務(wù)及家庭教師等職。還認為日本的家族特色是離婚之容易。日本的風俗男尊女卑,家族的財產(chǎn)皆屬于男子,離婚后男性可再婚,而女性的再婚則受社會非難。王桐齡認為日本夫婦關(guān)系不論是法律還是社會道德都是片面的。
4.關(guān)于中國和日本
在《東游雜感》中,王桐齡痛感“日本以東亞盟主自命,竭全國上下之力,以調(diào)查我國國情,其所組織之社會團體:若東亞同文會,東亞協(xié)會,東亞學術(shù)研究會,斯文會,啟明會等,所處之雜志,若新支那,東洋,東洋學報,東亞研究,斯文,支那美術(shù),東洋哲學,東亞之光,東洋學藝雜志等;凡我國之道德,倫理,政治,法律,宗教,教育,歷史,地理,文學,美術(shù),實業(yè),軍備,交通,外交等諸要端,無不分門別類,詳細研究”。[4](P222)出版之單行本堆積如山,對于我國國情了如指掌。相反,中國無知之人太多,對于世界、東亞、日本則一無所知。自稱為聰明智慧之士或者以新人物自居者終日大聲疾呼,痛斥日本之無禮,每天都高喊排日,而日本國情如何,如何抵制則一無所知。
確實,甲午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后至20世紀20年代,中國向日本派遣數(shù)萬留學生,但日本國情究竟如何,對于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來說,仍然是個謎。王桐齡身在日本心系中國,他在強烈批判中國人的無知的同時,利用留學之機在學術(shù)研究的同時,親自調(diào)查日本,撰寫文章,介紹日本。從這個意義上說,王桐齡的論述特別有意義。他不以日本國情調(diào)查為目的,但是卻站在了日本調(diào)查的前沿。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對于祖國的關(guān)心。可惜的是,他的呼吁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四、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觀
1934年9月,王桐齡以考察之名赴日。此時,王桐齡已經(jīng)是國內(nèi)知名教授,并且也已是知天命之年,和前幾次渡日相比,這次赴日考察更加深入,所到區(qū)域以東京為中心,足跡也達日本關(guān)西、東北等地區(qū),所到之處均有游記詳細記錄。游記的最后一部分基本上都附有自己的旅行感受。通過這些,不但可以再現(xiàn)30年代日本的情景,也可以反映出王桐齡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所關(guān)注的焦點。
1.交通便利、乘務(wù)員熱情
王桐齡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游記中,幾乎都寫到了日本的交通工具。火車、電車、汽車的便利性、車掌的熱情、處處為乘客著想的理念以及日本人的守秩序都給王桐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高尾山游記》《日光游記》《東京附近觀櫻記》《環(huán)游伊豆半島記》《吉野觀梅記》《水戶觀梅記》等文章中認為日本的火車是做買賣,凡事為乘客著想,而中國的火車屬于辦公事,絕不為客人著想。旅游季節(jié),鐵道局也特意加開電車,迎送游人。而且車掌待客恭敬有禮,非中國車掌做夢所見。值得注意的是,他關(guān)注到“火車煤煙可以攪亂市內(nèi)空氣,東京人口稠密,空氣容易變壞,故開入東京市內(nèi)之火車照例在市外卸下火車頭,換上電車頭,再開入市內(nèi)”。[5]由此可見30年代東京的環(huán)境保護意識。日本旅客買票,上車皆按照先后順序,不爭先恐后;最大之車站,同時數(shù)處賣票,數(shù)路上車,秩序井然;趕不上第一次者,可以坐第二次、第三次;長途火車票,往返火車票可以通用兩日以上,三個月以上。絕不會讓乘客為難。旅客上火車是站上職員在入口處檢票,下火車時在出口處收票,車掌只管維持秩序,車上并不查票,不似中國車掌帶領(lǐng)許多武裝巡警,用偵緝隊捕盜形式,檢察官問案之口吻,來向旅客索票。
2.女性參與社會、戰(zhàn)爭時期可在后防轉(zhuǎn)用
王桐齡也注意到這一時期日本的汽車、輪船公司之賣票生、招待員皆女子,升降機之司機生亦女子,茶館、飯館、旅館之堂倌也用女子,日間勞動之農(nóng)人亦多女子,不似中國舊式女子,只會擦粉、帶花、裹腳,也不似新式女子,只會燙頭發(fā)、穿高跟鞋、聽戲、看電影、逛公園。[6]由此可見他對日本女性的認識,他認為日本社會中多有女子活動,既可為社會服務(wù),又可為家中掙錢,利人利己。事實還不僅如此,他認為汽車為戰(zhàn)爭時運輸利器之一,而日本國民中能司機者多,則戰(zhàn)爭是可以收轉(zhuǎn)運之效。而司機中,女司機也有不少,日本政府時時整軍經(jīng)武,作有備無患之預(yù)備。汽車之車掌概用女子,練習有素,一旦有戰(zhàn)事起,男子征赴前敵,此輩女子即可在后防司轉(zhuǎn)用。[7]在他看來,中國不論舊式還是新式女性,都非理想中的女性。而日本政府經(jīng)略之武備,則給當時中國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可惜這些都未引起中國人的足夠重視。
3.極力保護古跡、森林
日本人迷信神權(quán),高尾山上松杉成林,概系善男善女奉獻,有人保護,無人砍伐。不似中國人自私自利,全國多不毛之山,山上之樹皆被砍伐。“中國社會系無秩序之社會……社會全體腐敗,絕不能讓一家單獨生存,只好同歸于盡爾。”[8]“吾儕老百姓只宜安之苦命,不必生氣,且生氣亦無用也。”[8]日本人保護森林,滿山皆樹,蔥翠盎然。中國摧殘森林,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樹木斬伐殆盡。
4.儒教之國、禮儀之邦
王桐齡認為日本是儒教流行之國,重禮貌,崇謙讓,凡火車、電車上滿人時,有老人后上車,照例少壯者起而讓座,婦人背負小孩子上車,也常有人讓座,不似中國,先入者躺臥后入者罰站;也不似我國,老人上車,無人讓座。“日本人極忙,自政府至一半勞動者全國合成一有機體,向同一方向進行。……蓋公德心發(fā)達,凡事實事求是,負責任,守信用,不敷衍,不因循,不為一己個人私利,抹殺社會大家公益,不為口號,不為標語,不說虛話,不重宣傳,此誠為我國民所宜取法,然亦絕非我國民短期內(nèi)所能作到者也。”[9]
日本人能勤、能儉、能操作,男女老少皆能生產(chǎn),無游手好閑者。日本人無架子,小車站之站長時常持帚自掃站臺。不似中國站長官僚氣重,大小事皆須喚人,自己之手絕不會動也。日本人又潔癖,火車到終點,電車,自動車回至車庫時,即刻擦洗。女車掌忍苦耐勞之氣概實不亞于男子,不似中國女子弱不禁風。日本人善于宣傳,同時即為客人謀便利。“日本人好潔,故火車,電車,自動車內(nèi)俱較為整潔。此非車掌維持之力與查房掃除之功,蓋國民之習慣然也。日本人守秩序,凡多人聚集之地,絕不大聲說話。”[10]日本人“愛國心,愛社會心之強,守秩序,重公益心之勇,非自私自利之中國國民所能夢見”。日本為儒教國,其社會習慣,親親,貴貴,尊賢,尚齒,平素優(yōu)待老人。日本多山、多水而少平原,除去水災(zāi),旱災(zāi),蟲災(zāi),雹災(zāi)以外,尚加上震災(zāi),風災(zāi),冷災(zāi)得于天者獨薄,人人奮勉,男女皆克勤克儉,有嗜好者極少,故社會秩序得以維持,而且日有進步。[7]
5.反面的中國和中國人
與對日本及日本人的贊美之言相比,將王桐齡所描述的中國稱之為日本的反面似乎也不為過。他認為中國人所稱小鬼之日本,為歷史上之日本,時至今日,已經(jīng)完全不同。東京面積比北平大4倍,東京人口比北平多3倍。工業(yè)之發(fā)達,商業(yè)之繁盛,經(jīng)濟力之集中,亦壓倒上海、廣州、天津。建筑之莊嚴偉麗,道路之寬大整潔非中國可比,……有志者宜發(fā)奮求自強耳,勿得以一罵了之。不僅如此,他認為中國國民閉塞,對于外省,外府人往往含有歧視之意。而日本則開通,對于外國人與以平等待遇,不巴結(jié),亦不欺侮,與中國從前之排外,現(xiàn)在只媚外迥乎不同。“九一八為日本國難紀念日,各處開會演說,到處游行,健忘之我國國民,從前之口號標語,所謂打倒……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治外法權(quán)者,何以噤若仗馬寒蟬,屁都不敢放也。”[9]“九一八”之際,王桐齡所看到的日本到處都是開會演說、游行,本來是中國的國難紀念日,居然在日本成為了日本的國難紀念日,面對這諷刺性的局面,王桐齡表達了自己極大的憤慨,對中國表示了極大的失望。他認為中國人只顧自己,不顧國體公益,與此等國民談自治,多見其不能成功也。
以上可以看出王桐齡在20世紀前三個年代所關(guān)心的焦點雖然不同,許多地方甚至也有矛盾,但其中也不乏一貫性。通過對他的赴日經(jīng)歷及他的日本觀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展示出他在三個不同年代的日本觀的變化軌跡。透過王桐齡也可以看出,民國時期中國人的日本觀變遷過程。
從20世紀10年代的稍顯主觀性的日本觀向二、三十年代的歷史的、全面的日本觀發(fā)展。第一次在日期間,他利用假期去京都考察。在短暫的時間中就注意到東京與京都的“新”與“舊”,這些從建筑樣式等直觀的觀察來看也并非不可,但是在短暫的時間中觀到人的意識的“新”與“舊”恐非易事。而二、三十年代在日期間,他所關(guān)注的點不斷增加,從日本人到日本的國家、生活、環(huán)境意識等各方面均有涉及,而且對于日本人的民族特性也進行了歷史性的分析。
隨著在日本生活時間的增長,王桐齡對日本的感情也在不斷加深。從第一次京都旅行的稍微主觀的、簡短的、片面的論述到二、三十年代全面深入的論述;從單純的東京生活到后來他的足跡遍及日本各地,他對日本的批判逐漸減少,相反的對于中國和中國的批評卻不斷增加。此時正處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于正在處于大正民主期和二戰(zhàn)前夜的日本,想來并非沒有批判之處,想必這些都是王桐齡有心之選。
王桐齡的日本觀隨著時代的推移不斷深入。他在關(guān)注日本的同時,也和中國相比較,將目光也投向了遙遠的祖國。王桐齡的日本觀隨著時期不斷變化的同時,其作為中國人對祖國的關(guān)心則是始終如一的。他從日本的風土人情、風俗文化、社會構(gòu)造、民族特性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并將之介紹給中國。他強烈呼吁中國人應(yīng)該將注意力投向一海之隔的鄰國日本,并為中國人努力向日本學習而大聲疾呼。他比普通的中國人更加深入了解日本,在指出日本和日本人的優(yōu)點的同時,強烈批評中國及中國人的盲目自大。他盡可能的收集日本的相關(guān)資料,將同處東亞的日本介紹給中國;他以日本為參照,在否定中國人的劣性的同時,不惜大量筆墨反復強調(diào)日本人的優(yōu)點,為中國人忽視日本而大聲疾呼。
[1]潘懋元,劉海峰.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高等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陳學恂,田正平.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留學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3]王桐齡.日本東西兩京之比較[J].教育雜志,1910,(12).
[4]王桐齡.日本視察記[M].文化學社,1928(2).
[5]王桐齡.高尾山游記[J].文化與教育,1934,(39).
[6]王桐齡.日光游記[J].文化與教育,1934,(38).
[7]王桐齡.環(huán)游伊豆半島游記[J].文化與教育,(45).
[8]王桐齡.高尾山游記[J].文化與教育,1934,(39).
[9]王桐齡.游東通訊(三)[J].文化與教育,1934,(34).
[10]王桐齡.水戶觀梅記[J].留東學報,19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