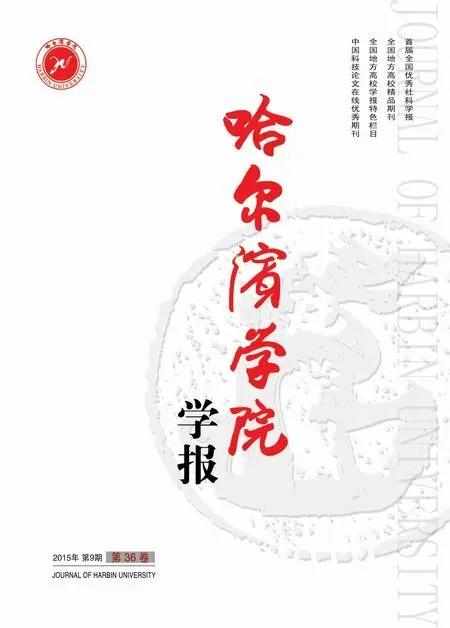對不可抗力作為環境侵權免責事由的探究
朱建芳
(福州大學法學院,福建福州 3 50108)
一、環境侵權中不可抗力的本質揭示
“不可抗力”是來源于《法國民法典》的一個法律概念,隨著時代的變遷,不可抗力的范圍也有所變化。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相關法律都將不可抗力界定為“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事實或社會現象”。同樣,在我國民事法律規范以及環境保護法規中也都將“不可抗力”界定為“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但是,不可抗力這一傳統的定義并不能將其所涵蓋的對象與范圍闡釋清楚,筆者認為還應探討如下問題:
其一,采用何種判斷標準來界定“不可抗力”內涵中“不能預見、不能避免與不能克服”才最能夠體現立法者的立法旨意。根據對不可抗力的判斷依據的不同,學界形成了主觀說、客觀說與折衷說三種觀點。主觀說僅從主觀角度來評判,認為應當以侵權行為人的預見能力與防御能力來判斷不可抗力是否能夠預見,若侵權行為人已經在主觀上盡了最大的注意義務,仍然不能防止損害結果的發生,那么已經發生的客觀事實就是不可抗力。客觀說不關注人的主觀性,它認為不可抗力中的不能預見與不能避免是一種與人的主觀意志無關的,客觀的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無法控制的客觀事實。但是,由于單個人的力量及其薄弱,絕大多數的自然現象與社會事件都不因個人意志而改變,因此“一般人無法抵御”等限定性術語在客觀說中被用以界定不可抗力,由此可見,客觀說并不單純的以自然現象和社會事件為要旨,將客觀現象與“一般人”“理性人”的防范風險能力相聯系,這就形成了折衷說。主觀說,以人的主觀狀態為衡量標準,個體差異極大會造成一千個人一千個標準的無標準狀態還會賦予法官超乎尋常的自由裁量權;而客觀說則完全忽視行為主體認知能力的差異性,用同一僵硬的客觀標準來量化責任,這也會導致一些專業技能或者經驗豐富的行為人借此逃避責任。所以,我們認為折衷說更為合理,折衷說對客觀現象的判斷原則是一般理性人的標準;而較高的特殊標準適用于例外情況。可見,折衷說既克服了主觀說的過度差異無標準又彌補了客觀說的僵硬性,不僅為法官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裁判規則,而且具有適度的靈活性保證了具體環境侵權案件結果的公平性。這與環境侵權中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的初衷相契合。
其二,傳統理論將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損害排除在“不能預見、不能避免與不能克服”的客體之外,其所定義的客體僅限于客觀現象本身。筆者認為,環境污染損害中不可抗力的客體不應局限于客觀現象本身,因為不可抗力不是自然學科上的概念,而是具有一定目的取向的動態的法律概念,其概念的界定必然關涉到人類生活,否則難以體現不可抗力在環境污染損害中保護環境受害者利益的目的性。如沙塵暴本身與法律無任何關系,只有當風沙彌漫湮沒村莊導致他人損害時,才有必要討論沙塵暴是否構成不可抗力。由此,不可抗力在實踐中作為法定抗辯事由的必要性之一就在于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現象關涉到人的有價值的行為,特別是由客觀現象造成的損害是關涉到侵權行為人的作為與不作為。可見,純粹的客觀事實并無法律價值,只有將客觀事實對人類造成損害的評價納入進來,不可抗力在環境侵權中作為免責事由才具有法律意義。
不可抗力作為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需要秉持其內涵中的三個必備要素。第一,“不能預見”,它包括了人類在現有的認知水平下根本無法預知到,也包括了人類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進行預見但是不能夠及時準確的預見不可抗力發生的時間和地點具體性、延續時間的長短以及影響范圍的深廣等。原則上“不能預見”是在現有技術水平基礎上,以一般或者同行業或類似行業的人的預見能力為標準來判斷;但如果有充分證據證明環境侵權行為人的預見能力高于一般人的預見能力,則應以行為人較高的預見能力為標準來判斷。第二,“不能避免”,是指侵權行為人在事后采取了合理的措施仍不能防止結果的發生。第三,“不能克服”,它是指損害結果的發生是人類能力所無法控制的,也就是在不可抗力發生之后,即使侵權行為人迅速采取了合理措施也無法阻止損害結果的發生和擴大。但是,一律要求不可抗力不能或缺上述三項要素任何之一,很容易出現結果不公的情形;因為在很多情形下即便環境侵權人能夠預見也采取了相應措施也沒能夠阻止損害結果的發生。因此,在環境侵權中,針對那些侵權人行為人能夠預見到但是無法防止結果發生的客觀情況也可認定為不可抗力。特別是,不可抗力在具體的案件中,需要用利益衡量規則來甄定不可抗力是否構成免責事由,才能體現這一法律概念的旨意。
二、環境侵權中不可抗力的原因分析
(一)無法預見性
無法預見性是指人們無法及時、準確預見客觀現象造成的損害結果。無法預見分為完全無法預見和無法準確預見。完全無法預見,如非洲的埃博拉熱帶病毒、廣州的登革熱、海嘯、地震等;無法準確預見,要結合個案中不可抗力構成要件進行綜合性的評定,比如在地震多發區,就應該在建造房屋時考慮到房屋的抗震等級,低級地震引發的房屋倒塌就不能完全用無法預見來對抗。由此可見,無法預見性還要求行為人即便是預見了也無法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損害的發生。這與刑法中“欲而不能”不歸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二)無法避免性
無法避免性是指環境侵權行為人已經對不可抗力進行了有效的預知,并且采取了相應合理的措施,但是損害結果并不因采取了合理措施而減少或不發生。有的學者采取較高的行為標準,認為無法避免是侵權行為人在盡了最大的努力、采取了一切可采取的措施之后仍然不能避免災難性的結果發生,這樣的標準顯然是對行為人過于嚴苛。雖說事實上很多事情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建造抗震等級極強的房屋和具有牢固防御功能的大壩可以對抗劇烈地震引起的房屋倒塌以及千年一遇的洪水引起的堤壩決堤,但是這樣高質量高標準的規定并不符合我國當代的國情,而且如此巨大的耗資也不是任何一個開發商都能承受的了。
(三)客觀事實性
客觀事實性是不可抗力區別于行為人行為的一個重要標志,不可抗力應是獨立于人的意志外的客觀現象。強調不可抗力的客觀事實性,就在于不可抗力發生的客觀事實切斷了行為人的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使得不可抗力成為免責事由的主張得以成立。
三、對不可抗力作為環境侵權責任免責事由的探究
將不可抗力有條件的作為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是我國環境保護相關法律的原則性規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引起,并經侵權行為人及時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環境污染侵害的發生,侵權行為人免于承擔責任”,在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以及《海洋污染防治法》中都有相類似的規定。從這些規定看,對不可抗力的范圍作了嚴格的限定,僅將其限定在“自然災害”中,而作為社會現象的戰爭、罷工以及重大政策調整等僅在《海洋環境保護法》中作了些許規定。環境侵權損害中的侵權行為人依據的不可抗力免責還必須苛以一定條件:一是除了不可抗力致害外不允許有其他因素參與,如若不符合“完全”由不可抗力所致,則是不能免責的;二是若環境侵權行為人欲尋求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就必須證明其在不可抗力發生之后及時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來防止損害結果的發生,否則,行為人是不能夠免責。實際上,法律也有將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的標準降低的例外規定,采用的是單個標準即只要是完全由于不可抗力導致的損害就能免責。最為典型的例外規定就體現在新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中,只要是由于不可抗力的發生導致水污染損害結果的發生,環境污染排放者就豁免了賠償責任,這里的例外規定就沒有要求侵權行為人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來防止結果的發生,把不可抗力的雙層標準降低為單個標準,標準的下放其作為免責事由的范圍自然也就擴大了。
在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法》將戰爭行為這一人為災害有條件的規定為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也就是完全是由戰爭的爆發而引起的,環境侵權行為人也及時采取了相應措施,但結果依舊不能夠防止戰爭行為對海洋環境造成的污染損害的,那么環境侵權行為人就豁免了環境污染侵權責任。美國的有關法律將戰爭行為規定為免責事由中的不可抗力,是可以豁免責任的一種意外事故。戰爭作為環境侵權中的免責事由,美國有關法律也對其進行了嚴格界定,即需要行為人及時采取合理措施人不能避免環境損害結果的產生才能夠免責。
對于不可抗力能否作為環境侵權免責事由的爭論從未間斷過,學界主要有三種學說,分別是肯定的觀點、否定的觀點以及折衷的觀點。否定說無一例外將不可抗力排除在環境侵權免責事由之外;折衷說是以一般人的注意義務為標準來判斷是否發生了不可抗力。持肯定觀點的學者注重不可抗力的客觀事實在侵權行為人與環境損害結果之間所起的作用。傳統上環境侵權的歸責原則是無過錯責任原則,換句話說,也就是侵權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與具體環境侵權案件中免責事由的依據無關,過錯與否已經排除在免責事由的原因之外。一般情形下,環境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總是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因果關系,但是不可抗力的發生就像一把利劍將兩者的的因果關系切斷了。其次,根據環境的外部不經濟性決定了有些環境侵權在社會生產生活中是必要的,如若對生產者苛以繁重的義務則不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筆者認為,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是需要具有一定條件的,一律不分具體情況將其作為免責事由有失偏頗,理由如下:
首先,不可抗力發生并造成損害結果時,雖然侵權行為人和受害方主觀上均無過錯,根據肯定說的觀點,侵權行為人免責了,但是受損害的一方的損失難道就無從救濟嗎?在某些發達國家,國家承擔著因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的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受害方的損失。在我國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環境侵權中受害方的損失完全由國家來承擔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若將受害方的補償置之不理,一味地尋求環境侵權人在不可抗力環境侵權案件中的責任豁免,而讓環境侵權受害人承擔環境保護侵權損害的后果,這不僅不符合現代民法追尋的“實質公平”的精神,也不符合現代侵權法中“日益保護受害人利益”的意旨。
其次,在適用高度危險責任歸責原則的環境侵權案件中,因發生不可抗力而造成環境污染侵害時,環境侵權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很難說是沒有因果關系。正如,擁有劇毒物質的企業在不可抗力發生時導致有毒物質的泄露而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損害,一方面不可否認不可抗力是造成環境損害結果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們就能夠無視污染企業中存在的劇毒物質與環境損害結果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嗎?顯然不能。因為沒有企業有毒物質的存在就沒有環境損害結果的發生,也就無所謂環境侵權。我國《民法通則》第123條規定:“從事、高壓、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等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如果能夠證明損害時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這里“高度危險作業”的規定就排除了“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通過分析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可知,某些高度危險環境侵權屬于危險責任,而危險責任的理念初衷苛以環境侵權行為人以更高的注意義務。雖然不可抗力的發生切斷了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的發生,并且也不能從字面上表明侵權行為人具有過錯的主觀狀態,但損害結果在實際層面又與侵權行為人的行為和物件有關聯,如若完全免除侵權行為人的責任,那么處于弱勢地位的受害方得不到合理的補償,這也就不符合環境侵權中危險責任原則的立法旨意。在“高度危險作業”中,環境侵權人通常已經投了保險,發生環境污染侵權事件時,由侵權行為人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是環境危險責任的應有之意,在這個層面上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就明顯不公平。既然在有些環境污染侵害中,排除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是具有合理性的,那么,能不能根據各種污染物質導致環境污染侵害只是一個量的積累的過程導致的,進而把環境污染侵害的事實進行一般化,將不可抗力排除在環境侵害的免責事由之外。
最后,若非得將“不可抗力”作為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對“不可抗力”苛以嚴格的限定解釋是應當并且是必要的。第一,是否發生了屬于免責事由的不可抗力,應該由具有相關資質的權威機構來認定。是否屬于環境侵權案件中的不可抗力需要具有一個標準,而這個標準就是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中的標準。第二,對不可抗力中“不能預見”的評判標準應當是一般理性人的標準,因為環境侵權行為人自身情況各不相同,若以當事人的預見能力為標準勢必會造成司法不公。再者,作為免責事由中不可抗力的“不能避免不能克服”,除了環境侵權人在不可抗力發生之后及時采取了合理的措施之外,還需環境侵權行為人在環境污染侵害之前也采取了合理的措施,而事前預防也是環境法所注重的一個理論趨向。第三,理論上,“及時”與“合理”本身就是一個外延相對模糊的詞,但是法律的可預測性要求相關法律法規對“及時采取合理措施”中“及時”與“合理”作一個比較明確的界定。
四、應對“不可抗力”的解釋加以嚴格限制
第一,對“不可避免及不能克服”這兩要素需嚴格把關。若當事人以不可抗力為免責事由,環境侵權人不僅需要對不可抗力進行了有效的預見,而且還需要在不可抗力發生之前以及不可抗力發生之后確實及時采取了相應措施來防止損害的的發生和擴大;第二,如果環境侵權人在事前對“不可避免不能克服”的情形有所預見,卻仍然為己私利鋌而走險從事經營活動,則“不可抗力”作為免責事由不能成立;第三,國家應對企業配備的先進的凈化設備和防護措施規定一個技術標準,以便采取措施進行預防,如未采取或未完全采取,視為過失,則不能免責或不完全免責,對于可預防而未預防所帶來的擴散的損害仍然需要承擔責任。
綜上,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不可抗力并不當然作為環境侵權的免責事由,其成立免責的條件是環境侵權行為人有證據證明:其在不可抗力發生之前以及不可抗力發生之后均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來防止環境污染損害結果的發生。如果行為人無法證明自己在事前以及事后采取了合理措施是不能夠免責的。對采取合理措施時間上的雙層限定以及對不可抗力作為環境侵權免責事由的嚴格解釋,無不體現法律解釋的慎重與可行性。這樣就會苛以環境侵權人較高的注意義務,這已經部分地反映了無過錯歸責適用不可抗力的精髓,適用不可抗力的大前提應當是行為人于主觀上的善意,之后才是個案的責任平衡,視不可抗力的影響因子而予以部分減責,而非不加區別地適用不可抗力以免責。
[1]劉凱湘,張海峽.論不可抗力[J].法學研究,2000,(6).
[2]李顯冬.侵權責任法經典案例釋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葉林.論不可抗力制度[J].北方法學,2007,(5).
[4]楊立新.侵權法論[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5]周友軍.地震中工作物致害的侵權法救濟[J].社會科學戰線,2008,(9).
[6]梁清.地震作為不可抗力免除民事責任的原因力規則適用[J].政治與法律,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