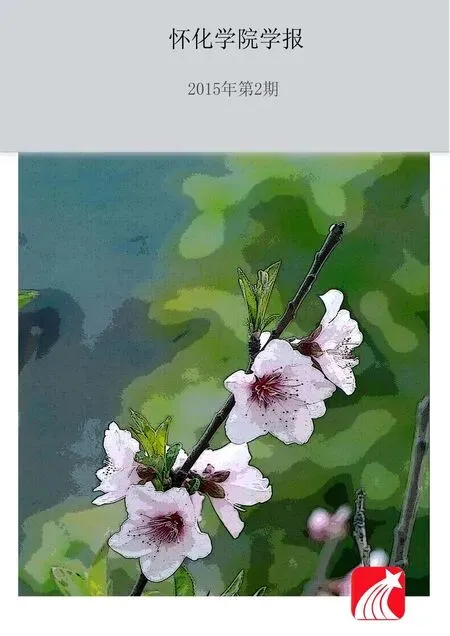飛散之傷與愛情靈藥
——《疾病解說者》中四則婚姻故事的“創傷理論”解讀
沈謝天
(上海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上海201306)
飛散之傷與愛情靈藥
——《疾病解說者》中四則婚姻故事的“創傷理論”解讀
沈謝天
(上海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上海201306)
《疾病解說者》是印裔美籍女作家裘帕·拉希莉斬獲普利策小說獎的處女作。本文從作品總共九則短篇故事中抽取四個婚姻故事構成故事環,在利用“飛散”的社會學、人口學意義闡明移民婚姻的病癥根源之后,采取“創傷理論”分析“斷裂性焦躁”在四個婚姻中的具體癥候,并通過解讀“飛散”在全球化語境下收獲的新意說明新“家園意識”的確立是移民婚姻關系和整體生活恢復健康的最佳方案之一。
裘帕·拉希莉;《疾病解說者》;飛散;創傷;斷裂性焦躁
憑借處女作《疾病解說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1999)贏得2000年普利策小說獎后,時年33歲的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1967-)在讀者圈和批評界同時贏得盛譽和關注。拉希莉出生于英國倫敦,成長于美國羅德島,父母是第一代孟加拉族印裔移民。青年時期的拉希莉在波士頓大學先后獲得英語、創作、比較文學三個碩士學位,以及文藝復興研究博士學位。對喬叟、彌爾頓等經典作家的熱愛讓她立志將所學與所好應用于自己的寫作[1]。譚恩美(Amy Tan,1952-)如是評價拉希莉的文風:“很有文采……文字流暢,敘述從容,難以相信作品出自一位年輕作家,而且是第一部作品。”[2]獲譚恩美盛贊的“作品”就是拉希莉的處女作——短篇小說集《疾病解說者》。
一、疾病發生:飛散的病原義
飛散的社會學、人口學定義是其本義,也是移民之癥的病原所在。飛散(diaspora)的詞源是希臘詞diaspeirein。前綴dia-指“散開”(apart or across),speirein指播種、散布(to sow,scatter)。古希臘人用“飛散”指當時的人口流動和殖民狀況,即某民族由于政治、經濟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離開故土,在異國他鄉重獲生機。在《舊約》(Deut.18:45)中再現時,“飛散”是指上帝有意讓猶太人散到世界各地。猶太人的飛散先后經歷耶路撒冷被毀和巴比倫王國鎮壓等歷史重挫,此詞因而富含“歷史受害”(victimhood)心態[4]115。現已成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的印度在近代史上的首波飛散潮也與“歷史受害”聯系密切。在英國殖民統治階段,大批印度契約工(indenture laborer)飛散至宗主國,從事經濟作物生產。艱苦的勞作和深重的剝削形成了印度飛散群體的集體創傷記憶(collective traumaticmemory)。獨立之后的印度掀起第二波飛散潮,為超過136個國家帶去了大約2000萬移民[5]。印度由此成為當今世界的移民輸出大國。良好的教育和穩定的工作讓這批移民中的大部分人獲得了目的地國家的公民身份,工作、生活環境大為改觀。印度民族的創傷記憶卻并未因此消弭,而是以新形態繼續深度影響飛散群體的物質和精神生活。
飛散與生俱來的“斷裂”效應在移民身上造成的不適(discomfiture)與焦躁是這種“新形態”的主要癥候。薩爾曼·拉什迪認為,移民受困于三重“斷裂”(triple disruption),“包括根的丟失、語言以及文化的錯位”[6]。“斷裂”對移民們的威迫是“持續、不明的”(constant,unidentifiable)[7]88,它讓移民們“騎跨于兩種文化之上,掉落于兩張板凳之間”[6],由此表現出形色各異的“斷裂性焦躁”。成為“我們這個世紀最重要的構成性(formative)經驗”[5]的“斷裂”,成為《疾病解說者》中婚姻疾患背后的發生機制。
在開篇故事《臨時停電》中,舒庫瑪爾(Shukumar)和秀芭(Shoba)原是一對幸福的二代印度裔移民夫妻。二人的孩子在生產過程中不幸夭亡,夫妻關系進入冰點。幾無交流的二人只能在為期5天、每天1小時的臨時停電中,因看不到彼此而勉強對話。夫妻關系的裂痕源于二者間深刻的文化斷裂。雖同為二代移民,“舒庫瑪爾待在印度的時間沒有秀芭多”①(12),因為水土不服,父母從不在舒庫瑪爾記事后帶其返回印度。成年后,舒庫瑪爾只是通過教科書了解印度史,“就好像它和其它課程一樣”(12)。秀芭則要“印度化”得多。“印式思維”告訴她“沒有孩子的婚姻被認為是平庸(banal)和不完整的(incomplete)”[8]102。想起丈夫因出差未能陪自己進產房的往事,又親見喪子之后的他一如常態,秀芭痛感夫妻在分享悲傷方面的不對稱。不信任(distrust)轉化為疏離(alienation),疏離擠走了往昔的愛戀。夫妻緣分宛若停電,成了臨時的事。
標題小說《疾病解說者》中的夫妻關系中埋藏有深重危機——達斯夫婦的二兒子鮑比(Bobby)是達斯太太(Mrs.Das,即Mina)與丈夫朋友通奸所生。夫妻倆與子女們一起初訪故國印度。純美式的穿著和口音讓導游卡帕西先生(Mr.Kapasi)將長著印度人面孔的達斯一家歸于一般外國游客一類。“‘哦,米娜(Mina)和我都出生在美國’,達斯先生帶著突如其來的自豪感宣示說。”(45)丈夫對夫妻二人美國公民地位的自豪宣示讓妻子米娜陷入“身份”危機。擁有美國“身份”的米娜卻在生活中嚴守印度規則。米娜和拉杰(Raj,即Mr.Das)因雙方父母是印裔移民社區中的老相識而認識、相戀。在雙方父母的撮合下,二人感情迅速升溫,還未完成大學學業的他們便匆匆成婚,隨即生下長子——羅尼(Ronny)。因傳統婚姻成為印式主婦的米娜過上了溫奶喂子的日子,沒有了事業、社交和愛好。面對在下班后只會耍逗孩子而對自己鮮有問津的拉杰,米娜只能借助與拉杰朋友的肉體交流求得一時的麻醉與解脫。
《森太太》中的標題人物因婚姻而受迫成為第一代移民,因此,相較米娜,森太太身負更深的文化“裂度”。隨森先生來到美國后,森太太為了打發操持家務之外的時間,接了一份看孩子的活兒。她對自己看護的白人孩子埃利奧特(Eliot)說:“這兒,在這個森先生帶我來的地方,我有時候因為太過安靜而睡不著。”(115)習慣了鄰里間熱鬧聚談的她,在寧謐的夜晚體嘗“斷裂”之苦。一句“森先生帶我來的”盡顯森太太的不甘與不愿,印證了飛散人群固有的“受害心理”。森太太絲毫沒有為丈夫跨越文化斷層的想法,她依然通過穿紗麗、點朱砂的方式與故土保持聯通。森太太在故事結尾處遭遇車禍,前來處理的交警看到她額頭的朱砂,便“認為森太太還弄傷了自己的頭皮”(134)。文化斷裂加厚了森氏夫妻間的隔膜,二者間的互不認同反過來又加深了裂度。惡性循環之下,婚姻幸福已無從談起。
二、疾病癥候:失調的婚姻
《疾病解說者》中的幾個家庭同在“斷裂”中徘徊、掙扎。他們同患重疾,受制于同一癥結,呈現出駁雜的癥候。心理學家將“斷裂環境”(disruptive environment)引發的癥候群稱作“斷裂性焦躁”(AbD),它可以導致患者在社交、職業,尤其是家庭領域內的功能障礙(dysfunction)[7]94。
《臨時停電》中的夫妻雙方因在受“印度化”的程度方面存在差異,妻子秀芭認為丈夫舒庫瑪爾不解喪子之痛,因此丟棄了對丈夫的信任。“不信任引發孤立(isolation),而孤立本身又會加劇信任的缺失。”[7]92陷入痛苦循環的夫妻二人讓“疏離”成為情感生活的唯一注腳。攻讀博士學位的舒庫瑪爾無心寫作論文,“他反而想起他和秀芭是如何在僅有3個臥室的居室里成為相互躲避方面的專家的,他們盡可能長時間地待在各自的房間內”(4)。停電周期到來之前,秀芭會在進臥房之前對丈夫說一天中唯一的話:“別太辛苦。”(8)出于“沒話找話”目的的“關心”將夫妻間本屬常態的溫存儀式化了,這形同官方聲明的“囑咐”同時讓婚姻沒有了溫度。持續5天的停電給了夫妻倆最后的“溝通”機會。身陷黑暗的夫妻倆因無需直面彼此而有了對話的可能。這一怪相背后的潛臺詞是夫妻雙方已無顏且無心面對彼此。“當房子黑下來以后,有些事情會發生。他們倆又可以談話了”(19)。秀芭在第五晚已恢復正常供電的情況下依舊關了燈,她向丈夫挑明前四晚對談的目的在于向丈夫提出分居。夫妻雙方在前四次夜談中的自爆其丑原來是妻子設計來增強彼此厭惡感的手段,為的是最后“自然地”提出分居要求,而并非是丈夫預計中的婚姻轉機。丈夫對對談意圖的美好解讀與妻子預設的目標截然對立,這說明“斷裂環境”造成的疏離根深蒂固,溝通與緩和只是“臨時”的,夫妻關系本身也是“臨時”的。
與《臨時停電》直達婚姻生活的內核不同,《森太太》通過刻畫主人公在生活困境中的具體行為來反映夫妻關系中的難破之局。丈夫對自己不聞不問,森太太只有操持家務的權力。她完全摸不到融入北美新生活的渠道,對故國難斷的情感粘連讓她在“斷裂”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每當森太太提到“家”,她“指的是印度,而不是她在里面切菜的那間公寓”(116)。去印度人開辦的魚市買魚集中體現了森太太對故國的眷戀。她坦言“那里的魚嘗起來一點兒也不像印度的魚”(123),即便如此,她也能在這些“至少是新鮮的”(123)魚身上尋找家鄉的味道。然而,丈夫的指令一下,森太太必須擺出了一副樂于融入美國社會的姿態——學駕駛。“森先生說只要我拿到駕照,一切都會好起來”(119)。對此深度懷疑的森太太學車是因為另有想法,她問埃利奧特:“我能一路開去加爾各答嗎?那要花多長時間,埃利奧特?走完1萬英里要多長時間,如果我每小時開50英里的話?”(119)眼見回歸故土無望,森太太用近似控訴的腔調聲明自己拒絕融入新國度的決心——“我恨它。我恨駕駛。我不會繼續了。”(131)像森太太這般不能認識和解讀“斷裂環境”的移民,“需要在混亂之中緊靠某些完全確定(absolute certainty)的東西”[7]92,這本應是丈夫們應當承負的責任。既然丈夫成不了自己在陌生國度里的歸宿,森太太自然難脫對故國的情感依附。從她在駕車闖禍之后提供給交警的唯一解釋——“森先生在大學里教數學”(134)可以看出,美國和丈夫都沒有邁進森太太的心田。對美國交規,她一無所知;丈夫對她而言,只有“教書匠”這一個冰冷的身份。
在《疾病解說者》中,同處“斷裂環境”的米娜和森太太一樣有傾吐欲,因為“受困于‘斷裂性焦躁’(AbD)的人會有言說和分享苦惱的強制性需求”[7]95。森太太對埃利奧特談印度,米娜則對導游卡帕西先生袒露隱私。導游只是卡帕西先生的兼差,他的主業是為當地的一位醫生充當古吉拉特語翻譯,即替醫生解說各位古吉拉特族病人的癥狀。聽到這里,原本漠然淡定的米娜突然興味盎然,對卡帕西先生的主業發出“真浪漫(romantic)”(50)、“真雅致(neat)”(51)的贊嘆。亟需傾吐惱人隱私的米娜只是將身為“疾病解說者”的卡帕西當成了可以聆聽、解說甚至解除她內疾的人。“你不理解么?八年來,我不能對任何人說這事兒,不能對朋友說,當然也不能對拉杰說。”(65)吃驚非小的卡帕西不能理解達斯太太怎會向陌生人訴說隱私。米娜于是接著解釋到:“我希望你可以讓我好受一點兒,說正確的話。推薦一些治療方法。”(65)她寄望于“疾病解說者”,卻從未反省自己的癥結究竟何在。米娜是一位飛散斷裂(diasporic disruption)的受害者,她身披美式外衣,內心卻依然被印式思維左右。“她的印度式內心將一起孤立事件轉化為了她必須背負一生的巨大包袱。”[8]104斷裂環境之下,包袱難除,痼疾難愈,米娜只有不斷表現傾吐欲這一種選擇,被生活逼入死角的她只是將卡帕西先生當作重復性傾訴行為中的一個對象。
水利工程施工進度控制,主要包括編制進度計劃、實施進度計劃、檢查與分析實際進度及進度實時調整四個方面內容,具體過程如圖1所示。
三、疾病治愈:靈藥的配制
“拉希莉強調,為了適應和調整,彌合夫妻間的情感和精神距離非常必要。”[9]32“適應和調整”是醫治婚姻頑疾的一方靈藥。“彌合夫妻間的情感和精神距離”暗示了靈藥配方的核心成分—愛情。愛情加快實現“適應和調整”,“適應和調整”又會反過來為愛情升溫。這一良性循環的發起者應是印度裔男性移民。關于這一點,拉希莉首先從反面給予了提示。
在《疾病解說者》中,導游卡帕西先生被米娜拉入了自己隱秘的內心世界。他的“在場”反襯出丈夫拉杰的“缺席”,米娜的行為同時縱容了自己的逃避和丈夫的漠視,因而根本無法實現“疾病”的“解說”。“在場”的卡帕西先生盡管英語流利,但他扎根印度本土,從未有過任何飛散經驗,因而與身為第二代移民的拉杰沒有可比性。他完全不能理解處于文化斷裂中的米娜會有怎樣的治愈需要。米娜也與卡帕西幫助過的那些文化背景單一的古吉拉特病人有著天壤之別。卡帕西先生因而只能憑單向度的印式思維將米娜對自己的“興趣”誤讀作某種引誘。當發現并非如此后,“卡帕西先生感覺受了羞辱,因為達斯太太(米娜)居然讓他解說她那常見、瑣碎的隱疾”(66)。被“常見”和“瑣碎”羞辱了的卡帕西用一句“達斯太太,您是真感覺痛苦呢,還是感到內疚?”粉碎了米娜的治病夢想,實現了報復,同時也暗示同屬飛散人群的丈夫才是唯一的治愈希望所在。
作了鋪墊的拉希莉終于在《第三塊大陸、最后的故土》中推出了移民丈夫中的正面典型。作者將對理想丈夫的所有期待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同時,“最后的故土”照應了其“完結篇”的地位,拉希莉借此安排暗示將對全書中的各種“疾病”給予最后的關懷與治療。
丈夫應當承擔起先行者和學習者的角色。率先實現“適應和調整”的丈夫才能幫助妻子盡快融入新環境,從而讓婚姻生活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1964年離開印度的“我”先供職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圖書館,在麻省理工學院圖書館謀得差使后,前往美國這片家鄉和英國之外的第三塊大陸。飛機上的“我”便通過閱讀《北美留學手冊》開始了解美國。在“基督教青年會”提供的簡陋寓所暫住期間,“我”不但借助《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繼續學習美國生活,還僅用一周時間適應了最典型的美國早餐—牛奶加麥片。“我”在租住克羅夫特太太房子的六周時間里完全實現了“美國化”。103歲的克羅夫特太太教會了“我”對包括“阿波羅登月”在內的所有美國大事說“了不起”(splendid)(180),讓“我”明白了準時、衣著得體和恪守男女關系準則對形成美國品格的重要性。老太太過世后,“我”坦言:“克羅夫特太太的去世是我在美國哀悼的第一起死亡,因為她本人是我欽羨的第一個生命。”(196)對凝縮了百年美國文化特質的克羅夫特太太頂禮膜拜表明“我”的美國化過程已經完結。一個美式的“我”做好了迎接印度妻子瑪拉(Mala)抵美的技術準備。
此外,移民丈夫還應調適對待妻子的基本態度。以責任感為第一要素的待妻之道才能為將至的愛情鋪路。“我”與瑪拉的婚姻由男方的兄嫂安排。未見妻面,“我”就清醒地認識到:“這是大家期待我實現的一份責任。”(181)責任感讓丈夫的技術準備產生實效。丈夫主動出擊幫助婚姻雙方跨越“斷裂環境”造就的情感天塹。一天,“我”目睹一位推著嬰兒車的印度裔女子被一只由白人婦女牽領的小狗襲擾。這一幕大大增強了“我”的責任感,“我”在內心深處表態:“照顧好瑪拉是我的責任,我要歡迎她,保護她。”(190)
技術與態度方面的準備決非全部,能否切實地幫助妻子和自己實現婚姻和移民生活的雙重和諧根本還在于丈夫在妻子抵美之后的行事水平。“我”攜帶妻子前往探視克羅夫特太太。老太太是“我”短時間實現美國化的助推者,這樣的會面在幫助瑪拉認識美國生活方面意義重大。在從頭到腳審看身著民族服飾的瑪拉之后,“克羅夫特太太帶著我所了解的那種等量的驚異與喜悅宣告說:‘她是一位完美的女士!’”(195)。克羅夫特太太的盛贊象征了美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相互認可、交匯融合的可能性,也堅定了夫妻二人一同尋找幸福的決心。“在克羅夫特太太家客廳的那個時刻就是我和瑪拉之間的距離開始縮短的時刻”(196)。之后,“我”在波士頓城內安排了各種節目讓夫妻倆度過了一段蜜月般的美妙時光,“我”還向瑪拉敘說各種往事,最終令自己與瑪拉在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都實現了融合。
技術和態度方面的雙向準備以及不折不扣的執行力讓移民丈夫們調制出治愈婚姻頑疾的靈藥。服下了靈藥的夫妻雙方將共同駛入幸福生活的快車道。移民夫妻在新生活中的新心態、新定位是治愈的真諦、“靈藥”療效的精髓。
四、幸福真諦:飛散的治愈義
拉希莉在《第三塊大陸》里用珠聯璧合的夫妻關系配制出治愈移民創傷的愛情靈藥,以此將整個故事環的立意由“疾病解說”層提升到了“疾病治療”層。移民在新國度、新生活中形成的新心態是評價治愈效果的唯一標準,而“家園”意識應成為新心態的內核。“家園”凝聚了人類共有的繁衍發展的生命力,表達了人類落地生根、代代相傳的生存愿望,這一點在“飛散”一詞意義的古今沿革中可見端倪。
“飛散”的希臘詞源diaspeirein意指花粉的飛散和種子的傳播生長。此意已孕有無限生機。后因被用來指涉猶太民族史上悲慘、恥辱的遷徙史,該詞一度被譯作“流散”。即便如此,不可阻擋的人類生存欲依然固守在“流散”的詞義中,因為猶太人在巴比倫蒙受羞辱的同時,還將自己的民族文化精髓,比如神話、傳說、歷史、法律等匯集為《圣經》的雛形。當代文化研究者們在繼承“飛散”古義中的生機之外,賦予了該詞更多主動作為的意義,讓它成為一個“靈活的能指”(a dynamic signifier)[4]113。“飛散”的當代意義中少了離鄉背井的凄涼感,多了一分“扎根新地,創造新生活”的豪邁志趣。飛散視角下的“家園”意蘊更加博大恢弘,它“不一定是落葉歸根的地方,也可以是生命旅程的一站”[4]113。“家園”不再是自己離開的那個地理存在,而是飛散者為了實現更高質量的生命而在意識、情感和文化身份上依屬的地方。“家園”既是一種意識,也是一種跨越國界、民族的胸襟和“在世界中發現家園”[4]116的志向。
“在世界中發現家園”是不可攔阻的全球化進程對“家園”的新解。新的“家園”意識要求飛散者以廣闊的胸襟、全面的準備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兌現“家園”的本質精神——落地生根的歸屬感和踏實心境。對于印度飛散者而言,其本土文化中的榕樹(the Banyan tree)意象揭示了該民族在發展新“家園”意識方面具備的潛能。“和榕樹——印度生活方式的傳統象征——一樣,他(指印度飛散者)將自己的根伸向好幾塊土壤,當別的土壤枯竭的時候,他可以從剩下的那一塊吸收養分。他根本不會無家可歸,因為他有好幾個家,這也是他在這個世界上感覺越來越自在的唯一原因。”[10]12“不會無家可歸”,因為印度飛散者有處處為家的胸襟;“越來越自在”,因為他們敢于更新自己的家園意識。對印度飛散者在“家園”意識方面的開拓性和包容性,拉希莉有著清楚的認識。這體現在她將個人第二部短篇小說集命名為《不適之地》(Accustomed Earth,2008)上。此名源于霍桑小說《紅字》的序言:“倘若世世代代都在同一處不再肥沃的土地上反復扎根,人性就會像這片土地上反復種植的馬鈴薯一般,難以繁茂茁壯。我的孩子們已誕生在他處,只要他們的命運仍在我的掌控之中,他們必將在不適之地扎根。”[1]“在不適之地扎根”是貫穿拉希莉整個創作歷程的基本旨趣,是她對包括印度移民在內的所有飛散者發自內心的呼告,也是移民之“疾患”獲得治愈的唯一判斷標準。
“家園”意識讓飛散者擺脫文化“斷裂”和“錯位”引發的“疾患”,成為扎根一地、放眼世界的“國際公民”。《第三塊大陸》中的“我”和妻子瑪拉就是仗憑愛情靈藥重建“精神家園”的成功例子。美國公民的身份和一個在哈佛大學讀書的優秀兒子是夫妻倆和新“家園”互相認同的外在體現。小說結尾處,拉希莉借“我”之口對受挫的兒子,也是對全體未脫疾困的飛散者說出了一段怡情勵志的話,激發他們生根新“家園”的斗志——“當他感到泄氣的時候,我告訴他,如果我可以在三塊大陸上生存下來,那么他也沒有什么克服不了的障礙。”(197 -198)
《疾病解說者》中的真正“解說者”其實是裘帕·拉希莉本人。從自己的移民生活經驗出發,拉希莉不僅“解說”了移民之癥的病根和癥候,還通過一個由四個婚姻故事組成的故事環提示讀者,在守望相助的夫妻關系中可以配得愛情靈藥,這靈藥能讓移民們脫離飛散斷裂造就的溝塹,重塑“家園”意識,在落地生根的踏實心態下盡享全球公民的幸福。作為終極治愈標準的新“家園”意識本質上是飛散者對新地文化的趨同(accommodation)或吸收(assimilation),其先決條件是飛散者“應該拋棄本土文化的某些現存特色”[5]70,而代價就是“他們會體驗到與故國(homeland)的疏離感”[5]70。因此,在作品中凸顯文化認同重要性的同時,拉希莉等當代飛散作家也應在跨民族的語境中更好地“解說”故土的歷史文化,形成“更豐富的語言”[11]118,才能契合飛散“反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12]的精神特質,從而不讓飛散在僵死的后殖民主義“一言堂”中枯萎與終止。
注釋:
①本文對小說文本的引用均譯自Lahiri,Jhumpa.Interpreter ofMaladies[M].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99.后文中僅標明頁碼。
[1]李靚.第三塊大陸下的潛文本[J].外國文學,2012(4):15-21.
[2]王麗亞.講故事的藝術:朱帕·拉西里及其《疾病講解員》[J].外國文學,2013(2):3-10.
[3]Brada-Williams,Noelle.Reading Jhumpa Lahiri's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as a Short Story Cycle[J].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S.,2004(3-4):451-464.
[4]趙一凡.西方文論關鍵詞[C].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5]Ramakrishna,N.&V.Ranjini.Immigrant Experience in Jhumpa Lahiri's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and The Namesake[J].Distribution of 1989-90 Beginning Postsecondary Students,2008(1):64-74.
[6]Kaur,Tejinder.Cultural Dilemmas and Displacements of Immigrants in JhumpaLahiri's The Namesake[J].The Journal of Indian writing in English,2004(2):34-44.
[7]Knafo,Danielle.Living with Terror,Working with Trauma:A Clinician's Handbook[M].Lanham:The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Inc.,2004.
[8]Gaur,Rashmi.Nine Sketches Interpreting Human Maladies:An Assessment of Jhumpa Lahiri's Stories;Jhumpa Lahiri,The Master Teller:A Critical Response to“Interpreter of Maladies”[M].New Delhi:Khosla Publishing House,2002.
[9]Rao,A.Rama Krishna&R.V.Jayanth Kasyap.A Critique of Immigrant Psyche:A Study of the Selected Works of BharatiMukherjee and Jhumpa Lahiri[J].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2008(1):25-33.
[10]Jain,Jasbir.Writers of the Indian Diaspora:Theory and Practice[M].New Delhi:Rawat Publications,1998.
[11]Benjamin,Walter.Illuminations[C].New York:Schocken,1969.
[12]Clifford,James.Diasporas[J].Cultural Anthropology,1994(9):35-47.
Diasporic Trauma and Love Panacea:Trauma Theory Inspired by Reading the Four Marriages in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SHEN Xie-ti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Ocean University,Shanghai201306)
Interpreter ofMaladies is the debut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by Jhumpa Lahiri,an Indian-American woman writer,which earned itswriter 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 in 2000.Selecting fourmarriage-related stories from all together nine stories in the collection to form a cycle,the paper first interrogates the sociologicaland demographical definition ofDiaspora so as to lay bare the etiology of ill immigrant marriages,then by virtue of Trauma theory,analyzes the specific symptoms in the fourmarriages known as Anxiety by Disruption(AbD),and in conclusion,elaborates the cultural implicature of Diaspora which newly captures in the contextof globalization so as to submit that the internalization of a new Home Consciousness in the immigrants should be one of the best prescriptions that can help an immigrant regain the once lost health in both his/hermarriage and entire life.
Jhumpa Lahiri;Interpreter ofMaladies;diaspora;trauma;anxiety by disruption
I106
A
1671-9743(2015)02-0077-05
2014-12-18
沈謝天,1980年生,男,江蘇海門人,講師,博士生,研究方向:美國文學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