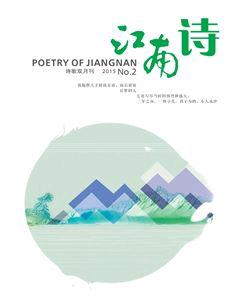“我說出”,“我看見”,“我抓住”
——詩人伊甸精神肖像
◎沈健 Shen Jian
“我說出”,“我看見”,“我抓住”
——詩人伊甸精神肖像
◎沈健 Shen Jian
一、千禧之年:“名字正式改為伊甸”
在公元新千禧之年深秋一個工作日,筆名伊甸完全覆蓋真名曹富強,標志著詩人伊甸的公民身份在法律維度上得到了國家確認。在詩集《黑暗中的河流》“伊甸創作年表”中,詩人鄭重記下一筆:
“2000年,嘉興教育學院與其他幾所學校合并為‘嘉興學院’,我在文學院仍然教寫作與當代文學。身份證和戶口本上的名字正式改為伊甸。”
上述輕描淺寫的“改”字,及其修飾狀語“正式”,我更愿意讀之為羅蘭·巴特“零度寫作”范式的一個詩句,中性、客觀,近乎新聞敘述,一行荒唐字,滿腔辛酸淚。自以筆名伊甸正式向漢語詩壇跋涉起算來,到世紀末整整18個年頭,詩人伊甸的靈魂蝸居在鍋爐工、大學生、教師曹富強的肉身內,經受了怎樣一種“我正歷盡滄桑”的憋屈與淚奔?
眾所周知,1949年后所構建起的身份認同與戶籍管理制度的鐵血運轉中,作為個體百姓骨肉欲裂的痛感,如果不是親歷其齒縫內部的殘酷絞動,并且擁有“說出”能力者,誰又能夠深切體會,并透徹“說出”?就曹富強而言,比如稿費單收款人“伊甸”,不是被查無此人退回原址,就是在派出所、街道辦、工作單位的大紅印章之間反復拉鋸;再如1988年女兒伊水出生后,戶口申報時由于與父母姓氏不一而遭遇的扯皮與口舌。諸如此類,無以窮盡,有形的桎梏與無形的刑枷,對以自由為天性的詩人來說意味著什么?當靈魂脫下了曹富強的外套,而與肉身伊甸融合之后,詩人的生存將有何種變化?這種變化對詩人的寫作會產生何種影響?這,需要我們以歷史的顯微鏡去細細究察。
在撰寫《吹進靈魂的風:伊甸論》一文時,我曾寫道:“從曹富強到伊甸的歷程,是一個俗世之人走向著名詩人的歷程,是曹富強在藝術之路上脫胎換骨的歷程”。現在看來,僅僅從藝術視角考察其間的嬗變信息,也許還只是方法論上的皮相之見。從曹富強進展到伊甸,實現詩人與公民身份的雙重確認,讓日趨衰弱的伊甸肉身收納詩人伊甸不斷強大的靈魂 ,也許不僅僅意味著方法論上的進化,其間潛藏著本體論日益成長壯大的蹤跡,是否值得我們深思?在詩集《黑暗的河流》中,伊甸非常自信,仿佛重新生長出觀照世界的器官,“我看見”,“我說出”,“我抓住”,一種理性主義主體在場的寫作姿態,低調而謙卑,閃耀在伊甸的文字叢林之中,“漸漸地逼近著冰山”。
二、“我看見”:“沉默著沉默著有人不沉默了”
《黑暗中的河流》共收209首小詩。“看”可以視之為詩人主體存在的關鍵動詞。直接以“看”來統領的組詩《看夜》有7首。另以“看見”、“我看見”、“對視”、“看不見”、“驀然回首”為題的詩大約20來首。以“看”作為關鍵詞義在文本內逐一搜索,與“看”、“目”、“視”、“瞧”等眼睛相關的詩涉及近百首。
詩人流沙河在《白魚解字》一書中,對“看”字作了非常有趣的解說,他用小楷寫道:“‘眼睛’二字形聲,已屬晚造。‘眼’即目,‘睛’指眼珠。甲骨文‘目’多為左眼。注意內眼角,瞼皮搭下,謂之蒙古皺折,為我東亞人之特征。篆文‘目’作偏旁,只好豎立,大不近情。篆文‘看’,左手搭棚遠方。‘見’比‘看’進一步,本人去見面”。這段文字抄列在此,作為“我看見”的肉身在場支撐,將詩人伊甸直接膠著在“低處”、“暗處”、“深處”、“弱處”、“別處”……而不是像羅·巴特所謂的那樣“寫作主體自身悄悄抽身走開,留下自己的‘符號—影子’來虛擬地與現實打交道。”
《黑暗中的河流》就是一首典型的以伊甸肉身在場介入存在的詩:
“我們看不見河流/但是它在流/我們聽不見水聲/但是它在流//我們愛它,我們給它們寫一千首贊美詩/但是它們在流/我們恨它/我們發誓忘記它/但是它們在流//我們遠遠逃開,一去不返/但是它們在流/我們尋找它,像尋找圣地一樣虔誠/但是它在流//我們氣急敗壞地吼叫,咒罵,威脅/但是它在流/我們取消它,刪除它,否認它的存在/但是它在流//黑暗愈來愈黑,愈來愈暗/但是它在流/天塌下來,堵塞了它以外的所有河流/但是它在流。”
“河流”,由數不勝數的水滴構成,是母性、生命、自由、愛的象征空筐。作為一個時間性總體意象,如若與《廣場》對讀,則會產生時空拆卸、打亂、重組、新建詩性時空的審美效應:
“那些鴿子白得/像是紙做的//那些灰塵嚴肅得/像是穿便衣的黃金//……那些石縫里殘存的血跡/像問號等待注釋//……//那些遺忘,那些冷漠/像是洪水漫過廣場……//那些石板下沉默的泥土/像冷峻的時間——一切的見證者。”
上述詩句有節選,將其中過于直白的句子去掉后也許更具發人深思之震蕩力量。“廣場”是塊狀固化了的“河流”,而“河流”則是流動液態的“廣場”;“廣場”既有總體性大一統的國家治理空間象征意涵,又粘附著開放、自由、多元心靈訴求空間的能指語義;“河流”也是如此,既有“流動、開放、汲納、激情”等活力磅礴的隱喻,也包羅著“死水、臭水、干涸、消失”的死亡修辭。當《廣場》與《黑暗中的河流》匯聚于“見證者”這一歷史性意象時,詩,對自由的政治訴求被巧妙轉換為審美的詩學訴求,顯性的社會命運修辭被隱性地轉換成歷史命運修辭,啟迪心智的力量沛然而起。
出生于1953年的伊甸事實上是與北島同代詩人。北島大他4歲,芒克大他3歲,舒婷大他1歲,而王小妮則小他2歲,顧城小3歲。作為外省詩人,伊甸因文化信息的落差而成為后“朦朧詩”一代詩人,幾十年的寫作所創寫的泛擬人化的抒情話語,已經為詩人贏得足夠的聲名。如果詩人僅僅停泊在時空意象宏大主旨下搖鏡頭式地羅列他的“看見”,那么,其同質化寫作的局限性將成為一種個人風格的陷井。正是在這樣語境下,詩人不斷地放低身段,“轉型”、“換血”,以“黑暗”參與人與受害人的雙重身份,沉入陡峭的“黑暗”,“學會在黑暗中看透黑暗。”
“血流著流著不見了
開槍的人松了一口氣
淚流著流著不見了
指揮殺人的人松了一口氣
呼喊聲響著響著不響了
所有的人松了一口氣
……沉默著沉默著有人不沉默了
地下的靈魂松了一口氣”
這首詩只有短短8行,題為《血流著流著不見了》,“不見”是“看見”的另一面,“看不見”的原因非常復雜,既有“看見”主體能力、勇氣、膽識問題,也有阻擾力量的邪惡、強大、無底線問題。詩通過日常口語的普泛平樸,寫出了深蘊歷史人心的時間偉力。
顯而易見,對瞬間的尖銳質疑,對永恒的本質追尋,呈現出的是一種典型主體在場品格,一種從理想主義出發,雜糅著陀斯妥耶夫以降的現代詩學品格:質疑而非盲從;個人而非群體;肉體而非物質;在批判中建構,而非在消解中毀棄。立基于此,伊甸完成了詩學自覺的轉身,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他變得節制、客觀、鎮靜了。詩人早期關注的公共事件與外部歷史主題,通過戲劇性場景內化為一個個“我看見”:
“它依然凸著白眼珠/死死地盯著我。我鼓起勇氣與它對視/‘看誰盯到最最后!’我一步一步/向它逼近,它的眼珠突然消失了/咄咄逼人的光芒——蜘蛛死了/它不是被我盯死的。一只早已死去的蜘蛛/用一粒掉在它頭上的白墻粉/審判了我,譴責了我,恐嚇了我”——《與一只蜘蛛對視》
“整整兩小時/我就這么坐著/盯著書桌上一張白紙/整整兩小時/我就這么盯著——/盯著——盯著——/書桌上一張白紙/整整兩小時/我不喝茶,不小便,不想女人/書桌上一張白紙/大腦中一張白紙/我盯著——盯著——盯著——/盯得兩張白紙/一點點滲出血來”——《白紙》
“起先以為是一種錯覺:看黑看得太久了/從黑中看出了白。像要反駁我似的/那白一點點亮起來,它仿佛在說/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看著天一點一點亮起來》
仔細察辯這一狀態,“我看見”中的“我”,已經接近物我合一主體間性的“我”,相當于莊子“吾喪吾”中的“吾”,通過渾茫與蒼涼、包容與厚重、沉郁與執著來觀照對象并蓄發詩意。《與一只蜘蛛對視》、《白紙》特別富有意趣,它們通過戲劇性的“緊張”描述,讓詩歌的話語主體直接外化為一種“行動”,讓獨幕劇式的事實在運行中凸現其自身發展的力量與意味,情感評判和價值傾向如水隨形深蘊其中。在這樣寫作中,伊甸變得那么謙卑、和藹、低姿態:
“我看見了未來——它多么模糊”(《羊城夜雨》);
又是那么的清醒、自律、博大:
“對龐大的劫難必須俯瞰/對細小的柔情必須仰視”(《帕斯捷爾納克》)。
他甚至渴望通過“慢”來抵達“快”,通過“少”來達成“多”:
“我喜歡看一些老人/慢悠悠地散步/慢下來,慢下來……甚至停住腳步/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下看看/我羨慕他們/有那么多好看的東西/我想,與其老了才慢下來/不如現在就慢下來/我就可以看到/更多好看的東西”——《看老人慢悠悠散步》
這是一種歷盡滄桑的絢爛,飽嘗憂患的成熟。詩,在這樣的語調與節奏中,不再是黃鐘大呂震蕩人心,而是個人化幽徑上的獨省沉思;美,不再是懸擱在隱喻天空中宏大的預設理念的傳達,而是潤物無聲的悄悄話,悄悄地修正人心,喚醒感性。
三、“我說出”:“我的喉嚨發不出一絲聲音”
“我說出”,是“我看見”的主體衍展,肉身在場支撐著我們對存在目擊之后的詰駁與拷問。在《說出》一詩中,詩人寫道:
“我想代一棵草說出它被歧視的痛苦/代一縷風說出它無家可歸的惶惑/代一片落葉說出它的衰老、它的疾病/代一粒泥土說出它的委屈——它竭盡全力奉獻/卻擺脫不了被踐踏的命運……我代它們說出了這一切/我就不用說自己的什么了”
存在于“被代表”境域內的卑微生命,其痛楚、委屈、惶惑、抑郁、焦慮,是那么地逼真而觸目,但他們“說出”的能力已喪失殆盡,更別說“說出”權利與通道的自主運用!在“我”代為“說出”的語鏈中,“草、風、雨、落葉、泥土、天空”……這些天地環宙間底層草根、形態各異的卑微生命,通過“伊甸”之唇“說出”他們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獲得了尊嚴的確認,重樹了權利的大纛。
我們知道,話語權是人權核心。“說出”,就是直擊真相,就是對存在的重新命名;“說出”就是“替”人“行道”,就是在“黑暗的河流”中,“點燃小小的火焰”,讓意義重返人心,照亮絕望;“說出”就是要像薩義德所定義的那樣,以“流亡者、邊緣人、業余者”角色,“對抗正統與教條”,“對權勢說真話”。
而這,需要能力,更需要勇氣。生活中的伊甸不善言辭,小說家草白在《那個叫伊甸的詩人》一文中,以女性的敏銳直覺看出,伊甸是一個“不擅于說話的人”,有一種“天性中的笨拙,倔強和隱約的孩子氣”。確乎如此,伊甸從來不曾滔滔不絕,永遠也不會繪聲繪色,普通話很“方言”,急起來還會結結巴巴。但是,伊甸在他最初的詩歌中卻輕松灑脫,陽光詼諧,找不出任何吐字木訥、話語澀滯的蛛絲馬跡。
“勞動者又從黎明出發了/歧路上已派烏鴉駐守/喜鵲的歌唱代替了知了的聒噪/指引一條沒有陷阱的道路/每一顆心都是一曲英雄交響樂/有著黃河般膚色的人群/命運注定了黃河般曲折的經歷/命運注定了奔向大海的使命”——《開桔花的土地》
這是1981年詩人參加浙江“桔花詩會”的一首詩片斷,節奏昂揚鏗鏘,激情浩蕩澎湃,意象富蘊豐盈,結構開闔自如,與后來詩人構思奇巧、意象鮮活的“生活流”詩歌一起,為詩壇留下了樂觀主流的精神肖像,至今仍令人不無贊嘆。
到了寫作《喧鬧的正午》的時候,伊甸明顯地有了“口吃”“失語”的癥候。
“蟬兒叫得多么起勁/像撒嬌的孩子任性地呼喚著親娘/少年的嚷嚷聲穿過魚網/像無賴的黑魚在水塘里竄來竄去//迎親的鑼鼓聲愈來愈近,男女老少涌向村口——仿佛整個世界都要成親//……如今喧鬧的是鋼鐵,是錢幣,是遺忘/這個衰老的正午,我的喉嚨發不出一絲聲音”
“正午”是一個詩人十分偏愛的明亮語象,約翰·多恩就曾寫過“正午,它的下一分鐘就是黑暗”,表達了對遼闊光明的“正午”稍縱即逝的眷戀與悸怖。是的,“正午”是一個開放性的語域,它指向充盈、豐富、旺盛、壯年、成熟、豐收、燦爛、廣闊、自在、無限、客觀……這樣一些強大的生命能指。然而美好得“仿佛整個世界都要成親”的“正午”,卻突然筆鋒一轉,墮入了“衰老”的“如今”,進而生發了毀滅性“失語”。顯然,這是一場個人柔軟內心的空前火災,也是一場人學文明的史無前例的海難,跌宕其間,人何以堪?置身其中,“我的喉嚨發不出一絲聲音”,“我的舌頭銹跡斑斑,而城市的舌頭——灰塵飛揚的馬路,卻整日絮聒不休”。究竟,這是一種悲催到何種程度的時代鏡像?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海子之死與女兒伊水的出生,以及身邊親朋文友生離死別的慘遇,驅使著伊甸對過往的天真進行觸及骨髓的反思與批判,大量的閱讀與對話讓他獲取了一種“一個人走進黑暗”的能力。“新千禧年”前后,伊甸“替”人“行道”“說出”的語速明顯慢了下來,語調也趨于低沉、凝重,像“赤裸著身子的河流,被北風卡住了喉嚨”(《羊群和老人》)?“用沉默說話,用唯一的黑色概括生命”(《樹殤》)。
在想象力的嚴寒與生命力的荒涼中,詩人孑然一身,“走進黑暗”,口中念念有詞:
“你必須有比這片廢墟更大的耐心/甚至,更多的傷口……”(《在廢墟上》)。
眼中所見耳中所聞:
“一場冷酷的雪面無表情地埋葬了/大地上所有的問候、祝福/嘆息、哭泣、申辯、控訴……”(《在沉默中》)。
究竟,這是怎樣一種囁嚅,一種哽咽,一種曼德斯塔姆式被“掐住喉嚨”的控告?究竟,這是一種怎樣一種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我怕我配不上我承受的苦難”,一種葉芝式的“向生活,向死亡,投上冷冷的一瞥”的沉默與悵惘?究竟,這又是一種怎樣的個人悲涼之景像?
這簡直就是一個Internet時代的哈姆雷特!一幕又一幕,目睹著他那靈肉吁請與良知索要,黑暗已不僅僅是某一肉體的黑暗,而是他所屬群體的良知黑暗;“衰老”也不僅僅是肉體的“衰老”,更是他所屬時代的“衰老”。
就這樣,詩人伊甸找到自己的方式,泅渡在“黑暗的河流”中,“讓我用沉默說出尊嚴”!他深深地相信,在光明和真相“開始說話的一天,我們終將全部變成啞巴”(《童年的冰》)
四、“我抓住”:“抓住自己的良心,直到抓出血來”
在知識分子身不由己地內嵌于利益網絡之中的今天,疏離體制,恪守尊嚴,“抓住詩歌這只扶手,在角落里站穩”(《角落》),除了伊甸,誰還能夠保有這樣的定力?
“你路過角落/或者一直呆在角落/你像一位秋收后田野里撿稻穗的老農/辛勤地撿拾這里的悲憫/和安詳”——《在角落里》
除了伊甸,誰能像塞弗爾特那樣失聲吞語:“讓我抓住……抓住自己的良心……直到抓出血來”(《詩人》)。除了伊甸,誰耐得住秋收后大地遼闊的寂寞,放棄物質的狂歡與欲望的消費,安享于悲天憫人的感恩、沉思與慈祥?
“抓住”是詩人連接世界的一個“榫扣”,也是世界聯接詩人的一個“鐵錨”。一方面,肉身必須“我抓住”,通過“抓住”確認肉身“在場”,向虛無、荒誕亮出反抗的“一朵小火焰”;另一方,世界必須“抓住”我,通過“抓住”顯現時間永恒、美的短暫和人的虛無。隨著年歲增長,一種衰老、病痛、死亡的恐懼幾乎“抓住”了詩人,身體每一個風吹草動的細小變動和身邊親朋的任何壞消息,給他脆弱身心施加的打擊都是致命的。而隨著智慧的成長,對命運、生死、殉道與意義的思考,詩人的靈魂越來越達觀,因樂天知命而“學會“彎成一個直角”,沉醉于“用一把鋤頭跟土地親密地交談。”(《在山村》)
2014年,伊甸正式退休,女兒結婚。在退休之前,他連續兩次被嘉興學院學生評為“心目中的好老師”。這個榮譽完全由學生投票產生。在9月份開學典禮上,他代表老師作新生發言:
“大學時代,我們要學好我們的專業,更要在精神和人格的層面上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優秀的人,一個有創造精神的人,一個正直、善良、獨立、理性、對人世間的美好事物充滿熱愛的人,一個有強烈責任感的人,一個能夠分辨是非善惡的人,一個對復雜的人生和社會有基本判斷力的人。”
發言在微信貼出后,點贊與跟帖者不計其數。絕大多數是伊甸歷年來的學生。是的,無論教書,還是寫詩,或者育女,抑或打牌、娛樂,伊甸都以一個徹底忘我、全心投入的“在場者”姿態“抓住”今天,“抓住”此刻,“抓住”詩人伊甸的“在場”創造,“抓住”公民伊甸的人生承擔。
即將出版的詩集《顫栗與祈禱》(或名《在天地之間》),是一本以“我在”我“抓住”為主題的詩集。全書190余首小詩,長短不一,全都由“在……”為題,昭示出一種對人生和世界充滿熱愛與負責的詩人絕不怯場、永不退場的“介入”:
“像一連串問號的瘋狂旋轉//你忘了哪是天,哪是地/你被裹挾,被綁架/你沒有一秒鐘的時間呼救/你的掙扎比不掙扎/還要糟糕//在監獄里可以咬牙等待/在黑夜里可以仰望星光/在漩渦里你無法控制自己的任何動作/你丟失了全部思想//它甚至不讓你流淚/不讓你流血/不讓你感受疼痛//它要你徹底暈眩/它要你百分之百忘記/你還是一個——人//你甚至不是一滴水/你什么也不是/你只是暈眩本身。”——《在漩渦里》
“漩渦”是流體力學作用于水的結果,也是風在大自然中高速旋轉的結果,具有豐盈的生命、自然、力量、心靈、場域的象征意義。這首《在漩渦里》,是詩人主體清醒地“抓住”自己清醒肉身的宣示。只要稍有松懈,就會“你什么也不是”,就會成為“暈眩本身”。而“漩渦”的存在價值恰恰是因為有“你”的角力,因為“抓住”了“你”而意義培增。“你”與“漩渦”之間緊張,是詩人與世界緊張的互文縮寫。
讀一讀這首《一個人走進黑暗》:
“一個人走進黑暗/走進這塊比世界還要大的巖石/他不是來尋找寶藏/他來看看這黑暗/摸摸這黑暗/他想發現它堅硬和柔軟的部分/黑暗最柔軟的部分/也像蜈蚣、蝎子和蛇/又狠毒又狡猾/但他走進了黑暗/他要看看這黑暗/摸摸這黑暗/他要用自己最堅硬的部分/去撞擊最黑暗的部分/只要撞出一點火星就夠了/只要有一點火星/……黑暗/就不會比世界還要大了”
這是一個令人窒息存在象征,“黑暗”大過整個世界,懷著“只要有一點火星,黑暗就不會比世界要大了”的癡妄與執著,“一個人走進黑暗”內部與深處,他要“看看”“摸摸”“撞擊”“黑暗”,他要“抓住”黑暗最堅硬的部分,他也讓“黑暗”“抓住”自己最堅硬的部分。就這樣,在與專制、暴力、虛無、死亡諸如此類“黑暗”的角力中,詩人蕩滌內心黑暗,完善自我人格,贖拯個我靈肉。
這個“走向黑暗的人”,就是詩人與公民合一的伊甸!
五、微詩微解:“吹進靈魂的風”
2014年9月5日微信“朋友圈”伊甸發了一段文字,伊甸的詩《吹進靈魂的風》,并配“沈健賞析”,查了《浙江先鋒詩人14家》一書,與這段文字有出入,這是我寫的嗎?恍兮惚兮。轉錄如下,結束本文:
“小時候,風能吹倒我的身體/但吹不進身體里面去//長大以后,風吹不倒我的身體/卻能一點點吹進身體里面//中年時,風吹進骨頭/有時我聽見骨頭里飛沙走石的聲音/風正一點點吹進我的靈魂/等到靈魂灌滿了風,我要在靈魂的壁上//戳一個洞,‘呼——’/把自己的身體吹得杳無蹤影”。
生命的歷程就是一個層層遞進的方程式,靈魂的成長與肉體的衰老正好成正比,骨子里飛沙走石、布滿自然與社會內容的時候,正是肉體搖搖欲墜之際。“吹進靈魂的風”,為理解“衰老的正午”提供了詮注與參考,是生命應對種種“火災”的審美細雨。
風是詩人們喜歡用的一個意象。“我麻痹的靈魂要向它飛去,好讓我呼吸故鄉的薰風”,葉賽寧渴望的是自由主義的愛情之風;“好風不吹兩遍,百思能煉純金……嶄新的思想在一切之廢墟之上誕生……啊!讓它們震顫吧,讓它們震顫吧!……讓它們的銳利將我們激勵!猶如那浸了松脂的弦索被樂師的指尖彈奏……”佩斯的風是比風還廣闊、比風還自由的創造之風;“主啊!是時候了,夏日曾經盛大。把你的陰影落在日規上,讓秋風刮過田野……”里爾克吁請與懇求的風中,飽含了對生命完滿之際靈魂無可皈依的孤獨和迷惘,滿載著超越自然秩序,抵達上帝神性的渴望。吹進伊甸身體里的風,既有政治秩序的壓抑,也有現實人生的宿命,更有俗世的人向超凡的神修煉進程中的無奈與悵惘,一種超越一切的自由之吁請,一種趨于永恒的懇求,一種對神性的憧憬。在靈魂的壁上戳一個洞,讓偉大的自然把自己回收茫茫宇宙中去,實乃生命化境:消失即誕生,瞬間即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