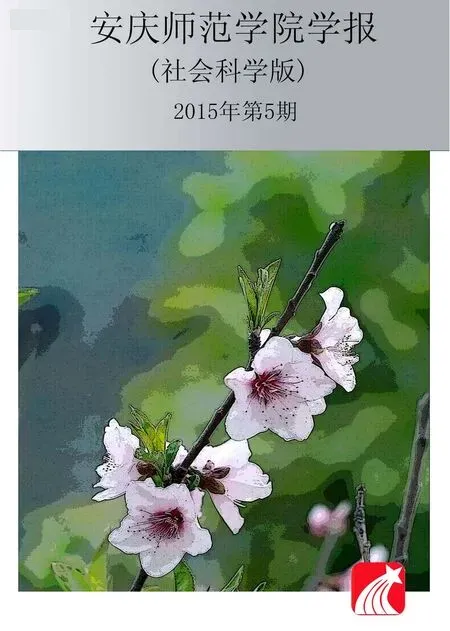《史記·范雎列傳》創作主旨新探
謝模楷,王春霞
(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 安徽 安慶 246133)
?
《史記·范雎列傳》創作主旨新探
謝模楷,王春霞
(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安徽安慶246133)
摘要:《史記·范雎蔡澤列傳》描寫范雎“復仇”的故事,多有可疑之處,其中存在有司馬遷加工創作的成分。“信威于強秦”是范雎傳記重點描述的內容,其傾向和態度明顯,集中體現了傳記的創作主旨,并寄托著作者對輝煌人生的向往。
關鍵詞:范雎;創作主旨;司馬遷;《史記》
范雎作為戰國時期的風云人物,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司馬遷作《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下文凡出自《史記》者,直接以篇名行文,不另說明;此外,為突出傳主及行文方便,下文以《范雎列傳》指代《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中記錄范雎的部分),生動記錄了范雎相秦十余年的事跡,其人物形象對后世產生很大的影響。歷來學者評論這篇傳記,多注重對范雎是非功過的分析,以及對范雎、蔡澤二人高下的比較,較少見到對傳記創作主旨的深入發掘,而洞悉《范雎列傳》的創作主旨,才是理解本篇傳記的關鍵所在。本文將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對這個問題展開論述,并由此進一步探析《范雎列傳》背后司馬遷的內心世界。
一
《范雎列傳》全文,由議論和敘述兩部分交錯組成。議論部分主要為三段說辭。第一段是范雎未見秦昭王之前的上書,他殷切希望見到秦王,以達到游說秦王的目的,“一語無效,請伏斧質”。秦昭王見書信后,“以傳車招范雎”,范雎第一步目標實現。第二段說辭范雎已面見秦王,主要表達的是“遠交近攻”的戰略思想,此段說辭后,昭王拜范雎為客卿,主治軍事。第三段說辭是在數年后,范雎已得到秦王信任,說辭的主要思想是“強公室,杜私門”,結果是宣太后被廢,“四貴”被逐,范雎為相。
這三段說辭,均采自《戰國策》原文,只有少數文字變動[1]。抽掉這些說辭,敘述部分就連在一起,構成一個完整而生動的故事:魏國人范雎,為魏中大夫須賈門客,隨須賈出使齊國,回國后遭須賈誣陷。丞相魏齊棒打范雎,致其肋折齒斷,然后扔范雎于廁中,令其遭受賓客便溺侮辱。范雎更名張祿逃到秦國,游說秦王成功,被任為秦相。須賈出使秦國,方知秦相張祿乃昔日范雎。范雎廷辱須賈,逼殺魏齊,終于報仇雪恨。
范雎向須賈復仇的故事,不見今本《戰國策》,取材出處不明。《韓非子·難言第三》載:“范雎折脅于魏。”[2]則范雎在魏國有“折脅”之事。范雎因何“折脅”?《韓非子》沒有說明,但隨后有議論:“此數十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暗惑之主而死。然則雖圣賢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君子難言也。”由此可以推斷,范雎在魏國游說“悖亂暗惑之主”不成,而導致“折脅”受辱。而這個“悖亂暗惑之主”顯然不可能是中大夫須賈,那么會不會就是魏王呢?當然這只是一種猜測,但除了《范雎列傳》外,并沒有其他任何證據證明,須賈就是令范雎“折脅”的仇人。
范雎逼殺魏齊則更可疑。據《范雎列傳》載,秦昭王為范雎報仇,約會平原君,迫使趙王殺魏齊。首先,秦昭王約平原君“會飲”事,僅見《范雎列傳》。秦王與平原君約會,乃是諸侯國的大事,按照司馬遷創作的“互現法”,《史記》相關篇章應該有記錄。如《孟嘗君列傳》載孟嘗君出使秦國,《田敬仲完世家》、《秦本紀》也有記載;《春申君列傳》載春申君出使秦國,《楚世家》有記載,《秦本紀》也有相應記錄;《平原君虞卿列傳》載平原君出使楚國,《趙世家》、《楚世家》有記載,《春申君列傳》也有相應記錄。而獨平原君出使秦國,僅見《范雎列傳》,連平原君本傳也無片語提及。其次,魏齊被迫自殺的時間,《范雎列傳》沒有明確說明,但侯嬴當時曾勸信陵君接納魏齊,信陵君猶豫不定,魏齊憤而自殺。據《魏公子列傳》載,侯嬴為魏國隱士,為信陵君所用,曾獻計信陵君竊符救趙,后在信陵君赴趙救邯鄲之圍時自殺。魏齊自殺時,侯嬴尚在,則魏齊自殺時間更在邯鄲解圍之前。但《戰國策·齊策三》及《平原君虞卿列傳》都明確記載邯鄲解圍之后,趙王與樓緩、虞卿等人有數次討論,則邯鄲解圍后虞卿尚在趙,虞卿協同魏齊去趙更在邯鄲解圍之后,那么《范雎列傳》記載魏齊自殺在邯鄲解圍之前就不可能。
王慎中曰:“此傳議論辭說,悉本《國策》;而敘事貫串,則太史公筆也。”[3]1范雎復仇的故事,司馬遷所本材料已無從查考,但其復仇對象多有可疑之處,且在《史記》中也多是孤證。由此我們推斷,范雎在魏國折脅受辱,這是存在的事實,它是司馬遷確立《范雎列傳》創作主旨的觸點,傳記的內容不能說全是杜撰,但肯定有司馬遷加工創作的成分,而整個故事的情節玄妙、褒貶抑揚,則更是太史公的手筆。
二
分析了《范雎列傳》文本撰寫的情況,下文再結合歷來學者對這篇傳記的評論,進一步剖析其創作主旨所在。根據韓兆綺所編著《〈史記〉箋證》[4]之注釋與集評,學者們評論《范雎列傳》,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第一,范雎的為人。如司馬光曰:“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扼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甥舅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哉!”[5]羅大經曰:“雎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6]50董份曰:“范雎脫死亡而取相,其恩仇快意,氣焰灼然。及蔡澤一說,即讓位棄印如振埃洗垢,不得顧藉,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3]23-24這些對范雎為人品格的評論,褒貶皆有。
第二,范雎的功過。如蘇轍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及雎任秦事,殺白起,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于內,并折于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于秦也。”[7]姚苧田曰:“范雎人品心術皆高,其有功于秦亦甚大,某于評點《國策》中每亟予之。”[8]這些對范雎的評論,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第三,范雎、蔡澤二人游說的難易。如黃震曰:“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雎攘之也難;范雎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攘之也易。”[9]鐘惺曰:“穰侯戚而相,方有功,持其所有也甚堅;雎疏而相,方負罪,求釋其所有也甚急。取所堅持者于戚而有功之人,與受所欲急釋者于疏而負罪之人,順逆固已不侔矣。”[10]認為范雎游說成功,要比蔡澤困難。
第四,范雎、蔡澤二人的高下。如楊維楨曰:“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為戒,使非澤乘其日昃之勢,吾固未知其死所……及澤代雎,不數月即幡然引去,又不俟逐雎者逐我,優游于秦,以封君令終。”[3]24羅大經曰:“雎必俟澤反復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雎遠甚。”[6]50對二人的高下比較,主要在于功成身退的智慧,認為蔡澤要比范雎高明。
以上評論,立足于范雎、蔡澤二人“策士”的身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點評,各有立場和道理,但沒有抓住《范雎列傳》的創作主旨。從傳記“太史公”曰,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馬遷對上述論題不以為然的態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強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司馬遷認為,范雎、蔡澤二人是當世的辯士,但他們的辯才并不就是他們取得成功的絕對條件,強大的秦國才是它們游說成功的根本原因;其他游說諸侯白首無功者,也并不一定是因為他們的辯才不如范雎、蔡澤,很可能是他們游說的諸侯國不如秦國強大。如《韓非子·五蠹》云:“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于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于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范雎、蔡澤二人的游說,無論孰難孰易,二人的智慧,無論孰高孰低,在《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中并沒有根本的意義,“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范雎、蔡澤以白衣而取卿相之位,在戰國風云變幻的時代大顯身手,影響當時,流傳后世,就值得司馬遷為他們作傳。至于范雎的功過是非、人品高低,在本篇傳記中也沒有根本的意義。
三
《太史公自序》:“能忍詬于魏齊,而信威于強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這是司馬遷為范雎作傳的寫作綱領。聯系太史公曰。“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這篇傳記的創作主旨就清晰地體現出來,即志士因困境而激發出不屈的奮斗,最后達到理想的人生境界。
具體到《范雎列傳》的創作,“忍詬于魏齊”是困境,三篇說辭是“奮斗”,“信威于強秦”就是理想的境界。“忍詬于魏齊”的描述著墨不多,主要是陳述事實;三篇說辭抄錄《戰國策》,并沒有多少傾向和觀點;“信威于強秦”才是傳記重點描述的內容,其傾向和態度明顯,描寫裊娜多姿,集中體現了《范雎列傳》的創作主旨。
首先,司馬遷極力描寫昭王對范雎的信任,這是范雎能夠“信威于強秦”的前提條件。《范雎列傳》里,昭王對范雎幾乎是無限度地信任,如昭王寫信約會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愿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于關。”這是以秦國的名義為范雎個人報私仇。又如范雎為報恩用鄭安平為將,結果鄭安平率兩萬人降趙,按秦法范雎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曰:‘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秦昭王對范雎的仁慈與寬厚,與我們想象中的“虎狼之秦”簡直有天壤之別。
其實真實的情況并非如此。據《戰國策·秦策三·應侯失韓之汝南》:“自是之后,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慮也。”顯示秦王對范雎并非無限度地信任;《戰國策·秦策三·秦攻邯鄲》記載,范雎推薦的太守王稽謀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請藥賜死”,顯示秦王并不對范雎特別寬厚。司馬遷作傳記,幾乎照錄了《戰國策》里所有關于范雎的材料,但這兩條卻沒有選取,明顯可見其創作傾向。另據《戰國策·秦策三·范雎曰臣居山東》載:“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桓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叔父。’”《范雎列傳》載秦王對平原君所說與此略同。結合上文分析,筆者疑心秦王約平原君“會飲”,很有可能是司馬遷根據《戰國策》的這段記載加工而成,目的就是為了突出秦昭王對范雎的寵信。
其次,司馬遷重點描寫范雎對須賈的復仇。有了秦昭王的絕對信任,范雎成為戰國歷史上的風云人物。其“信威”諸侯之處實多,如施行反間計,挑動趙國任用趙括為將,致使趙兵四十五萬被秦將白起大破、活埋。這是戰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絞殺戰,該是何等的威勢,而《范雎列傳》里只一筆帶過,卻把筆墨的重點放在對須賈的報仇之上。范雎報復須賈,情節曲折,頗具傳奇色彩,如一篇“絕妙小說”,對此評論者頗多。筆者認為,司馬遷撰寫范雎復仇,重點在于突出范雎之“高”與須賈之“卑”。比如須賈使秦,從秦相門下知道范雎就是張祿:
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于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賈不意君能自致青云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發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按《史記·穰侯列傳》載有須賈致書穰侯,止秦罷兵攻梁事,其忠心、才干皆有可觀,不似此處須賈“低到塵埃”的形象。兩篇對看,可知史公正是以須賈之“卑”襯托范雎之“高”,文中借須賈之口直接道出“不意君能自致青云之上”,更說明了這一點。吳見思評曰:“一邊面有驕色,一邊心如死灰,純是乞命之聲,寫來神妙。”[11]
值得注意的是,范雎復仇。還有一個插曲。須賈使秦,范雎微服私訪,須賈不知,見范雎“貧寒”,取其綈袍相贈,這個意外的舉動,使得須賈絕處逢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這個情節被后人津津樂道,它為范雎復仇增添了一抹溫情,但并不妨礙司馬遷突出范雎“信威”,反而顯得更加真實。茅坤曰:“專要摹寫雎之辱于魏齊,顯于秦,因以報復于魏,故于恩怨處盡力裊娜。”[3]13
四
司馬遷描寫個人在困境中激發不屈的奮斗,從而達到人生理想的境界,這也是《史記》表現的重要思想。如《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皆云:“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蘇秦列傳》:“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虞卿列傳》:“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后世云。”司馬遷身受“困厄”與他們相似,“憤書”的精神也與他們一脈相承,這是司馬遷創作《范雎列傳》的動機,也是傳記的創作主旨所在。需要討論的是,《范雎列傳》的這種創作主旨,寄托了司馬遷怎樣的情懷。
論者通常把《范雎列傳》的主旨歸為“復仇”,這是可以斟酌的。《史記》里的“復仇”,以伍子胥為最。伍子胥隱忍十九年,支撐他的唯一信念就是復仇,所以他違反天道人倫,對仇人掘墓鞭尸。范雎對仇人魏齊,只取其人頭,對須賈更是只有“跪門吃草”的懲罰。若是聯系范雎當年受到的冤屈和折磨,這樣的“復仇”無疑太輕,尤其是須賈,確有百種取死之由。若范雎的信念就是復仇,就不能有微服私訪,也不會有溫情的“綈袍戀戀”。所以,范雎的“復仇”只是表象,并不是傳記的創作主旨。
確切說來,司馬遷“憤書”是為了“償辱”。如《報任安書》:“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吾償前辱之責,雖被萬戮,豈有悔哉!”通篇我們讀到的不是司馬遷的“仇恨”,而是他深重的恥辱。深重的恥辱必須用百倍的成功才能補償,所以司馬遷向往那種“高山仰止”的杰出成就,他希望站在功名事業的輝煌頂峰來品味人生。司馬遷以身膺五百大運相期許,這該需要建立怎樣的功業才能與之相匹配!他的理想太高,人生的期望值太高,而理想與現實總是相距太遠。因此他的心靈經常處于不滿足狀態,他的情感世界也異常干渴,這種空曠寂寞的情感世界,常常投射到《史記》的創作中,使他的作品有了異乎尋常的表現和感染力。所以《范雎列傳》“復仇”表象的背后,是司馬遷對困厄中奮起的不屈斗志的稱贊,是對功成名就“信威”天下的向往。在此不妨把“高山仰止”四個字還給司馬遷,以表達后人對這位困境中奮發的偉人的由衷敬意。
范雎“復仇”的故事,出現一個“贈綈袍”的插曲,結合司馬遷本人的經歷及《史記》其他篇目來看,這也并不是偶然的。司馬遷當年身陷囹圄,多么渴望有人伸手拉他一把,但是“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報任安書》)。司馬遷在備受身體煎熬的同時,也飽嘗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所以他渴望人間的溫情,呼喚人與人之間的真情相待。如《管晏列傳》中集中描寫了這種真情,太史公曰:“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與這種呼喚人間真情相應的是,司馬遷批判了冷漠炎涼的世態人情,如《商君列傳》載商鞅欺騙公子卬而贏得戰爭,司馬遷曰:“卒受惡名于秦。”《樊酈滕灌列傳》載酈況騙呂祿交出兵權,使太尉周勃掌握了北軍,由此平定諸呂叛亂。司馬遷曰:“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由此可見,推崇人與人之間的真情相待,是司馬遷的一貫思想,這其中包含了司馬遷痛苦的人生體驗。所以在《范雎列傳》中,一場意外的“綈袍戀戀”,就輕易地化解了生死仇恨。它意在告訴人們,少一些冷漠,多一份溫情,說不定什么時候就能打開生活的大門;它引導人們用真情驅除心中的陰霾,過一種陽光的溫暖的生活。
參考文獻:
[1]何建章.《戰國策》注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0.
[2]韓非.韓非子[M]. 北京:中華書局,2007.
[3]凌稚隆.《史記》評林(第5冊)[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4]韓兆琦.《史記》箋證[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5]司馬光.資治通鑒(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7:53.
[6]羅大經.鶴林玉露[M].北京:中華書局,1983.
[7]曾棗莊,舒大剛.三蘇全書(第4冊)[Z]. 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362.
[8]姚苧田.史記菁華錄[M].北京:中華書局,2010:83
[9]黃震.黃氏日鈔[M]//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8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275.
[10]鐘惺.史懷[M]. 北京:中華書局,1985:110.
[11]吳見思.《史記》論文(第5冊)[M]. 上海:中華書局,1936:84.
責任編校:林奕鋒
中圖分類號:I20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730(2015)05-0043-04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5.011
作者簡介:謝模楷,男,湖北仙桃人,安慶師范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王春霞,女,安徽安慶人,安慶師范學院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4-11-23
網絡出版時間:2015-11-11 10:42網絡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1111.104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