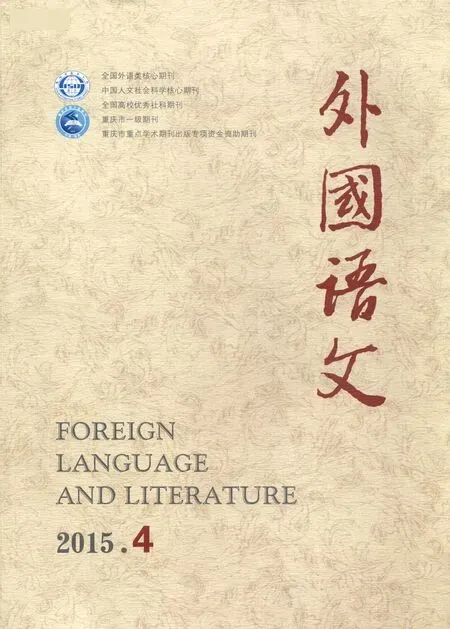個人記憶與歷史書寫——大江健三郎《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的歷史敘事探析
蘭立亮
(河南大學 外國語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1.引言
《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天皇制批判主題小說的代表作。小說講述了一個35歲的青年在醫院的精神病房中口述自己少年時代的經歷和創傷體驗,試圖通過重構記憶講述超國家主義者的父親一體化的故事。小說標題來自于父親和參加暴動的士兵前往地方城市時高唱的由德國作曲家巴赫創作的康塔塔。父親將原德語歌詞中的God(上帝)一詞替換為“天皇陛下”。在“天皇陛下,親自為我拭去淚水”這句歌詞的感召下,主人公長期陶醉于在父親指揮下戰斗至死的幻想中。從整體來看,小說結構基本由兩部分構成。一個是主人公在1970年這一時間點上講述的10歲那年與父親一起參加暴動的經歷以及自己中學時代所遭受的精神創傷,這一部分由身兼遺言代執行人和筆錄者雙重身份的妻子記錄下來,主人公將之稱作“不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同時代史”;另一部分就是對他講述現場進行描述的內容,這部分在文中用括號括了起來,主要是他的母親和妻子在記錄現場對他講述內容的質疑和修正。作家石川淳在小說發表當年的《朝日新聞》“文藝時評”欄目中指出,這部小說很好地展示了大江式文體巧妙的處理方式。“小說標題有點艱澀,但正文與外表相反,毋寧說是明晰的。小說結構看上去凌亂不堪,但是作者刻意為之,甚至為突出這一點不得不對時序進行改變。通過這一必然的改變,作品世界逐漸浮現出來。讀者如果不主動悄悄潛入這個七曲八拐的場所,估計很難看懂。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此展開的原本就不是故事,而是狀況。明確地說,在這部作品中,事物猶如達利筆下的時鐘那樣,軟如糖果,自由伸縮,讀者只要理解這一點就夠了。”(石川淳,1990:494)也就是說,和1961年發表的反天皇制小說《十七歲》、《政治少年之死》相比,這部小說更注重對時代狀況的描繪。在創作技巧上,它和以探索潛意識意象而聞名的超現實主義畫家達利的變形手法具有相似之處。在這部小說中,大江將小說形式實驗和反天皇制主題緊密結合,以荒誕現實主義手法來呈現歷史的沉重,隱喻地表現了他對天皇制問題、歷史問題的深刻思考。正是在這一點上,這部小說在大江健三郎的小說形式實驗中具有了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
2.父子關系的隱喻:從家庭到國家
《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的父親是一個過度肥胖、晚年患有膀胱癌的人物,他行動遲緩、笨拙,看上去有點滑稽。小說對父子關系描寫著筆不多,只描述了父母圍繞在中國打仗的哥哥做了逃兵一事而激烈爭吵時,父親寧愿哥哥被殺死也不愿他背叛國家的強硬態度。小說并未深入父親的內心世界,甚至沒有直接描述父親的容貌。他記憶中的只是小時候睡在倉房地板上仰視看到的父親“正挺直他高大的身軀,叉腿站在地板間里俯視自己”(大江健三郎,2012:78;以下此書的引文只標注頁碼)的形象,以及當時自己對父親微笑卻遭到他的無視而感覺“些許悲憤和羞恥”的復雜心理。在傳統文化觀念中,“父”是秩序和保守的象征,父親高大的身軀,猶如小說中用粗體字表示的“那個人”一樣,成為一個概念性的、特權化的代表性符號。“《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中,將天皇擦去戰爭結束時領導暴動的父親那因為戰敗而流下的悔恨的淚水這一意象置于中心,使‘父親—天皇’這一意象式的連帶關系具有諷刺意義地和戰前、戰中的‘家族國家觀’重合。”(柴田勝二,2012:58-59)也就是說,家庭中令人生畏、充滿威嚴的父親形象,和代表國家的天皇一樣成為一種權力的象征。主人公由于自己的微笑遭到“高大的”父親無視而感受到的“些許悲憤和羞恥”這一復雜的情感,體現了對父親尊敬甚至是崇拜的同時,在其潛意識中也存在著一種相反的、對父親充滿敵意的強烈情感。不難看出,這部小說沒有像傳統以父與子為主題的小說那樣糾結于父子兩代人具體的矛盾和生活細節,而是借助父子關系的形而上屬性,將矛頭直接指向了作為共同體之父的天皇,使“父與子”這一母題具有了強烈的象征性和隱喻性。
與對父親既崇拜又悲憤的復雜情感相應的,是主人公潛意識中殺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結:
母親,官方倉庫家唯一幸存下來的我們,必須結婚、生很多孩子。那些由于近親結婚而生下的畸形兒,我們要趁他們還是紫色嬰兒的時候,一個不留地勒死。為了子孫后代的繁衍,我們只能留下四肢健全的孩子。不僅如此,還必須要為殺死那個人作為補償。(42)
少年時代醉酒的他站在母親床邊說的這些話,體現了他潛意識中的弒父情結。在《圖騰與禁忌》中,弗洛伊德對原始部落的弒父行為進行了細致的精神分析。他認為,在原始部落中,男孩生命早期的戀母情結和父親崇拜是同時存在的。兒子們在俄狄浦斯情結的驅動下合力殺死一直崇拜的父親,并通過分食他的肉來加強對父親的認同感,試圖借此與父親一體化,將父親強大的力量納入己身。“精神分析學的研究已確定圖騰動物事實上即是一種父親影像的投射,因為它的特征里包含了圖騰被殘酷地屠殺,然后,接受哀悼。這種情感上的矛盾,也是現在存在于小孩子身上甚至可推廣到小孩長大后的那種父親情結。”(弗洛伊德,2005:151-152)或許可以說,在年幼的主人公的潛意識中,父親之死對他來說就是一種潛在性的期待,這也是母親所說的在槍戰發生前他意識到危險而離開父親乘坐的木車這一真相的深層原因。期待父親死去的這種罪惡感同時也強化了他對父親的回憶,成年后的他將死去的父親像圖騰那樣神圣化,相信自己和父親一樣得了癌癥,通過模仿父親晚年的行為試圖與其一體化,進而在與父親所代表的國體中尋找自我身份認同。
不難看出,小說主人公少年時代的成長經歷不僅僅是個人成長問題,還關系到在以同一化為基礎形成的男性共同體的身份建構問題。殺死父親成為共同體的一種儀式。小說中對戰敗不滿的青年將校推選父親做領袖,試圖從軍用機場奪取戰斗機,偽裝成美國飛機去轟炸皇宮的目的,就是通過殺死發布宣言的天皇,讓他“作為國體真正地復活,化作普通的菊花更加真實也更加神圣地開遍整個日本,開在每一個國民的身旁”(110)。就像原始社會被兒子們殺死的部落族長——父親成為圖騰被膜拜一樣,父親形象又成了共同體的精神支柱——天皇制思想的隱喻。猶如殺害圖騰一樣殺死宣布人間宣言的天皇,使天皇像圖騰那樣徹底成為日本人的精神結構。作為一部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作品,《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采用了俄狄浦斯這一原型,使小說在顯性的故事框架下具有一個與之發生內在聯系的隱性框架。然而,它不是殺父娶母的簡單翻版,而是賦予了這一原型新的時代內涵,使小說主題具有一種象征性,進而產生了審美意義的增值。
在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看來,“原型是一種經由成為意識以及被感知而被改變的無意識內容,從顯形于其間的個人意識中獲取其特質”(榮格,2011:7)。原型以象征和隱喻的方式反映出集體無意識的某些具體意象,它深深地鏤刻在人的心理結構之中。這部小說的弒父意象,可以說是大江憑借豐富的想象力和對原型的敏感,將集體無意識及其結構形式從一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存在的呈現。俄狄浦斯神話是弒父原型的同時也是替罪羊原型的代表,蘊含在這一原型之中的就是人類的暴力。從他的家族譜系來看,父系一族的家族史和日本近代以來的侵略史密切相關。他的祖父是參加過日俄戰爭的軍人,父親曾在滿洲間諜機關做民間右翼,他的家族歷史本身就是一部暴力史。主人公清醒地認識到,弒父行為只是一種幻想,自己根本無法擺脫暴力血脈的影響。對血緣的恐懼,使他不想讓悲劇在下一代身上發生,唯一能做的,猶如俄狄浦斯通過自我放逐給忒拜城帶來和平一樣,他幻想自己像晚年的父親那樣死于癌癥,讓妻子與外人通婚,讓兒子轉變國籍來達到對天皇制文化共同體的徹底逃離,使暴力血脈到自己為止徹底結束。在這個意義上,他幻想和父親一體化的行為自身就是一種自我懲罰,一個帶有悲劇色彩的替罪羊的形象就這樣被建構出來。
3.內部暴力的呈現與身份認同的焦慮
在這篇小說中,從他的弒父情結到父親駕駛飛機轟炸皇居的幻想,均是一種暴力的呈現。在主人公看來,所謂的國體即天皇制,就是共同體暴力的源泉。而對暴力的渴望存在于人的內部,這也是主人公試圖通過自殺、自殘而發現的內容。在受到高年級一群不良少年的欺負時,他用鐮刀割破自己的手掌,用流著鮮血的手掌向不良少年們的頭目發起了挑戰。
由于過度緊張而陷入沉思的他,用只有狗耳朵才能聽得見的聲音對那個人喊道:喝我的血吧!這是為你準備的!他感到此刻的自己仿佛正佩戴著刺刀,和從軍隊逃跑出來的家伙們一起再次來到仲夏時節地方城市護城河旁的街道上,等待時機向銀行發起攻擊。(29)
用粗體字表示的“那個人”,在此指的是要向他施暴的不良少年頭目,和后面指示父親、天皇的“那個人”一樣,是一種與暴力相關的特權化存在。在此,發生在兩個不同時間的事件——高中時代的他以自殘的形式對欺侮自己的不良少年的反抗與他陪伴父親為發動暴動前往銀行這一行為,在敘述的現在這一時點上重合。連接二者的,就是對暴力的渴望。這一設置極富象征意義,與對外在暴力的批判相比,他“以極快的速度傷害了自己的肉體,并對此感到強烈的喜悅”(29),這一感受體現了大江試圖通過對個人精神層面暴力因素的挖掘,將天皇制批判和戰后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問題聯系起來的匠心。
在收錄這部小說和帶有科幻色彩的《月男》兩個中篇的單行本《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1972)的前言《連接兩個中篇的作家筆記》中,大江明確指出了天皇制對日本人政治想象力的束縛:
我寫這兩個中篇小說的同時,將束縛我們想象力的枷鎖反過來作為自己的線索來接受,試圖盡可能地將自己從頭到腳用這一枷鎖捆綁結實。這些枷鎖來自于貫穿過去和將來的天皇制,從用這些多樣的枷鎖束縛自己開始來設法獲得自由的作家,將《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中帶著深色泳鏡、自稱癌癥患者的人物置于右側,將悔悟而加入環境保護運動的逃跑的宇航員置于左側,使他們成為將想象力推向前方的一組滑輪。(大江健三郎,1972:7-8)
可以說,大江深刻地認識到,作為一種精神結構,天皇制貫穿日本近代歷史,甚至會影響到未來。透過1970年三島由紀夫的自殺行為,大江發現了天皇制對日本人精神的束縛以及日本人精神層面的暴力傾向性,這促使他對天皇制的批判轉向了個人的精神層面。
在這部小說中,內心的暴力傾向性更直觀地體現在對主人公內心瘋狂的描繪上。大江對主人公身份認同的單一性、排他性一面從精神層面加以把握,并將之與三島的自殺聯系起來,嘗試探索戰后日本人精神層面的瘋狂問題。父親是信奉國體的民族主義者,母親則是在大逆事件中被殺害的反天皇人士的后代,他掙扎于父親代表的天皇制和母親代表的反天皇制的血脈之間,一直處于身份認同的焦慮之中,無論哪一方的血脈都使他精神受到了禁錮。他試圖讓妻子與自己的美國朋友通婚,讓孩子轉變成美國國籍,“期待通過這一方式使自己的血液完全從天皇以及xxx亡靈(xxx指外祖父——筆者注)的陰影下解放出來獲得自由”(116)。主人公這種對個體身份曖昧性存在的焦慮最終導致了他的精神異常,通過在幻想中對記憶的扭曲來獲得與父親所代表的天皇一體化。與天皇一體化本身,就是大江所謂的用天皇制枷鎖束縛自身,并由此出發獲取精神自由的嘗試。可以說,帶有瘋癲性格的敘述者的設置就是作家展開文學想象力的翅膀,通過塑造由于天皇制思想的束縛而精神異常的主人公,作者通過瘋狂探討現代人身份認同的創作動機。小林敏明指出,大江的天皇制批判與作家少年時代的國民學校的“愛國少年”教育以及戰后作家克服此情感的誠懇的自我解剖行為密切相關。“引起社會轟動的《政治少年之死》是促使作為作家的大江必須進行自我剖析的直接契機。之后大約過了十年,以三島事件為契機重新拾起這一主題的時候,對大江來說,‘天皇’已經清晰地作為他一生的課題牢牢地存在于其意識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得不說《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是開啟大江文學新紀元的重要作品。”(小林敏明,2008:117)在這部小說中,大江將身份認同問題作為生存危機呈現出來,體現了作家重建身份認同的焦慮以及以反諷的形式對當下束縛日本人政治想象力的天皇制的批判。
小說從整體上可以看作是第三人稱敘述者的心靈自傳。小說的“筆錄”部分采用的是第三人稱限制視角,夾在筆錄部分之間的括號里面的部分采用的是第三人稱外視角。小說形成了雙重結構和雙重視角,表現出來的內容是互相齟齬或對立的。筆錄部分看似冷靜的回憶式的敘述,展現的卻是非日常的狂想世界,是試圖與絕對權威一體化的精神想象。括號里的部分總是與記述的當下密切相關,是對記述部分的質疑和修正,巧妙地導入與主人公相對的富有象征性的母親的眼光,將自己的講述相對化,也進一步將主人公的記憶回溯至歷史的語境中加以檢驗。一條孝夫認為,小說的這一雙重結構設置是“為了避免作者從瘋狂的內部描寫的內容在瘋狂者的對白中結束的危險”(一條孝夫,1997:224)。的確,母親、妻子這一女性視角的導入,使小說文本因此具有了一種分裂性,形成了反諷的結構。在母親看來,主人公和父親都沒有認真考慮轟炸皇宮的事情,那些在他看來為了國體不惜犧牲的軍官,完全被降格為攜著錢財逃跑的猥瑣的騙子。而且,母親認為暴動事件本身就是一場鬧劇,甚至根據士兵全部死亡而軍官們不知去向這一點將其看作是一場有預謀的搶劫銀行的犯罪事件。母親的視角是站在反體制一方的另類視野。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滿洲國,那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那么愚蠢!而他一生中所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情,就是帶著這孩子去參加什么所謂的反抗運動!其實,那個人也明白那是一次注定失敗的偽反抗。(114)
母親指出,父親也并不是為國體殉死,而是被誤認為銀行強盜而遭射殺,父親只是這一事件的替罪羊,這毫不留情地打破了他對父親之死的幻想。大江通過對父子二人的幻想進行徹底否認和批判的母親這一女性的眼光,挖掘那種潛藏在共同體內部、帶有集體無意識性質的暴力。篠原茂指出,在這部小說中,與“同時代史”的口述者相對的筆錄者、與對天皇和父親崇拜的他相對的作為社會主義者女兒的母親分別作為批判者承擔著將現實相對化和滑稽化的作用。那種滑稽化也在多重的結構上成立。比如,“他”帶著崇敬之意將父親和天皇稱為“那個人”,母親帶著輕蔑的口氣稱丈夫為“那個人”(篠原茂,1973:293)。可以說,母親和妻子這一女性視角的導入摧毀了日本具有漫長歷史、以男性共同體為核心、以天皇制為代表的牢固的文化體系,從事物的另一面,也就是從女性文化的新視點來營造一個倫理道德觀念和對歷史認知方式的新的層面。在這個意義上,主人公的身份認同不僅僅是一個心理事件,而且和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大江通過主人公身份認同的建構不僅對現代日本人精神層面天皇制的束縛進行了深入探索,還自覺地從性別立場出發,通過對父親所代表的天皇制這一權威存在的滑稽化,以及對女性參與歷史建構的描述,來達到精神反思、文化反思的最終目的。
4.真實與虛構:搖擺的“同時代史”
從表面看,《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講述了主人公少年時期的一段人生經歷,但小說遠遠超出了傳統人生成長故事的范疇。在敘述者講述故事的同時,記錄講述內容的記述者即“遺言代執行人”通過打斷敘述的連續性不斷將敘述從過去拉回講述的現在,并通過對講述內容的質疑等手段試圖引導敘述者正視現實本身。敘述者甚至開誠布公地宣布講述內容的虛構性和幻想性:
事實上,你明知自己患有無法醫治的癌癥,而且即將進入昏睡狀態直至死亡,為什么還以堅定的口吻講述和實際病情完全矛盾的狀況呢?“遺言代執行人”接著說,將這些虛構的事實逐一置換成文字,這樣一來被記錄下來的謊言反而變成了事實。這讓我覺得不舒服,有種硬把自己的手指握在筆上進行記錄的感覺。“他”聽后立即反擊道,即使醫生命令你現在必須戳穿那家伙患有癌癥的謊言,也于事無補。因為,每當你說出這個謊言的時候,它就會變成一個實體漂浮在你的大腦周圍。而你,則只能呆然佇立在由這謊言形成的如蚊群般的星柱狀實體之中。(9)
在此,敘述者和記述者都認識到語言在歷史和記憶中的建構功能。由于謊言和事實都要通過語言來表述,是語言的建構物,即使是謊言,通過語言的修辭功能也會建構出新的現實來。同樣,記錄下來的“同時代史”的真實感,更多地來自于其形式上的“逼真性”,而非來自客觀真實。敘述者通過敘事動機的表白自我揭露文本虛構性的同時,也是向記述者或讀者暗示后面自己所要講述的父親在暴動中被射殺這一歷史記憶,并不是依賴于事件本身的真實性,而是依賴于能有效營造“逼真性”幻覺的敘述慣例。大江通過自揭虛構的元小說技巧,在將歷史作為個人記憶來講述的過程中凸顯了歷史的虛構性和敘述性,從一個側面暴露了所謂“客觀”、“真實”的歷史文本中所隱藏的敘事邏輯和意識形態。敘述者對敘事成規決定著一個被描述的事件是否真實這一點有著清醒的認識。小說中的“他”明確表示,之所以故意使用第三人稱進行講述,是“為了寫起來容易一點”(18)。也就是說,敘述者采用第三人稱的講述方式的目的是隱蔽自己的聲音,讓記述者或讀者覺得事件仿佛未沾染任何主觀色彩似地在自主呈現,更便于記述者記錄,這也是他認為歷史書寫應該具有的立場。不過,通過考察可以發現,敘述者呈現的這段歷史缺乏一個穩定的支撐,這個經歷和講述“同時代史”的人,或者說這個歷史主體,僅僅呈現了自己的一段記憶,但拒絕對事件和人物的真實性做出任何保證,甚至用元小說式的“侵入式敘述”公開聲明其虛構,根本無法為讀者提供一種穩定感和可靠感。敘述者“我也說不清是否真的經歷過自己所說的這些事情。說起來,是否和現實一致,這本身就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15)這一敘事態度,體現出他對所謂的能夠客觀描述的現實主義的批判。小說敘述者對語言建構功能的強調,解構了所謂的“歷史真實”。敘述者和記述者在此公開探討了真實與虛構(謊言)的關系,對書寫行為本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謊言和真實并不是截然相反的兩極,謊言可以通過言說、書寫行為而成為真實。在此,敘述者對自己講述的“同時代史”的態度本身呈現出濃厚的新歷史主義傾向。
敘述者認為,在自己被癌癥吞噬的瞬間,過去、現在和將來就凝聚在現在之中,自己就可以重新建構歷史。“那個時候,那個仲夏午后將會變成一個可以任意選擇的、如彈性織物般的‘現在’,出現在‘他’的面前。即將真正變成癌癥人的時候,‘他’就會愉快地進入這個‘現在’深邃、寬廣的內部。”(123)小說為暴動事件安排了三個可能的結局。第一個結局是母親指出的1946年8月16日在銀行前發生的街壘戰中,父親“左手將軍刀舉過頭頂,右手做出示意‘別開槍、別開槍’的動作。但實際上,他還沒來得及說一個字就被擊斃”(110)的情景。第二個結局是在街壘戰中,除“他”之外,所有人都被射殺,父親右手揮舞著軍刀,左手從木箱里伸出來,用手指著前方,告誡他要活下去,并牢記自己看到的情景(112)。第三個結局是他幻想的與父親(天皇)一體化的情景。背后中彈的他認為只有那個人(與天皇一體化的父親——筆者注)才能為自己擦拭臉上的鮮血還有淚水,在通往銀行入口處的石階上,向身中數槍、用一只手臂揮舞著軍刀的父親(天皇)爬去的情景(123)。關于暴動三個結局的設置進一步明確暴露了文本的虛構性,因為真實的現實是既定的、無法選擇的,而小說虛構則有無數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不同于那些沉迷于文字游戲,甚至脫離了歷史和現實的元小說,它將后現代表現手法與社會歷史語境結合起來,展現了記憶和歷史可以根據意識形態進行重塑這一本質,呈現出不同權力話語和意識形態對歷史的建構。
敘述者的“同時代史”對戰后日本政治、社會狀況的指涉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向了文本外的歷史和現實。他在敘述中特意強調“同時代史”的現實指涉性。在當下的他看來,戰爭是非正義的,“出現在這部‘同時代史’的那個人,假如沒有在戰敗后不久城市的巷戰中被殺死,那么理應接受遠東軍事法庭設立在峽谷森林中的臨時法庭的審訊。因此,從現在開始我所要講述的,是對聯合國、對我們這個顯然是戰犯幸存者操縱的國家政權所表達出的最為切實的關心。”(8)不難看出,他對戰爭的侵略本質還是有著正確的認識的,表現出對當下日本是被右翼操縱的國家這一政治現實的不滿。從這一點來看,猶如主人公同時具有民族主義者的父親和反天皇制后裔的母親兩種不同的血脈一樣,他的思想也具有兩義性,使其自身成了一個文化人類學中騙子、小丑式的人物。他帶著泳鏡,幻想自己得了癌癥,試圖與父親(天皇)一體化的努力看上去滑稽可笑,但正是通過這樣一種形式,達到了對禁錮現代日本人思想的天皇制的諷刺和批判。他所講述的“同時代史”,不僅僅是一種對過去時光的再現,它具有開放性,是對權威的、只有一種聲音的歷史的反抗。它不斷地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搖擺,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
5.結語
將《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置于反天皇制小說的譜系上可以看到,這部小說與早期的《十七歲》(1961)、《政治少年之死》(1961)相比,反天皇制這一主題具有很強的觀念性,從而使小說對三島的批判、對否定民主主義的天皇制的批判缺乏具體性。在這個意義上,黑古一夫毫不客氣地認為這部作品“未必是成功之作”(黑古一夫,1998:39)。不過,大江之后兩部反天皇制巨作《同時代的游戲》(1979)、《水死》(2009)分別在對歷史的重構和“殺王”等民俗學要素的運用上繼承了這部小說的風格,特別是《水死》在小說形式上所呈現出表層結構與深層神話原型的結合、“殺王”意象所體現的與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對決這一主題就是這部小說反天皇制主題的延續和深化。小說通過個人言說的記憶來重構歷史的手法表現天皇制枷鎖對現代日本人精神禁錮的同時,呈現出對宏大歷史質疑的新歷史主義傾向,體現了大江省察歷史與現實的理性精神和解剖自我靈魂的自省精神,展現了作家在天皇崇拜和戰后民主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時代精神之間進行文化反思的積極姿態。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主題表達還是形式實驗,這部小說在大江文學中均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
[1]柴田勝二.民主主義の逆説——大江健三郎と三島由紀夫の戦後[M]//松本徹.三島由紀夫研究12三島由紀夫と同時代作家.東京:鼎書房,2012.
[2]大江健三郎.二つの中篇をむすぶ作家のノート[M]//大江健三郎.みずから我が涙をぬぐいたまう日.東京:講談社,1972.
[3]大江健三郎.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M].姜楠,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4]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M].文良、文化,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5]黑古一夫.天皇制——デモクラット大江健三郎の決意[G]//島村輝.日本文學研究論文集成45大江健三郎.東京:若草書房,1998.
[6]卡爾·古斯塔夫·榮格.原型與集體無意識[M].徐德林,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
[7]石川淳.石川淳全集(第 15巻)[M].東京:筑摩書房,1990.
[8]小林敏明.想像される<父>とその想像的殺害——大江健三郎『みずから我が涙をぬぐいたまう日』を再読する[J].新潮,2008(8):176 -191.
[9]篠原茂.大江健三郎論[M].東京:東邦出版社,1973.
[10]一條孝夫.大江健三郎——その文學世界と背景[M].大阪:和泉書院,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