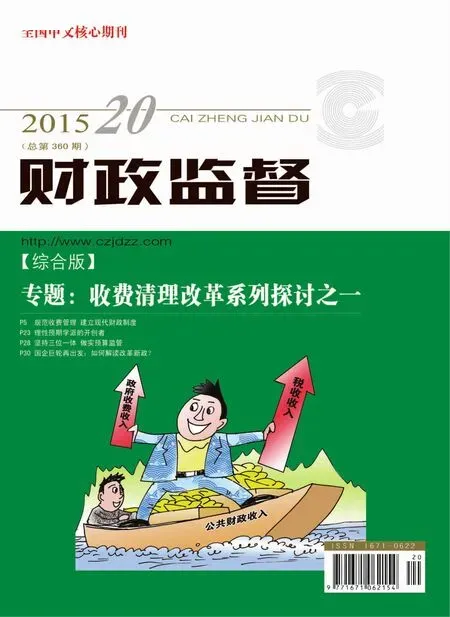自序
自序
寫詩這么多年,談及出詩集,依然心有躊躇。詩歌是個繞彎子的功夫活,如果只是為了附庸風雅,簡單哼哼幾句,弄一個書號,請一個名人作序,是不能自詡為詩集的。
我與詩歌的緣分可以追溯到高中時代。那時候不善言辭,課外時間都用來讀詩寫詩,時不時在學校油印的小報上發表小詩。雖然沒有稿費,但能贏得老師和同學贊許的目光,心里也美滋滋的。畢業前語文老師對我說:“你的詩寫得很不錯,將來走到哪里都要堅持。”高中畢業后,下鄉當知青,當民辦教師,回城后考上大學,做過企業會計、雜志編輯、公務員。一路走來,面對人生種種,我始終懷揣這份堅持。
其間,我寫了幾年散文,詩歌擱置了一些年頭。大約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仿佛被一個亢奮的時代激活,內心有一種無法言說的萌動,于是朝花夕拾,又開始寫詩。這些年,我常常與詩友調侃,活到這個年紀,人變懶惰了,世界也變小了,不愿意多說話,只想借助詩歌這一隱含寓意和秘密的表達形式,用最短的字句抒發最真實的愛恨情仇。
散文與詩歌是不同的表達文體。在我看來,散文好比河上泛舟,可以盡情盡興,靈動釋放。而詩歌好比地下掘井,宜適度收斂,有所節制,把更多空間和想象留給讀者。好詩的最高境界是“留白”,無需過度地修飾和雕琢,無需華麗的辭藻。我認識不少詩人,除了一些名人和大家,民間和網絡都有一些高手。我寫詩,無意從眾,無意粉飾太平,我只想把自己的詩歌寫得小眾一點,輕松一點,個性一點,冷峻一點,甚至犀利一點。有時我想,一個瘋狂、浮躁、功利的年代,詩歌如能充當一劑鎮靜良方,那該多好。
寫詩是一件無比快樂的事情。我曾在一首詩里寫到一個場景:一條清蒸武昌魚端上餐桌,女兒沖魚聞了聞,說真香,妻子用筷子戳戳魚眼,說新鮮,我沉吟片刻,說了一句:水里的精靈,睜著眼,酣睡……她們先是沖我翻白眼,說我拐彎抹角,不好好說話,繼而相視而笑,一家三口其樂融融。
寫一首好詩,需要窮盡一個詩人一生的閱歷和心智,而我天生愚鈍,缺少與生俱來的基因傳承。對于詩歌,除了癡迷和敬畏,我只有以勤補拙。無數個深夜,我輾轉反側,為突然想到的一首詩,一個句子,一個詞,披衣下床,把它們記錄下來,然后摟著它們酣然入夢。更多的時候,我會一個人對著天空發呆,直到一首詩的誕生。我喜歡尼采的一句話:如果你能靜坐5分鐘,你就離神近了一步。我喜歡這樣的安靜與孤獨。
這些年我一直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奔走,當我走在街井市巷,或站在田間地頭,感知生存與死亡的種種況味,總會被眼前的事物所觸動。歇下來的時候,沏一杯清茶,溫一壺老酒,守著詩歌,守著故居或異鄉相忘江湖,一天很快就會過去。細細想來,紅塵的美好,不過如此。
我不是詩人,也從來沒有想過要當詩人。生活中,我始終將自己視為一株靜觀人世的草木,將詩歌視為靈魂的碰撞與救贖,視為我生命的點綴和精神皈依,安于每一個風輕云淡的日子。人生各有所樂,你喜歡麻將,我羨慕你;你喜歡韓劇,我羨慕你;你熱衷股市,我羨慕你;你談論中美外交,我羨慕你……這些,我都不懂。我寫點小詩,想你不會咒我矯情。
《草木之心》是我出版的第二本詩集,它匯集了我近幾年公開發表的部分詩歌。付梓在即,心有忐忑,因為時至今日,我仍沒有寫出幾首令自己滿意的詩歌,在這里,我只能虔誠地向詩歌鞠躬,向閱讀這本詩集的朋友鞠躬。
自言自語,權且作序。
趙武松
2015年夏于武昌東湖
(本欄目責任編輯:王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