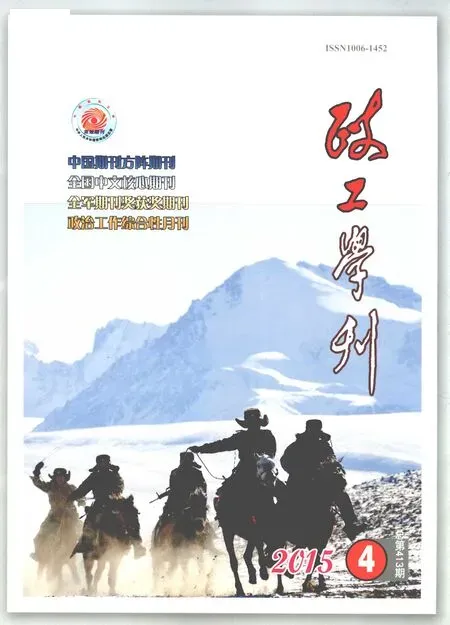美國智庫一瞥
☉陳如為
美國智庫一瞥
☉陳如為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庫”概念。習近平總書記也在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強調,要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和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智庫。一時間,“智庫”成為熱詞。不過,要說起一個國家的智庫影響力,就不得不提到美國。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研究項目發布的《2014年全球智庫報告》顯示,2014年全球共有智庫6681個,其中美國智庫最多,為1830個,中國智庫數量居第二位,為429個。以綜合影響力看,全球前10名的頂級智庫中,有6個是美國智庫。所謂綜合影響力主要看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提出了多少原創思想和新的政策建議;二是為政府輸送了多少專家型官員;三是舉辦了多少高級別的研討會;四是在教育公民看世界方面作出了哪些貢獻;五是在幫助政府官員調解和處理沖突方面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二戰以來,美國歷任總統提出的各種戰略和對策,其原創差不多都來自美國智庫。例如,美國第一個私營研究機構——布魯金斯學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它先后建議美國政府參加兩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后,它立即提出,美國對外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對內“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創建聯邦預算規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建議。又如,二戰剛爆發,外交關系協會搞了一個大規模的“戰爭與和平研究項目”,先后向美國國務院提供682份研究成果備忘錄,其中“占領德國”“創建聯合國”“遏制蘇聯”等政策建議,均來自上述備忘錄。再如,冷戰結束出乎美國預料,老布什政府不知如何應對。對蘇聯研究極深的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蘭德研究院很快提出“擴大北約”“退出反導條約”“建立導彈防御系統”等冷戰后美國的主要戰略構想和建議。美國大學里的知名學者也不甘寂寞,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于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成為2001年“9·11”事件后所有智庫研究反對恐怖主義對策的基礎。
隨著智庫對美國戰略思想和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智庫內知名專家越來越多應邀進入政府擔任要職。同時,越來越多的下野官員回到智庫繼續從事研究事業。這種所謂的“旋轉門”對美國智庫的發展、影響,包括對政府盡可能正確地決策,起到良性循環作用。一方面,進入政府的專家學者不再空懷壯志,紙上談兵,而是一展抱負,實現理想,而且他們從政后比其他官僚更愿意聽取智庫的意見。另一方面,回到智庫的前政府官員,由于在職期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再研究問題時,其思路和提出的對策針對性更強,更易于被政府內的決策者采納。
據統計,頻繁出入這種“旋轉門”的專家學者,大多數來自布魯金斯學會、對外關系協會、傳統基金會、美國企業政策研究所等智庫。他們當中擔任過國務卿的,有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喬治·舒爾茨、詹姆斯·貝克、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擔任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有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康多莉扎·賴斯等。至于擔任其他部長、副部長、助理部長、局長職務的專家學者,更是多如牛毛。統計數據顯示,僅在里根總統任職的8年中,應邀走出美國智庫進入政府的專家學者,竟超過150人。最新的一個例子是,美國國務院常務副國務卿威廉·約瑟夫·伯恩斯于2014年11月3日辭職,到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接任總裁。
美國的民間基金會慷慨支持各領域的前沿研究,而不是救濟貧困者。他們認為,救濟貧困者是政府的職責。美國文化崇尚“強”,認為“強”即是“美”,瞧不起“弱”,認為“弱”即是“惡”。所以,爭強好勝、強者應當更強,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符合達爾文進化論中的“優勝劣汰”理論。美國第一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就是當時的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于1910年捐資建立的。此后美國鐵路大王亨廷頓、報業大王赫斯特、汽車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都曾捐巨資幫助各行各業的智庫。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隨著信息網絡工業在美國西海岸異軍突起,微軟、惠普、英特爾等公司的老板們在暴富之后成立的“蓋茨夫婦基金會”“戴露普家庭基金會”“穆爾夫婦基金會”等,依然是美國各類智庫資金的重要來源地。“戴露普家庭基金會”捐款五原則中最重要的兩條是:支持和獎勵各行各業已作出最杰出貢獻的個人和組織,特別是支持和獎勵最杰出的思想和努力;要有長遠的眼光,發現和支持那些在提高效率方面最有可能作出獨特貢獻,或最有可能作出戰略性貢獻的個人、組織、項目等。
智庫是文明和文化的高級載體。西方文明和美國文化的基因缺陷,也遺傳給了美國智庫。西方文明和美國文化過分崇拜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這導致美國智庫在研究國內問題時,出發點和著眼點往往是個人利益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集團利益和局部利益,在研究國際問題時,其出發點和著眼點往往是極端自私的“美國利益至上主義”,甚至不惜從“美國例外論”的角度思考問題和對策,導致很多本來有可能解決或緩解的國際國內問題,長期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智庫曾就如何防止美國卷入危機有一場大辯論。東部智庫的主流意見是,美國政府應當把重點放在加強跨大西洋經貿關系上;西部智庫的主流意見是,美國政府應當把重點放在跨太平洋經貿關系上。筆者曾就此詢問過幾家美國大企業的老板,美國智庫都說自己的研究是獨立的、客觀的,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東西部智庫的專家學者給出的答案如此不同?他們的回答一語中的:你得看看他們的研究經費是從哪里來的。
由于美國文化中極端自私的基因遺傳給了美國智庫,在研究世界問題時,美國智庫還自覺不自覺地給美國政府出了不少餿主意甚至壞主意。美國政府至今不簽署152個國家批準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200l年帶頭退出183個國家批準的應對氣候變暖的《京都議定書》,冷戰結束后,出爾反爾,單方面退出它同蘇聯簽署的《反導條約》,研究部署美國導彈防御系統和戰區導彈系統。美國甚至用“多重標準”對待189個國家批準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它同非條約簽字國(印度)開展核合作,對非條約簽字國(以色列)擁有核武器“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對非條約簽字國(朝鮮)搞地下核試驗進行制裁、封鎖,甚至以動武相威脅。可以說,在所有這些遭到世界多數國家嗤之以鼻的美國對外政策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國智庫的影子。
【作者系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轉自《時事報告》)